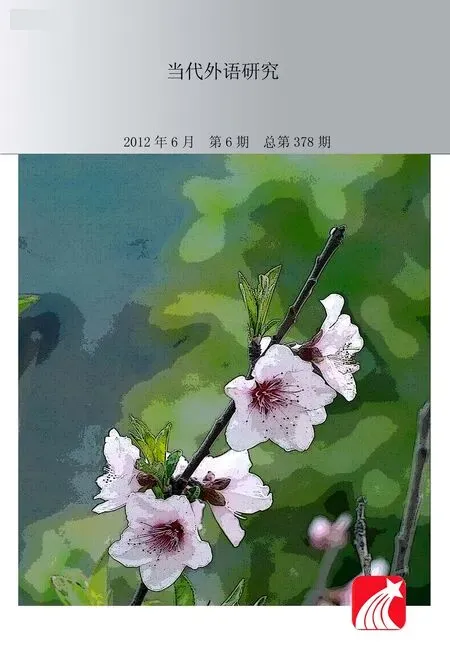另一种“现代”
——莱纳德·伍尔夫个案研究
李博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1926年5月5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我坐在出版社……莱纳德在写稿……梅纳德很激动,想让贺加斯印发这期的《国家》”(Woolf 1980)。莱纳德(Leonard Woolf)是作者的丈夫,梅纳德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Maynard Keynes),贺加斯(Hogarth)是伍尔夫夫妇在家中创办的出版社,也是弗吉尼亚的工作室,《国家》全名《国家与雅典娜》(TheNationandAthenaeum),是以凯恩斯为老板、莱纳德为文学主编的一本书评周刊。这段头绪众多的记述恰可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文人交往、写作、出版、编辑交织并行的文学生活的日常状态。本文尝试在这个背景下,以莱纳德及其出版活动、期刊编辑与书评写作为核心,考察那个年代英国“现代主义”(modernism)文学产生的空间,还原当时的几个文学关联,以此为“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的最新界定提供一个佐证。
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指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现的一股文学思潮,代表作家包括庞德、乔伊斯、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特点包括与过去的文学传统断裂,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颠覆现实主义叙事手法,革新文学形式,运用意识流、倒叙、意象的碎片化等(Baldick 2001:140)创新的文学表现手法。文学史多描述“现代主义”文学为一种精英小众文学,是纯而又纯、阳春白雪、反大众、自给自足、孤芳自赏的(Huyssen 1986)。近年来,这种倾向被扭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主义”不能仅指向庞德、艾略特、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几位作家,还须另有名称指代同时代里与他们并存的其他类型或样貌的文学实践。“现代主义”的范畴开始扩大,甚至有人用复数的modernisms指代这一时期各种形态的文学样式(Levenson 1999:7)。到了2004年,代表英国文学权威论断的《牛津英国文学史》之现代卷出版,起名《现代运动:1910-1940》,恢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认为当时正在发生的文学变革为一种“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的提法(Connolly 1938)。与1963年老版只介绍八个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新版介绍了两百个作家,其中一百个附有进一步细读指导(Baldick 2004)。也就是说,几乎无人不“现代”。又或者说,“现代”的精英之意完全被消解。从主观姿态鲜明、所指范围狭隘的“现代主义”到侧重时间、包容一切的“现代”,如此转折可说是现在这个时代对彼时文学图景的最大化复制,似乎代表了当下西方文学史学界更为多元宽容的价值观。莱纳德就在这扩大的画面上占据着一个微妙位置。
莱纳德素以弗吉尼亚的丈夫闻名,但就其实践而言,应是身份多元的文化人,兼具小说家、政论家、编辑、记者、出版家和传记作家等多重角色,是著名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对“现代主义”的兴起与传播起过相当作用,又长期担任工党国际与帝国问题顾问,自称“古怪”的社会主义者,是个极复杂的人物。作为一战后国联理论的阐发人之一与工党智囊,他在政治学界早已占据一席之地,但在文学界还只位列边缘。虽不乏小规模的专门研究①,但大多数研究者提到他,仍只为辅助考察弗吉尼亚②,而且即使如此,也似乎没能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智识伴侣的他能够为一般被认为“前卫”、“先锋”的女作家提供精神资源,这是多么具备复杂性的一件事。下文将聚焦彼时文坛的两大争论,即“高眉”、“中眉”与“低眉”之争(brow-beating),传统与实验之争,从而检验身兼出版人、期刊编辑和书评人的莱纳德对现代文学之理论构建与实践活动的复杂立场。
1.“高眉”、“中眉”与“低眉”之争
欧洲传统以眉/额之高低判断人之聪明美貌,高眉(high-brow)为聪明美丽,低眉(low-brow)为丑陋愚钝,中眉(middle-brow)为庸俗无趣。三者代表三种文化姿态,是英国二、三十年代一场文化论争,本质是维多利亚时期以来长期把持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与出身中下层的作家和大量刚刚摆脱文盲状态加入到读写行列里来的一般人关于文学权威与批评标准的争论。“眉”的标准不同于“传统”与“现代”:高眉不一定现代,中/低眉也不一定传统。“眉”也不完全等同于阶级:高眉不一定对应贵族和中上阶级,中/低眉也不一定对应中/下阶级。弗吉尼亚就说她认识的高眉里既有公爵夫人,也有杂役女工(Woolf 1932/1942:178)。“眉”还不同于性别:高眉不一定非得是男性写作,中/低眉也不一定非得是女性写作,虽然的确大量中眉作品都属于女性写女性。但是另一方面,“眉”的划分又与阶级、性别和文化品味交叉勾连,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意义投射。对整个以高眉著称的布鲁姆斯伯里小组(包括伍尔夫夫妇)来说,这场争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亚于——甚至强于——“实验”(即“现代”)与“传统”之争,因为这影响到了作为作家和媒体人的他们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自我认知,甚至迫使他们经历了一场身份危机,并在定位自己的过程中锻造了他们以智识(intellect)、理性(reason)、文明(civilization)为主旨的文化价值观。
《牛津英语词典》对“眉”的定义围绕一个中心词“智识”展开:高眉是智识成就或兴趣超绝之人士,有时自认比普通人高明,此时语含贬义;中眉只有——或者认为自己只有——中等文化兴趣;低眉没有——或者不认为自己有——智识或品味。三种人里只有高眉时有贬义,原因似乎就在“自认高明”上,但是自认蠢笨比自认聪明好就好吗?这正是当时论战的关键。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戴斯门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责问现在的高眉们为什么对自己的智识水平表现出一种可笑的怯懦,为什么他们能够允许随便一个笨蛋认为自己更聪明(MacCarthy 1931)?布鲁姆斯伯里小组的朋友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认为高眉之所以耻称高眉,全社会之所以普遍“崇拜愚蠢、崇拜无知”是十九世纪末教育普及的结果。教育普及并没能使所有人获得精神满足或者物质回报,反而令很多人大失所望,认为读书无用。而高眉之所以不见容于现代工业与消费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因为他们不热爱消费,最满足于独坐一室读书。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大规模工业生产与疯狂消费的鄙视(Huxley 1931)。这种见解如今仍然犀利。被认为是“高眉女王”的弗吉尼亚承认自己深受此称号的困扰。她把矛头对准中眉,她定义高眉是在乎头脑的人,低眉是在乎生活的人,中眉两者都不在乎,只想要金钱、权力、名声和威望,是最无创造力的“中间派”(Woolf 1932/1942:180)。莱纳德(1927)关注的中心议题则是:为什么有些流行作品很快湮灭,有些则流传下来,不仅成为经典,还给读者以阅读的愉快,也就是说成为高眉?结论不难推断:高眉代表人类最成熟最智慧的判断,而且高眉的文艺寓教于乐,不仅有智识的高度,也有寻常的乐趣。相比麦卡锡与赫胥黎的挑战,以及流露其中的焦虑与不满,莱纳德的结论低调朴实,实用性强,又从容自信,代表了莱纳德在出版、编辑和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原则。
首先,作为出版家的莱纳德非常“高眉”和“现代”。他与弗吉尼亚1917年在自己家里成立贺加斯出版社,专门出版弗吉尼亚的著作,为的是省却她向外投稿与被人修改的痛苦(出版人和审稿人自然都是男性),因此贺加斯一问世就有极其“女权”与自主的一面。以至于到了1925年弗吉尼亚终于可以说“我是英国唯一能够自由书写的女人”(Woolf 1978:42)。这还是一个很“个人”、很“独立”的出版社。它不以赚钱为目的,不吸引投资,不扩大规模,坚持其“小”,为的是怕外人影响出版决策。在出版内容上,莱纳德从不重印经典或旧作,只出新书、当代书、非商业性质的书,比如最不好卖的政论与诗集(1923年出版“限量版”《荒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也致力于推介新思想,比如1924年在大出版社认为赔钱的情况下出版弗洛伊德的著作,成为弗洛伊德在英国的唯一出版人,可以说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实验,即关注人物心理的意识流叙述提供了理论支持。莱纳德的私人阅读也很“前卫”,到老年仍极爱《荒原》,并坚持认为弗吉尼亚最具实验精神的意识流小说《海浪》是她最好的作品。
作为期刊编辑的莱纳德也有另一面,即必须中和,无法太“高眉”。虽然编杂志与办出版社都必须考虑平衡艺术与受众和赢利之间的关系,但显然作为出版人的莱纳德更自由,作为文学编辑的他必须向杂志老板、负责杂志另一半版面的政治编辑、读者和市场妥协。英国报刊历来都依附不同政党或意见团体,做一家之言,这是极重传统的英国的现实政治,与“左右”都包的“现代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③。《国家》本是自由党背景(老板是自由党经济学家凯恩斯),后来由于有工党势力渗透,遂向左翼倾斜。从本质上说,《国家》既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喉舌,又是执政的保守党的传声筒。杂志读者则兼具自由党和工党身份,有读者来信说自己虽“生长在自由党内,但久已是社会主义者”(Cobb 1924)。
莱纳德在这份周刊的地位稍嫌尴尬,因为他并不认同自由党的政治政策和文化品味。他评价他任编辑之前的《国家》“仍然是格拉斯顿式的自由主义,浸淫着复杂精致或者富有教养的不服从”(Woolf 1967:96)。而“1914年以后的自由主义者们应该认识到自由主义,正如爱国主义一样,是不够的,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很多自由党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在文化上做‘普通人’,好市侩,不欣赏阳春白雪,并错误地以此为骄傲”(139)。这与阿诺德总结反智是英国中产阶级的最大问题是契合的。在莱纳德看来,反智不仅是自由党人的问题,更是他最痛恨的英国全社会的积习,即国民“不相信智识,只顺从本能”(Woolf 1925:461)。这使文学编辑莱纳德与政治编辑胡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产生分歧,造成了他们日后的决裂。莱纳德认为“任何一篇好文章都会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所以他不准备取悦所有读者。亨德森则认为好文章应该人人都喜欢,所以莱纳德说,“如果只他[亨德森]一人做主,他会把《国家》办成《威斯敏斯特公报》”(Woolf 1978:268)④。亨德森则抱怨莱纳德启用太多布鲁姆斯伯里书评人,给他们太多自由,使《国家》的风格过分“高眉”。弗吉尼亚最后的评价是:《国家》不是“我们的骨肉”,它只是个“温吞的杂志。既不是这也不是那……”(265)。
可是亨德森认为太“高眉”的作者,莱纳德却认为“星光熠熠”(Woolf 1967:129),并骄傲其数量之多,为当时所有其它周刊所不能比拟。如果从初创的1828年算起,到莱纳德任职时,《国家》已有差不多百年历史⑤,也被誉为彼时“全国最知名周刊之一”(Henry 2003:16),但为何后世名声不及艾略特的《标准》(Criterion)和利维斯的《细察》(Scrutiny)?这是因为首先它不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小杂志”。莱纳德一生编辑刊物虽多,却几乎从未参与“小杂志”的编写,大概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就不必再有自己的杂志。“小杂志”多不长命,如《暴响》(Blast)只出了两期;或发行量不大,例如《标准》只卖400本,无法与发行量动辄上万的“大”刊——如大力挞伐先锋文学《荒原》的《伦敦水星》(LondonMercury)——相比。小杂志作为世纪末情结的体现,观点激进极端,加速了维多利亚文化的崩塌和分裂,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传播起到过很大的推介作用,是文学史家回顾现代主义文学的关注重心。莱纳德在这方面的缺席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在“现代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内的缺席。“小杂志”只是当时文学期刊的冰山一角,如莱纳德一般的大刊(以发行计)主编面对的才是更广泛的文学受众。
其次,莱纳德的文学评论大部分以书评形式出现,少有艾略特式的专题论文。他不像I·A·理查兹那样致力著书,这也造成他不闻名于后世、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的学院派学术批评。书评是当时活跃于报刊杂志的文人的首要书写方式,是文化工业上的重要一环。它连接作者和读者,出版商和市场,代表时代的标准,塑造普遍的文学品位,也直接影响书籍销量。直到现在,《纽约时报书评》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仍是英美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杂志。二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多元形态。一方面,书评仍旧活跃,承担了一大部分文学批评的功能;另一方面,1925年《英国研究评论》(ReviewofEnglishStudies)创立,标志着批评的专业化与学院化逐渐确立并不可逆转。莱纳德可说是在最后的传统文人与职业/学院批评家之间生存的一代。
书评影响既大,遭到的质疑也激烈。1932年,Q·D·利维斯(F·R·利维斯的妻子)发表《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抨击由书评人、广告、文学文章和当时流行于英美的读书俱乐部组成的所谓“文学中间人”,认为他们代表了中眉价值观,严重损害了读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助长了大众对二流文学的兴趣(Leavis 1932)。书评被贴上了中眉的标签,等于二流和庸俗。伍尔夫夫妇和利维斯夫妇都是无可质疑的“高眉”,但在“文学中间人”一事上,莱纳德的认识似乎复杂得多,对市场的态度也比较实事求是。既然教育普及使得读书和写书的人多了起来,他既不像利维斯那样回望“过去的好时光”,以十七世纪为圭臬,浩叹今不如昔,也不要压缩这个市场,因为他知道更多的人会加入到读写中来,这一潮流不可逆转(Woolf & Woolf 1927/2006)。此外,只要作者想卖书,书评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Woolf 1939)。而且他认为书评不易,书评者需对文学有广博的知识和理解,对评判标准有正确的感觉,对艺术作品有精微的情怀。书评者是文学作品的好裁判。书评不仅有用,评好了也极难极危险,因为好书评比小说还要颖异。雷蒙·莫迪莫(Raymond Mortimer)曾对伍尔夫夫妇说:“写书评好于写二流小说”(转引自Smith 1996:200)。沃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也宣称“对于现代阅读而言,再没有其他体裁比‘书评式的文章和文章式的书评’更核心的了”(转引自Collini 2008:223)。
因此,书评对莱纳德而言,是一种有价值、很“高眉”、很“革命”的文体。他在《国家》提供的书评专栏“书的世界”(The World of Books)里与读者做着周复一周的娓娓笔谈,实践着体现智识、理性与文明的劝说,这三者是莱纳德的自奉。作为公学和剑桥古典教育的产物,他终生信仰“文明”,即古希腊哲学提倡的“理性、宽容、自由、民主”和“社群中的利他主义和良善意图”,反抗“野蛮”,即“无理性、不宽容、暴政、迷信”(Woolf 1924c: 381)。“自由、文明的个人主义”(free civilized individuals)则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布鲁姆斯伯里价值观的总结,他的阶级分析把布鲁姆斯伯里看成是资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可供调节自身机能的一个小团体,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但充其量也只能复制资产阶级文化,而非对之做出根本改变(Williams 1980:163-165)。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团体发展到后期,其精神气质蜕变成为“极端的主观主义”,最在乎的只是为什么社会不能允许某些人过有教养的生活(威廉斯2010:56)。威廉斯强调“教养”(civilized),而教养对莱纳德这个既是高眉的审美家,又能积极投身女权运动、社会主义合作运动和反帝反殖民的工党智囊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用阶级分析的话语一言以蔽之,还是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个人”的美好追求?
莱纳德的读者不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少数精英,而是受过一般教育、向往文明与教养的约翰逊式的普通读者⑥。这也指向弗吉尼亚希望通过文学批评遭遇的“普通读者”:他与“评论家、学者不同。他受的教育较差,天赋也不突出。他为自己的兴趣读书,并不是要传授知识或纠正别人的见解”(Woolf 1925/2003)。这显然是一种民主倾向,并不排除刚刚告别文盲的下层人。其次,莱纳德的编辑组稿和自己的专栏都体现出一种虽然包括“现代”,但并不与“传统”割裂的更宽广、更日常、更亲切的阅读品味。首先是英国文学,其次是古典(希腊多于拉丁)文学、外国(美国、欧洲大陆、间或印度)文学、游记、日记、通信、国内外政治、种族与民族、一战、宗教、历史、哲学、语言学、法律、犯罪与罪犯、科学与科学家、自传与传记、出版与编辑、动物、体育、以及各个阶级、各行各业的人。这其中流露的是对希腊文学文化不加保留的热爱,对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的强烈兴趣,对维多利亚作家作品的熟悉,对女性的尊重、对贵族愚蠢守旧的批判嘲讽,对寻常生活的享受(如板球)、人都有的好奇心(比如对犯罪、男女情事)和对普通人的兴趣。内容亦俗亦雅,雅俗共赏。
这种对普通人的兴趣表现在莱纳德对普通人能够胜任的传记、日记、通信的重视。他将日记定义为普通人“通向不朽的途径”,意思是说作家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普通人只要像十八世纪某乡村牧师一样事无巨细、老老实实地每天写日记,写上三十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阅读显然与“主义”无关。莱纳德关心的是生活本身,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琐事,是那些过日子的人。他对传记的迷恋也表现了类似情怀。他感兴趣的人不仅有名人伟人,更有海盗、理发师、罪犯等社会小人物和边缘人。这体现出一种平民史观,即认为历史是人人参与的结果,而非只由“王公贵人与历史大事”(Woolf 1924a:574)构成。这最终形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体心理学”(communal psychology),即造成社会变革的不仅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还有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同一个社会各成员的思想变化。而研究人的思想变化的最好办法之一是读他的自传和传记,写作传记与自传的坦诚可以涤荡社会上虚伪的空气,净化人的意识,创造更真实自由的人际关系。
2.“传统”与“实验”
文学创作手法的“传统”与“实验”之对立是后世文学史回顾“现代”文学时为其设定的首要问题。但首先需说明modernism这个词的出现是个后见,1940年前几乎不用。终其一生,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没管自己叫过“现代主义者”(modernist),她只说自己是“现代者”(modern)。当然“现代者”对她而言就意味着革命与激进,具有爆炸性的含义。她也管自己叫“乔治朝人”(Georgian),以示和维多利亚朝(Victorian)和爱德华朝(Edwardian)——尤其是其代表作家威尔斯(H.G.Wells)、本涅特(Arnold Bennett)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区别,其命名本身就意味着变革与叛逆。她诟病这三人的写作重物质、轻精神、不写人的灵魂,而真正的小说家要传达人类“变动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精神”(转引自王佐良、周珏良1994:11),尤其是那“瞬间的存在”⑦。艾略特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则是三位一体:“宗教上的英国国教-天主教徒,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守派”(Eliot 1929:ⅶ)。只从自我定义,很难把这两人归到同一阵营。当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反抗最近的过去,如弗吉尼亚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小说家的颠覆,艾略特对浪漫派诗歌的反动以及对十七世纪玄学诗派的推崇。这也成了莱纳德定义“现代”的基础。
虽然自己是个“高眉”与“现代者”,莱纳德对“现代”文学的理念却不乏疑问。1929年底一篇名为《帕那索斯山上的布尔什维克们》的书评便表现了这种质疑(Woolf 1929:402)。这题目本身便体现着一种颠覆。帕那索斯山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神山,缪斯的居住地,象征古典与传统,代表旧的文学秩序,如今被布尔什维克占领,自然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的代表是艾略特(旧诗的毁灭者)和斯特拉奇(旧传记的毁灭者),均为莱纳德的好友。
被评的书叫《当代文学的传统与实验》(TraditionandExperimentinPresent-dayLiterature),是个合集。作者有十位,均为“最现代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传记作家”。莱纳德说读此书的目的是发现为什么“现代文学”那么不好懂,为什么“现代文学”需要一个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形式,但他承认自己读完了颇失望、疑惑。他说这些作者并不能看出“何处传统结束、何处实验开始,他们只好一个接一个地总结说成功的实验就是传统”。他自己对传统和实验的定义是:传统的诗人好比蒲柏和丁尼生,他们能从传统艺术形式中找到合适的表达工具,他们想唱的调子适应时代精神、适应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现在。革命的诗人,如华兹华斯和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反叛最近的过去和大部分的最近的现在。他们可能创造了传统,但即便果真如此,也并不是籍利用现有传统,而是籍毁灭现有传统而创造传统”。这个定义不算复杂,意义在于阐明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历史上的绝对时段,而是对特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反应。华兹华斯、史文朋和艾略特虽分处三个世纪,但都是“现代诗人”。而且“传统”与“现代”并非价值判断。“现代”之谓固然语带褒奖,“传统”之说也并不因此贬值。华兹华斯、史文朋和艾略特不因为是“现代”诗人就好过蒲柏和丁尼生是“传统”诗人。这和后来很多“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大不相同。
莱纳德还反对传统和实验的二元对立,因为仅这两极无法覆盖文学图景的全貌。传统和实验之间还有一个更加复杂宏阔、晦暗不清的场面。例如,莫特拉姆对英国小说的回顾无法决定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亨利·詹姆斯和哈代当属现代还是传统,贝尔斯福德对小说实验的讨论竟然只字不提乔伊斯和《尤利西斯》。这些举例说明不是所有文学实践都能严密切合预先设定的范畴,任何一种概念先行的分类方法都会遭遇某些对象无法归类的尴尬。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最难以解释的想象力的结晶,是超脱于理论之外的。这也正是一个人读多了后世的各种理论与归纳,头脑中已经形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只有两三个“大家”、五六个“小家”之后,突然接触到当时一个人所著三百篇书评,而他记录了上百个作家和几百本作品后,禁不住感到惊讶和反思。
有时莱纳德的质疑比传统与实验的对立更为激烈,比如对于文学批评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莱纳德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对“‘事’、对问题、对困难真正感兴趣”,而不是对“人和名人”感兴趣。批评应该能回答两个问题:“要批评什么?批评了有什么用?”既然大多数现代批评家们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他们只好批评批评家,于是制造出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批评“跳蚤”:
1600年,莎士比亚写了一出悲剧,1688年德莱顿写了一本书讲莎士比亚的悲剧……1920年T.S.艾略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讲德莱顿讲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文章;1921年米德顿·默瑞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讲艾略特这篇讲德莱顿讲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文章的文章;1924年威廉姆斯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讲默瑞讲艾略特讲德莱顿讲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文章。(Woolf 1924d:113)
这段书评涉及到的艾略特的文章与莱纳德自己也有关系,因为当时贺加斯刚出了艾略特的《向德莱顿致敬》。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包括三篇文章:《约翰·德莱顿》、《玄学诗人》和《安朱·马维尔》,均讨论十七世纪文学,尤其是德莱顿的诗歌与评论。这是艾略特的重要诗歌批评,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文章主旨在于显扬十七世纪诗歌的奇思妙想,提倡恢复英国诗歌从十八世纪起被中断的心理分析传统。莱纳德很骄傲自己出版社的小册子和政论文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讨论空间,但他似乎对自己推动的现代批评事业,包括对他的好友艾略特,都颇为不敬。说德莱顿、艾略特和默瑞三位是寄生虫,是跳蚤,哪怕出于对“过度阐释”的忧虑,也实在言重了。
3.结语
王佐良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指出:“现代主义……不是文学的全体,经过若干年,甚至不是文学的主体。传统的现实主义仍然强大有力,但也在变化,不断出现新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同时,还有大作家不属于任何流派而屹然独立于文坛”(王佐良、周珏良1994:13)。的确,距离“现代文学”的初生已有百年了,我们终于能够摆脱“现代”代表进步、“传统”代表守旧的价值判断,比较淡定地看待那时的书写了。从1923年到1930年,七年发表三百多篇书评,莱纳德虽不是批评大家,却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和道德准则,也从不刻板说教。虽然被书评的形式与篇幅所限,七年来好比做八股文章,却难得一直保持流畅自然。而且,从他特立独行的出版、中和市场需要与智识追求的编辑和坚持“高眉”标准却面向普通读者的书评,我们发现那些表面矛盾的文学理想实则可以和谐共存。真实具体的文学存在是那些看似对立的“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各种力量的相依相生。
附注:
① 如对小说《丛林里的村庄》(TheVillageintheJungle)和《智慧的处女》(TheWiseVirgins)、四篇短篇小说《珠与猪》(“Pearls and Swine”)、《月光下讲的故事》(“A Tale Told by Moonlight”)、《两个婆罗门》(“Two Brahmans”)和《三个犹太人》(“Three Jews”)、文学评论集《文学、历史、政治论文集》(EssaysonLiterature,History,Politics,etc.)以及五卷自传均有少量评论。
② 这类研究又可分两种,一种是伍尔夫夫妇传记,如Spater和Parsons(1977),Alexander(1992)和Rosenfeld(2001)。一种是以某种主题出发,对他们作品或文化活动的研究,如Schröder(2003)、Wollaeger(2003)和Willis(1992).
③ “左”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倾向,例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右”指对法西斯主义的赞赏,例如温德海姆·路易斯曾一度美化希特勒。
④ 《威斯敏斯特公报》是份晚报,人称“俱乐部报纸”,发行量不大,但对自由党的忠诚度很高。那些自由党的绅士们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通常会去各自的俱乐部,在等待晚上的社交活动开始前就看这份报。
⑤ 《雅典娜》成立于1828年,《国家》成立于1906年,1921年两刊合并为《国家与雅典娜》。1931年更与工党立场的《新政治家》合并为一本杂志《新政治家与国家》。
⑥ 约翰逊博士曾说:“我高兴与普通读者意见一致,因为诗的荣誉即便有学识的教条与精妙的提纯,最终还是由读者的常识决定,而不受文学偏见腐蚀。”
⑦ “moments of being”指刹那间的顿悟与存在感,参见Woolf(1976).
Alexander, P.F.1992.LeonardandVirginiaWoolf:ALiteraryPartnership[M].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Baldick, C.1990/2001.OxfordConciseDictionaryofLiteraryTerms[Z].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aldick, C.2004.ModernMovement: 1910-1940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bb, E.1924.Letter to the editor [J].Nation&Athenaeum35(11): 349.
Collini, S.2008.CommonReading:Critics,Historians,Public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nolly, C.1938/1961.EnemiesofPromise[M].Harmondsworth: Penguin.
Eliot, T.S.1929.ForLancelotAndrewes[M].Garden City: Doubleday, Doran.
Henry, H.2003.VirginiaWoolfandtheDiscourseofScience:TheAestheticsofAstronom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xley, A.1931/2001.Foreheads villainous low [A].In R.S.Baker & J.Sexton (eds.).AldousHuxleyCompleteEssays(Vol.3 1930-1935) [C].Chicago: Ivan R.Dee.246-50.
Huyssen, A.1986.AftertheGreatDivide:Modernism,MassCulture,Postmodernism[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eavis, Q.D.1932.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M].London: Chatto & Windus.
Levenson, M.1999.Introduction [A].In M.Levenson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Modernism[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
MacCarthy, D.1931/1935.Highbrows [A].In D.MacCarthy (ed.).Experience[C].London: Putnam.308-11.
Rosenfeld, N.2001.OutsidersTogether:VirginiaandLeonardWoolf[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röder, L.K.2003.Tales of abjection and miscegenation: Virginia Woolf’s and Leonard Woolf’s “Jewish” stories [J].TwentiethCenturyLiterature49(3): 298-327.
Smith, A.1996.TheNewStatesman:PortraitofaPoliticalWeekly, 1913-1931 [M].London: Frank Cass.
Spater G.& Ian Parsons.1977.AMarriageofTrueMinds:AnIntimatePortraitofLeonardandVirginiaWoolf[M].London: Jonathan Cape & Hogarth.
Williams, R.1980.The Bloomsbury fraction [A].In R.Williams (ed.).CultureandMaterialism:SelectedEssays.London: Verso.148-69.
Willis, J.H.Jr.1992.LeonardandVirginiaWoolfasPublishers:TheHogarthPress, 1917-41 [M].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Wollaeger, M.2003.The Woolfs in the jungle: Intertextuality, sexu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modernism inTheVoyageOut,TheVillageintheJungle, andHeartofDarkness[J].ModernLanguageQuarterly64(1): 33-69.
Woolf, L.1924a.The ‘pageant’ of history [J].TheNation&Athenaeum34(16): 574.
Woolf, L.1924b.The road to immortality [J].TheNation&Athenaeum35(5): 146.
Woolf, L.1924c.A civilized man [J].TheNation&Athenaeum35(12): 381.
Woolf, L.1924d.Lesser fleas [J].TheNation&Athenaeum36(3): 113.
Woolf, L.1925.Plato the Dago [J].TheNation&Athenaeum37(15): 461.
Woolf, L.1927.Hunting the highbrow [A].In L.Woolf (ed.).TheHogarthEssays[C].New York: Doubleday Doran.135-59.
Woolf, L.1929.The bolshies on parnassus [J].TheNation&Athenaeum46(11): 402.
Woolf, L.1930.The ideals of journalism [J].TheNation&Athenaeum46(20): 674.
Woolf, L.1939.Appendix [A].In V.Woolf.Reviewing[M].London: Hogarth.30.
Woolf, L.1967.DownhillAlltheWay:AnAutobiographyoftheYears1919-1939 [M].London: Hogarth.
Woolf, L.& V.Woolf.1927/2006.Are too many books written and published? [A].PMLA121(1): 235-39.
Woolf, V.1925/2003.TheCommonReader(Vol.1) [EB/OL].London: Hogarth.[2012-05-20].http:∥gutenberg.net.au/ebooks03/030031h.html.
Woolf, V.1932/1942.Middlebrow [A].In V.Woolf (ed.).TheDeathoftheMothandOtherEssays[C].New York: Harcourt Brace.176-86.
Woolf, V.1976.A sketch of the past [A].In J.Schulkind (ed.).MomentsofBeing[C].UK: Harvest.64-137.
Woolf, V.1978.TheDiaryofVirginiaWoolf(Vol.2) (A.O.Bell & A.McNeillie eds.) [M].London: Hogarth.
Woolf, V.1980.TheDiaryofVirginiaWoolf(Vol.3) (A.O.Bell & A.McNeillie eds.) [M].London: Hogarth.
雷蒙·威廉斯.2010.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王佐良、周珏良.1994.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