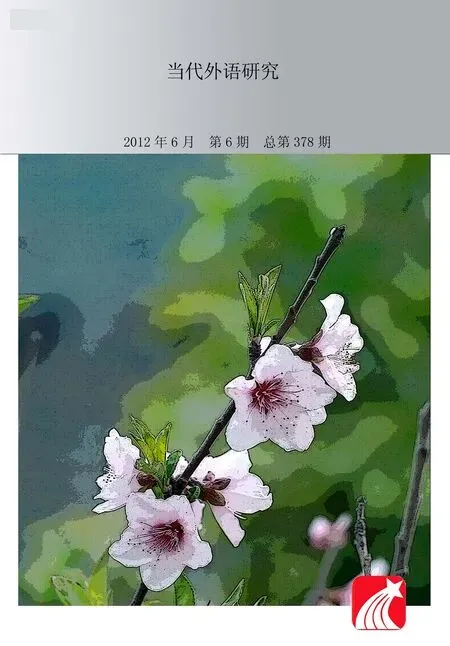“语言奥秘”与“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之二
范连义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201620)
1.引言
古希腊以降,语言就是人们研究的对象。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霍布斯等人对语言知识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论述,但引发近50年语言知识大探讨的当是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开始之时,就有不少语言学家、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反对乔姆斯基的理论,而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大都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Pateman 1987:120)。
在《句法结构》刚发表时,就有人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是一个骗子的理论(蔡曙山2007:153)。有人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错讹百出(corrupted linguistics),甚至认为乔姆斯基明知自己的理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却故意抛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语言共相或生成语法理论。他的欺骗是故意的,他的理论是一种虚饰甚或是一种虚张声势。他剽窃别人的思想,贬低别人的研究。这些批评有什么依据?我们把乔氏和维氏二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或许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2.乔姆斯基对语言难题和语言奥秘的区分
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伊始,就受到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质疑和挑战,如奎因、戴维森等。他们根据自己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的解读,从诸多方面对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知识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Lyons 1968:3)。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脑的一种属性,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语言,是一种I语言。这种语言与外在语言E语言相对。这种语言的初始状态就是乔姆斯基定义的“普遍语法”,或者是一种“语言器官”,或“语言习得机制”。正是这种语言习得机制使得个体的语言获得成为可能。挽言之,在一定的语言经验的触发下,个体语言就会自动生长,直至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社会交往对于语言的获得虽不可或缺,但只起到触发的作用。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对这些大脑的属性进行研究。“有许多问题可以引导人们进行语言研究,但就我个人而言,使我着迷的是人们何以能够进行学习?通过语言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大脑的内在属性”(Chomsky 1972:103)。可见,对乔姆斯基而言,语言研究只是一种手段,他旨在通过语言研究理解人类的大脑属性。这也难怪乔姆斯基说他的语言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最后要归于生物学研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乔姆斯基把语言研究分为三个方面:语言知识的性质、语言知识的起源以及语言知识的使用。他(Chomsky 1986:3)又把语言研究的基本问题定义为:(1)语言知识是由什么组成的?(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之后,他(Chomsky 1988:3)又把这些问题进一步表述为以下四个问题:(1)这种系统的知识是什么?(2)这种大脑中的系统知识是如何出现的?(3)这种系统知识在话语中是如何被使用的?(4)构成这种系统知识及其运用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17、18世纪哲学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柏拉图难题,罗素把它重新表述为:“人与世界接触的是那么的少,个人的经验那么有限,可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莱布尼茨认为柏拉图的思想基本正确,但这种知识必定“清除了先在的错误”。换句话说,人类的有些知识是天赋的,是基因决定的一种生物属性。第三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感知难题(perception problem)和产出难题(production problem)。感知难题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有关,产出难题则与我们说什么和为什么这么说有关。后一个难题我们称之为笛卡尔难题,即“语言创造性使用的一面”。笛卡尔及其追随者注意到:在正常的语言使用中总是不断出现与语境相适合的新词。显然,这些新词与外在的刺激和内在的状态无关。它唤起听话人的思想,使他们在相同的语境下也会以相似的方式进行语言表达。在正常的言语中,一个人并不是仅仅重复他刚刚听到的话,而是创造出新的语言形式,即以前未曾说过的甚至语言史上从未发生的语言形式,而且这些话语并不是杂乱的表达(Chomsky 1988:5)。
笛卡尔认为人和其他生物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存在类似于机器,其行动都是受外力决定的。而人类有可能依照外界的刺激去行动,也有可能做出相反的行为。人可以假哭、假疼,但如果说一条狗在那里假装痛苦,就会让人觉得费解。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就是人类区别其他生物存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乔姆斯基看来,人能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不仅在笛卡尔时是奥秘,现在依然是个奥秘。他还认为,和其他生物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局限,不可能对这种问题进行解答,所以他把这种笛卡尔式的问题称作是奥秘。奥秘虽然令人着迷,但人类不可能找到答案。而与语言相关的其他问题,乔姆斯基则认为只是难题而已。无论这些难题多么繁杂,人总是有希望找到答案的,如人们可以通过对个体语言的研究从中发现一些普遍的规则。近几十年生成语法的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这种思想。
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思考》中用一个章节对“难题”和“奥秘”进行区分,在以后的许多著作中也多有论述(Chomsky 1976,1988)。难题是指“语言获得中的认知结构是什么样的?这种认知结构发育成熟的基础又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育成熟的?”(Chomsky 1976:137)。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生成语法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题。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人先天具有某种心理机制,儿童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的基础上,才能在如此有限的语言经验或语言刺激的情况下获得如此丰富的语言知识。这种心理机制从“初始态”经由与周围环境的变化直至进入“恒定态”(steady state)或者说是“最终态”(final state)。尽管人们目前对这些心理机制知之甚少,甚至将其视为奥秘,但乔姆斯基相信无论这些问题多么复杂抽象,人们仍然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乔姆斯基(Chomsky 1976:138)认为,“知识结构不论是出于知识的初始态还是恒定态,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难题而不是什么奥秘,如果问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知识的?为什么人们能做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我们的回答则只局限于我们的直觉和悟性,……‘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问题’,在笛卡尔讨论‘他心’(the other mind)问题时是个奥秘,现在依然是个奥秘。”
在乔姆斯基看来,用“类推”和“概括”并不能解释语言的创造性,如“he is eager to please”和“he is hard to please”便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生成语法理论认为,如果普遍语法的限制足够充分,儿童靠少量的语言经验就可以选择出一部远远超出证据范围的充分且复杂的语法,一部可以提供与已有证据没有“类推”或“概括”关系的语法(Chomsky 1976:148)。从生物学上讲,人脑是一个给定的系统,具有它自己的适应性和局限性。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乔姆斯基还援引了皮尔士和康德的观点。如康德对人类局限性的论述是,“我们对表象和纯粹形式的认知图式是一种艺术,它深藏在人类的灵魂深处,其活动的真实模式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也不可能得以窥见”(转引自Chomsky 1976:148)。
3.乔姆斯基遇到的质疑和挑战
生成语法理论认为语言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对人的先天语言知识进行研究,并认为通过研究,人类是可以发现这些共有的语言知识。如果普遍语法原则足够清晰,它就可以对无限的语言结构表达进行预测,这些原则可以通过个体语言直觉进行检验、修正、完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语言器官,知道人类先天所具有的语言知识,那么语言学习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解决,儿童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在极少的语言经验下运用这些语言知识,这也就解决了柏拉图难题。乔姆斯基的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挑战,如杰罗德·卡茨(Jerrold Katz)认为一个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种非心理的、抽象的、柏拉图似的语言。这种语言被称作P(Platonic)语言,它不同于乔姆斯基的I语言,也不同于外在的E语言。“这种语言独立于人的大脑,也独立于外部的对象,但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和心理或物质对象一样实存的东西”(Katz 1981:12)。这种对象不受时空的限制,“抽象对象根本就不是一种理想的对象,它们并不表征什么心理或心理的东西,……相反这些抽象对象是另一种本体,它与心理或心理对象不同,和经验科学中的实际对象一样,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对象进行正确的陈述”(Katz 1981:56)。
乔姆斯基对语言研究问题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否有道理?他所说的语言难题能否有望得到解决?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对此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奎因,达米特,普特南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成语法的研究前景提出自己的质疑。根据帕特曼(Botha 1991),这些哲学家或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乔姆斯基把社会的语言当作个体的语言,否认语言社会性的一面,他错误地认为通过个体的语言直觉检验就可以获得所谓的普遍语法规则;(2)乔姆斯基把外在的或公共的语言看作是内在的或个体的语言来进行研究,他们引据的大都是维特根斯坦的私有语言论证;(3)语言能力或能流利地说出一种语言是后天训练的结果,而乔姆斯基则错误地认为能流利说出一种语言是因为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4)乔姆斯基错误地把一种开放的语言知识看作是一种封闭的知识,而这两种知识之间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前者是一种事实性知识(knowledge-that),而后者则是一种技术性知识(knowledge-how)。
如这些质疑果真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有关,那么我们如果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当中的主要概念入手或许会对生成语法有更深的理解。
4.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生活形式观
“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语言游戏”一起构成维氏后期哲学的灵魂。“生活形式”是一条主线,维氏后期哲学思想和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生活形式”在其已出版的著作中仅有七次,而在《哲学研究》(Wittgenstein 1997)中就出现了五次。
维特根斯坦本人对“生活形式”并没有给出任何定义,后来的研究者因此有着不同的解释。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1)文化-历史的解释:生活形式等同于文化形式、风格和结构,生活形式是使社会和文化成为可能的形式构架,它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没有解释力,只能在解释链条的末端,是给定之物;(2)“有机的”解释:对人类而言,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如同消化和排泄一样。我们不是通过学习才会使用语言,相反,我们是天生具有这些用法的,因而我们是盲目地使用语言,犹如自然反应一般;(3)语言游戏的解释:“生活形式”等同于“语言游戏”,使用语言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Hilmmy 1987:180-2)。
Baker和Hacker(1985)则从以下几点理解生活形式:(1)生活形式是一个生物的概念,具有物种的属性,人类只有一种生活形式,它是人类的一个物种属性并反映了人类的本质。也可能存在其他的我们可以想象的生活形式,但这些是其他物种的属性本质(如火星人等);(2)与人类不同的生活形式难以为人类所理解,即便狮子能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机器人的行为反应和人类的行为反应有本质的不同,具有不同生活形式的物种不可能和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它们的语言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3)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其他不同的生活形式,想象其概念的形成,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关这种生活形式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概念和语言使用的规则不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有如此的本质,我们就必定有如此的行为活动;(4)就语言的用法而言,反映的是人类生活形式的一致性。这里生活形式是在指我们“共同的自然反应”(common natural reaction),或者是指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共同的实践。
乔姆斯基也说,在人类看来是“奥秘”的东西,在火星人看来或许根本就不是,火星人学不会我们的语言,因为它们和我们有着不同的物种属性,反之亦然。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乔姆斯基所说的“奥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罢了。任何“存在”(being)都在其相应的生活形式上进行沟通、交流、生活等诸多的活动。人类作为一种存在,语言是其本质属性。即便有火星人,我们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语言,因为我们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我们有着如此的生物结构,我们能如此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个生物属性,是生活形式使然,这没有什么奥秘可言。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乔姆斯基所不懈追求的普遍语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也注定不会有什么前途,或者说这种追求注定是无果的。我们都同属于人这个生物种属,虽然我们的语言在外观上千差万别,但我们能相互理解,这不是什么普遍语法在起作用,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物属性,我们的生活形式相互交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动物却不能,这是人类物种属性的使然,是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
5.比较与议论
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是一种共性,人类成员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语言的获得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而不是学习的结果。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意义实现于具体语境中,离开具体的语境无法谈论意义,我们的语言使用是在生活形式这个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互理解,因为我们之间有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有着共同的生活形式。意义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对象。当然维特根斯坦并不是要否定人有一种内在的属性,他更愿意把这种人类的属性视为一种内在的东西、心灵的东西,而心灵的东西是无法琢磨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语境当中才能确定意义。
“意义”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主要论述的问题,“意义”与“理解”,与“意义的解释”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理解是一个本质的,而符号则是一个非本质的”(Wittgenstein 1997:39)。符号的生命是人赋予的,但人们却倾向认为与符号相连的是人的心理过程,“似乎是与语言使用相伴的必定有一个心理过程,就是通过这个心理过程语言才得以发挥作用……我们会受到诱惑而这样认为,语言活动由生物的和非生物的两部分组成,非生物的部分就是我们对符号的处理,而生物的部分则是我们对这些符号的理解,而这生物活动的部分似乎是在一个比较奇怪的中介(medium)——人脑中进行,而正是这个我们所不太理解的人脑的机制或本质使得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Wittgenstein 1975:3)。的确,我们能够如此地思考是因为我们有如此的大脑,为什么会如此思考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和乔姆斯基的思想似乎有点相通,但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先天的大脑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因为“一切都公开地摆在那里”。而乔姆斯基则试图通过研究来发现这种内在的东西,并对这些东西进行描述,进而解释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学会丰富的语言知识。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知识结构进行研究,去发现这些规则,为纷繁的外部语言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可在我们看来,即便有这么一种结构或语言知识的存在,我们也未必能够对它们进行正确的描述。我们能记录一首曼妙的二胡曲子,但记录下来的乐谱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二胡曲子,因为总是不断地有新的曲子产生。庖丁解牛技术精湛,但是我们能清晰地解释其中的技巧或规则吗?乔姆斯基或许说科学家或语言学家可以做到,那么我们会问,他们是如何做到呢?是用日常语言还是纯公式?日常语言必定会产生歧义,纯公式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对某些语言事实的解释,并且对于同一个语言现象或语言事实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说有不同的公式,我们得到的只是公式的表达而不是公式的本身。
如果对某些现象不能进行很好的解释,人们就容易去假设这些现象背后必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起作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器官”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的假设。这种假设并无不妥,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如奎因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趋向”(disposition)。乔姆斯基试图对这种内在的东西进行精确描述,他的这种努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冲动。维特根斯坦要人们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回到粗糙的地面,因为在他看来,意义存在生活中、社会中以及词语的具体使用中。
词语意义之间并没有一个有待我们定义的边界分明的界线,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相关的语言学研究中找到证据。根据Quirk等人(1974)的分类,动态动词(dynamic verbs)指的是行动(activities)、过程(processes)和事件(events),而静态动词(static verbs)主要用来指称事件的一种状态(states of affairs)(Lyons 1968:315)。从教学的角度讲,这种区分无可厚非,但如果从科学意义上看,这种区分很有问题,许多在语法学家看来是明显的静态动词却可以用来指称动作,而且从其划分标准来看,许多所谓的静态动词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它们自己设定的静态动词标准,如被它们划为静态动词的think、smell、have、be、love等词常常被用作动态动词,如“he is thinking”。人们越来越对这种区分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为语法学家的分类靠的仅仅是人们的直觉。但是“状态”未必一定要与“状态动词”相连,“行动”未必与“动态动词”相连。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指称一个状态如“水晶般的澄澈”(crystalline state),也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指称一个状态如“筋疲力尽”(a state of exhaustion)、“沮丧”(a state of depression)等等。“sleep”满足动态动词的标准,但很明显“sleeping”并不是一种“活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许多汉语言学家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不能套用到汉语中来,如汉语中的“在”是介词或是动词?“了”是词缀还是语气词还是动词?“苦了了苦”又该如何解释呢?汉语中的“躲猫猫”、“逗你玩”、“算你狠”、“童子鸡”、“夫妻肺片”等反映了什么普遍语法呢?撇开了生活形式这个大的语言使用场景,我们不可能实现语言研究目标。
Backer, G.P.& P.M.S.Hacker.1985.Wittgenstein:Rules,GrammarandNecessity[M].London: Basil Blackwell.
Botha, Rudolf P.1991.ChallengingChomsky:TheGenerativeGardenGame[M].London: Basil Blackwell.
Chomsky, N.1972.LanguageandMind[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omsky, N.1976.ReflectionsonLanguage[M].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Chomsky, N.1986.KnowledgeofLanguage:ItsNature,OriginandUse[M].New York : Praeger.
Chomsky, N.1988.LanguageandProblemsofKnowledge[M].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lmmy, S.S.1987.TheLaterWittgenstei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z, J.J.1981.LanguageandOtherAbstractObject[M].Oxford: Blackwell.
Lyons, J.1968.IntroductionstoTheoreticalLinguistics[M].Cambridge: CUP.
Pateman, T.1987.LanguageinMindandLanguageinSociety[M].London: Clarendon Press.
Quirk, R., S.Greenbaum, G.Leech & J.Svartvik.1974.AGrammarofContemporaryEnglish[M].London: Longman.
Wittgenstein, L.1975.PhilosophicalRemarks(R.Hargreaves & R.White trans.)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Wittgenstein, L.1997.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G.E.M.Anscomb trans.) [M].New York: Macmillan.
蔡曙山.2007.语言、逻辑与认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