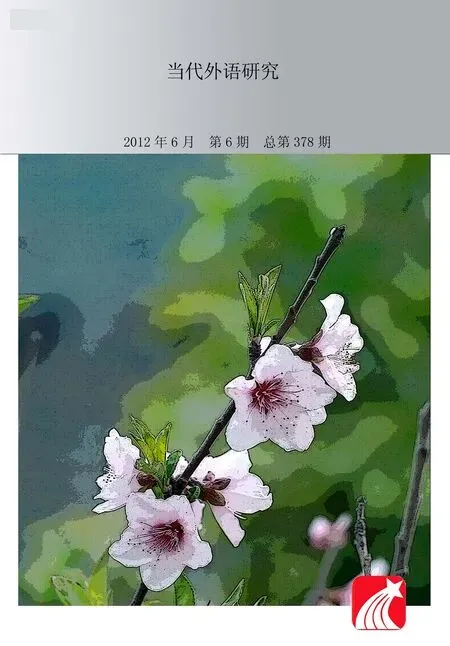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视角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传播与对外翻译
仝品生
(曲靖师范学院,曲靖,655011)
21世纪不仅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纪,也是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竞争、冲突、调和的世纪。对于各民族、各国家来说,如何实现自己的声音与身份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以及全球共同问题解决中的话语权问题。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崛起中的各种问题,决定了她将在国际事务中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必然是一个相互适应与不断认知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就是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对外翻译所面临的接受和认同。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极不协调的关系上,它给全球治理和自身发展造成了中国式的“失语”和缺憾。所幸的是,当前,国家对此已经有了深刻和充分的认识,学者也做出了多种视角的探讨。这些无疑都将对今后中国模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但纵观各家之言,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似乎是“走出去”的两张皮,二者是分离的。事实上,对外传播和对外翻译是人类文化发展和更迭中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它们直接关系到文明之间相互的适应和冲突的解决。据此,建立以接受为目的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就显得格外重要。
1.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从失语走向必然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指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文化有目的地、主动地或自发地向他国介绍和输送。早在周朝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礼记·王制》)的重要性,开始了“通”与“达”的传播和交流。秦汉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文化典籍大量流出。隋唐之际,沿丝绸之路传入亚洲各国,近代传入欧美。据张桂贞研究,中国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三种渠道:馈赠、贸易和掠夺(转引自贾春增、邓瑞2000:7-9)。馈赠是在中西交往中,通过使节的相互往来,把中国古典书籍赠与外国使节,从而使汉籍得以在国外传播;贸易是汉语典籍通过丝绸之路的陆路或海路和中国商品一道流出海外;掠夺主要发生在近代殖民入侵时期。西汉王朝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40~前124年)翻开了中国主动走向世界的第一页。东汉王朝西域都护班超遣使甘英出使大秦(Sina Major古罗马)(公元97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王马可·奥勒留·安敦尼努斯(Marc-Aurel Antonius)的第一位使者来到了汉朝宫廷,终于完成了中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该时期,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都以对方的地区为理想的王国,而且双方主要是靠丝织品等商品贸易来沟通。希腊语中的“丝”读作“Ser”,罗马人也把中国人称为“Sères”(塞里斯人),在《厄里特利亚海航行纪》中记述为“Thinae”,在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置于世界最边缘的东方(参见布尔努瓦1982:75-79)。辜正坤(2007:183)也认为,16世纪以前,我国很多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翻译成别的语言,像阿拉伯语等,西进至叙利亚一带,然后再经过当地的语言转译成拉丁文或其他语种,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东学西传却较晚,是迟至17世纪以后的事情。梁启超也认为:“中国知识界和外国知识界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为第二次”(转引自藏仲伦1991:56)。可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近代以前大多是一种自发的、器物层面的交流,而且接触的广度和深度都非常有限,这无疑造成了中国文化传播的缺失以及对中国形象的浪漫主义理解。
《文选·补之诗》载“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也就是说中国对内重视文治教化,对外强调恩威并施。这样的文化思想是内向性的,它直接把中国与世界放在了两种不同的视域之中,忽视了中国文化在他国的传播和认同,促使了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赤字现象,同时使得对内翻译相比对外翻译的严重入超,最终导致“自在之中国”与他者想象中的“镜像中国”出现巨大的差异和变形,阻碍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近代,由于1840年与1860年两次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开始认识到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1862年开办同文馆,1866年派遣出国人员。天朝大国优势的丧失使国家急于学习和模仿西方,因而在西学东渐中重视传入而忽视了传出,客观上造成了中西文化双向传播中巨大的逆差现象。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只能算作中国西化的副产品,而且主要是靠西方人(传教士和汉学家)来完成的。他们通过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或建立中国学、国际汉学或东方学来满足了解东方的目的。从此,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否定时期,专制和落后成为了异域的中国表征。①早期开展汉学研究的国家主要是法国(1796年6月2日建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1884年设立汉语讲座)、德国(1887年柏林建立东方语言研究院)、英国(伦敦大学1836年设立了中文教授之职)和美国(1851年出版《美国东方学会杂志》标志着东方学建立)。国际汉学的建立,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中国了解和认识的新开端,但认知渠道主要是通过传记、转译、合作翻译和全译。结果,中国形象大多建立在中国古典文化经典、断章取义的文学片段以及主观想象之上,是不实际、不客观的。另外,从新中国诞生之后,出于政治目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的负面报道和歪曲,致使中国文化意蕴的中国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让世界真实地了解中国,消除隔阂,扩大交流,我国从各个方面有计划、大规模地向海外进行传播。1986年7月成立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要同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机构、学术团体等进行交流合作。同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每年都安排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贾春增、邓瑞全2000:176)。目前还开通了两大国际卫星频道(CCTV4和CCTV9)以及6+3对外网络(六大中央级网站和3大地区性网站)。这些举措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中国之中国与他者之镜像中国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一些镜像中国还悄然得到了我们的认同,形成了阿里夫·德里克提出的“欧美人眼中的亚洲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问题(转引自周宁前言2007:2)。21世纪的今天,在西方对中国的旨趣不断增加的时候,在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产品、资本等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进一步认同的前提下,一种针对性、目的性和操纵性更强的,以接受为目的的中国文化形象传播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目的性和操纵性是针对不客观的国家形象而进行的修复和重塑,并不是违反客观、恣意伪造的一种传播策略。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中国文化发展的历时线索梳理并选取相关的对外翻译文献,使中国文化主体与变迁的脉络显得清晰可辨,从而减少西方读者的误判,最终把一个文化丰满的中国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消除国际媒体不实报道中的不良影响,变交往中的被动辩解为主动感动和感知。在对外传播策略上,在异化策略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关照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逐步做到“信达统一”。
此外,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在西方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支撑下发展了数百年的世界,物化的生存环境和心智已经难以承受我们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客观上也需要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为21世纪的人类发展作出世界意义的解答和规划。而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道德、和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案。1988年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巴黎宣言》就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转引自辜正坤2007:39)。近代,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也提出了非常鲜明的观点,他反对“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提倡“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钟叔河1985:278)。但是,当今世界是西化和美国化深重的世纪,要使西方世界主动地来接受中国文化或中国全球治理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就要像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强行输入给我们一样,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文化强有力地输入给他们”(辜正坤2007:40),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全球态度和参与方式。
2.确立以文化传播为目的的对外翻译观
辜正坤(2007:182)认为:“西方文化跟翻译大潮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亦是如此。”也就是说,翻译是文化构建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汉籍外译的历史大致始于公元508年~公元534年之间,即北魏时期(马祖毅、任荣珍1997:2)。近现代以前,我国汉籍的海外传播除了少数中国学者应国外要求翻译了一些之外,大多还是海外传教士在传播西学的同时对中国典籍所进行的一定量的外译和相关转述。西班牙人门多萨所撰的《大中华帝国史》于1585年问世以后,相继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并译《四书》,1593年费赖译《四书》并寄回本国。17世纪中期来华的郭纳爵、柏应理等人先后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贾春增、邓瑞全(2000:147)认为,“中国经籍和孔子学说的介绍完全得力于耶稣会教士”。在接受效果上,18世纪中国思想在欧洲,实现了法德两国的正面影响和英国的负面影响。虽然对法德两国来说都由此触发了哲学革命,但其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别。德国莱布尼兹、沃尔弗把孔子思想当作“自然神教”来接受,而法国百科全书派则把它当作“无神论”来接受(同上:151)。可见,早期中国对外翻译的规模是非常之小的,其目的性和针对性不过是“宣大国而柔远”,没有注意到中国形象在海外的接受,完全沉浸于天朝大国的主观想象之中,传播的载体相对单一和随意,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丰满的中国形象,从而导致了主体文化的变形和交往中的曲误。
利玛窦之后陆续来华的有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艾儒略(Julio Aleni)、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毕方济(Franciscas Sambiaso)、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人。对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主要有两种:一是如徐昌志所谓的“全属无谓”的消极否定态度;二是贵州人郭子章等人倡导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等破除民族藩篱的思想(参见钟叔河1985:24-25)。也就是要么被动接受,要么热情拥抱的态度,使中国西学的影响泛滥到迷信的地步,从而忽视了文化中的自我。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艾儒略1623年的《职方外纪》是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世界(尤其是欧洲)情况的书。书名的翻译体现了西洋教士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传统心理的手法,这是利玛窦译介成功经验的体现(钟叔河1985:26),也是“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翻译原则的最好诠释。这样的翻译方法也深得中国人的欢迎和支持。康熙曾亲自研究拉丁、俄罗斯语文,并指示教士译述中国经典,直至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门特11世派多罗(Tournon)来华禁止天主教徒在华祭孔、祭祖,康熙遂于1719年发布在华禁止天主教的诏书。但是传教士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译介不但对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某种触媒和增塑剂(同上:32)。与此同时,国人认识到了走出国门的重要性。相对来看,“在19世纪以前,仅有三个中国人由于偶然的机会到欧洲并留下了可信的记载”:1287年奉伊尔汗之命出使欧洲的景教徒巴琐马之《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1707年随艾约瑟去罗马的樊守义之《身见录》以及1782年被番舶救起而“遍历海中诸国”的谢清高之《海录》(同上:35)。林鍼(1824~?)的《西海纪游草》是“近代中国人用来测量外部世界大海(主要是美国)的第一只贝壳”(同上:50)。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才有了妇女出国的先例,如梁启超记述的康爱德以及钱玄同长兄钱恂之妻单士厘(1898年随夫到日本)。也就是说,中国对外翻译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被动的,同时历史上域外的中国形象多是西方人他观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新华社的对外报道以及外文出版社等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对外翻译和宣传,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和成就。其中,中国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作为对外传播的主力,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典名著、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的对外翻译和介绍。上世纪60年代,主要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和相关政治书籍。从80年代开始,翻译出版的范围、内容以及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一面将中国的文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用各国语言介绍出去,一面引进国外的作品和最新研究成果。作为中国翻译界的最大研究机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1982年成立,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1954年成立于巴黎)。2008年8月4日至7日,上海成功举办了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主题为“翻译与多元文化”)。2009年11月26日,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主体为“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会上,王晨强调,要建立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适应新形势,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实现在更大范围内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及实现“本土化”战略,切实增强对外传播的实效(陈日浓2010:249)。
3.来自西方的证据
从西方的圣经翻译实践来看,圣经外译经历了从圣俗之争到民族化的过程。在圣俗转圜的过程中,比较突出的是版本的权威性、合法性问题。而在民族化过程中,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民族化与平民化的问题。到了新旧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大多数都把自己的民族圣经版本权威化并通过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译介,同时也传播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使得西方化、美国化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同。早期大英帝国向海外派遣了大量的传教士,当前最大的海外圣经传播组织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者协会和美国圣经协会。它们几乎把新约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覆盖了世界约90%的民族语言(参见Baker 24)。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典型的翻译方法是:(1)原作的权威性;(2)一流学者的判定;(3)目的性与接受性原则;(4)为了不遗漏原文信息而采用的补充和注释等(同上:27-28)。Tymoczko就认为,“圣经翻译尤其局限于其翻译目的、相关的文化元素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等等,所以来自于圣经译者圈的理论家们就会囿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规划和预设所造就的理论观点”(Tymoczko 2004:28)。此外,“百年翻译运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翻译中心首先是巴格达然后是西班牙的托勒多),不但使东方发现了西方,也使西方在发现了自己的同时发现了东方。Burnett(2008)转述他老师的话说:“欧洲的文艺复兴、现代崛起是由两种知识的汇合导致的,一是来源于从君士坦丁堡出走的希腊文明,二是通过伊斯兰世界回流的古希腊-拉丁文明。”可见,以对外传播为目的的对外翻译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促使双方相互的认同和接受,最终使一种目的性的文化安排获得世界意义。
英国统治爱尔兰期间,就把翻译作为殖民方法。从都铎王朝(1485~1603)开始,翻译就成为了改变、输送、传播和迁移的主要手段(Tymoczko 2004:19)。直到18世纪末,由于Macpherson通过英语对爱尔兰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再现,爱尔兰人民才意识到英帝国主义的文化掠夺,同时寻找反抗文化清洗的办法。在这一民族复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策略是译者所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架构所决定的,而且在民族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策略也是不同的。在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受到英国文化的强大压力,只能采用“同化翻译”(assimilationist strategy)或归化翻译法;在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矛盾、斗争公开化的时期,采用“辩证翻译法”(dialectical strategy)或综合法(归化与异化的结合);在爱尔兰独立之后,采用“公开翻译法”(ostensive strategy)或异化法。翻译的“信”的幅度取决于如何翻译才能满足既定的政治目标(参见Tymoczko 2004:163-90)。
4.接受美学视域中的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在对外传播方面的缺憾和在对外译介上的赤字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不平衡,造成中国之中国与他者之镜像中国两者之间不平行。加之西方化和美国化给世界带来的话语强势,必然造成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和麻烦,大大增加了交往的成本。所以在当前的情形下,注重接受的对外翻译和对外传播就显得非常必要。它可以逐步修正“镜像中国”与“自在中国”之间的平衡,还可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公信度,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世界层面的意义。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外传播与对外翻译之间的协调,在多渠道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注重汉英翻译的重要作用以及所采用的原则和策略。同时也要求对外翻译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逐步纠正由于意识形态竞争导致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误解,使一个相对客观、丰满的中国在系统的文献对外翻译中建立起来并逐步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认同,使差异的世界价值观思想池中具有中国人民智慧的要素,把中国的世界治理方式融汇到世界方案之中。
从研究领域来看,19世纪以来,内向型研究已经让位于外向型研究,说明了双向平行研究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鉴于中国对外翻译和传播的现状,应该加强外向型和接受性为主的研究,从而平衡两者之间的不足。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时间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在各个领域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基于内部结构的语言描述和结构分析理论。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并行发展,外部结构的研究成为了最主要的研究旨趣。70年代,文本结构研究彻底地被德国学者姚斯等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冲破,一种基于主观主义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性理论把我们带入了研究中的“接受”和“效果”等重要视域。对于对外翻译来说,“改写”、“操纵”、“目的语读者的反应”等成为了原作重新获得生命和意义的重要手段。对此,姚斯提出了建立视野的三条途径可供参考:第一,通过熟悉的标准或类型的内在诗学的途径去建立;第二,通过它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熟悉的作品的含蓄关系的途径去建立;第三,通过虚构和真实、诗学和语言的实践功能之间的对立运动的途径去建立(姚斯、霍拉勃1989:342)。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接受性,以对外传播为目的的对外翻译策略应该首先以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其次,使翻译传播的内容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心理接轨,同时把当前传播内容与历史上存在的译文范本相结合并使之具有关联性,把已经存在的认知当作传播翻译成功的触媒;最后,通过异化翻译造成受众认知的差异性或陌生化,逐渐使翻译传播的内容获得接受。
但在文本意义产生方面,接受学主客观主义观点上的冲突造成了归化与异化翻译的尴尬处境,而调和也只能是在对原语文本有目的的结构选择和读者的接受两者中去寻找(姚斯、霍拉勃1989:387),即在对外翻译的选择性、针对性、目的性以及接受性方面予以考虑,而不是简单地争论该用什么方法翻译。而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对外翻译应该关注的是目的和效果以及与两者密切相关的实现方法等。按照哈罗德·拉斯韦尔的观点,传播应该考虑五个方面: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而根据威尔伯·施拉姆的观点,传播是“共同经验”范围内所达到的效果。这也解释了辜鸿铭英译《中庸》在海外得到成功传播和接受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正因为如此,王国维等人批评辜氏的翻译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余石屹:2008:3)。
接受学和传播学意义上的目的性安排能促使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的增强,改善中国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平衡关系,使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在各个认知层面上得以成功的实现。薛福成在《变法》篇中指出,“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钟叔河1985:336)。梁启超也曾把中国史区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这指出了中国文化不同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三个层级,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最终,“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以滋补本民族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在与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张岱年、方克立2004:97)。
据此,建立以接受为目的的对外传播和翻译,首先要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形象的内涵问题。根据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国形象所应该包含的要素主要有:先秦诸子文化思想;家族式封建帝制文化;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等。同时这也是传播与外译的一条中轴或主要路径。先秦文化突出的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基质,是文化的源流,是“杂”;自秦汉之后,中国文化在家国思想的融汇中得到了整合,文化走向统一,突出的是“合”;至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启蒙,突出的是“变”;而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其主要特征,突出的是“适”。其次,应该基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总结归纳中国文化主线,把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内涵和变迁结合起来,使文化传播和对外翻译能够充分反映中国自在的文化形象,同时依据西方视域中的中国文化形象进行针对性的补充和修正,逐步改变历史上理想主义和否定性的中国镜像。最后,重塑一个完善、丰满的中国现代形象,使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严格区分开来,完成中国经济强国与文化大国的融合,超越民族国家发展中的民族性、地区性,最终使中国形象获得世界意义。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文化内涵与意义的选取——修复——重塑三个不同的但联系发展的方面,是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结合。许源冲就认为,在英译汉诗的时候,应该“依也,意也,怡也”,最终统一于文化层次上(转引自余石屹2008:41-43)。
简言之,在对外翻译的实践中,要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目的,由归化翻译逐渐走向异化翻译,并把中国文化的异域接受当作首要原则,改善汉译英“不能卒读”的现状,然后逐步使中国文化的个性要素获得目的语民族的认同和接受,使之融入到世界主流文化之中,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方式。
附注:
① 根据周宁(2007)的研究,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在马可·波罗时代是理想化的,包含“契丹传奇式中国”、“大中华帝国式中国”和“孔教乌托邦式中国”,而1750年之后出现“否定的中国形象——专制、停滞和野蛮”,20世纪中国的形象是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
Baker, Mona.2007.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urnett, Charles.2008.TracingtheImpactofLatinTranslationsofArabicTextsonEuropeanSociety[OL].[2008-07-01].http:∥www.muslimheritage.org/topics/default.cfm?ArticleID=959.
Tymoczko, Maria.2004.TranslationinaPostcolonialContext:EarlyIrishLiteratureinEnglishTranslation[M].Shan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布尔努尔,L.1982.丝绸之路(耿昇译)[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陈日浓.2010.中国对外传播史略[C].北京:外文出版社.
辜正坤.2007.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贾春增、邓瑞全.2000.传承与辐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C].北京:开明出版社.
马祖毅、任荣珍.1997.中国古籍对外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姚斯,H.R.、霍拉勃,R.C.1989.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余石屹.2008.汉译英理论读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
臧仲伦.1991.中国翻译史话[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张岱年、方克立.2004.中国文化概论[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钟叔河.1985.走向世界[M].北京:中华书局.
周宁.2007.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