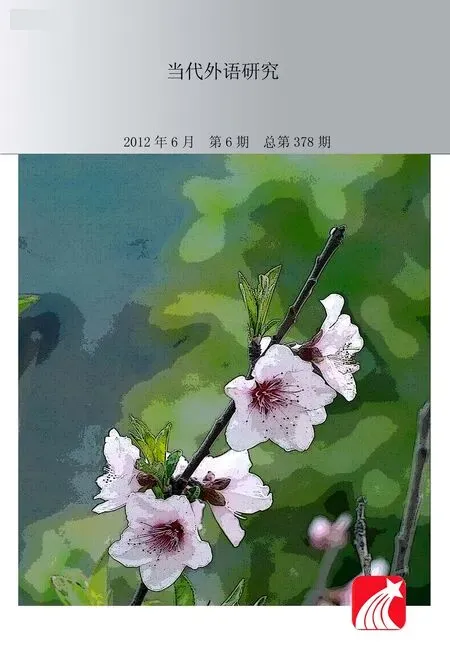翻译中的布白
蒋庆胜
(泸州医学院,泸州,646000)
1.引言
由于语言的线性特征,其在表征现实时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这被称为语言的不完备性,而这一属性常被视为灾难。分析哲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弗雷格(Friedrich Freg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曾不惜劳神费力准备(为科学领域)设计出一套精确的、完全符合逻辑的人工语言来代替日常语言。国内学者王爱华(2007)、王正元(2008)在其文章标题中都使用了“自救”一词,表达了对语言不完备特性的忧虑。我们认为,正是语言的这一特性成就了文本/话语的虚与实,在场与不在场的张力。维氏后期思想正是认识到了日常语言的魅力后呼吁,“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Wittgenstein 2005:54)。在尊重语言不完备性的基础上,如何保留原文的虚实之妙对于翻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虚白”、“布白”都源自书画用语,运笔作画讲究“布白”,把虚白部分保留得恰到好处才能使作品显得更有意蕴,虚实相映,相得益彰。翻译不仅仅要着眼于语言事实本身,还应通盘考虑文本/话语的语言与非语言部分,将原文的“实”与“虚”作为整体再现到译文中。
2.语言的不完备性和文本/话语的虚实
语言的不完备性是指语言结构不能完整地表达意义,暗含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意义完全来自语言的结构。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语言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认为语言的意义与外界不发生联系,仅由词语之间的关系就可确定。维特根斯坦的前期理论认为,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语言结构决定了世界的结构,从而赋予语言本体论的地位。其“语言图像论”意在表明语言之所以能表征世界,就是因为二者是同构的,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李菁2009:58)。这些似乎说明语言是完备的,一定的语言结构能够充分表述一定的意义。然而,与结构主义针锋相对的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不过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符号而已,一切意义都是人赋予的,可以无限延宕。解构主义完全瓦解了结构主义所认为的意义具有客观性的观点。而较为温和、客观的语用学以及快速发展的认知语言学等一致认为,语言是不完备的,语言意义具有相对客观性,但其本质是交际性的,必然要结合外部世界才能共同确定。维氏后期思想也意识到,“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产生于语词用法的多样性,归根结底就是生活形式的多样性”(李菁2009:134)。王爱华(2007)认为,语言的不完备性表现为:“首先,面对复杂繁多的现实,语言显得无能为力;其次,语言中充满了错误与假象”。也就是说,一方面语言通常只能表述一个事件的(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能将所有细节一一描述;另一方面,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并非总是精确的、符合逻辑的,而是具有模糊性的。古汉语中也早有言者表达了对语言这一特性的无奈,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等。又如例(1)中的“那个鬼”和“这种事”也具有意义模糊性。
(1) 费墨:怕那个鬼给你打电话是吧?
矿体主要富集在靠近断裂接触面的两层碎裂岩带内,2号主矿体便赋存于九曲蒋家208断裂所影响的第四层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带内,其具有品位高、形态简单、规模巨大的特点,在李家庄和水旺庄矿区2号主矿体分别占该区总资源量的93.81%和70.90%(表6)。因此在受2条断裂共同影响的区域内,钻孔穿透浅部破头青断裂继续钻进至九曲蒋家208断裂所控制的第四层绢英岩化花岗质碎裂岩带是最为重要的找矿目标。
严守一:麻烦哪!沾上这种事就是麻烦。①
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很难确定例(1)表达的是褒义还是贬义。例(2)由于表述的不完备,留下诸多空白,语义有延宕的可能,可产生至少6种解读。
(2) 我死了,你嫁人。②
a.(如果)我死了,你(就)嫁人。
b.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嫁人。
c.我(一)死了,你(就)嫁人。
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学生将思维聚焦到课文的重难点上,以便更好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情感,从而达到教学目标。通过学习,学生明白了一个自卑的孩子多么需要关心鼓励,人与人之间需要关心和鼓励。对“微笑着面对生活”这句话的理解也变得水到渠成。问题的提出,一要直指关键处,直奔重难点;二要精准,利于学生“以问促读”“以问促思”。
“这——”办公室主任有些窘迫,起身去为迟恒沏茶,忙乱中从口袋里掏出包9元的烟,试探地抽出一支递给洪程,“迟记者,差烟,抽支吧。”迟恒赶紧起身接住,场面上很少有人拿这种烟出来应酬,普遍的是几十元的,不说抬身价,起码保身价。一般公务员,正常的经济能力也只能买几元一包的烟抽,迟恒抽的更便宜,五块一包的“黄果树”,采访时有时不注意掏出放茶几上,对方一见,赶紧弄来包“云烟”为他换上,弄得迟恒很难堪,好像是他暗示似的。其实好烟差烟又怎样,抽上了他妈都是个死。
d.(只有)我死了,你(才能)嫁人。
e.我死了,你(却)嫁人。
f.(等)我死了,你(好)嫁人。
研究者疲于对语言的不完备性表达无奈或提出挽救措施时,往往忽略了欣赏文学语言③绝妙地运用了语言的这一特性所成就的文本/话语中虚实相生的意趣。如果把不完备性视为语言的固有顽疾而显得消极被动的话,那么文本/话语基于语言的不完备性对“虚”与“实”的巧妙运用及对其张力的运筹就显得积极和主动了。语言的不完备性使得语言能够脱离实用主义的窠臼转而在审美情趣上登堂入室。明明可以稍多着墨就可以把事件描述得更清楚,独具匠心的作者却惜字如金,寥寥数语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任人玩味。例(3)仅用28字就勾勒出一幅秋风萧瑟,让人愁肠寸断的图景。在例(4)中,明明可以简单表述的事情偏要多费口舌,非将“兵画”说成“丘八画”,使人摸不着头脑。
根据本隧道的工程环境特点,本次整治工程的总体方案采取隧道洞内套拱结合洞周地层注浆的综合治理方案。洞内套拱措施为在既有隧道结构条件下实施洞内套施模铸混凝土+钢架的二次支护结构,对既有隧道结构进行补强;洞周地层注浆采取洞内外联合注浆形式,并以衬砌壁后回填注浆为主,同时兼顾隧道周边地层改良加固之目的。考虑到本工程隧道空间狭小,基底钻孔和注浆操作均在洞内开展,而隧道基坑侧侧壁地层采用洞外施注的方式进行。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为新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具有无历史包袱、决策链条短、贴近市场一线、机制体制灵活等优势。但由于受到面向的“三农”、产业的弱质性、面对客户群体的复杂性、所处社会信用环境的脆弱性等因素制约,村镇银行强化内部审计策略开展内部审计显得非常必要。
(4) 冯玉祥常说,“我去画我的丘八画,去作我的丘八诗。”④
那么文本/话语中到底何为“实”,何为“虚”?例(3)中的“枯藤”、“老树”等字面义是“实”,留给读者想象和填充的空间是“虚”。“枯藤”、“老树”形象并不具体,但在读者头脑中却有千百种具体意象,或虬枝盘旋,或瘦小凋敝,或相依成林,或独立寒秋。“丘八”是“实”,由此浮现在读者脑海中那个人物形象的诙谐与幽默是“虚”。“虚”便是指这些“在使用过程中经过概念整合而出现的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王正元2008)。更确切地说,文本/话语的“实”为文字的直陈义,“虚”为文字的隐含义及以外的浮现义。文学创作中,“虚”是目的,“实”是手段,“虚境要通过实境来表现,实境要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袁新、郑海凌2011)。“虚”与“实”是一纸两面的关系,互为依托。虚实关系可粗略地分为两类: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为语言不完备性的直接结果,如例(2),后者为语言使用者有意利用语言不完备性所运筹的虚与实,如各种文体语言(如诗歌语言)、修辞手法(如析字,例(4);双关;拈连;委婉语)、语用含糊(如例1)以及蓄意误用(如例5)等等。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翻译问题。
译文2:参议员从地上拾起了帽子和勇气。(侯国金2011)
(5)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赵本山小品《火炬手》)
3.翻译实践中的布白
对语言意义的不同看法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翻译观。由结构主义语言观产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纯粹的语码转换活动,不涉及语言结构以外的世界。尤金·奈达(Eugene Nida)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结构主义翻译家。与之相反的解构主义由于完全否认语言意义的客观性,“主要致力于探讨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问题提醒等因素对于翻译活动的制约作用以及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李菁2009:3),忽略了语言本身。语用翻译学则认为,既要承认语言意义的相对客观性从而严肃认真地对待语言事实本身,又要充分考虑语言以外的各种因素,如文化因素、地域因素、作者自身因素等。因为“翻译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情境下的交际过程”(Hatim & Mason 2001/1990:3),且是一个多方(译者与作者,文本与外部世界等)参与的交际过程。文本/话语的虚白源自于文字以外的多种因素,它始于实的文字而归于虚的意象。因此,要演绎“虚”的美妙必然要通透“实”的意蕴。标题中的“布白”不是指翻译时的“再创造”,而是指把原文的虚实关系忠实地安排到译文中去。众多研究翻译的文献对于文字之“实”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似乎对文本的“虚”的安排少有着墨。本文认为合理安排原文虚实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原文本/话语的虚白进行关联地语用填充与取舍。
基于原文文字尝试多种方法来扩充“实”,也就是填充“虚”,把“虚”和“实”都还原成“实”。具体地说,由于语义有一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译者应尽可能的对原文进行关联的、“自由”的充实(free enrichment)(Carston 2002),把原文的直陈义、隐含意、作者意图、可能给读者造成的浮现义等都一一梳理。为何要做如此“繁琐”的工作?我们认为,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的地位如同法官,不是看哪一方更善言辞驳倒另一方就判谁胜,而是自己本身要对事件有极其丰富的准备和了解,才能不偏不倚。然后再将还原的“实”减去原文字的“实”,经取舍后,其“虚”的意境就将非常贴切。“取”就是决定怎样翻译原文字,一字不落地翻译还是减译或增译,无论增减都有侵蚀原文之“虚”的风险,“舍”就是通过“取”保留“虚”的意境而去除冗余的、关联度低的信息。如果将原文字的实表示为“实1”,填充后的实表示为“实2”,那么,虚=实2-实1。
译文:《魂断蓝桥》
(1) 填充原文——根据原文的整体格调(呆板/活跃/欢快/悲伤/客观/偏激……)丰富词汇的蕴涵,得到细节清晰、关系明确、意涵丰富的实2;
(2) 定位原文的“虚”(虚=实2-实1)。此时“虚”包含大量冗余信息,译者结合实1定位“虚”的可能内容;
(3) 翻译实1,即合理抽取实1,保留文本的虚白。
“合理”一词表明翻译不一定是逐字翻译,毫无增减。下面以例(3)第一句(3′)的翻译详述之。
“枯藤老树昏鸦”一句看似简单,由于作者未交待细节以及语言的不完备性,留予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1)数量。原文并未交代是一/多根藤,一/多棵树还是一只/群乌鸦。(2)空间关系。按照常规关系,枯藤与老树可能为藤缠绕树的关系,但如果(1)的解读不止一棵树而是几棵,那么枯藤与树的关系又当存疑了。再者,昏鸦与老树又是什么关系?是栖在树枝上还是刚从树上飞走?是一只还是一群?(3)乌鸦的状态。除了是歇还是飞的状态外,乌鸦在鸣叫吗?如果天/树上的乌鸦没有鸣叫应难以引起在马背上赶路的人的注意。如果有的话声音是哀鸣还是高兴?哀鸣的乌鸦可以映衬后文的“断肠人”,但自在得意的鸣叫声同样可以反衬旅人的落魄。相信读者还可以将这个过程进行下去。这个过程就是对原文的虚白进行填充的过程。据上文分析,对例(3)首句(3′)填充的可能结果如下:
(3′)枯藤老树昏鸦
结合作者的生平及创作背景,再综观全文风格与意境,认为c和d的理解似乎更贴切。再次回读原文时,相信此时的感受与初读时已大不相同。透过文字,头脑中萦绕着黄昏时刻,夕阳西下,苍凉的古树上垂着枯老的粗藤,一只孤苦伶仃的乌鸦啼血鸣叫的悲凉意境。那么,此时再翻译原文,在字词的拿捏上就更有意蕴和深度。全诗的译本至少有9种⑤,囿于篇幅仅选首句讨论。
b.几棵秃枝的老树上缠着干枯的藤,黄昏中,一群乌鸦鸣叫着飞回来,落到树杈的巢里。
c.一根粗而干枯的藤缠绕着一棵古树,并从枯枝上悬垂下来,黄昏中一只乌鸦无家可归,站在枯枝头哀鸣。
d.一根粗而干枯的藤缠绕着一棵古树,黄昏到来,一只/群乌鸦鸣叫着飞回老树准备回巢。
……
a.几棵秃枝的老树上缠着干枯的藤,黄昏中,一群乌鸦飞过树梢,飞向远处。
译文1: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翁显良译)
(11) “How is bread made?”
译文3: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许渊冲译)
译文4:At dusk, o’er old trees⑥wreathed with withered vine fly crows.(译者不详)
译文5:Withered vine, old tree, a raven at dusk crows.(周方珠译)
译文6:Withered vines, old trees, crows at dusk.(Fu Sherwin译)
译文7:Withered vines, old trees, evening crows.(赵甄陶译)
译文8: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W.Schlepp译)
译文9:Dried vines, and old tree, evening crows.(叶维廉⑦译)
翻译是对原文的形和义再现的过程。本文对形的翻译主张以形译形,如以诗译诗,以双关译双关,以轭配译轭配等等。“一定的形式表现一定的内容,神寓于形,形之不存,神将焉附?”(冯庆华2002:186)译文1至5在形式上与原文不符,原文为短语式,译文为分句式,导致译文用字过于繁琐。译文6至9在形式上则保留了原文短语式的干练。细节上,译文1和译文3将“藤”译为“腐烂的”(rotten)似乎与原文“枯藤”不符。译文2至7都译为“枯萎的”(withered),剩余译文都译为“干的”(dry或者dried),语义区别不大。在藤与树的关系上,译文1至4为缠绕关系,其余译文则悬置了这一问题;在乌鸦与树的关系上,译文1为“盘旋”,译文2为“归来”,且在“呱呱叫”(croaking),译文3和译文4为“飞走”,其余悬置。在几个意象的“数”上,译文1至7将树译为复数;译文2、译文6和译文7将枯藤译为复数;9种译文全将乌鸦的数译为复数!至于对虚白的处理上,由于“虚”总是要通过“实”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对“实”的分析就可感知对“虚”的取舍。译文1至5在定位原文的虚白上从填充到抽离走得太过,导致无法复原实1,显得臃肿。译文6至9词数不相上下,因此在对虚白的处理上也难分伯仲。总体说来,以上9种译文在意象的位置关系上见解不一;对“藤”、“树”、“鸦”的数量上多倾向于复数,原因之一恐怕是译为单数需使用冠词,会破坏全诗的节奏感和韵律。译文8恐怕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vine,tree均译为单数,crows却译为复数)。译文2在细节处理上更为至情至理,但用词太多(即“取”得太多),且使用的分句式与原文的短语式不符。译得过多侵蚀原文之“虚”,译得过少难现原文之“实”,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难以解决这一矛盾,于是走了极端。译文1至5想摆脱原文用字极少的束缚,大胆地译为短语式;译文6至9,特别是译文7,又显得太死,使读者难以琢磨原文的情感。例如对原文第二句“小桥流水人家”的处理,“小桥流水”无争议,但在“人家”的处理上可商榷。如译文1译为“a pretty little village”,稍显啰嗦。译文3、译文5、译文8和译文9都用了cottage一词,虽可隐喻地理解为“人家”,但诗歌语言既要讲究美感,还要讲究入情。“话语不仅传递言者的想法/思想,还显示言者的态度。”(Sperber & Wilson 2001/1995:10)我们认为在原作者眼中,“人家”的“家”字释放着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由此衬托“断肠人”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悲凉。否则原文也尽可用“房屋”,“草房”(译文5就译为“thatched cottages”)。cottage一词虽简练,但显得冷冰冰的,这恐怕不是作者希望传达的含意。此诗前两句翻译为“Withered vine,old tree,returning evening crows;Tiny bridge,flowing brook,little hamlet homes”⑧似乎更入情,对译文读者的情感有更合理的引导,且韵律上有重心感,但仍有对原文之“实”译得过多的嫌疑。我们始终认为,在翻译时要对原文进行足够的、关联的语用充实,在下笔翻译时,再合理地把填充的内容释放掉,留取真正的“实”才能保证原文的“虚”。更多译例分析如下:
(6) Seven days without water make one weak.⑨
译文1:一周没水喝,使人变虚弱。
译文2:七天没水喝,让人受(瘦)一周。(蒋庆胜、蒋仁龙译)⑩
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水利信息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需要加快建设、重点发展。近年,在金华市水利局的大力支持下,信息化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已初步建成水利门户网站、电子政务、防汛综合业务数据管理、水雨情监控测报等信息化系统,在信息发布、政务公开、防汛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水利信息化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在全球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水利信息化不进则退,必须顺应信息化发展潮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为新时期水利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撑。
此例为双关。原文的“实”是一音两词两义,weak由于音的相邻/相似关系还关涉了week。进行填充至少可得两层意思:(1)一周没水喝,使人变虚弱;(2)七天(没有水)组成一个星期。如何将两层意思如同原文一样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就是翻译的布白与取舍的问题了。译文1只译其一未译其二。译文2“七天”与“一周”相对,“瘦”与“一周”表明使人“虚弱了一圈”,“(忍)受一周(一个星期)”,虽稍显牵强,但都形成了呼应,译出了原文的“实”,保留了原文留给读者的对语言的精妙和幽默的感受。
(7) McCartney, 59, lost his first wife Linda to breast cancer in 1998.
译文1:麦卡特尼今年59岁,他的第一个妻子琳达1998年死于乳腺癌。
类比思维是根据两个或多个对象的内部属性、关系等就某些问题的相似性而推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的一种推理思维形式,是数学探索中常用的一种数学思维方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尽快理解新知识,特别是难点的理解。比如,在介绍连续型随机变量X的概率密度的概念时,书本中直接给出满足F(x)=f(t)dt的非负可积函数f(x)为X的密度函数。学生会很难理解这一概念,教师可以设计如下问题:
译文2:麦卡特尼今年59岁,他的第一个妻子琳达1998年因患乳腺癌离开了他。
译文3:麦卡特尼今年59岁,他的第一个妻子琳达1998年因患乳腺癌去世了。
译文4:麦卡特尼,59岁,于1998年让乳腺癌夺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琳达。(笔者译)
此例不仅是对委婉语lost(死)的翻译,还应考虑隐喻性用法“lost…to…”。仔细分析全句,“59”作为插入语,并不重要;言者/作者使用lost一词表明其对麦卡特尼的遗憾。从达意上看,译文1至3均可达意,但译文1没有使用委婉语,不妥;译文2和译文3似乎只注重委婉语的翻译而忽略了整句话要传达的虚实关系。在缺乏更具体的语境的情况下,译文1至3还有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原句没有明确指明麦卡特尼“今年”59岁;其次,“第一个”暗含有“第二个”,给译文读者留下不必要的想象空间,根据常规关系理解应多为一夫一妻制,“第一任”显然更好;再次,对“lost...to...”这一隐喻性用法没有体现。翻译不是翻译某一点,而是应就全句/全文的虚实关系通盘考虑。
(8) The senatorpickeduphishatandcourage.
译文1:参议员拣起帽子并鼓起勇气。
工地数年摸爬滚打下来,黑健成长为一个项目经理,更成为公司一名施工生产的干将。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王经理总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开疆破土”,通过在建工程承接其他任务,2004年他到泰达博物馆银珠公寓项目,为公司顺利搬迁到天津打下基础,2011年他带领团队到哈尔滨,通过做哈西万达陆续在哈市承接万达茂、富力江湾、华南城等项目,从一个项目,到一个办事处,如今已经成为公司支柱型分公司。
仅从语义传达上看,两种译法都能达意,甚至感觉译文1更自然。但译文1似乎缺乏对原文的真正理解,抹杀了原文利用拈连这一修辞手法传达睿智、讽刺与幽默的意图,“语用标记值为零”(侯国金2011)。译文2用“拾起”接上“帽子”和“勇气”两个宾语,与原文读者一样,译文读者会觉得“拾起勇气”是搭配错误。说明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获得了相同的感受。可见,在“实”的处理上稍有不慎,无意间就把原文的“虚”更改甚至毁灭了。
(9)WaterlooBridge
如何对原文进行填充?办法之一就是“共情”,“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Langer 1986:75)。情感与文学作品有很强的象似性。用共情的方式去经验原作者的创作环境及创作过程能使译者对原作有更深的理解。“观察并不是都用眼睛,也常涉及到思维跟情感”(申丹、王丽亚2010:89)。然而怎样的经验能算得上准确的体验,这难以说得清。因此,为了避免臆断,我们认为要用尽量多的方式去经验原作,“共情”的作用在于使我们的语用充实更有方向性,更加关联。当然,并不是所有填充出来的信息都是有用信息,有些是无用的。但这对于下一步对“实”的取舍也即对“虚”的铺排是大有裨益的。接下来,选择一种相对完满的已填充的原文义(即实2)再抽出原文的实(即实1),释放掉不关联的信息,就得到原文的虚白。最后,对实2进行翻译,则译文就会隐现和萦绕着原文的虚白,使得“实”更加饱满圆润,从而成就贴切、对等的翻译。整理上文步骤如下:
陶慕侃吃了一惊,赶快拆开。他还想或者这位朋友是病倒在那里了;他是决不会做和尚的。一边就抽出一大叠信纸,两眼似喷出火焰来地急忙读下去。可是已经过去而无法挽回的动作,使这位诚实的朋友非常感到失望,悲哀。
此为一部经典电影,其汉译也可谓经典。如果将它翻译为《滑铁卢桥》也不会引起多大反感,但如果按照本文所说的填充工作,翻译起来就复杂多了。首先要对这部影片进行观赏,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去感知原作,也就是对题目进行填充,还要对可能的汉语译名进行填充和取舍,最后,发现此故事的精髓与汉语的一则典故完美契合,由此便诞生了《魂断蓝桥》这一译名。
(10) The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love are gone;/The worm, the canker, and the grief,/Are mine alone.
译文1:年华黄叶秋,花实空悠悠,多情徒自苦,残泪带愁流。
译文2:我的岁月似深秋的黄叶,
爱情的香花甜果已凋残;
只有蛀虫、病毒和灾孽,
是我的财产。
译文3:我的岁月如黄叶,
爱的花果已凋残;
蛀虫伤悲与灾孽,
独与我纠缠。
此为乔治·拜伦(George Byron)诗“OnThisDayICompleteMyThirty-SixthYear”(《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全诗中的一节。一、三行押韵,二、四行押韵,第四句略短。译文1虽更像汉语(古)诗,但与原文意义相差太远,原文的“实”都不存,“虚”将焉附?译文2与原文步步相随,只是译文添加形容词如“深秋的”,“香”,“甜”似乎稍显繁琐。因此译文3(笔者译)减去了译文2中如“深秋的”,“香”,“甜”等修饰语,基本还原了原文的“实”。译文对原文的“实”增译一分,原文的“虚”就会被侵蚀一分,同理,原文的“实”被漏译一分,原文的“虚”就可能被误增一分。理想的情况是尽量保持原文的虚实之妙。译文3省去译文2的形容词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译文2: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丁祖馨、Burton Raffel译)
“I know that!” Alice cried eagerly.“You take someflour...”
“Where do you pick theflower?” the White Queen asked.“In a garden, or in the hedges?”
“Well, it isn’t picked at all,” Alice explained: “It’sground...”
“How many acres ofground?” said the White Queen.
译文1:“面包是怎么做的?”
“这我知道!”阿丽思急忙回答,“你拿一点面粉……”
白王后问:“你在哪儿摘的花?在花园里还是在树篱上?”
在职业的选择上,漂亮女人如蛾逐火地喜爱抛头露脸的行当。比如唱歌跳舞做演员,偏偏都是吃口青春饭的事,便是风光,其时也短,很难登峰造极,成为一方大家。当一般的人人到中年,正朝气勃勃,卓有成效地做着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漂亮女人却已经花事阑珊,走下坡路了,只好自怨自怜,哀叹红颜易老,青春难留。
“唉,根本不是摘的,”阿丽思解释道,“是碾出来的……”
下肢深静脉血栓是骨科常见术后并发症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是肺栓塞的来源,特别多见于骨科大手术。骨科大手术包括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和髋部周围骨折手术。血栓在中医属于脉痹症,气虚血瘀凝滞是重要的发病机理,现就我院院内中药制剂益气通脉汤预防骨科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报道如下。
白王后问:“有多少亩地?”
译文2:“面包是怎么做的?”
阿丽思很快地说:“那我知道,你先得拿点儿面……”
JONES & SHIPMAN 10 精密外圆磨床的诞生得到了哈挺全球各个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哈挺亚洲区总裁张静娟女士在新品发布会中说道:“在近30年的时间中,哈挺的产品遍布全球,随着市场的改变与升级发展,哈挺也开启了新的征程,就是‘中国造’。”而哈挺本次发布的JONES & SHIPMAN 10精密外圆磨床正是“中国造”的典型代表产品。
在《去殖民的文化研究》一文中,陈光兴将“文化研究”定位为全球性去殖民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实践在于揭露殖民认同关系中所形塑出来的文化想象。而《“发现台湾”,建构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一文力图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台湾文化、殖民问题的反思,切入台湾文学的定位问题。此外,刘亮雅的《文化翻译:后现代、后殖民与解严以来的台湾文学》、陈建忠的《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论:现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等一系列著述从后殖民角度发掘出了台湾从日据时期开始被压抑的历史以及被遮蔽的作家作品,打开并有效拓展了台湾重写文学史的论述空间。迄今,如何探索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互动仍有待进一步开掘。
那白皇后说:“挂面还是切面?宽条儿的还是细条儿的?”
“唉,不是一条儿一条儿的面,”阿丽思解释给她听,“是和面,是一块一块的……”
“几块几毛?”那白皇后说。
译文3:“面包是怎么做的?”
“我知道!”爱丽丝抢着说:“首先准备好原料……”
“哪里调的颜料?”白王后问道:“在后花园还是篱笆下?”
“不,不是调的,”爱丽丝解释说:“是打(的)……”
“打?几打?”白王后问。
译文4:“面包是怎么做的?”
“这我知道!”爱丽丝抢着说:“先得有面粉……”
“哪里去涂的面粉?”白王后问:“在后花园还是篱笆下?”
“不,不是涂的,”爱丽丝忙解释:“是磨……”
“摸的?上哪家摸的?”白王后问。
吕煦(2004:222)称,此对话“要是译成汉语,双关所形成的幽默趣味将荡然无存”。原因是独立的双关好译,但成篇章的双关既要译出双关,又要前后衔接、合情合理实属很难。此对话中的斜体字是谐音双关的佳例。Flour与flower同音,ground为多义词,作名词取“地面”义,作动词取“研磨”(grind)义。王后将flour(面粉)曲解/误听为flower(花),因此后文用了动词pick(摘),爱丽丝没有意识到王后偷换了词,纠正说“面粉”不是“摘”的,而是“磨”(ground)的,王后再次将动词“磨”刻意曲解为名词“地”,因此问“几亩地”。从关联上看,爱丽丝认为flour与ground(磨)有逻辑关系,与pick(摘)是误配,需纠正;王后看来,flower与pick关联,ground(地)与acre关联。她们两条线的结合点是flour与flower同音,后来的“How many acres of ground”更属王后故意打趣、刁难。这种看似无理的曲解符合王后与爱丽丝的悬殊身份,也是原文的“虚”之所在。因此翻译时,在flour与flower的同音上需一致,原文内容由此走向分歧。至于后文不必刻意强求逻辑,因为王后知道自己是故意曲解、非逻辑的,如果太“逻辑”会显得王后要么耳聋,要么理解能力有问题。
虽然此为一部经典的儿童读物,但如果原文使用了双关且未解释,那么译者也应该相信译文的儿童读者也能理解双关。译文1的直译不仅未译出双关,而且译文零散不已,前后内容关联度极低。译文2只有前两句还能找到原文的踪迹,但原文flour与flower是音相同,译文由“面(粉)”转换到“面条”是义的转换,方法已经不一样了。从第三句起,译文与原文已相差太远,完全改变了原意。如果脱离了“实”而只取“虚”,原文成了引子,译文是据引子的“再创造”,这并非好的翻译,况且译文2中的白皇后给读者的印象恐怕除了强词夺理外,毫无幽默感可言。因此既未照顾到原文的“实”,也未能再现原文的“虚”。译文3在第一处双关处用了“原料”与“颜料”的谐音,在第二个双关(ground)上使用了与原文意思稍有走样的“打”字,但意蕴差不多,“打”也有数词(十二)和动词(打磨)两层意思。缺陷在于“颜料”与“在后花园还是篱笆下”显得牵强,但“在后花园……调颜料”并非完全不合逻辑。译文4用“面粉”关涉做面包的面粉和女士上妆的“脸粉”两层意思,因此王后用了动词“涂”,而爱丽丝没有明白王后偷换了概念纠正说面粉是“磨”的,王后打断她的话故意曲解为“摸”(偷)的。关联度是足够的,遗憾的是最后一句中的ground兼具动词与名词义,译文实难丝丝入扣。但从译文3和译文4都能清晰可见白王后在明处,故意刁难、打趣,爱丽丝在暗处,天真无邪。此例的“虚”主要在于体现语言的灵动,以及其中的智慧与调侃。
4.结语
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听”篮/足球比赛了,解说员的嘴不可能同时多角度、多维度地播报比赛的现场,说到底是语言的线性和历时性特征使然。无奈之余,我们在听的过程中根据解说员的播报,运用语用充实能力关联地浮现现场的画面,仍然可以觉得栩栩如生。翻译时在处理文字之“实”时还应有意识地把握文本/话语的“虚”以及合理引导读者头脑里的“虚”,目的就是尊重原作的虚实布局,给译文读者一个大致等同的“局”。路径之一就是利用我们大脑的语用充实能力先将文本/话语的“虚”与“实”关联地填充出来,尽量把原作留给读者的可能画面都充实出来,然后再还原原文的“实”,这一去一来看似无聊,实则别有洞天。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不仅是译者与作者、读者、现实世界的交流,翻译实践者还要与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美学家、修辞家以及其他翻译实践者交流。
附注:
① 出自电影《手机》。
② 该例及后文a-f均转引自赵彦春(2005:107)。
③ 文学语言对于虚实的运用尤其精彩、醒目,但并非其他体裁文本的语言就无“虚”与“实”。这是由于语言的功能性使得某些文体(如科技语言)的实用性更强从而显得其“虚”不那么重要或有诗意,因此翻译起来更注重“实”,甚至“化虚为实”,如“British rail engineer at its Railway Technical Centre at Derby have trimmed weight and drag substantially.”被译为“位于德比郡的铁路技术中心的英国铁路工程师大大削减了列车的重量,增加了牵力”(详见范武邱、杨寿康2001)。此译将“trimmed weight and drag”这一拈连拆散翻译就是“化虚为实”。
④ 引自陈望道(2008:119)。
⑤ 译文1和译文3引自陈宁宁(2008),译文4引自刘姝虹(2011),译文5引自桂永霞(2011),译文2、译文6至9引自顾延龄(1993)。
⑥ 在刘姝虹(2011)中为tress,笔者更正为trees。
⑦ 其完整英文名为Wai-lim,Yip,通译“叶维廉”(http:∥baike.baidu.com/view/639496.htm)。
⑧ 从赵甄陶译文修改而来,全文翻译详见蒋庆胜(2012)。
⑨ 原文及译文1均引自刘金玲(1999)。
⑩ 详见蒋庆胜、蒋仁龙(2012)。
Carston, R.2002.Linguistic meaning, communicated meaning and cognitive pragmatics [J].MindandLanguage17: 127-148.
Hatim, B.& I.Mason.2001/1990.DiscourseandtheTranslator[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Langer, S.1986.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perber, D.& D.Wilson.2001/1995.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Wittgenstein, L.2005.哲学研究(陈嘉映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宁宁.2008.《天净沙·秋思》四种译文赏析——兼谈诗歌翻译的可译性限度[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6(4):82-84.
陈望道.2008.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范武邱、杨寿康.2001.科技翻译的虚实互化[J].中国科技翻译14(2):1-4,54.
冯庆华.2001.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顾延龄.1993.马致远《天净沙》英译赏析[J].外国语84(2):12-14.
桂永霞.2011.《天净沙·秋思》英译的修改——与Schlepp先生商榷[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3(2):89-92.
何自然、李捷.2012.翻译还是重命名——语用翻译中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1):103-6.
侯国金.2008.语用学大是非与语用翻译学之路[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侯国金.2011.拈连的语用修辞学解读和“拈连译观”[J].外语学刊163(6):109-14.
蒋庆胜.2012.语篇视点译观——以十篇《秋思》译文为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3)(待刊).
蒋庆胜、蒋仁龙.2012.相邻/相似律视角下的英语谐音双关翻译[J].英语研究(待刊).
李菁.2009.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金玲.1999.英汉双关语结构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24(9):12-14.
刘姝虹.2011.从德莱顿的“诗歌翻译三分法”看英译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J].科学时代(上半月)(4):96,105.
吕煦.2004.实用英语修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申丹、王丽亚.2010.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爱华.2007.语言的不完备性:明达语言与语言自救[J].外语学刊134(1):19-28.
王正元.2008.浮现意义对语言不完备性的自救[J].外语学刊141(2):22-26.
徐莉娜.2003.委婉语翻译的语用和语篇策略[J].中国翻译24(6):15-19.
袁新、郑海凌.2011.文学翻译中的虚与实——以屠格涅夫作品汉译为例[J].俄罗斯文艺(4):57-62.
赵彦春.2005.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