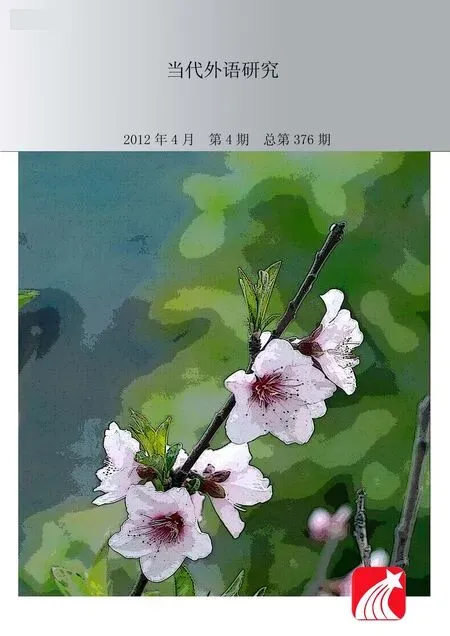历史的空间书写
——论《根》的空间政治性
刘 彬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510665)
在对美国黑人文学进行研究时,奴隶制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但提及它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这种制度带给美国黑人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创伤以及对这种制度的控诉,往往忽视了对文学中再现的奴隶制本身的认识和揭示。非裔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里创作的《根》(1976)是二十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延续。哈里“从头道来”,从“根”掘起,将美国黑人乃至整个美国的一段历史艺术地再现,从而赋予此书史诗般的光辉。用后现代空间理论来解读这段被还原的最没有民主、最没有自由、最没有人权的历史,将有助于人们充分认识历史的空间建构。
二十世纪末哲学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空间转向”被认为是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它是“空间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后现代的空间既是产物,也是力量。一方面,空间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被生产之物,而非传统意义上物理的、自然的、中性的处所,亦非承载社会现实的客观均匀的媒介、框架和器皿。另一方面,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使得空间具有生产性和政治性(汪民安2005:101)。后现代空间理论为文学研究提供全新视角,用它阐释《根》挖掘的这段历史将揭示“空间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同上:104)。奴隶制的社会现实通过社会空间的差异性分配,通过对空间中黑人的身体规训、对黑人的空间实践的控制,从精神、肉体和物质各个方面奴役黑人。空间变为社会的空间,社会则成为空间生产的社会。易言之,奴隶制生产了奴隶空间,而奴隶空间折射出浓厚的权力意识,具有政治性。但被发配在“第三空间”中的黑奴们从未停止过抗争。因此,美国黑人的血泪史是社会权力关系通过空间策略性地和政治性地生产的历史,是黑人栖居空间日益边缘化和日益狭小的历史,也是黑人利用空间不断进行抗争的历史。
1. 社会空间的划分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空间观。他认为,人们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空间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他(1991:30)由此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简言之,空间的分配和再分配由利益驱动,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
对空间的开拓与占有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征,这也是资本“解域化”本质带来的必然结果。现代资本主义如要继续发展,就不但要进行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还得在全球范围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进行全球空间大生产。美国奴隶制便是全球范围资本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白人奴隶主与非洲黑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空间上的控制和被控制,表现为权力阶层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等级化并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功能。
《根》中的叙事起始之时是1750年早春时节,这里原始但有序,宁静又和谐。部落、长老、妻儿;狩猎、捕鱼、旅行。这些人物关系和日常生活构成了彼时的社会空间和空间中的权力秩序。由于未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滋扰,这个较为封闭的空间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礼俗:播种和庆丰的歌舞与祈祷仪式、篝火边大树下长老的议事会、森林中男子的成年典礼、村落之间特有的击鼓传递信息的原始方式、每位孩子诞生时村民的欢喜之情以及给孩子命名时的神圣与庄严,等等。
这个空间极富浪漫色彩:晨雾荡漾的肯必波隆河弥漫着红树林的浓郁麝香味,河两旁畅茂滋长的草木、两岸熟睡中的狒狒、树丛中的野猪、栖息林间的百鸟和苍鹭齐飞的河面为它蒙上了田园诗般的静谧祥和。在更宽广的支流上,“成千上万的海鸟在天空翱翔,组成一道天际彩虹似的巨毯”(哈里1999:4)①。栖息在这片广阔天地中的男人都被誉为“旅行家、贸易家”。他们行走于广袤的空间,体格健壮,精神富足。这里的主体和空间相互渗透,相互构成,主体对空间滋生了强烈的寄托性感情。这个稳定、惯常和节奏缓慢的空间只有流动递进的时间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人们在此扎根。
然而,殖民者摧毁了一切。殖民主义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其权力运作从一个空间穿越到另一个空间,即从宗主国空间移至殖民地空间,通过破坏、瓦解殖民地空间秩序,构建出新的空间秩序。土著居民原有的空间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整个村庄和部落都被烧毁。世代缔结的原始纯朴民风开始蜕变。为了利益,这里开始了杀戮与背叛。
这片原始村落被纳入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流程中,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利益版图的一部分。在由殖民者绘制的世界版图上,非洲成为“黑暗的中心”。黑暗是危险的,也是野蛮邪恶的,必须由现代文明来拯救。白人殖民者“挑起白种人的担子”(王佐良2006:106),以救世主的身份侵入这片土地。在白黑二元对立的话语系统中,黑低劣于白。于是,成千上万像“我”的祖先卡巴拉·康达·金特那样的黑人被掳掠到美洲大地并且受制于白人统治。从这个由土地、植物、动物填塞,通过血缘来架构的丛林空间中,他们被连根拔起。
在宗主国的土地上,空间不再是黑人自由游走的场所。这里的空间被划分为一个个农场。每一个农场犹如一个缩微的社会,折射出社会权力支配关系。奴隶主阶级把从非洲掳掠来的黑人康达以及他的黑奴后代们安排在诸如奴隶排房[也称“奴役房”(204)]、菜园、农场、鸡和猪圈等最低层的空间中。住在“过度闷热且密不通风的泥屋”(377)中,康达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掉入陷阱的动物”(173)。那些白人奴隶因为肤色优于黑人而拥有自己独立的小木屋,有相对的自由。白人主人则居住在“好像和谷仓一般大”(254)的、刷得白白的独立气派的大房子中。他们的居所就是农场的中心,是权利的象征,任何重大决定都在此构想并被宣布。整个农场就象一所全景式敞视式监狱,奴隶主的大房子就是位于监狱中心的那个瞭望塔,安坐房中的白人躲在窗后便可窥视一切。更重要的是,黑奴无法确知何时、哪扇窗会闪现那双权利的“眼睛”。如此一来,黑奴便被“可见”却又“无法确知”②的权力囚禁起来,白人由此确保权力自动地、匿名地但又持久地发挥作用。
最令黑奴羡慕的工作就是厨娘,她是唯一可以在大宅子中干活的人。因为可以接触主人,她的消息最灵通。表面看,她的地位似乎被拔高了。但厨房是一个艰辛劳作但又得不到任何回报的苦涩空间。它“代表着家庭中的屈从位置。厨房……成为权力结构的测量砝码……厨房是社会结构刻写在家庭空间中最深的痕迹”(汪民安2005:167)。
显然,黑奴、白奴和白人奴隶主占据着不同的空间。奴隶主用具有差异性的空间等级来划分阶级的空间间隔,从而压迫黑奴。这种层级性空间成为社会等级的记号,是一种惩罚结构,是被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
2. 对空间性存在的身体的规训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身体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身体的历史”(转引自汪民安2005:18)。福柯(2010:154-155)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对白人奴隶主而言,黑奴的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对身体的控制和侵犯从非洲黑人被强行捆走那一刻就开始了。小说中,康达等人在海上四个半月的漫长航行是最触目惊心、最能体现身体暴力的章节。
贩卖黑人的这艘船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各种身体规训机制,集中体现了权力、身体与空间的关系。
在海上,包括康达在内的所有黑人男女只能蜷曲在甲板下狭小、闷热、散发着恶臭的船舱中,终日黑暗笼罩。只有舱门开启,才知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白人则占据着甲板以及所有具有操控功能的空间,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对关押者肉体、行为和时间的安排,即通过对黑人的身体、日常行为、精神状态和语言使用等全面监管,白人强行规训和改造黑人,将其驯服成符合白人道德、法律和习惯的人,从而保证奴隶制的社会秩序和权威。
在甲板上白人将对触犯了律例的黑人实施公开的肉体刑法:或者当众鞭挞肇事者至皮开肉绽,然后浇海水用钢丝球洗涮伤口;或者砍掉肇事者的一条腿;或者直接把人丢入大海。这些场面如同《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犯人的肉体”和“断头台的场面”两章节所描述的中世纪的酷刑一样血腥。“公开处决是展现武装的法律的一种仪式”(福柯2010:83)。它展示的是胜利,显示了施暴者对罪犯所行使的优势权力。公开处决的目的是杀鸡儆猴,令人心生恐惧。
捉或买到黑奴后,奴隶主最首要的任务是通过规范和训练等手段塑造可以使用的驯服的身体。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摧毁黑人逃跑的意志,让其最终接受现状。康达被卖为奴隶后,先后四次出逃,每次都被抓回来接受极为残酷的、致人于死地的身体惩罚。第一次他被吊在树上接受鞭打,“每落一鞭,他的整个身子都像是要裂成两半”(187),直到昏死之后鞭笞才告终止。第二次被抓后,康达双手被绳子绑紧,体力尽失,全身发抖。之后,他被严密监视,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恶毒鞭打。第三次,白人土霸用枪顶着康达的头,工头则扯光康达的衣服,让他全身裸露在冰天雪地中。皮鞭抽得他皮开肉绽,直到他意识模糊,眼前一片漆黑而倒下。最后一次的惩戒最为严厉:他被生生砍去了右脚板。从那以后,他再没逃跑过。康达后来不得不羞愧地承认:“他已开始喜欢这个农场上的一切现状,而不愿冒着逃跑时会被抓或被杀的可能”(238)。在长期的合法的规诫性权力母体中,诞生了在肉体上被驯化的黑奴。
权力对身体侵害和压迫的极致便是对黑人女性的任意蹂躏。康达的女儿济茜因帮助逃走的男友写通行证而被“高尚”的华勒主人卖到了别处。乍到那儿,十六岁的她便被新主人强暴,后来生下了儿子乔治。在她之前,这家的厨娘也曾饱受主人的蹂躏。强暴是对黑人女性身体的严重侵害,但对白人奴隶主而言,这是一种资本投资。当时的混血儿在奴隶市场有着可观的标价,尤其是褐色的女奴。当白人奴隶主可以肆意强暴女黑奴时,这种行为便不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性罪恶。
奴隶主通过对黑奴身体的戕害将黑奴驯服为温顺的可以使用的“汤姆叔叔们”。因此,奴役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身体过程,是对身体进行侵犯、惩罚和改造的过程。
3. 空间实践的规约
等级空间划分和身体惩戒的最终目标和结果是限制黑奴的空间实践,使其“规范化”。“规诫性技术”围绕这个目标建立起详细的律例。称为“提琴手”的黑奴曾对康达说:
照他们的法律…当我厌恶拉提琴时,白人打断我的手……那些法律条文每六个月就会在白人当地的教堂里宣读出来。在他们成立一个新殖民地后,首先就盖一座法院以通过更多的法律,然后再盖一间教堂来证明他们是基督徒……有条法律规定黑奴不准带枪械,甚至不准带有像棍棒的木杆……被抓到没有旅行通行证而四处游走,就会被抽打二十鞭。直视白人的眼睛,就抽打十鞭……举手打基督徒,就抽打三十鞭……发现你说谎,耳朵就被割掉,说谎两次,双耳都要割掉…杀了任何白人要被吊死……。(228)
除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每个农庄的主人还会为黑奴制定不同的规矩。稍有触犯,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此外,法律“不准黑人受教育、读书或写作,也不准给黑人任何书籍,甚至不容许黑奴击鼓——任何非洲物品都不准”。所以“提琴手”忠告康达:“我告诉你,你必须忘记这种非洲土语”(同上)。
这些为惩罚抗逆而设立的各种制度是一个推行“规范判断”的过程,显示了奴隶制对黑奴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改造。空间划分和身体惩戒已成功地驯服了黑奴的肉体。对奴隶主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他们辅之以一种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精神惩罚。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奴隶主剥夺奴隶的教育权利,生产制造差异。识字的黑奴结局通常悲惨,所以,康达的妻子蓓尔极力掩饰她识字的真相,即使和康达结婚后也没敢马上告诉他这个事实。后来蓓尔又极力阻止女儿济茜认字。另一方面,奴隶主抑制文化差异,试图在一个异位空间迫使黑奴文化失忆,塑造另一个文化个体,改变其认知模式,结果便是混杂性文化的诞生。白人禁止黑奴使用非洲土著语言,禁止谈论非洲的一切,禁止非洲的宗教,以基督教取代之。康达习惯每个月把一颗石头放进葫芦里以计算自己的年龄,但这种行为引起主人的怀疑而被警告。此外,通过买卖奴隶,解构家庭稳定性,也可达到消除黑人文化传统的目的。
抹杀黑人文化最常见也是最有力的手段便是更换名字。殖民者深谙空间的权力含量,拥有空间即拥有权力。为黑人命名是将黑人“消音”,使之成为“无声的他者”。康达被卖后被命名为“托比”。厨娘蓓尔、车夫山森、鸡仔乔治等都是白人强加的名字。不仅如此,每个黑奴在自己的名字后必须冠上主人的姓氏。比如,康达在第一家农场时叫托比·李,卖到另一家农场时又叫托比·华勒。身处异位空间的黑奴强烈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权力,感受到非洲文化的不在场和黑人自我身份的剥夺。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化和精神都被抽空。
骑墙于白人文化与非洲文化之间的黑奴们在内心深处产生了深深的异化感。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现代“外乡人”(stranger)。作为外乡人,“他们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齐美尔2002:143)。身份的流动性和内心的漂泊感使得非裔美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斩断与非洲故土的联系,他们渴望精神的回归和身份的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7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潮便是这种情绪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4. 对空间的反抗
列斐伏尔指出,“对空间的不驯服同对空间的驯服的历史一样古老”(转引自汪民安2005:110)。福柯也有类似的看法:“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可能会有抵抗。我们可以永远不落入权力的圈套,我们总能在确定的条件下依照某种精确的策略减少它的控制”(转引自凯尔纳1999:71)。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为这种抵抗设想了具体的承载空间和方式。他认为,由“阈限的”或“间隙的”或“之间”等范畴构成的“第三空间”为被殖民“他者”提供了反抗的可能。“他者”通过“表演性的模拟”生成一种“差异性的再现”,这样产生的讽刺效果削弱并破坏了统治者的权威(王宁2009:201-203)。事实上,这些黑人“属下”们在“第三空间”以一种“微观革命”的方式对抗着规诫性和规范化机制。
这种抗议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白人奴隶主试图利用话语系统建构臣服的主体。然而,黑人在被迫学习白人语言时却生成了一套“模拟两可”的“混杂”话语。它既模仿原体,又有意与之不同,这就是黑人英语。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认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个人……借助这种策略性行为来反对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转引自凯尔纳1999:319)。胡壮麟(2007:170)也说“语言影响思维”,“言为身份”。黑人英语意味着一个与殖民者不同的思维世界,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一个有悖于殖民者原始意图的身份。黑人们用从“中心”“使之不纯”的策略解构了殖民统治话语的神话,暴露了殖民体制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动摇了权力的霸权地位。
再次,在文化传统上,“康达”们冒着生命危险默默而又坚忍地守护着非洲文化。康达每天清晨别人未醒时,会偷偷向故乡的阿拉神做早祷。女儿出世后,他不顾妻子的哀求,趁夜深人静将女儿抱到奴隶排房外,按照非洲村落的习俗给她实施出生仪式。对非洲黑人而言,名字是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名字是身份。尽管知道孩子的命名绝不能以异教徒的方式进行,康达仍然固执地给女儿选取了“济茜”这个带有非洲色彩的、听起来怪怪的名字。这是对白人话语的反抗,是一种身份诉求。女儿刚懂事,康达便给她讲述了铭刻心中的有关非洲的一切,并教她简单的非洲土语。当济茜有了孩子乔治后,她如同当年父亲康达那样,把非洲的一切口授给乔治。后来乔治的妻子玛蒂塔又把这一切口授给自己的下一代。如此,非洲的文化传统在一代又一代黑人中顽强地传承下来,成为黑人们在这块异土的立命之本。立足于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黑人才能摆脱各种强加的身份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刘彬2010)。
在用语言文化进行“解身份认同”和“反身份认同”(塞尔登2006:226)的同时,《根》也让“逃跑”贯穿于黑奴的历史。“逃跑”是一种“大众越轨行为”及逃避规诫的策略。小说详细描写了康达的四次逃跑,更多黑人的逃亡事件则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散落在故事中。对黑奴而言,逃跑意味着自由和解放。不管白人奴隶主采取多么高压的政策,“逃跑”两字始终潜藏在每个黑奴心中,从来不会提起,但永远不会忘记。权力虽无所不在,但绝非无所不能。
5. 结语
在空间理论视域下,《根》描述的寻根是长途的物质空间跋涉,是家园空间的回归之旅。《根》再现的黑奴历史是政治性的空间生产的历史。首先,奴隶制通过划定等级社会空间秩序将非洲划定为野蛮之地,将黑人定义为“异己”和“他者”,将他们放逐在社会的边缘,排除在社会事务之外。其次,通过对身体的侵害、规训与惩罚,将黑人驯服为黑奴,接受“他者”的被殖民身份,从而臣服权力。最后,通过肉体和精神上的空间制约实践,强迫黑人运用白人的语言、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和行为准则来认知世界,以此“漂白”他们的心灵。但是,倔强不屈的黑人们利用分配给自己的“第三空间”,要么采用精神文化上的或温和或隐蔽的方式,要么通过逃跑和暴动等或激进或公开的身体方式表达对权力的反抗。
美国黑人历史就是划分空间、规范空间、反抗空间的历史。
附注:
① 下引此作只注页码。
② 所谓“可见”,是指被囚禁者的眼前应当不停出现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知道自己时刻受到监视。所谓“无法确知”,是指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受到监视,但他心里应当清楚自己随时会受到监视。参见朱刚(2006:298)。
Lefebvre, H. 1991.TheProductionofSpace[M]. Oxford: Blackwell.
道格拉斯·凯尔纳.1999.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胡壮麟.2007.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拉曼·塞尔登.2006.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彬.2010.解读《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属下的多重声音与身份策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4):69-73.
米歇尔·福柯.2010.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齐美尔(德).2002.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童强.2011.空间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民安.2005.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王宁.2009.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佐良.2006.英国20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亚历克斯·哈里.1999.根(郑惠丹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朱刚.2006.20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