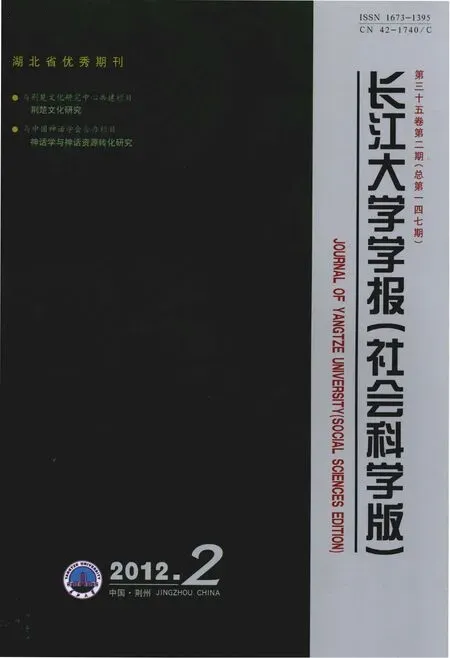“说参请”考释
——“说参请”源流研究系列之一
庆振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说参请”考释
——“说参请”源流研究系列之一
庆振轩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对于宋代说话中的“说参请”,由于资料的缺失,历来聚讼纷纭。“说参请”由佛门禅堂说法问答而来,是带有宗教性的特种说书,旨在借佛门参禅悟道,劝俗化愚,弘扬佛法,《青琐高议》相关篇目可以为据。
说参请;青琐高议;考释
多数论者根据宋人有关记载将宋代“说话”解释为四家,“说经”、“说参请”、“说诨经”为其中一家。除了皮述民先生在《宋人“说话”分类的商榷》[1]一文中提出异议外,几可成为定论。但“说参请”内容究竟何指,它是否可以在当日勾栏瓦舍中单独演出,是否有“说参请”话本传世,以及“说参请”与“说诨经”区别何在,历来研究者多疑似之词。回顾在小说史的研究中人们对“说参请”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说参请”研究现状的了解。王国维先生认为“说参请”在宋代“说话”四家中,应独立为一家:“《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2](P39)而大多数论者主张将“说参请”附于“说经”[3](P116);皮述民先生则认为“说参请”属于“小型技艺”,“非正统说话”[1]。这是较具代表性的三种意见。之所以出现这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看法,是由于人们据以立论的资料不同。王国维先生是依据《都城纪胜》的记载以立论的:“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原意该是以小说、说经、说参请以及讲史为四家。”[4]而后两种观点则是由于没有发现“说参请”话本,据《问答录》立论的,从而认为“说参请”形式短小,“要在瓦舍中作长时间的表演是难以想象”[3](P116)的,“只是说话节目中的调剂性表演”[1]。这样,就把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问答录》是不是“说参请”话本,据以立论是否正确?
一
我们先由宋人关于“说参请”的记载,探求“说参请”的性质。宋代有关记载如下: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5](P11)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6](P196)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说经、诨经:长啸和尚、彭道、陆妙慧、余信庵、周太辩、陆妙静、达理、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借庵、保庵、戴悦庵、自庵、戴忻庵。”[7](P106)
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静、陆妙慧。”[8](P16)
由以上摘引的宋人有关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宋代“说经”、“说参请”艺人全是空门中人,以上四处记载,无一例外。其次,“说参请”的内容、方式与“说经”有明显的区别: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孙楷第先生说,“宋人‘说话’之‘话’,当故事解。”[9]准此而论,作为宋代说话其中的一家,“说经”即讲说佛家经典故事;“说参请”,则讲说的是佛门参禅悟道的故事。“说参请”故事中的人物当是一“宾”一“主”,“主”为佛门高僧,“宾”为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最后,我们据宋代“说参请”艺人的特定身份和有关记载可以推断,宋代“说参请”所讲“则纯粹出世问题”,是“带有宗教性”的“特种说书”[10](P14),是宋代说书僧尼借讲说佛门高僧参禅悟道的故事,以娱悦听众,弘扬佛法的。
基于我们对宋人有关“说参请”资料的分析理解,我们认为,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六收录的5篇小说最类“说参请”话本。[11](P200)篇目如下:
《顿悟师》遇异僧顿悟生死《成明师》因渡船悟道坐化《大眼师》用秘法师悟异类《自在师》与邑尉敷陈妙法《用城记》记圆清坐化诗
为了分析认识“说参请”话本的特性,兹录《顿悟师》[11](P239-240)一篇:
法师名顿悟,姓蔡,赵州人也。师二十丧妻,日号泣。有老僧诣门求斋,师曰:“吾方有丧,日夜号泣,几不可活。子何故求斋也?”僧曰:“生者死之恨,死者生之恨,生死存亡,徒先后尔。余知之矣,不复悲矣。”师曰:“夫妇之私,死生共处,义均一体,乌得不悲?”僧曰:“平生有耳目手足相为用而成一体,汝一旦寸息不续,则分散在地,不相为用,况他人乎?”师乃豁然顿悟,曰:“名利得丧,足以伐吾之真宰;爱恶嗜欲,足以乱吾之真性。其生如寄,其死如归。”乃作礼愿役左右。僧乃为师立法名曰顿悟,为师剃度。后因南去往江州东林。
一日,知郡王郎中谓师曰:“修行子要往西天去如何?”师云:“会得东来意,即是西归意。”太守云:“何人会得?”师云:“好日法会得。”太守曰:“云之门坦然明白,师之门不密主人。”师云:“吾家门户无关闭,入得门时恰似至。”太守知师异人,待以殊礼。师遂辞寺众,入广山结庵而坐。不久,师坐化,乃留诗于壁。诗云:
精神若还天,肉身又还土。
上下都还了,此身元是主。
惟有一点云,不散还不聚。
纵然却还来,未脱寻常母。
若更善修日,西方是吾祖。
篇末有刘斧简短的赞语。令人感兴趣的是,通过这些“说参请”故事,我们可以窥见宋代“说参请”的独特艺术魅力。
宋代勾栏瓦舍中的“说参请”源于佛门参禅悟道,但又与之有明显不同。“说参请”僧尼艺人偏重于讲说高僧、尼僧劝化世人的参悟故事,把禅门“同道方知”的参悟禅机寓于讲说奇异故事之中,用匪夷所思的故事吸引听众。顿悟师遇异僧,言语之间,悟彻死生之理,以一寻常僧人受到太守礼遇。大眼师能令进士石坚“知终身举世休咎”,用异术使其知六道轮回。自在师能令凶悍的县尉敬信礼拜。法师圆清能预知死期,且知道兄长见访,死而复生,临坐化前讲说佛经,使平素憎恶自己的僧人钦服等等。僧尼艺人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异人异事,故事中的宾主参悟,宣扬佛门教旨,使人悟彻名利得丧、爱恶嗜欲、荣华富贵,皈依佛门。其劝教世人,弘扬佛法的特色是十分显明的。
这些“说参请”故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它们均合于宋人关于“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的记载。五篇全部讲的是宾主参禅问道的故事,并且宾方无论是太守、进士,还是情钟世昧的丧偶者,最终通过宾主言语参问,必然敬信佛门,也切合宋代“说参请”艺人皆空门中人的特色。
刘斧所录五篇“说参请”故事长短不一,短小者如《成明师》不过百字,稍长者如《大眼师》只有千字。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说参请”故事短小,“要在瓦舍中作长时间的表演是难以想象”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从刘斧辑录的“说参请”故事中可以看到,这些“说参请”故事是可长可短,伸缩性极大的。《自在师》一篇在写到县尉敬信之后曰:“师复为尉敷演百种妙法。”《用城记》也记法师圆清“大开说百千至妙之道,无上至理之门”。由此推想那“百种妙法”、“百千至妙之道”在僧尼艺人吸收了说书艺人的舌辩之才后,“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古今,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12](P173),于有声有色的讲述之下,应是相当吸引人的。因此,我们认为“说参请”在宋时是可以单独开讲的,而不仅仅是作为说经的入话或插入部分。
二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刘斧生活的时代以及《青琐高议》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关于刘斧生活的年代,我们据《青琐高议》中有关作者生活经历的片言只语可以知道,刘斧早年时代当在宋仁宗年间(该书前集卷二《巨鱼记》“嘉祐年余侍亲通州狱吏”)。他在后集中称司马光为温公(后集卷二《司马温公》)。司马光于1086年病逝,赠太师、温国公。据此,他后期生活至少当在哲宗时代,甚至更后。刘斧生活的时代,宋王朝“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是节相次,各有观赏。京城汴梁瓦舍勾栏之中,百戏杂陈,不避“风雨寒暑”[13](P165)。据理推之,尽管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北宋僧尼“说参请”的记载,但北宋时汴梁有“说参请”、“说经”的存在恐怕是确切无疑的,不然,我们很难解释从唐代寺院俗讲到南宋临安的“说经”、“说参请”的发展过程中在北宋会出现一大段空白。
可以作为我们这种推论佐证的是,宋人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中记有一则苏东坡与歌妓琴操戏为参请的故事:
东坡在西湖,戏琴曰:“我作长老,尔试来问。”琴云:“何谓湖中景?”东坡答云:“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琴又云:“何谓景中人?”东坡云:“裙拖六幅潇湘水,鬓挽巫山一段云。”又云:“何谓人中意?”东坡云:“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东坡云:“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大悟,即削发为尼。[14](P483)
吴曾是北宋末南宋初人,与刘斧生活的时代相邻,所记又是苏东坡与歌妓琴操的故事。据此而论,则北宋不仅有说参请艺人活动,并且影响颇大,以致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正由于刘斧生活的时代有僧尼“说参请”的存在,他才有可能录存“说参请”故事。我们为什么说《青琐高议》别集卷六的5篇故事是“说参请”话本呢?是由该书的性质推断的。
《青琐高议》内容庞杂,但集中记述多有依据,乃编辑前人作品而成书。该书所记传奇有作者姓名的有十余篇,其记述前代及当时人物轶闻的,也多见于前人著述,未有作者署名的作品,也并非全出于刘斧手笔,只是经过他文字上的改编。因此,我们推想,该书别集卷六所录5篇“说参请”故事,除《用城记》明确署名为汉川杜默外,其他4篇“说参请”故事可能是他记录当时流传的,甚至可能是他直接在书场上听到的僧尼讲的“说参请”故事,只不过在文字上稍为润饰而已。也许正是有见于刘斧收集前人小说,摹拟宋人说书形式辑成该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归入《宋之拟话本》一节讲述,并认为,该书“文题之下,已各系以七言”,“皆一题一解,甚类元人剧本结束之‘题目’与‘正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及文章”[15](P80)。赵景深先生在《〈青琐高议〉的重要》一文中也指出:“更重要的,此书……可以说是故事的宝库。”[16](P93)该书比较严格的分类编撰的体例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青琐高议》“集中记述,实际多依类编辑,例如后集卷一记医、卜、相、画;卷二记名公大臣;卷三卷四多证异物和冤报;卷五传奇;卷八记科第荣耀;卷九记龙、鹿、鱼、蛇等等”[11](P2)。该书别集所收篇目较少,其分类显得更为条理清晰一些:卷一至卷四为传奇,卷五为灵怪,卷六为说参请故事,卷七为梦兆。《青琐高议》一书尚有神仙佛道故事多篇,因其均不合“参禅悟道”之旨,与别集卷六几篇小说不侔,均不属“说参请”故事之列。也许刘斧编撰时,正是有见于此,才将这五篇“说参请”故事特归为一卷的。
由于我们确认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六的5篇小说是宋代的“说参请”话本,并据以探求“说参请”的特性,所以有必要辨明一般论者所称引的《问答录》是否是“说参请”话本。
三
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收有《问答录》一卷,题“宋东坡苏轼撰”。此书日本内阁文库有抄本,题名为《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孙楷第先生曾著录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里。张政烺先生在《〈问答录〉与“说参请”》一文中最早提出《问答录》是“说参请”话本:“此书托东坡居士、佛印禅师为宾主,以参禅悟道之体,述诙谐谑浪之言。其事皆荒唐无稽,其辞多俚猥亵。虽以‘语录问答’为名,纯属小话舌辩之流,故知是说参请之话本也。说参请者以说话为主,触景生情,可增可减。其话本仅提供记忆,不必背诵原文,故可字句枯窘如此。”[17](P2)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和陈汝衡先生《说书史话》、《宋代说书史》皆沿用了张先生的说法。
但我们根据《问答录》的内容及宋代“说参请”的特性判断,该书不是“说参请”话本。《问答录》一卷记事27则,除《联佛印松诗》条及袭改“孝宗幸天竺及灵隐”与辉僧问答一则稍涉禅理外[18](P2),余皆与参禅悟道无关。在宋代,僧尼到勾栏瓦舍“说经”、“说参请”,目的在于弘扬佛法,劝俗化愚,所以所讲宾主参悟故事总是以佛门高僧为主,宾最终都是要敬信主的。而该书大多数片断,多显东坡滑稽之智,口舌之能,“喧宾为主”,有时甚至是对僧众的嘲笑,如《为佛印真赞题答》:东坡一日会为佛印禅师题真,赞云:佛相佛相,把来倒挂,只好擂酱。别一日,佛印禅师却与东坡居士题云:苏胡苏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盖子瞻多髯也。据理推之,本意为弘扬佛法的“说参请”僧尼艺人是不会把这些有辱佛门的片断当众演说,去自骂自身的。该书实在是“伪书中之至劣者也”[19](P744)。书中所记苏小妹与秦观的往来歌诗数则,更远离了参悟之道。
正由于《问答录》与宋代“说参请”的参禅悟道之旨不类,明人赵开美在该书题辞中写道:“东坡以世法游戏佛法,佛印以佛法游戏世法。二人心本无法,故不为法缚,而诙谐谑浪不以顺逆为利钝,直是滑稽之雄也。彼优髡视之,失所据也。”赵氏在这里所说的优髡当即说书的僧尼。在说书的僧尼看来,这《问答录》是难以为据的,怎么能说是“说参请”话本呢?
面对《问答录》不涉参问禅理的事实,张政烺先生也认为:东坡、佛印往还事迹“流传既久,展转傅会更不考察事实,兼为迎合听众之低级趣味,益杂市井嘲骂之语,于是禅机少而恶谑多,遂成此书之形式,去参请之义远矣”[17](P4)。胡士莹先生也说,该书“所记东坡、佛印问答,都是彼此嘲戏之辞,与参禅悟道等事不类”[3](P116)。
正因为《问答录》在内容上远离宋代“说参请”的“宾主参禅悟道”之旨,只是袭用了宾主问答的形式,所以它不能算是“说参请”话本,而把它视为“商谜行令”、“俳调之词”更为合适。[20](P188)
那么,是否如胡士莹先生所说:“较早的《都城纪胜》里,只有‘说参请’的记载而无‘诨经’,这是否说明那时的‘说参请’还规规矩矩地说些‘参禅悟道'之事,没有到‘诨’的地步。稍晚的《梦粱录》于‘说参请’之外,增出了‘诨经’一项,两者并列,亦可想见‘说参请’或‘说经’的一支已经逐渐变‘诨’,但正规的‘说参请’仍保留着。最晚的《武林旧事》已只有‘诨经’而无‘说参请’了。这是否意味着‘说参请’已逐渐为‘诨经’所取代”了呢?我们进一步推而论之,《问答录》是不是“说诨经”的话本呢?
我们的看法是,说参请、说诨经“是从释家禅堂说法问答发展而来的,有它的历史渊源”。但即以其源头而论,“禅门古德,问答机缘有正说,有反说,有庄说,有谐说,有横说,有竖说,有显说,有密说”[21](P3)。僧徒问答的反说、谐说即后来“说诨经”的源头。我们推测,在佛门说书的僧尼看来,也许并无“说诨经”、“说参请”之分,其名目之不同,只是著录者的看法。人们把表现参请故事的“庄说”、“正说”当成了“说参请”,而把“谐说”、“反说”当成了“说诨经”。由于后者在瓦舍之中更吸引人,更受欢迎,到后来说书的僧尼讲说时多“谐说”、“反说”,宋人著录的就只有“说诨经”而无“说参请”了。
我们可以想象,当表现僧众参悟禅机的“说参请”由僧寺进入瓦舍勾栏的时候,一定会为赢得观众,使之通俗化、故事化、艺术化的,会为迎合听众增加“诨”的成分,于笑谈谐谑之中禅理寓焉。但无论如何,不会“诨”到不涉禅理的地步,因为一越过了这个界限,它就不属于“说参请”、“说诨经”,而属于宋代说话的另一种“说诨话”了。因此,《问答录》非但不属于“说参请”话本,也不属“说诨经”之列。
我们的结论是,“说参请”作为活跃在两宋瓦舍之中,讲说“纯粹出世问题,带有宗教性”的“特种说书”,有其独异的特点,佛门僧尼借讲说奇异的佛门参禅悟道的故事,以吸引听众,劝愚化俗,弘扬佛法,偏离了这一点去探求“说参请”话本是不合适的。
[1]皮述民.宋人“说话”分类的商榷[J].北方论丛,1987(1).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赵景深.南宋说话人四家[J].宇宙风,1940(9).
[5]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6]吴自牧.梦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7]周密.武林旧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8]西湖老人.繁胜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9]孙楷第.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J].文艺报,1951(3).
[10]陈汝衡.说书小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店,1936.
[11]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罗烨.醉翁谈录[A].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1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A].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14]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6]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0.
[17]张政烺.《问答录》与说参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18]张端义.贵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20]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摘要[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
[21]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Commentary on Shuo Can Qing——one of the Series Study of the Source
QING Zhen-Xuan (Faculty of Art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00)
Due to deficiency of materials,opinions on Shuo Can Qing of the Song Dynasty differ widely all through ages.According to Qing Suo Gao Yi and other related articles,Shuo Can Qing,aparticular kind of religious story-telling,came from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Buddhism interpretation.It aimed to teach the Buddhist wisdom and promote Buddhism among the common.
Shuo Can Qing;Qing Suo Gao Yi;commentary
I207.41
A
1673-1395(2012)02-0009-04
2011-12-12
庆振轩(1955—),男,河南偃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