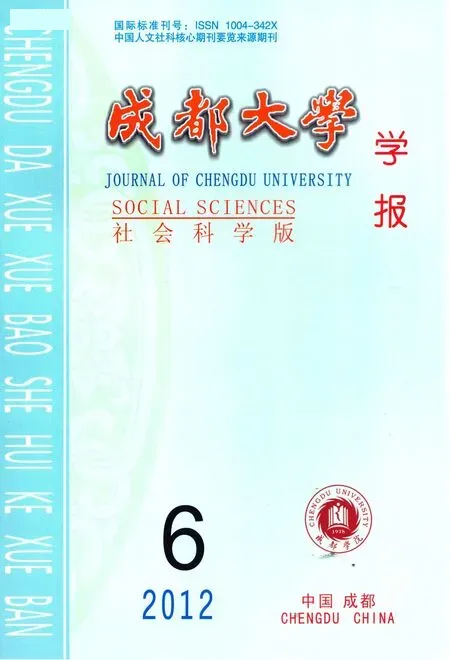试论《人间词话》中的“气象”内涵
熊 娟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00)
“气象”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与“境界”相比逊色很多。在叶嘉莹先生看来,“气象”是“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之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风貌”[1]236但所论不多。佛雏在《王国维诗学研究》中讨论了“象”,但未讨论“气象”,认为“气象”只是“偏于主体的审美意识”[2215。李铎先生《论王国维的“气象”》一文专论“气象”问题,明确指出:“‘气象’是境界的量化概念,是指境界深厚之程度,同时又是与创作主体的修养相关的概念”。[3]33但他对气象内涵的讨论不够深入。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分析气象内涵,探讨这些内涵对传统气象观的继承与发展,并对气象与境界、格调、神(韵)做一个简要比较。
一 “气”、“象”、“气象”的意义渊源
从“气”的字源上看,它涵盖了“天”(自然)与“人”两个方面。许慎《说文解字》:“气,云气也,象形。”《国语·周语》:载虢文公所言“农祥晨正”则“土气蒸发”。《庄子·齐物论》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据此,气为云气、风气和地表水气一类自然之气。另外,《说文解字》在解释“欠”字时云:“张口气悟也,象形,从人上出之形。”《十大经·行守》云:“气者,心之浮也。”据此,气尤为出入口鼻的人体气息。气最初是个哲学概念,指构成天地万物初始的最基本的物质。经过儒、道、阴阳等诸学派的丰富和发展,气逐渐演变为伦理学和美学中的概念,渗透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
总体而言,“气”的内涵有两个维度:一为物质。气在先秦主要有“气”、“精气”和“元气“三个概念。《管子·内业》篇说:“凡物之精,此(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名)气。”认为万物以至星宿、鬼神、圣贤都是气所构成的。《管子·枢言》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是生命的基础和源泉。
作为物质的气有独特的特征。《周易·乾卦》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明气的质有差别。《论衡·幸偶篇》说:“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气的不同和多少决定了不同个性的存在形式和优劣成败。这为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气还有运动和力的属性。《老子》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吕氏春秋·尽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论衡·儒增篇》:“人之精,乃气也;气乃力也。”王充在这里将气与力等同之,气的多少就是力的强弱。这些特征为精神维度的气奠定了基础。
二为精神(道德)。孟子的“养气”说(《孟子·公孙丑》),荀子的“治气养生”说(《荀子·修身》),不仅将气论与生命保健联系起来,还将气论扩大到道德伦理精神领域。魏晋时期,用气来评品人物精神普遍存在,集中体现在《世说新语》里。到了曹丕,用气评品文章,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不仅指作者的主观精神,还指作者的精神在作品中的表现,但侧重点在作家主观方面。其后文论中的气,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以作家论为中心,“气”依然指作家的主观精神及其秀杰正大的力量与气势。陈子昂《修竹篇序》的“骨气端翔”,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文有神来、气来、情来”都属于这类。在这一类中,气常与神、志、意、情等并举或连用,表明对创作主体的分析进一步地细致深入。气本有质的差别,曹丕将其分为清、浊二体,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抑的阴柔之气。但历来的鉴赏批评,大多指前者。钟嵘《诗品》云“仗气爱奇”,皎然《诗式》云“风情耿介曰气”。司空图《诗品》论“精神”曰:“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另一种论气的倾向则是以作品的气为主。气主要指作品的艺术形式,同时也与主体精神有所联系。如李德裕在《文章论》里说“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刘大櫆“以字句、音节求神气”之类即是。他们特别讲求字句的精警挺拔、行文气势的畅达闳通、声调音节的跌宕起伏,将气的贯注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谋求理想的艺术效果。
“象”指一切可视之物,如将天体称为“天象”。《易经》中六十四卦,即为圣人模仿天象而创造的符号,称之为“易象”。所以《易传·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但“象”的目的在于传“意”和“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言”(《易传·系辞上》)。所以,象主要指象征之意。
“气象”内涵主要在于“气”,但与其他由“气”派生的概念相比较又是重“象”。“气象”本义是大自然的景色和现象,它与四时朝暮的气候和山川风貌相关。较早使用“气象”的是皎然的《诗式》,它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陶宗仪《说郛》卷七十九上)气象氤氲的艺术效果生于对体式的透彻了解和纯属营构。体势是作品总的格局和势态,那么气象则是针对作品全局而言的。韩愈《推士》诗云:“逶迤晋宋间,气象日凋耗。”此处气象应是指建安时代精神的反映。宋代以后,气象使用频率增高。严羽多次使用“气象”,但意义却随情景有变化。严羽《沧浪诗话》云:“唐朝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在《考证》中曰:“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这里的气象意义分别指时代精神和作者的胸襟。在《诗辨》中又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将气象视为诗歌艺术创造的五个基本方面之一,应是指诗歌的总体风貌。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称:“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诗人玉屑》卷一)此处的“气象”也指诗篇总的精神面貌。明胡应麟《诗薮》曰:“至淮南《招隐》,叠用奇字,气象雄奥。”(卷一《古体上·杂言》)又曰:“唯工部诸作,气象嵬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卷四《近体上·五言》)此二处应为气势之意。叶燮《原诗·外篇上》云:“七古及诸体必盛唐。于是以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法着为定则。”该气象与严羽所论气象相似。刘熙载《文概》说:“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气而倚重以肖之者。”此气象为总体风貌之意。
综上所述,传统“气象”的涵义主要有三方面:一、时代精神和作者胸襟;二、气势;三、作品的总体风貌。
二 《人间词话》的“气象”涵义
传统气象涵义虽丰富却具有复杂和不明晰的特点,意义随使用情境有别。运用“气象”的诗论家和艺术家们,要么未对气象进行阐释,要么只是进行了譬喻式的简单解释。因此,后人将“气象”概念界定为“指作品情态、境况的总体风貌以及艺术形象显示出来的气概和征兆”[4]132,和“指时代、作家、作品总的气概风貌的概念”[4]138。但却未对气象内涵作具体、细致分析。总体风貌为何种风貌,它包括哪些维度和方面,一直都未明确。
《人间词话》总共六十四则,其中提到“气象”的共有五则,分别为第十则、十五则、三十则、三十一则及四十三则。一般认为,作品前九则为作者的理论阐述,中间四十三则为批评实践,后十一则为引申部分。由于作者开篇明义提出“境界”为论诗词的总原则,批评实践围绕着“境界”展开,即有无“境界”和如何体现“境界”。由此,境界为总概念,气象、格调、神韵等为分概念,总概念是分概念的基础和前提。那么,这里的气象与传统气象内涵是否一致?依笔者拙见,《人间词话》中的“气象”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想、精当的语言及强健的力度。前人所言“气象”也含有这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内容,但王国维的气象融入了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在里面,较前人有所深入。
(一)诚挚的情感
作为文论的气象,唐以后经常与“浑然”、“雄浑”、“雄奥”及“雍裕”等词汇搭配,体现的是一种时代和个人精神,如“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严羽《诗评》)作为建安文学时代精神,“慷慨任气”便是其代表。所谓“‘慷慨’,即指直抒胸臆、意气激荡。[5]163这其中所隐含的主要为情感。“不论是感念世乱、抒发壮志,还是伤节序、叹衰老、嗟离别,只要情感鲜明动人,便都可谓之‘慷慨’。”[5]164魏晋以后,“诗缘情而绮靡”,“情者文之经”、“吟咏性情”等强调诗文情感的主张不断出现,言情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一大传统。那么,作为“作品情态、境况的总体风貌”的“气象”必然常包含情感之义在内。
虽然都强调情感,但王氏所指与前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情感是建立在真切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上,而不只是效果上的“情感鲜明动人”。所谓个体生命体验与叔本华的“直观”说相关。“直观”是在经验而非概念中直接把握对象本身(本质)的方法。王氏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充分表达了对王氏“直观”说的赞同,认为真正的知识、美术、道德、教育都来自“直观”,赞同叔氏所说的直观是一切真理之根本,直观为唯一之根据。那么诗词的情感则应是作者在直观的基础上,由个人上升到人类全体的情感。所以他在《文学小言》中说道“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处于离人游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6]6“体物”直接合于“造化”,这一过程即为直观。体物产生的结果主要便为真挚的情感。
纵观《人间词话》,涉及“气象”的五则无不表现了个体诚挚的情感,且都为主体从自我出发对世界人生宇宙的体悟,没有无病呻吟,也没有应制投赠的功利目的。作出有“气象”的作品,不一定为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诗经》、《古诗十九首》皆无名作者,却能作出“不隔”之作品,它们被王氏多次引用,视为范例。何能写出真切之作品?在于“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作为文人,就应该有独立人格、独特之生命体验,有非功利的审美态度的,将作文章看作为“游戏”,“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7]145
王氏如此强调“真”和诚挚,目的在于纠正清词的浮薄和无病呻吟之弊。有清一代,词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由朱彝尊开创,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崇尚清灵。其弊为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常州词为纠浙派流弊,提倡深美宏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要有寄托,推尊周邦彦[8]162。但其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无病呻吟,寄他人之情感。常州词的开创者是张惠言,王氏病之,曰:“固哉,臯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臯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删稿》二十五则)对张惠言的词学主张颇有微词。所以发出“宋以后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6]27的感叹。
在整个《人间词话》中,“真”是贯穿始终的原则,所谓“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7]77,“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7]40叶嘉莹先生将“境界”解释为“真切感受,真切表达”,是非常切合作者本意的。但真挚情感只是“气象”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有深邃的思想。
(二)深邃的思想
传统“气象”有强调“意”的涵义,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云:“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气象雄浑”直接与作品的“言外之意”相联系。刘熙载云:“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含,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雍裕的“气象”需要“意理精实”。“意”通常是一个和“言”对举的概念,就一般文章而言,是内容与形式;就文学作品而言,是指意蕴与形式。意蕴往往包括思想,但其思想通常为建立在日常生活体验之上的感性思想,王氏所言深邃思想与之稍有区别。
王国维先生非常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他所指的思想既不是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也不是封建士大夫“家国天下”那套思想,而是通过“直观”直接把握到的“实念(idea)”。“实念(理念)”不是个体,而是“事物全类的常住形式”[9]271。在他看来,“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6]57他将艺术看作与哲学一样,都为探寻真理而作。所谓“真理”即脱离意志与时空的永恒思想。我国人思维具有体验性、整体性和直观性的特点,王氏对之非常清楚,故云:“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6]111因此,诗中思想也就常为日常生活的体悟,很少能上升到“实念”层面。在王氏看来,只有少部分的天才能达到,因为他们具有“独能洞见”的能力。中国文学史上,被他称赞的人寥寥无几,只剩下冯正中、李后主、苏轼等。因此,他钟情于那些富有深沉思想的文学作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深赞李白《忆秦娥》“纯以气象胜”,正在于诗人在写景中融入了自身对历史、人生的思考,不落窠臼,显得超迈脱俗,气象阔大,词中所蕴涵的历史兴亡之叹、人生无常之感恰是古今登临之作的共通主题,即脱离了时空限制的永恒之思想。这显示了李白作为天才诗人的独特发现,他将自身个体的生命体验放大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共通体验。相比之下,范仲淹的《渔家傲》虽亦有阔大之意象,但词人自身鲜活的生命体验被更宏大深沉的爱国情绪和立功情结遮蔽了,这样借景抒情就有些“隔”。至于夏竦的《喜迁莺》则有应制之作的共通特点,即自身生命体验与独立思考的严重缺失。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种气象耶?”(十五则)后主对世界人生问题的反思与追问,是一己和孤独的,但却是深沉深邃的。他俨然超脱了个体,进入对世界人生的思考。所以,“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十八则)后主是亡国之君,他作为一位君主并没有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是钟情于艺术,为何具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为在王氏看来李煜词(主要是亡国后)已突破一己之情感遭际,不再是“自道身世之戚”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对全人类生存困境与苦难的思索上。诚如夏中义先生所言:“李词虽涉‘身世之戚’,但由于感慨甚深,这就使其词境越出了个体性自怜自悯而赢得更为阔大隽永的艺术气象,即升华为人类体悟生命厄运时的一般诗哲符号。”[10]43因此“气象”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思考。
过分强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特别是诗歌自身的艺术性。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最终导致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清王夫之《明诗评选》卷八),这是前车之鉴。但强调文学作品思想要深邃,不一定就是重议论、重理。
(三)精当的语言
作为作品总体风貌的“气象”,其形成无法离开语言。明胡应麟《诗薮》曰:“至淮南《招隐》,叠用奇字,气象雄奥。”(卷一《古体上·杂言》)“钱、刘诸子排律,虽时见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调孱弱,初唐鸿丽气象,无复存者。”(卷四《近体上·五言》)说明“气象”与“字”、“语”、“句”和“音调”这类语言形式相关。
王氏也极为重视诗词语言形式,但他以“情景”论(境界论)为前提,即“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达到该条件即为“不隔”,“不隔”便能够直接引起鲜明生动的形象感。他在第七则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也就是说,字词精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境界”问题。陶渊明的诗作在王国维看来是有气象的,因其有情有景,且语言精当,最终产生“不隔”效果。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四十一则)但精当是建立在“情景论”之上的,否则也就为“装饰之字”。正如其在第五十七则所言,“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此道已过半矣”。它们没有真情与真景,所用字皆无精当可言。姜夔词作语言常被后人称道,有曰:“所写景物,往往遗貌取神,体会入微。以健笔写柔情,出语峭拨俊逸,格既高,情亦深,其胜处在神不在貌,最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8]163宋于庭谓:“白石念念君国,似杜陵诗。”后人对姜氏评价可谓极高矣。可王氏却一直对其颇有微词,道“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三十九则)五则涉及格调的词话,就有四则批评姜夔。究其原因在于白石缺乏“诚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未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6]8所以,王氏“气象”对语言的强调是建立在情感和思想基础之上的。
回顾王氏讨论“气象”的五则,有“气象”的作品确乎“语语都在目前”。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字。’‘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这些被王氏称道的句子无不通过精当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抒情主体的精神状态。三十一则对陶渊明诗的“抑扬爽朗”和薛收赋的“嵯峨萧瑟”之“气象”的赞美,细究之也便为其通过精当的语言体现了作者对生命人生的透彻体悟。
(四)强健的力度感
在力度感这一点上,王氏气象继承了传统气象的涵义。“气象”作为由“气”派生出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气”的特质。如前所述,气有运动和力的属性。那么有“气象”的作品也必或隐或显地包含了这一特征。这力度感来自作品情感、思想和语言三者浑然一体而形成的力量。所谓力度感,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因素强烈程度的感知”[11]980。作为诗词,他们的审美因素主要有语言、由审美意象组合所产生的情感和思想。语言作为艺术传达媒介,其语音的抑扬顿挫、浑厚宏亮、婉转柔软,节奏的轻快、滞重、急促、舒缓皆能形成一股或强或弱、或顺或阻的语流和感染力。真挚情感本身就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因诗本身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产物,情感的张力扩至读者,让读者亦为之动容。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深受启发,让情感不停留于感性的吟咏感叹,而是进入一种超脱观审状态和“游戏状态”。这三者的混成一体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之流。
第四十三则赞赏幼安词,说“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慨,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横素波、干青云”的原文是“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说的便是其由内到外的整体给人以一种强健的气势和力度感。
三 气象与意境、格调、神(韵)的关系
气象,作为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中的概念,如前所述,一般被界定为“指作品情态、境况的总体风貌以及艺术形象显示出来的气概和征兆”,和“指时代、作家、作品总的气概风貌的概念”。而《人间词话》中的“气象”,其意义从叶嘉莹先生和李铎先生的解释看,他们皆指作者的精神风貌。文学被称为人学,诗词作为抒情性的体裁,作者的情感、才气、抱负等在作品中体现,是毋庸置疑的。用艾布拉姆斯《境与灯》中的观点看中国的文学和诗论,中国的文学和诗论其实主要为“表现说”。因为我们的传统一直强调“诗言志”、“诗言情”、“文品即人品”。因此,将“气象”解释为人的精神风貌甚为恰当,但有失之笼统的嫌疑,或许我们更应该从文本本身去解释。依笔者拙见,《人间词话》中的“气象”是指建立在“情景”论(或“意境”)基础上的,有关作品整体风貌的概念,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真挚的情感、深邃的思想、精当的语言及强健的力度感。
(一)气象与意境之关系
境界(或境),在《人间词话》中使用多达33次。但意义不尽相同,它们有些是传统文论中的习惯用法之义,有些则为《人间词话》所独有的、作为评词基准的特殊术语之义。作为王氏特殊术语的“境界”,确为中国传统意境概念发展最为成熟的形态。它明确成为中国诗词的最高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其典型特征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六则)。徐复观先生认为“境界实即情景问题而已”。[12]121那么,“真景物”和“真感情”则为境界的构成要素,这跟其在《文学小言》中所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一致。可是,在王氏看来境界有深浅,“上焉者意与境浑”,因此,诗歌风貌有别。作者独以李白、李煜等几首诗词作品为有气象之作,而又说“至意境两浑,则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樊志厚〈人间词〉序二》)。因此,境界是气象的前提,而气象又是境界深的作品的特征。
(二)气象与格调之关系
“格”最初指“量度”和“技法”,“调”最初指“和”与“旋律节奏”。随着后人应用的增多,其意义也不断生成,两者都逐渐具有“意”的内涵。特别是当二者结合后,一方面既保持了二者原初意义,又使“意”的意味得到增强,另一方面还增加风格特征与价值判断意义。格调在明清两代成为诗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因为前七子率先提出“格高调逸”作为衡量诗文艺术风格特点的主要标准。他们企图从诗文的体格声调出发通过“法”和“悟”达到汉唐诗文的浑融化一的境界。清代词以姜夔和周邦彦为师,对格调技法的学习风气更是浓厚。基于明清注重格调的弊端,王国维先生力图纠正,因此在《人间词话》中反复批评白石的“格高”。“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一则),“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三十八则),“‘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三十九则),“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四十二则),“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四十三则)。五则涉及格调的论述中就有四则批评白石的高“格”。
从严羽的“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和叶燮的诗“以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法着为定则”来看,宋以来,人们讨论诗词作品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这几个方面处理好了,便为佳作。但在王氏看来,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不如他提出的“境界”,“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人间词话删稿一三则)有“境界”,其他要素便都具了。从整个六十四则内容看,他谈到了气象、格调以及诗体,不同的是他自始至终以“境界”贯穿。
因此,“格调”,在《人间词话》中相当于严羽“五法”中的“格力”和“音节”,强调作品语言、旋律和章法。在王氏之前,“气象”与格调、兴趣、体制一起为作品的构成因素,这是从形式上所做的划分。但这里,作品从内容上划分为“情”与“景”。气象、格调、神韵、体制等只作为作品的质素,不具有共同构成文章的功能,它们共处于“情”与“景”二分法的“统帅”之下。气象具有涵盖内容和形式的特点,而格调在这里却主要指文章的偏形式的质素。
(三)气象与神韵之关系
气象与神(韵)皆为诗词作品的质素。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作品的思想和情感,不同点在于它们不在同一维度。前者指深“意境”作品的特征,后者指作品的总体精神。
神(韵)在《人间词话》中共出现四次,分别为“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十四则),“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三十二则),“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三十六则),“词人想象,直悟岳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四十七则)。这四则中的“神“除了最后一则所指不同外,皆为“神韵”范畴内的“神”。
“神”本与“形”是一个对举的概念,构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形”是“神”的基础,“神”是“形”的生命。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最早出现在人物品评中,《世说新语·巧艺》:“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此,“‘神’便指人物的精神风貌、气质个性或是万物生机活力的根本,之后便广泛运用于画论诗论中”。[13]29但随着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发展和深入,“神”最终发展到“韵”字,进入到了一种超越“形神”之论的更精微、更深入的审美状态。而作者和读者那种深邃渺然的思绪、天然不可凑泊的微妙意趣,也被归为一个“韵”字。在王氏这里神为神韵之意,只不过由于与人相比拟,神与“貌”便为一个对举概念。他对东坡词一直赞叹有加,称为“有境界”,在《人间词话删稿·四七》中说:“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而对白石则认为“无内美而但有修能”(《人间词话删稿·四八》,可知,“神”即为“内美”,也就为包含情感和思想在内的精神之意。
:
[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李铎.论王国维的“气象”[J].济南:济南大学学报,2005.
[4]蔡钟翔主编.中国古典美学词典[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5]罗宗强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6]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8]姚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夏忠义.王国维:世纪苦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2]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编[M].中国台北:学生书局,1984.
[13]韩林德.境生象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