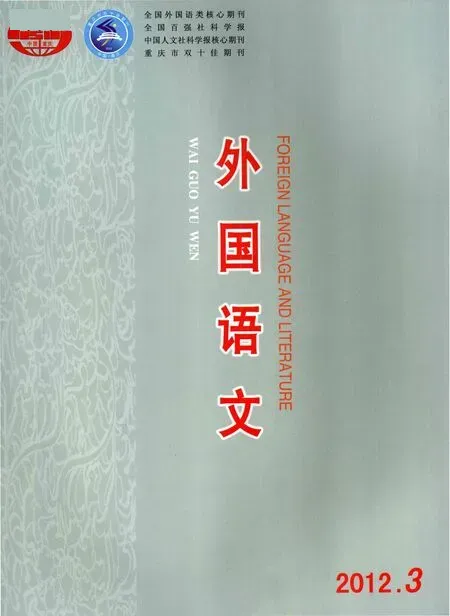翻译即阐释之再思考——谈伽达默尔哲学阐释观在译学中的批判性理解运用
邱 扬
(四川教育学院 外语系,四川 成都 610041)
1.引言
伽达默尔是西方哲学史上少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不仅震撼了整个哲学界,也对包括宗教、文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等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真理与方法》的核心理论“阐释学”(hermeneutics)在我国逐渐升温,对我国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伽达墨尔以多元、开放的对待一切传统文本的态度——延续和更新的态度,为翻译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助于我们翻译实践中抛弃经学主义者的独断专横,也有助于我们摒弃译学中对绝对真理追求的幻觉。然而,或许伽达墨尔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意识到了什么,因而并没有在《真理与方法》这本最应该讲究方法的书中为我们提供出一套完整的理解与阐释的程序和方法。这一匪夷所思、疑窦丛生的悬念,难道是伽达默尔先知先觉于后来者某种未定性的暗示与期待?
我们很难用翻译的思维去推测和臆断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但阐释学的核心“理解”与翻译实践中的“理解”异曲同工,同出一脉,是文本研究的理论前提,其终极目标是通过文本“理解”后的“阐释”或“翻译”来获得原作品最本质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伽达默尔看来,它只能是历史与现在、译者与原作者、原文与译文间一种动态的、“视界融合”后的合法“妥协”,而非文本绝对意义。这一着眼文本现实意义、跨越传统翻译标准解读理念的超现实主义,着实给翻译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然而,在这场文本失去绝对意义的历史与现实、译者与原作的对话中,怎样才能既正确理解和把握伽达默尔宏观阐释学之精髓,又能保持翻译实践不会“潜易原著之精神”的翻译尺度,的确值得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小心对待。
2.翻译与阐释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理解、思维、文字表述活动。要完美地在译文中表现出原文本所具有一切,不仅需要译者娴熟的语言技能、专业知识、文化背景,同时还需要译者在“语际”或语言“符号”的转换中具有相关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阐释学的主体研究是对文本“理解”的研究,于翻译理解、表述有着相同、相似却各有侧重的研究方向。阐释学之所以在我国一经引入便受到译学界追捧,成为一种时尚,其主要原因是伽达墨尔哲学阐释学对文本“动态”研究的宏观思想,从理论上为解除译学翻译中的某些困惑找到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的路标,不再简单地指向“寻求”文本翻译中的绝对标准(这个世界本生就不存在绝对标准)和探索文本的绝对意义,而是把时代、历史、文化、作者、译者、读者等诸多因素融为一体,承认和接受文本与译者因历史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认知差异——即文本自身与译者理解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合理的。中外学者几千年对翻译理论、翻译标准、翻译认知的探索过程和诸多实例也正好或多或少地印证了这一观点,但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断定,翻译只不过是脱去哲学阐释学外衣后的另一副面孔?
也许对多数学者而言这一假设只不过是一个笑话,但见诸于国内各类学术期刊混乱地将诠释、阐释、解释、翻译等同、并列或相互替换(学术术语翻译与运用的不严谨性)、以及《翻译即解释,对翻译的重新界定——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以下简称《界定》)、《文本的未定性与翻译的解释性》(以下简称《未定性》)、《翻译理解的哲学解释学阐释》(以下简称《阐释》)①以上三文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2期、《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4期和《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等各种研究命题却让我们不得不再次质疑翻译究竟是什么?显然,《界定》之概念并非作者随意为之,而是取之于哲学阐释学后的深思熟虑。可这类含混而矛盾的命题(伪命题?)却潜意识地以哲学阐释学名誉混淆了阐释与翻译间某些特定不同的基本概念,把读者诱入理论迷宫、在伽达默尔闪耀的光环下,顺理成章地玩了一把A变B的概念游戏。这场游戏中,游戏者所依据的主要核心理论便是直接来至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有关翻译论述的核心讨论。伽达默尔(1986:496-499)认为:
在语言鸿沟作用下,正是阐释学的模棱两可,才使翻译者经常遇到的困境得以清楚显露……翻译者必须表明自己作何理解,必须找到一种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仅仅是翻译者自己的语言,而且也是适合于原文的语言……因此翻译者的情况和解释者的情况从根本上说乃是相同的情况……因此,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Auslegung),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
从伽达默尔上述论断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取两个概念:一是伽达默尔用哲学家的眼光,客观清晰地勾画出了翻译过程与阐释过程相同的一面;二是伽达默尔另辟蹊径,脱身纷乱冗杂的译论派别之争,进而以宏观视野的价值评判,直接跨越了“直译”、“意译”、“忠实”、“等值”等诸多东西方传统价值取向的翻译标准。如果说第一种概念因翻译与阐释某些内涵的相同而无可辩驳,那么第二个概念很可能会因失去传统翻译含义所指,其译文结果难免不让人想起“17世纪法国译评家梅纳日批评德·阿布朗古尔德的‘优美而不准确’的翻译作品时,所联想到的是一位他‘爱恋过的女人,她很美,但不忠’”的评语。(许钧、穆雷,2009:3)这一法兰西式的浪漫评语,恰如其分地勾画出了阐释与翻译间内涵与外延相似却又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很难不质疑上述《界定》的硬性解读,尽管作者小心谨慎地补上了不够自信的后置定语——哲学诠释学的翻译观!《未定性》之解读,也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质疑推敲,究竟是文本未有定性还是不同译者(读者)的视野、理解或阐释(翻译)方法未有定性?而《阐释》中翻译标准与哲学阐释观的冲突作何解答?上述文中诸多源于解构主义多元认知与伽达默尔阐释说的混合概念,着实让人有些头晕,但翻译内涵的严谨性、制约性却容不得译者和理论研究者自圆其说或自娱自乐。
上述所言之文,文里脉络不乏辩证理性之词,对翻译思考有一定启迪意义,但怎么也逃不出被质疑的宿命,因为“从语义学的角度看,‘阐释’的意义就是答疑”(李砾,2006:1)。现代汉语词典对“解释”的定义也即“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显然,这类“依其定义,阐释,即解开疑问,让人明白”的答疑功能与传统乃至当今翻译所寻求文本的“确定性”和“对等性”原则是大相径庭的。伽达墨尔之后阐释学批判者美国文学理论家E.D.赫希指出,“他关注的不是一种阐释是否有用或者是否能自圆其说,而是阐释能否正确地传达文本的意义,希望有一个有效阐释的具体标准。”赫希在其专著《阐释的目标》里清晰地说明了这一观点,“阐释要有一个基本的伦理规则,如果没有追求事实的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规则,阐释上就仅仅剩下怀疑和相对主义了;那样,所有阐释都可以成立,但将导致无是无非。”(Makaryk,1993:360)阐释如此,翻译亦然。反之,翻译内涵就仅剩下一地鸡毛,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译者又怎能从中体现出“原作的风格和所有的流利?”奈达先生“等值”学说;纽马克“全部翻译问题最终归结到如何写出既传达原意又语言规范的目标语文本”(Newmark,2001:17);严复百年不败之“信达雅”经典翻译理论无一不围绕和涉及翻译标准、规则来进行的。
翻译研究引入哲学阐释学元素,并非为了淡化其固有特性,而是通过广阔的外延更好地研究和丰富这一学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和奥斯·沃伦在文学批评时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具体的艺术作品本身。同期的英国人F.R.利维斯也提出,应该“把诗歌当成诗歌”来研究。(王亚丽,2006:273)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翻译当成翻译”而不是别的什么来研究呢?
3.视野融合与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伽达默尔在阐释学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视野融合(Horizontverschmelung)。认为理解者和阐释(译)者的视野(Horizon)不是封闭和孤独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就是视野扩大和视野交融的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体”。伽达默尔用这一崭新的认知解析了一个长期让译者困惑的实践性问题——即语言、文化、作者、译者等多种不对等因素所引发的文本中的某些不可译性。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lodt)认为,“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伽达默尔同样认为,任何形式下的翻译不过是带有译者主观色彩文本意义横向或纵向的转化,因此“翻译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我国许多学者在翻译实践探索过程中,尤其在各类方言、谚语、比喻、符号、音韵、诗歌等方面也得出相同结论:正所谓“形式转换了,音韵转换不了;音韵转换了,意义转换不了;意义转换了,形式又转换不了”(许钧、穆雷,2009:6)。面对这一难题,要在目标语中实现原文本的所有意义,我们只能另借其道,采用非直接性“翻译”的“视野融合”,因为不同语言间的转换并不存在绝对的、一对一“等值”的文化和文字符号,故多数情况下,译者只能“合法”妥协,“脱去原作的文化外衣”,抛弃绝对求真的理想,按不同时代对原文本赋予新的生命和解读。也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有效化解传统翻译标准制约下的部分翻译困惑,帮助身陷异域文化语境中的译者脱身于文本与目的语语言结构中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翻译过程就是一个“视野融合”的过程,翻译的结果更是一个“视野融合”的结果。
视野融合包含着许多与传统翻译理论标准有别的反叛特征,其内涵不再把翻译视为是原作僵硬的过去,而是原作的新生与延续,因为谁也无法真正复制出作者文本中隐藏的内容。然而我们发现,视野融合在拓展传统翻译理论内涵与外延的同时,又引发出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没有具体方法和规则的制约,译者的视野很容易在译者主体性和历史时段片刻性的“融合”中占据主导作用,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导致翻译中原文本的偏差和失真。究其翻译本质,其实翻译自身属性并不依附于译者的外在社会形态,乃是根置于文本内化的语言文化形态而非外在客观条件。因此,研究翻译,理应把方向转移到文本“内部”,由内而外地去“关注文本的形式结构、技巧、语言、语义以及符号本身的意义”。(王亚丽,2006:273)我们有理由认为,视野融合虽然从理论上为翻译实践解决了“不可译性”的顽症,但同时也仅是翻译中的手段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讲,视野融合是化了装的“意译”,而非翻译全部。
从理论上讲,“不可译性”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不管译者怎样设身处地把自己想像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里过程的重新唤起”(伽达默尔,1986:498),这一共识并无歧义。二是文化冲撞与语言结构差异导致不同文本无法取得完全一致的形态表述,这一点,至今也未在翻译实践中找到万全之策。但我们认为,表述形态终会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认知和时间滞后为代价的某种形式得以释放。这一过程所需要的,仅仅是译者的智慧和读者“羽毛与石头哪个先着地”的认知体验,必定巴别塔(Babel)历史的存在意味着人类语言文化总体脉络是同为一体的。外来词如阿拉伯数字1、2、3……在各类语言中的运用;英语口语 Bye、Ok、Yes、No 以及行业术语 IT、PC、Internet……在各国原态的直接引入;可口可乐、家乐福、沃尔玛、肯德鸡、拷贝等汉语音译手段等,正是目前翻译中释放“不可译性”为“可译性”现找到的最强方法之一,直接而又不失原意地彰显出异域文化以及文本中蕴含的所有意义(可见,一切“翻译即解释”的解读在此黯然失色)。
借助西方著名女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一段“阐释无异于庸人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的辛辣评语,译者更应明白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有进一步探索和丰富翻译手段的勇气,进而穿透文本,去寻找到那“直达作者精神世界及其全部生活过程的心灵沟通器”。
4.“前理解”与阐释的主体性
伽达默尔站在巨人肩上,超越施莱尔马赫原作者对其作品拥有最高解释权的观点,认为施莱尔马赫追求文本“唯一正确”的意愿仅是一个不可得以实现的愿望,用“前理解”与“历史偏见”之概念、阐释了译者在理解原作的过程中“无法超越历史时空和自我现实境遇”去客观地对原文加以理解的各种因素,这样译文的阐释将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个人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和历史偏见(前理解),进而导致文本内涵不再是作者或译者的个人所属,而是两者合法“对话”后的产物。换句话说,翻译的结果是作者与译者间动态对话的结果,并没有唯一的正确,而仅仅是“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对历史文本的理解过程”。
伽达默尔这一理论的好处在于终结了译者翻译中绝对“求真”的幻想,坏处则是理解阐释翻译观“文本本无正解”后具体实践中的某些无所适从。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谈到了阐释的模糊性,认为正是阐释学的模糊性才使得译者必须在困境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这一没有具体方法所指的选择、极有可能因译者个人偏见而割断原作与译文、原作与读者、历史与现在的各类文化元素,把一个只能是“作者的意图”变成了“译(阐释)者的意图”,从此让读者迷失了“透过文本表面找到本有所指”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过度阐释”,常能造就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神话。中国文化中的图腾“龙”、“凤凰”、“麒麟”、“貔貅”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是几千年过度“阐释”的结果。难怪有学者无不担心地指出:“‘过度诠释’导致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不能不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忧虑,历史可能被合理解释吗?如果有,这种合理解释的原则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①2002年3月14日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去世,享年102岁。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与文汇报“学林”版于3月18日联合举行了一次题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的学术座谈会,该引文源于本次座谈会的内容纪要。
对于上述忧虑,读者并没有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但伽达默尔却用一段耐人寻味的叙述解析了翻译与原作间的关系,“翻译者必须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入另一个谈话者所生活的语境中。这当然不是说,翻译者可以任意曲解讲话人所指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必须在新的语言世界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作用”。(伽达默尔,1986:496)用历史的眼光看,伽达默尔这一论述无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译者对作者、译文对原文的依附关系,让译者获得了与作者平等的阐释地位,表明翻译不再是文本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实现原文本意义的创新过程。过去隐身的译者终于现身前台,从而在文本的操作过程中引出了两个主体性——文本主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的纷呈局面。这一结果或许符合“文化学派”代表勒菲弗尔“翻译就是改写”(Translation is a rewriting)之惊世骇俗的论断,但译者对原文本内涵和外延的泛化改写又显而易见地会带来一个可预知的混乱——即阐释的多重性带来译(读)者多重理解的混乱。如果在这场没有主体权限和翻译标准为制约的译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译者具有主宰地位的主体性阐释极有可能淡化乃至扭曲原作的本意,阐释的结果岂不如同潘多拉打开的魔盒,让谬误漫天飞舞?译者前理解先入为主的个性张扬,很难不让人怀疑翻译学与翻译自身存在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正如佛教初传中国,原本并无宗派之分,后因佛典翻译路径不同,师承各有法脉,经论互异,便有了后来的八大宗派。虽说这一结果对弘扬佛学并无害处,于翻译实践,却让我们感到了一丝担忧。这种担忧再次让我们想到了翻译对于原文的可靠性。深圳大学王辉先生在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研究中表述的现象就属又一个实例:通过天朝大臣“一相情愿的修改乃至编造(译者主体性张扬下的‘前理解’)”,把一份严谨的、以英王之名、由“特定写作班子字斟句酌、精心制造出来的”,“以对等姿态表达友好交往意愿的国书”,变成了英方向中方“输诚纳贡的英吉利国表文”,并由此导致中国“错失了现代化的良机”的恶果(王辉,2009:27-32)。背离文本原意,百害而无一益的阐释,其根本问题乃是译者“前理解”与文本主体性的权限问题。
不可否认,阐释的方法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作者意图,但阐释自身的主体属性决定了它在文本中的出现之时,必然是原作文学性、语言风格、艺术手段被割裂和清除之时,这种割裂和清除的结果,对处于阐释者之后的读者而言,宛如游巴黎卢浮宫却鬼使神差地到了菜市,强权性地被剥夺了与原作者隔空击掌的心灵感应。我们必须看到,离开了翻译标准制约后的阐释,在前理解的作用下,其文本内容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阐释者(译者?)而非作者的主体认知体现,是阐释者在特定时代局限下对原作者心路历程的猜摸。其文本结果,有可能符合了阐释学的宏观理论,内容却必然与翻译本质分道扬镳。因此,翻译即(阐释)解释之论断,这类近似于让牧羊人辨不清狼与狗的理论认知,终归会给翻译带来危害。
5.结语
浸润于哲学思辨或跨学科的学者多以哲学的态度来谈论研究语言文化本身,其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自然更多的出于哲学范畴。以哲学范畴去研究谈论语言文化,乃至跨文化的翻译,尽管这一思维为语言、文化、翻译等等研究扩大了外延,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但事物的本质和属性却不会因不同的认知方法而改变!翻译理论研究者必须保持清醒,溯本清源,认真对待西方文论,辨别不同领域中理论指导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贯通脉络,不可在理论研究的迷宫里错失方向。哲学理念可适用于一切领域和范畴,但终归不能取代这些领域和范畴的本质属性。正如曹明伦先生(2007:109)所言:“把其他学科引入翻译研究并不是要把翻译变成其他学科,把翻译置于任何视域下审视翻译也依然是翻译,而把翻译视为(或作为)任何现象来研究都并不排除把翻译视为(或作为)翻译来研究。”
方法服务于主体,翻译毕竟不是“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众生随类各得解”的经学佛论。研究翻译,还是让翻译自身说话,话语权的约定有利于翻译健康发展,毕竟翻译学并不是阐释学“意义”下另建的一个影子世界。
[1]Makaryk,Irena R.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Z].Toronto:U of Toronto Press,1993.
[2]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FLEP,1988.
[3]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李砾.阐释/诠释[C]//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6]王亚丽.解释[C]//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37.
[7]王宁,刘辉.从语符翻译到跨文化图像翻译:傅雷翻译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8(4):28-33.
[8]王辉.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J].中国翻译,2009(1):27-32.
[9]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