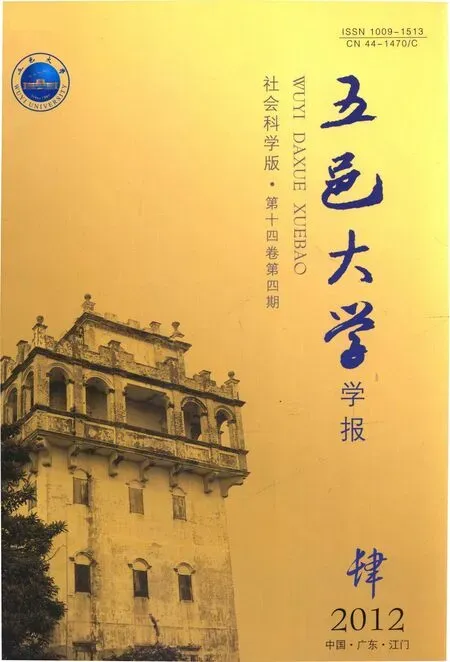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
姜海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经筵制度从汉代开始形成,经过中古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元代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主动认同并践行汉族文明。对于元代经筵制度的开设、沿革、内容及贡献,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作了梳理。可参见陈高华、张帆、刘晓所著 《元代文化史》一书,以及张帆《元代经筵述论》、王风雷 《元代的经筵》等论文。不过,以上研究多只是就经筵开设本末作了探讨,其实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对于当时帝王思想乃至执政理念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他们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其中经筵制度对于儒化元朝帝王,促使他们推行儒化、汉化政策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汉族儒士大夫也借助经筵制度 “得君行道”的机会,向皇帝宣扬经学、理学,通过他们不但强化了程朱之学官学化的地位,而且直接促使了元代中后期经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传播,尤其是儒家之道在现实中的运用与落实。本文试从经筵对当时经学、理学的影响,以及经筵制度的存在与设立对蒙元的儒化、汉化着手,来探究经筵与蒙元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经筵制度设立前蒙元的经筵侍讲及其影响
元代开设经筵制度始于元朝第六位皇帝泰定帝(1323—1328在位)。当然,在泰定帝之前,忽必烈、成宗、武宗、仁宗等皇帝已经诏命儒臣为其入侍讲读。甚至更前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也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向身边儒臣请教,经筵的雏形初备。如成吉思汗时期,儒士耶律楚材就时常陪伴大汗左右,以备咨询。据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 “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 (耶律楚材)发之。……国制:凡敌人拒命矢口一发,则杀无赦。汴京垂陷……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始然之。”[1]可以看出,从太祖成吉思汗开始,虽无经筵之设,但耶律楚材已或多或少担任了经筵官的角色,不过在名称上不叫做经筵。的确,后来成吉思汗采纳了很多耶律楚材的建议,尤其是很多儒家的戒杀、仁政等政治理念,这为蒙古汗国初期认同儒学、主动汉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后来窝阔台汗继续任用耶律楚材作顾问,让其扮演经筵官的重要角色。耶律楚材更是利用 “得君行道”的机会,向窝阔台宣扬儒家学说,实施儒家之道。比如, “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1]创立了新的朝议,使得蒙古君臣有了高低尊卑之分,从而提高了大汗的威望,耶律楚材由此得到了窝阔台的信任。正是由于耶律楚材极力宣扬并劝说皇帝践行儒家学说,使得窝阔台认同了 “马上”得天下但须文治整顿天下的道理。与此同时,在耶律楚材的推动下,蒙古政权在现实中注重民生事业,比如不杀汴京一民、减轻赋税等。另外,蒙古也非常重视儒士与儒学,使 “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还在燕京、平阳等地设置机构,整理儒家经典,等等。这些都促进了儒学在蒙古汗国的推广与应用,对后来蒙元诸帝推行汉化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
在蒙古汗国时期,经筵尽管没有正式开设,但蒙古大汗注重吸收身边大臣、儒士们的建议,以提升自己的执政水平。最为典型的当属忽必烈。忽必烈建立了大元,“用夏变夷”,此举标志着蒙元政权性质的转变。同时,他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将都城由漠北迁往大都,此举直接促使了忽必烈等蒙元贵族强化汉化政策,以便适应大一统帝国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需要。其实,忽必烈在未即帝位时期,便非常重视经学、儒学,他曾延请大量汉族儒士大夫为其讲读儒家经典与思想,史书记载说:“帝 (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这对于即位后的忽必烈接受儒学、推行汉法有重要意义,如元人郝经在其 《上宋主请区处书》一文中所言:
圣德集于主上,资赋仁明,乐闻善道,喜衣冠,躬礼逊乐,贤下士。自在潜邸,已符人望,于是致之先帝,而退守藩服。聘起儒生,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尝以为创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务也。[3]
可以看出,忽必烈在位30余年,积极有为,“聘起儒生,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即他在潜邸诸儒如刘秉忠、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人的宣扬和建议下,主动认同了儒家学说,并迁都大都,推行汉化政策。这些与类似经筵制度下诸儒的劝说、宣讲有直接的关系。《元史·商挺传》中便说:“(忽必烈)留意经学,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 《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2]而据元人王恽 《追谥先太子册文》记载,忽必烈之子真金更是 “尊师问道,日御经筵”[4],《元史·裕宗传》说他:“毎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2]。这些侍讲儒士不但向皇帝宣讲儒家经典与思想,而且还向其身边贵族宣扬儒学,如忽必烈侍讲之一的赵璧便是如此。元人虞集在其 《道园学古录·中书平章政事赵璧》中评价曰:“自公始以国语译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5]这些都说明,经学、儒学在忽必烈朝已经由经筵侍讲得到广泛宣传,受到了君臣的高度重视。
由于蒙元政权自忽必烈开始推行二元政治、文化体制,所以其儒化、汉化政策并没有彻底推行,不过为了维护中原地区的既得利益,笼络中原儒士大夫,此后诸帝如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继续类似经筵讲习的习惯,诸帝也都注重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学习。如成宗便时时召请儒士左右为其讲学,元人苏天爵记载云:“元贞、大德之初,天下号为无事。(成宗)退朝之暇,优游燕闲,召公读 《资治通鉴》、《大学衍义》。公开陈其言,缓而不迫。凡正心修身之要,用人出治之方,君臣善恶之迹、兴坏治忽之由,皆灿然可睹。帝从容咨询,朝夕无倦。……帝曰:‘侍讲读,非臣所能及也。’遂召焦公入侍顾问。秦州孝子以事亲闻,公荐于帝曰:‘忠孝无无二道,此其人材必可用。’帝命中书,锡五品官。其人果以能官称,公之论建,率此类也。”[6]他在侍讲焦养直的建议下,任用孝子为官,弘扬孝道、敦化社会风气。仁宗由于自幼生活在汉地,更是对儒家经典与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如元人欧阳玄在其 《书义》中所言:
陛下曩在东宫,仁孝之资,英毅之略,闻于天下也久矣。既而征四方书,以考古今。飞龙之初,大召宿儒询问要道。临御之后,不迩声色,不事游畋,凡耳目之娱,营缮之事,秋毫不经于心,惟经籍史传,日接于前。于是大兴儒科,黼黻至治。[7]
不仅如此,他还在现实中实行儒家之道,最重要的便是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是元仁宗更是蒙元政权儒化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蒙元贵族主动接受汉化的必然结果,彰显了经筵制度对儒化、汉化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
二、设立、完善经筵制度及其意义
泰定元年 (1324)正式开设经筵制度。《元史·泰定帝纪》对此记载云:
(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 《帝范》、 《资治通鉴》、 《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帖木儿领之。[2]
可以看出,经筵所讲的内容除了汉族史籍 《帝范》、《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之外,便是儒家经典 《尚书》以及宋代理学家真德秀的 《大学衍义》,由此说明经学、理学依旧是朝廷关注的重要内容。尽管 《四书》是当时元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但是文献记载讲习 《四书》的地方并不多,这就说明皇帝经筵讲习比较务实。到了泰定四年 (1327)七月,朝廷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 《元史·泰定帝纪》所载,“经筵讲读官,非有代不得去职”[2],经筵讲官从此有了固定的职位。这样一来,经筵讲席虽有人员流动,但在职位上却被制度化了,有助于经筵的稳定发展。当然,这次开设经筵制度,并不是说泰定帝较以往更重视经学、儒学,而主要是为了获得儒士大夫的认同、维护王权体制。所以当经筵一开,很多儒士大夫非常欣慰,如 《京华杂兴诗》云:
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方将耀稽古,宠遇光属联。[8]
由于经筵制度是古代儒士大夫 “得君行道”非常重要的途径,在儒士看来,泰定帝开设经筵制度是肯定与认同儒学的一个信号,所以他们期待藉此让蒙元政权实现更高程度的儒化和汉化,尤其是为中原儒士大夫提供更多的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可以说,泰定帝开设经筵制度之初,的确赢得了诸多儒士大夫对其为政的赞赏,但由于受到蒙元本位主义思想的干扰,汉族儒士大夫们并没有因为经筵的开设而在政治地位上有极大的提升,故经筵制度的开设,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此后文宗、顺宗等继续推行、完善经筵制度,经学、程朱理学也由此继续得到朝廷的关注和重视。如元文宗天历二年 (1329),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元史·官志》载,“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2],“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9]。院内设有专门的官吏负责,这实际上是专职的经筵机构。元文宗时期还敕命虞集等人,按儒家经典 《周礼》与 《会要》的体例编纂了长达800卷的 《经世大典》,以此强调蒙元政权与以往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后元顺帝将奎章阁改为宣文阁,选欧阳玄、黄溍、许有壬等儒臣讲解经学、理学。据元人汪克宽 《宣文阁赋》记载,朝廷 “制作宣文阁于大明殿之西北。皇上万机之暇,御阁阅经史,以左右儒臣为经筵官,日侍讲读”[10]。经筵制度的开设与实施,表明了元后期朝廷对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重视,程朱理学依旧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得以宣扬。
元代后期的诸帝,在经筵讲习的熏陶下,对经学、儒学颇为重视,并积极践行儒家之道,由此直接促使了以元代皇帝为核心的贵族阶层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加速了蒙元政权儒化汉化的进程。这一点正如张帆先生所言:
中国古代经筵的主要意义,原在于对皇帝进行儒家思想熏陶。对少数民族皇帝来说,经筵的意义尤为重大,等于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了解汉文化的课堂,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汉化和儒化。元代经筵的情况即是如此。①
由于蒙元也推行汉族君主独裁体制,所以君主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他在现实中对儒学的贯彻和推行的进展,也由此决定了蒙元政权儒化、汉化的水准。当然,“如从总体上纵向比较,则无论就汉化或儒化程度而言,元代皇帝与北魏、金、清诸朝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皇帝相比均显逊色”。①
三、经筵制度与蒙元儒化、汉化的强化
经过经筵熏陶的元代皇帝,大部分都积极推动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比如元文宗便是典型的一位。据 《元史》记载,他曾派遣官员到曲阜代替自己祭祀孔子,颁赐古代儒学先贤以封号,还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在元代历代皇帝中还是首次。同时,文宗还广泛表彰忠孝节义、孝子烈妇之事。他严禁色目人以及汉人践行蒙古人与非儒家的习俗,据 《元史·文宗纪》载,1330年朝廷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2],同时鼓励蒙古人、色目人接受实行汉人习俗。深受经筵熏陶的皇帝不断推行儒学、汉化,成为元代皇帝为政的重要特点,这正如元人欧阳玄在其 《曲阜重修宣圣庙碑》中所言:
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养之法始备。武宗皇帝煟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 《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皇妣为启圣王夫人,改衍圣公三品印章。[11]
元后期历代皇帝如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明宗等,无论是受到非正式还是正式的经筵侍讲的熏陶,不但 “尊孔崇儒”,更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由此直接促进了经学、理学持续性的发展和完善。当然,蒙元帝王重视经学、儒学,关系到中原精英阶层对蒙元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蒙元政权在中原政治统治与既得利益的巩固问题。即使是元末时期的顺帝亦是如此,尽管当时朝廷遭受着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冲击,但他们对于经学、理学依旧热情不减。整个元代,各地共建书院193所,其中在顺帝时期就建了60所,占总数的31%。[12]可以说,元朝书院几乎遍天下,正如清人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所言:“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13]这一时期儒学学校也一度达到建设高潮。值得关注的是,元代的书院、学校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金、宋时期,在范围上也延伸到了漠北、云南等边陲少数民族地区。顺帝甚至派十道奉使巡行天下,“采访贤俊”,以为朝廷搜罗隐逸人才。蒙元统治者这些推重理学的举措,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程朱经学、理学以及继续笼络汉族儒士大夫来挽救政治危机。所以说,经筵制度促使了蒙元统治者对经学、儒学的重视。汉化继续推进,理学也迅速传播,这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有重要的意义。
经筵制度不仅对当时元朝宗室有直接影响,也促使当时的经筵讲官及朝中大臣对经学、儒学的关注,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积极推动经学、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如经筵未开时期的耶律楚材、许衡等人便是如此。元中期经筵开设之后,当时为元帝讲解儒家经典要义的王结、赵简、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还有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等人亦是如此。他们作为当时的经筵讲官,除了为元帝讲解儒经要义之外,还借助自己的力量积极宣扬、发展和推行儒家学说,使得蒙元政权的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注释:
①参见张帆 《元代经筵述论》一文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 《元史论丛》第五辑第136-150页)。
[1]苏天爵.元文类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濂,等.元史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郝经.陵川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王恽.秋涧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虞集.道园学古录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苏天爵.滋溪文稿 [M].文渊阁四库书本.
[7]欧阳玄.圭斋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胡助.纯白斋类稿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杨瑀.山居新话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汪克宽.环谷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欧阳玄.圭斋文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赵连稳,朱耀廷.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43.
[1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