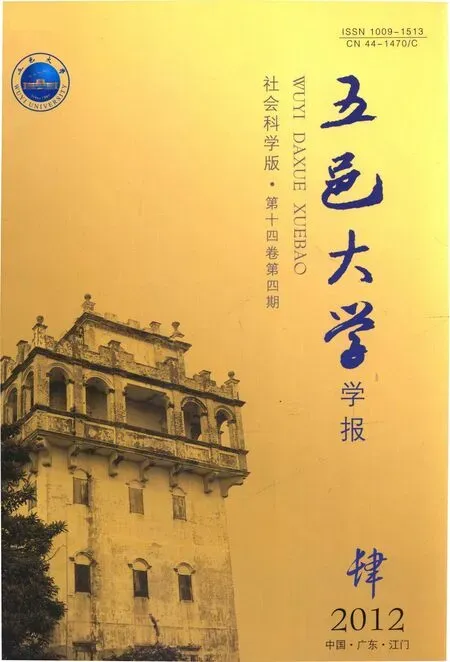刘宗周论陈白沙 “似禅非禅”说辨析
刘红卫
(五邑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广东 江门 529020)
刘宗周对白沙心学 “似禅非禅”的定位,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刘宗周的定位并不准确,但由于 《明儒学案》的特殊地位,这种影响又是决定性的。学者多从白沙心学中寻找论据以验证或批判刘宗周的观点,却往往忽略了刘宗周儒学体系的结构特点对其评价白沙心学的影响。牟宗三极力推崇刘宗周的儒学体系,但又称其不 “透澈”,在体、用关系上不够畅达。而在心体割裂的视阈下考辨白沙心学,是刘宗周得出 “似禅非禅”结论的根本原因。“勿忘勿助”是陈白沙哲学理论的基本体证工夫,他在 “勿忘”工夫的基础上确立了 “先立其大”(《孟子·告子》)的儒学门户,“勿助”工夫则使陈白沙将 “体”与 “用”相贯通,实现了 “本体自然”的哲学构架。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本体自然、承体起用是陈白沙自然主义的核心内涵。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将孔颜之乐与自然相结合,在 “道物无对”、“物各付物”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对儒家文化和人生价值观的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刘宗周将 “体”、“用”割裂,无法体验到本体自然、承体起用的奥妙,故而将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指为“似禅非禅”。陈白沙的体证工夫是 “勿忘”,禅学的体悟工夫是 “坐忘”;陈白沙的 “勿忘”工夫指向仁、善、理,是实有、实存,禅学的 “坐忘”工夫则指向虚空;陈白沙的 “勿助”工夫是祛除私欲,禅学的禅定工夫则是一种私意安排。因此,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禅学泾渭分明。
儒、佛、道三家的关系一直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以佛、道文化为辅,三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儒家文化笃守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 “立功”的人生理想,仕途受挫或人生失意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下,一部分人转向佛、道以寻求解脱,这就是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以佛、道文化为辅的含义。虽然一部分人在仕途受挫或人生失意的境遇下转向佛、道寻求解脱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但就此论断佛、道文化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而存在却有待商榷。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的文化系统,具有自身的调节功能,孔颜之乐与儒家 “立功”的人生理想相异度的人生价值观,成功地实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转向,这一点往往被学者所忽略。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与自然相结合,形成了自然主义哲学。刘宗周论陈白沙 “似禅非禅”,是站在佛、道文化对儒家文化补充作用的角度来看待陈白沙的自然主义,这种不甚精准的论断恰恰从侧面彰显了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对儒家文化价值转向的意义。
一、陈白沙 “本体自然”体、用观的形成
陈白沙治学与哲学境界大致分为两阶段: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之前是一阶段,主要以 “勿忘”的体证工夫为主,是在传统理学路径下探索儒家的心性之学;实现了心与理的凑泊之后是第二阶段,以“勿助”的体证工夫为主,陈白沙实现了 “体”与“用”的贯通、承体起用,由本体发用至自然,形成了自然主义哲学体系。陈白沙27岁师从吴与弼,开始接触到儒家心性之学及儒学的传承体系。吴与弼开启了陈白沙 “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陈白沙的 “立心”说建立在 “先立其大”的基础上,“先立其大”是儒学入学的门户。儒学的德性修为基本上有两条路径,一是由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所呈露的仁扩充至至仁,二是由恻隐之心所呈露的善扩充至至善。体证就是由日常生活中呈露的仁、善切实体验到仁、善的实存,并由此确立仁、善对人性的先入为主的理念,此即 “先立其大”。确立 “先立其大”的理念之后,就要用 “勿忘”的工夫执着于善,即 “择善而固执之”(《中庸》),在工夫纯熟之后,达到德盛仁熟的境界。陈白沙称师从吴与弼而 “未之有得”[1]883,未能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但实际上陈白沙已经确立了 “先立其大”的理念,陈白沙甚至因为 “勿忘”的工夫过度而引发了 “心疾”。只不过在此阶段,由于心与理尚未凑泊,陈白沙的儒学在 “体”与 “用”上是割裂的。
心与理的关系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它必然延伸至心体与性体的关系。陈白沙师从吴与弼,实际上走的是朱熹的路子。朱熹认为格物穷理,工夫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 “豁然贯通”[2],但是陈白沙始终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贯通。从陈白沙心学成熟之后的发展脉络来看,他无法实现心与理凑泊的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的先验性;二是朱熹对心、性、理的分述,从心性的角度讲,就是支离。朱熹所表述的理具有先验的性质,朱熹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3]P114在朱熹的理学系统中,理的先验性是无须理证和践证的,带有明显的他律性质,而陈白沙的心学则是纯粹的德性自律。同样,朱熹认为理与性、心的贯通也是无须理证和践证的,在天是理,在人则是性。或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朱熹曰:“不须去贯通,本来贯通。”[3]P219理与性、心贯通的逻辑无须践证,同样是他律。陈白沙要树立一个纯粹自律的心体,理、性、心的逻辑关系必须得到践证方才是自足和圆满。陈白沙笃守孔子的 “一贯之道”,他对心、性、理支离的分述颇有看法。牟宗三认为朱熹理学体系中的性体是一个静止的、没有创发功用的本体,心则被剥落成为了气质性的心。这样以来,有思维能力的心与静止而没有创发能力的性体被割裂开来,如此,由本体到发用、承体起用就无法实现。虽然朱熹用心统性情来拢合理学系统,但仍存有践证上的瑕疵,也正是由于此原因,心学的产生才成为必要。陈白沙与牟宗三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陈白沙在与学生及友人的通信中多次提到 “简易之学”,就是针对支离而言。
何以践证理的先验性及由理贯通至性、心的逻辑性以树立纯粹的德性自律?何以破解朱熹理学的支离分述而承体起用?这是陈白沙心学体系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勿助”工夫对陈白沙走出理学的迷局起了关键作用。“勿助”有三层含义:一是儒家治学之道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成是私欲,与儒学义理相背;二是对仁、善的体证是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建立在充分的人性之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无需任何外力的助长;三是承体起用,由本体至发用,也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的过程,无需外力助长。吴与弼开启了陈白沙“勿忘勿助”的工夫,但陈白沙在实现心与理的凑泊之前实际上没有真正领会 “勿助”的含义。在江门的山水间放松身心时,大自然的生化流行之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突然领悟了 “勿忘”工夫及孔子 “一贯之道”的含义。其弟子张诩云:
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其为道也,主静而见大,盖濂洛之学也。由斯致力,迟迟至于二十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真,本自圆成,不假人力。其为道也,无动静内外,大小精粗,盖孔子之学也。濂洛之学非与孔子异也。[1]883
“本自原成,不假人力”即天道化生万物,一切顺其自然,陈白沙称之为 “天道至无心”[1]57。人与自然 “一本”,自然如此,人亦如此。陈白沙曰:“夫心也者天地之心,道也者天地之理。”[1]942由生生不息的天道本体至化生万物之用,一切随其自然,湛若水将陈白沙心学的 “体”、 “用”关系表述为“天普万物而无心”[1]706,就是这个意思。建立在德性贞定基础上的心体,其发用自然是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流露,不假任何人力,此即孔子 “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境界。至此,陈白沙的心学才算真正建立。“心也者天地之心”实现了心与理、心与天的凑泊,不带有任何先验、他律的色彩。心体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具有创发功能的本体,其发用是仁、义、礼、智的自然流露,朱熹理学系统中的先验、他律、支离在此一并解决。“本体自然”是对白沙心学及其体、用关系的精湛概括。
二、体、用关系是陈、刘哲学思想分歧的基点
在刘宗周的人性论体系中,“意”是本体。刘宗周曰:“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善恶恶之意;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善无恶之体,此之谓太极而无极。”[4]901太极、无极是宋、明时期儒家学者讨论宇宙、人生本原的概念, “意”的本质是知善知恶,“意”作为 “无善无恶之体”是人性的本体,是人的德性基础。从刘宗周对 “意”的表述来看,“意”相对于人的认知是一种先在的理念, “意本如是,非诚之而后如是。”[4]911人能好善而恶恶,并非后天学习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生来就具有好善而恶恶的本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的本质是善的。刘宗周又曰:“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长,而恶自不起。”[4]916人对善与恶的认知能力是先在的,好善而恶恶作为人的本性,儒家的德性教化才成为可能。
意是 “无善无恶之体”,这个 “体”究竟是生生不息、具有生发能力的本体,还是一种静止的、没有生发能力的本体?这一点对于梳理刘宗周儒学思想体系的体、用关系非常重要。刘宗周认为心的作用就是思考,心是具有生发能力的气质性的心器官。如果 “意”是具有生发能力的本体,而心与意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就说明人同时有两个具有生发能力的 “体”存在,这是不可思议的,而心的生发能力是无可质疑的,这就说明刘宗周儒学体系中的 “意”是一种静止的、没有生发功用的本体。那么刘宗周儒学体系体、用的关系就是割裂的,承体起用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表述,这是刘宗周将陈白沙的本体自然视为 “似禅非禅”的根源。或问:“意与心分本体流行否?”刘宗周曰:“来教似疑心为体,意为流行。愚则以为意是心之体,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为体,心为用耳。”[4]937“意是心之体”的 “体”是 “知善知恶”、“好善恶恶”之体,是静止的、没有生发作用的本体。在刘宗周的儒学体系中,心是气质性的心,“意”之发用流行为仁、义、礼、智的周流贯彻,在逻辑上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刘宗周曰:“圣人心同太虚,一疵不存,了无端倪可窥,即就其存主处,亦化而不有,大抵归之神明不测而已。”[4]906圣人 “一疵不存”,为人处事是 “自诚而明”,故能做到仁、义、礼、智周流贯彻。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由于 “意”是静止的、没有生发作用的本体,心又是气质性的心,在体、用割裂的情境下,承体起用就成了逻辑假设,在践证上是无法实现的。既然在践证上无法实现,陈白沙的 “本体自然”自然就成了 “逃禅”。刘宗周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将天的主宰、流行与 “意”的主宰、流行类比,他曰: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谓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谓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为八节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没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处。[4]911
天是生生不息、发育万物的本体,故 “即主宰,即流行”,“意”不具有生发作用,用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来形容是不恰当的。刘宗周人为地将心体割裂为心与意,造成了其儒学体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刘宗周承认 “意”没有 “存发”的功用,这一点印证了他的儒学体系中的承体起用是一种逻辑假设,但刘宗周也没有将 “存发”的功用归于气质性的心,他曰:“人心之体,存发一机也。心无存发,意无存发。盖此心中一点虚灵不昧之主宰,常常存,常常发。”[4]937“此心中一点虚灵不昧”不属于心,也不属意,当归于何处?这就是割裂心体的必然结果。
在陈白沙的心学体系中,心体是一个生生不息、具有创发功用的本体,心体的自然流露就是仁、义、礼、智的周流贯彻,这就是 “本体自然”的含义。刘宗周将心体割裂为心与意,因而无法体验到心体承体起用的奥妙,又不能充分认识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对儒家文化价值观转向的意义,故而将陈白沙自然主义所表征的愉悦、自由归于禅学,得出了陈白沙 “似禅非禅”的错误论断。
三、从工夫论角度辨析 “似禅非禅”说
刘宗周关于陈白沙 “似禅非禅”的论断,与他对心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刘宗周的儒学体系中,“意”是 “知善知恶”、“好善恶恶”之体,心则被剥落为气质性的心。刘宗周曰: “大学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已,此四者,心之体也。其言意也,则曰好好色,恶恶臭。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故意蕴于心,非心之所发也。”[4]896“好善恶恶”是从本体方面论意,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是从气质方面论心,是心气的发用。念是气质性的心最明显的表征,是心之“余气”,是恶产生的根源。刘宗周曰:
今心为念,盖心之余气也。余气也者,动气也,动而远乎天,故念起念灭,为厥心病,还为意病,为知病,为物病。故念有善恶,而即物与之为善恶,物本无善恶也。念有昏明,而知即与之为昏明,知本无昏明也。念有真妄,而意即与之为真妄,意本无真妄也。念有起灭,而心即与之为起灭,心本无起灭也。[4]904
意是人生而具有的 “好善恶恶”的本性,对于人的认知而言是先在的;念则是人感于物之后而产生的主观意见,有合乎人情事理的,也有违背人情事理的,即 “起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4]901。 “有善有恶者心之动”[4]896,就是指心起念而言。
在刘宗周的儒学体系中,意对气质性的心有贞定作用。刘宗周曰:“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于是两物。”[4]936有了 “意”的定盘针作用,德性修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如果离开了 “意”的贞定作用,任凭气质性的心自行发展,那么正常的生理欲望及人生追求将转变成私欲、贪欲。刘宗周曰:
人心一气而已矣,而枢纽至微,才入粗一二,则枢纽之地霍然散矣。散则浮,有浮气,因以有浮质;有浮质,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为此四浮,合成妄根,为此一妄,种成万恶。[4]908
同样,离开了 “意”的贞定作用,德性修养工夫就变成了作弄精魂。正是顺着该思路,刘宗周认定陈白沙的心学之 “心”是气质性的心,需要定盘针 “意”来贞定。刘宗周评价陈白沙曰:“今考先生证学诸语,大都说一段自然工夫,高妙处不容凑泊,终是精魂作弄处。”[5]刘宗周之所以得出白沙心学作弄精魂的结论,问题在于刘宗周人为地将心体割裂为心与意两部分,这样在工夫的体证上出现了分歧。陈白沙哲学体系中的心体是生生不息、具有创发功能的本体,对本体的认识通过将父慈、子孝的亲情扩充至至仁及将恻隐之心呈露的善端扩充至至善的逆觉体证的路径,确立 “先立其大”的儒学门户,经过德性修为而至德盛仁熟,然后以贞定德性。逆觉体证是 “自明诚”,贞定德性是 “自诚明”,这是孟子 “集义”的工夫路径。刘宗周的体认路径则完全不同,意作为人性的本体是静止的、没有创发功能的,作为 “知善知恶”、“好善恶恶”之体对于人的认知而言又是先在的,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气质性的心如何去体认作为 “好善恶恶”之体的意?意带有明显的先验性,是认知性的,而非践证性的。学者不必问意何以是 “知善知恶”、“好善恶恶”的,接受这种理念就足够了。很明显,刘宗周的体认路径是对意的概念性袭取,这是孟子所谓的 “义袭”的工夫路径。刘宗周 “义袭”的工夫路径,将心与意人为地割裂,从而在践证上无法实现心与意的凑泊,这是刘宗周儒学体系最大的瑕疵。陈白沙在践证心与理的凑泊时,曾经因用功过度得了心疾,陈白沙面临的问题实质上与刘宗周儒学体系中践证心与意的问题本质相同。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旨在阐释人的愉悦、自由与幸福,本体而自然,承体起用,无须任何的用力与助长。刘宗周 “义袭”的体认路径无法感受到 “本体自然”的奥妙,气质性的心无法达到愉悦、自由与幸福的境界,故而刘宗周得出了陈白沙的自然主义“似禅而非禅”的论断。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陈白沙的心体是一个生生不息、具有创发功能的实存,而非虚空。从工夫论意义上讲,陈白沙的前期体证工夫是 “勿忘”,禅定的工夫是 “坐忘”,两者截然相反;陈白沙后期的体证工夫是 “勿助”,是儒家治学及德性修为过程中祛除私念、私欲而顺承本体自然,佛教试图摆脱人情世故的情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情欲,两者亦截然相反。因此,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禅学是泾渭分明的。
[1]陈献章.陈献章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朱熹.四书集注 [M].长沙:岳麓书社,1993:11.
[3]朱熹.朱子全书:第14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 [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