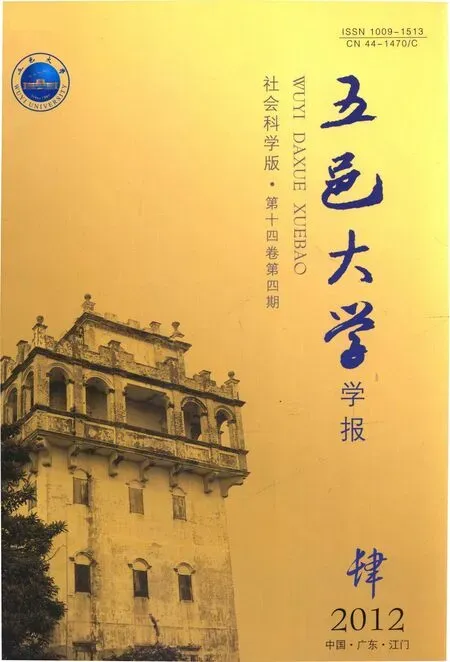张振勋与晚清政府的早期交往
魏明枢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张振勋 (1841-1916),又名弼士,青少年时期曾用名肇燮,广东省大埔县人,晚清著名的南洋华侨富商和侨领,曾任清政府首任槟榔屿副领事、署新加坡总领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仆寺卿,晚清华侨中获得中国政府最高官衔者,深受晚清及北洋政府的重视。他也是中国早期铁路经营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山东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创办人,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有着突出的影响和地位。
论者说:“自1893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槟榔屿的副领事以来,他一直与清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光绪十九年 (1893年)张振勋被清廷委任为驻槟榔屿副领事之后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文章作过探讨。李松庵曾以专节介绍了 “张弼士与清廷和北洋的关系”[3]163-168。M.R.戈德礼 《来自南洋的官僚资本家》第4章也讨论了1893年之后张氏与中国的关系[4]。本文拟对1893年之前张振勋与晚清政府的交往情况进行初步探讨,以揭示他进入晚清政府的轨迹。
一、张振勋与晚清政府官员的早期交往
李松庵认为: “张弼士发迹之后,热中功名,曾以巨资捐得 ‘三品京堂’。晚清的谴责小说家黄小配所著 《二十年繁华梦》中曾揭发了这件事。”[3]171但是,张振勋官至太仆寺卿,按清朝制度,京官最高只能捐到郎中,捐钱不可能得到太仆寺卿。因此,他与晚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官职的提升不能简单以 “巨资捐得”来概括。
张振勋确实很早就 “热中功名”,很早就以捐纳取得了候补知府、道台等官衔。按照颜清湟 《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 (1877-1912)》一书的研究,张振勋所捐的第一个官应当在1893年。张晓威则认为:“若从目前座落于槟榔屿的 ‘张弼士故居’所藏的一份 (‘乐善好施’)匾额观之,至少在光绪7年12月 (1882年1月)时,张弼士就已经捐得知府衔了。”[5]张振勋捐得清政府的官职,真正地拉开了他与晚清政府关系的大幕。
从现有资料来看,张振勋在国内的经济投资开始于光绪六年 (1880年)。光绪五年 (1879年),轮船招商局派遣广东试用道张鸿禄、候补知县温宗彦赴南洋、新加坡一带考察航运,同时也向华侨招集股金。第二年,他们来到了新加坡,并得到了张振勋与其他38名侨商的积极响应——共投资65 200两,其中,张振勋个人就投资了3 600两。[6]正如论者指出:他们的投资有助于轮船招商局应付怡和、太古等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压价竞销的排挤,并度过经营难关。[7]1879-1880年的轮船招商局是由盛宣怀所经办的 “有关富强大局的”两个经济实体之一(另一个是湖北开采煤铁总局)。[8]92作为轮船招商局在南洋的重要的华侨投资者,张振勋应当受到盛宣怀及有关官员的注意。
张振勋积极响应清政府在海外的募捐活动,与晚清政府的交往也因此逐渐密切。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因为筹赈江皖赈务,两江总督曾国荃特奏颁赠匾额十五面给南洋各埠、各帮与各该人,其中,槟榔屿张肇燮是 “义昭推解”[9]。光绪十七年 (1891年),李鸿章为直隶水灾赈捐有功的张振勋等人奏奖。[10]
上列有关张振勋与清政府的交往或许是零碎的,他与盛宣怀的交往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可以说,张振勋后来的飞黄腾达源于盛宣怀的提携。盛宣怀 (1844-1916),江苏省武进人,字杏荪、幼勖,号次沂、补楼、愚斋,晚清著名企业家、政治家和慈善家。他长袖善舞,“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11]张振勋与盛宣怀在商务方面有着特殊的关系[12],他们之间的合作 (特别是在晚清铁路建设方面[1])也是非常特殊的并且影响巨大。
并无确切史料说明张振勋与盛宣怀的第一次见面始于何时。据夏东元研究,光绪十五年 (1889年),张振勋主动向盛宣怀报告:“南洋各埠以荷、日 (即西班牙)等为首的殖民主义者,虐待他们属下的中侨胞民,请求速设领事以事保护。”[8]324又说:“值得一提的是,张振勋其名,在本谱中初次出现,他与盛宣怀算是新交。”[8]326则张与盛的直接交往应开始于这一年。但是,夏东元所据以立论的是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在此禀内,盛宣怀向李鸿章分析了在南洋荷属殖民地设领的可能性,并且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奏明……荷、日两国所属应专设领事者约四处。”[8]324-326因此,张振勋到烟台向盛面禀的时间不可能发生在光绪十六年 (1890年)之前。
查盛宣怀与李鸿章之间的往来电文,张振勋向盛宣怀反映荷属华侨受苛虐而请求速设领事之事,应当发生在光绪十七年 (1891年)。六月二十日 (公历7月25日),李在给盛的电文中说:“张既拟七月初四五回烟。”[13]376-377七月十六日 (8月21日),盛在给李的电文中则说: “张振勋已回 (南洋)”[13]386,可见,张、盛在烟台面谈应在当年的六、七月之交。
张振勋与盛宣怀在回忆中都提到过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们在烟台的面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五月间[14],张振勋回忆说:“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勋旋香港,今督办铁路大臣、前东海关道盛电邀至烟,商办矿务、铁路等事宜。”[15]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望日 (1906年8月4日)[16]35,他又说:“迨光绪十七年辛卯,振勋回粤,今督办汉阳铁厂、前东海关道盛电邀在烟台商办矿务、铁路等事宜。”[16]34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盛宣怀在致北洋大臣王文韶函中也说:“在东海关任内,查得烟台、天津、营口等处所产葡萄,可照西法酿酒,曾与广南槟榔屿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张振勋筹商创造,并于上年 (1894)延请酒师到烟台试造,尽合外洋畅销。”[17]
张振勋回忆张裕葡萄酒厂的最初萌芽时间时明确指出是在 “光绪十七年辛卯”,盛宣怀的回忆则是 “在东海关任内”,两者是相符合的,但张振勋在这一年具体到过烟台几次,他们在烟台究竟有过几次面谈,却由于史料缺乏而难得其详。这次面谈,盛与张两人此时可能仍然是 “新交”,却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正如论者所言:“1891年当张弼士通过香港时,接到了盛 (宣怀)的邀请,请他北上芝罘 (烟台)以讨论铁路经营和其他问题。尽管不知其细节,但此前这位清朝的现代化者与华侨资本家已经有了一大批合作。”[4]16
盛张两人在这一年面谈的主题是有关 “商办矿务、铁路等事宜”,这个主题却由于形势的发展及清政府铁路政策的变化而未能产生成效,直到甲午战争后芦汉铁路的筹建工作重新开始时,为了应付清政府的铁路 “商办”政策,盛宣怀才又重新找到张,并导致张振勋从此介入中国的铁路等经济建设中,成为侨商介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先驱。[18]他们之间面谈的副产品也相当丰厚:他们共同筹商并达成了创办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共识。从此,张振勋执著于在山东烟台种植葡萄以酿造中国的葡萄酒,终于创立了张裕公司,成为南洋侨商与中国官员合作最著名的成果。[19]
关于张与盛在烟台的这次面谈,张振勋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张榕轩说:“近新嘉坡领事张观察言:前在葛罗巴与法国总领事坐谈,出葡萄酒,饮之极甘。据云:若得中国烟台等所产葡萄酿之更佳。因默识于心,不能忘。今年,督办铁路大臣电邀至烟,坐中谈及此事,盛公谓曾试过,惜无酿师可靠,不果办。”[20]后来李松庵说: “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弼士为清朝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电邀到烟台会商兴办铁路、开发矿山的事,谈论间谈到了烟台的葡萄。”[21]“到了光绪十七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从香港抵达烟台,即与盛宣怀商量,着手筹办起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来。”[3]169
张振勋与盛宣怀在光绪十七年 (1891年)的面谈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华侨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华侨逐渐受到清政府重视的大背景下,以张振勋为代表的侨资即将在中国发生重大的影响。张振勋不但较早而且较多地向国内投资,在国内的赈捐等慈善事业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也因此与国内的高官较早地取得了联系,受到了晚清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等人的重视,这对他此后在晚清政府内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张振勋的设领请求及盛宣怀、李鸿章与荷兰的设领交涉
光绪十七年 (1891年),张振勋以 “办理荷兰国山东赈捐委员、候选知府”的身份到烟台时,盛宣怀正任职于东海关道 (光绪 “十二年,授山东登莱青道”),且 “系专管赈捐,为救穷民起见”而在荷属发动赈捐 (1887年夏和1890年春夏之交,山东两遭黄河严重水患而引起赈捐),两人之间对“赈捐”问题必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在面谈的过程中,张振勋向盛宣怀反映:“荷兰凌虐华民,应设领保护。”[8]325
盛宣怀随即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了简略而概括的禀报。据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8]324-325张振勋当是有备而来的,且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他希望通过盛宣怀向清政府反映南洋荷属华侨受殖民地政府虐待的情况,请求在南洋荷属殖民地尽快设立领事,以保护侨胞权益。其具体内容后来在不同的地方皆有所记载。
郑观应曾将 《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录寄给香港 《实报》总编辑潘兰史刊登,以 “普告同胞”。[22]583-593郑在给张振勋的信中又说:“承示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详述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惟华侨人数及弟前游各埠所查人数,与昨日 《申报》登南洋舵工所述诸埠人数不同,尚祈查考报告,请政府通饬该处公使、领事保护。”[22]642因此判断,郑所录寄内容应来自张振勋。
比较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和 《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的内容,则前者就是对后者内容的概述。比如:前者说:“荷国近来新例日苛,皆为华民而设,所定货物之税、人头之税,产业之税,皆倍于各国,其虐待有事之华民、无事之华民及身故之华民,皆异于待各国。”[8]324后者则将这些 “新例”加以详细的阐释。前者中的许多文字正是对后者的摘抄,如言荷兰已在中国设领事及其必要性的情况等。显然,《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与当年张振勋给盛宣怀的材料内容是一样的。
另外,《葛罗巴华商禀政府荷兰南洋各属土苛待华侨各款》与 《清季外交史料》卷166所载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1902年10月27日)《南洋华商呈商约大臣沥陈被虐情形请设立领事禀》[23]内容亦完全相同,只是前者比后者多了两款,即 “一、领事之设原为保护商民起见……”和“一、荷人侮蔑华人积习成性,开办之初定多掣肘……”[22]591-593。而这最后两款内容在 《盛宣怀上李鸿章禀》中显系重点,其文字亦多相同。有理由认为,这两份文件最初乃出于同一人之手。
张振勋给盛宣怀的材料与交给郑观应的材料,以及荷属殖民地华侨交给盛宣怀等商约大臣的材料,内容是一致的。这个材料不仅是张振勋个人的意见,更是荷属殖民地华侨的集体意见,且由集体所书,侨胞们乘张振勋北上之机,让他将此意见反映给清政府,他成了南洋荷属华侨的代表。
张振勋的材料中详细列举了荷属殖民政府刻意“苛虐”华侨的情况,他们认为,荷属政府的排华政策是由于华侨得不到祖国的保护所致,“各国居民安堵如故,此皆由各国均有领事以为保护,中国独无领事,直听其凌虐而无一人过问”。而当地管理华侨事务的 “玛腰甲必丹、雷珍兰等官,名为保护,实则为荷人之牙爪”。因此,侨胞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南洋荷属设领,以保护侨胞的权益,并论证了设立领事的条件及其可能性。[8]324-325
盛宣怀对于张振勋所反映的情况极为重视,并向李鸿章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说:“职道访闻张振勋在该国经商多年,极有体面,揆之闻俗问禁之义,彼于荷国政治人情揣摩熟习,必胜于暂时派往查探之人。既已远道来烟,自应饬令赴津禀谒宪台,以备顾问。但据声称:所请若不能行,恳勿宣露,以免荷人执以相仇,于公事无益,于彼有损。伏乞宪台俯鉴其微忱,曲赐保全,尤为公便。”[8]325盛宣怀曾想向李鸿章推荐张,但张当时担心一旦问题曝光而得不到真正解决会于已不利,因而并未与李鸿章见面。
李鸿章也将张振勋当作南洋荷属侨胞的重要代表。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1891年7月25日),李鸿章致盛宣怀电中说:“费使 (即荷兰驻中国的公使费果蓀,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廿年长期担任荷兰驻华公使——引者)[24]函到。本准欲令张振勋随同接晤,嘱其转致葛罗巴照护。张既拟七月初四五回烟,汝可邀令晤费。至前禀两层,总署不愿设领事糜费,尚无虑荷官阻挠;捐官职者由总署照会荷兰优待,恐署厌烦。汝晤费略与商及,我召费亦姑言之,行否固末可知,费极滑,无担当。”[13]376-377可见,李鸿章已就张振勋所反映的问题向荷兰驻华官员提出了交涉,但由于总理衙门对于设领问题态度消极,李并未坚持设领主张,仅强调要荷兰政府“优待”“捐官职”的华侨。
此后,盛宣怀与荷兰驻华官员就南洋荷兰殖民政府 “优待”华侨问题进行了大量交涉。六月二十四日 (7月29日),盛宣怀向李汇报了交涉的有关情况:“顷晤费使,专言华商在葛罗巴、日里等处捐赈。”对于设领问题,则说: “领事,总署既不愿,便不说白话。钧想然否?”[13]378同日,李复电,肯定了盛的主张。[13]378-379由此可见,盛宣怀与李鸿章所要给予保护和 “优待”者只是那些因为 “捐赈”而取得中国 “官衔”的华侨,即所谓的 “体面商人”。
荷兰人却一再推诿,一直强调作为荷兰外交官,他们只能向荷兰的驻葛罗巴总督 “函商”,建议他 “照各国体面商人之例”,对荷属华侨富商“一律优加看待”,但又说: “不知葛督如何办理,国家意思如何。”盛宣怀对此显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而只是让张振勋携 “费使”建议葛罗巴总督优待侨商的信回南洋,并 “嘱其先办数名,以试其如何优待。”[13]386盛宣怀与荷兰人的交涉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荷兰人之所以推诿和否定中方 “优待”体面华商的要求,根本上在于他们对华侨的亲华势力的恐惧。管理华侨事务的 “甲必丹玛腰”由荷兰人任命,当然会服从荷兰殖民政府。但他们担心:一旦“优待”张振勋这些 “体面商人”,必将在南洋培植一批亲华的侨领,从而损害荷兰人对华侨的管理。事实上,华侨在其设领的请求中也提出要 “就本地商人之有体面者派充之”,[22]591可见,有关 “体面商人”待遇问题的交涉实质上已经暗含着设领以保护华侨的意义。
在荷属南洋设立领事后来一直是晚清政府对荷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国在光绪六年 (1882年)首次向荷兰外交部提出设领问题[25],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在华侨的国籍问题上作出让步后,才得到荷兰在荷属印尼各地设领的允许。期间,荷属华侨不断请求清政府就荷印殖民政府苛虐华侨问题与荷交涉、并设领事以保护,清政府中的有关涉外官员也深知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因而不断与荷兰进行设领的交涉。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十二月,吕海寰在其奏折中亦回忆说: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吕作为出使德、荷大臣途经新加坡时,署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 “过船谒见”,吕 “以该道 (即张振勋)熟悉南洋各岛情形,即询以侨寓和属噶罗巴等处之华民,和人相待如何?据称:‘和国国家尚无恶意,惟噶罗巴等处之地方官,擅立苛政,待我侨寓之华民,奴隶不若,不与各国人一律看待,华民之受陵虐,皆因中国未设领事之故’等语。”[26]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1890年11月21日),驻英公使薛福成在 《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中讨论了在南洋各地增设领事的问题,建议在荷属苏门答腊之日里埠、噶罗巴、三宝陇三处设领。[27]
张振勋通过盛宣怀向掌握清政府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反映侨情并请求设领的行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最后无奈地演变为 “优待” “体面商人”的交涉,并且毫无所得,但他已经将侨胞们的集体意见传回国内,甚至因此与荷兰作了一定的交涉,这也是在漫长的荷属南洋设领交涉中重要的一次,足以让他本人在华侨中树立崇高的威信,也让他从此受到中国政府高官们的赏识和信任,他打开了通向中国政府的权力之门。
三、结语:与晚清政府早期交往对张振勋的影响
张振勋以其在南洋所创造的财产在侨居地为侨胞们做了大量实事,从而树立了侨领的权威;他又以其财产在国内做了大量的慈善事业,结交清政府高官,进而与晚清政府较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这种努力产生了极佳的效果。
首先,他跟对了人。盛宣怀是晚清政府中的经济实力派,李鸿章则是晚清政府中的政治权力掌握者。两人作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掌舵人,对于晚清社会以及晚清政府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通过他们,加上善于用钱开路,张振勋受到了张之洞、王文韶以及戴鸿慈等清政府高官的欣赏,最终通到了 “天上”——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甚至成了 “东南亚华侨在清廷担任高职的第一人”[28]。
其次,他找对了路。张振勋从一个广东大埔山区的放牛娃发展为南洋地区的千万富翁,这是一个经济巨人的崛起过程;从千万富翁发展为以实业救国的政府高官,这是富而思进,是民族认同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自我升华过程——他已经将自我奋斗融入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之中。
俗话说:良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张振勋与晚清政府的早期交往,极大地决定着他后来的人生轨迹,是他开始担任晚清政府实职 (即槟榔屿首任副领事)的重要条件。有论者认为,张振勋与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的 “客籍老乡”关系,是他能够担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的根本原因。然而,正如论者所说:“若能从张弼士本身的成就与特点,以及他和清朝政府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著手,应该更能清楚了解清朝政府和黄遵宪所作选择的考量,甚至亦可回答张氏为何愿意出任该职的原因。”[5]黄遵宪挑选第一任中国驻槟榔屿副领事时,张在中国已经拥有南洋其他侨领难于获得的人脉关系,即盛宣怀与李鸿章等清政府高官的重视。[29]
[1]魏明枢.张振勋与晚清铁路 [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294.
[3]李松庵.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 [G]//广州文史资料,1963 (10).
[4]GODLEY M R.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1893-1911[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5]张晓威.晚清驻槟榔屿副领事的创设与首任副领事的派任 [J].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004(7):243-284.
[6]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 [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983-988.
[7]戴鞍钢.客家人与上海近代化历程 [M]//丘权政.客家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150.
[8]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 (上)[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9]赠颁旌扬 [N].叻报.1889-8-12 (5).
[10]吴汝纶.李文忠公 (鸿章)全集:奏稿73[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2122.
[11]胡思敬.国闻备乘 [M].上海:上海书店,1997:15-16.
[12]魏明枢.张弼士创办张裕公司述论 [C]//房学嘉,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425-443.
[13]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 (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清德宗实录:第6册卷420[M].北京:中华书局,1987:509.
[15]张振勋.奉旨创办酿酒公司记 [M]//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82.
[16]张振勋.创办张裕酿酒有限公司缘起 [N].商务官报,1907-03-09.
[17]夏东元.盛宣怀传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79.
[18]魏明枢.张振勋与芦汉铁路的筹建 [J].史学月刊,2009 (5):91-99.
[19]马智慧.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办及其早期发展研究(1892—1916)[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20]张榕轩.述法人葡萄酿酒之美 [M]//海国公余杂著:卷一.影印本.2005:57.
[21]李松庵.张弼士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 [G]//广州文史资料,1963 (8):105.
[22]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3]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166[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660-2664.
[2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市师范大学历史系.清季中外使领年表 [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
[25]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一八五一-一九一一年)[M].粟明鲜,贺跃夫,译.姚南,校订.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176.
[2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58:4810.
[27]薛福成.出使奏疏[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835-847.
[28]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 [J].南洋问题研究,2006 (1):59.
[29]魏明枢.张振勋担任槟城副领事的人脉关系考[M]//房学嘉等.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12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