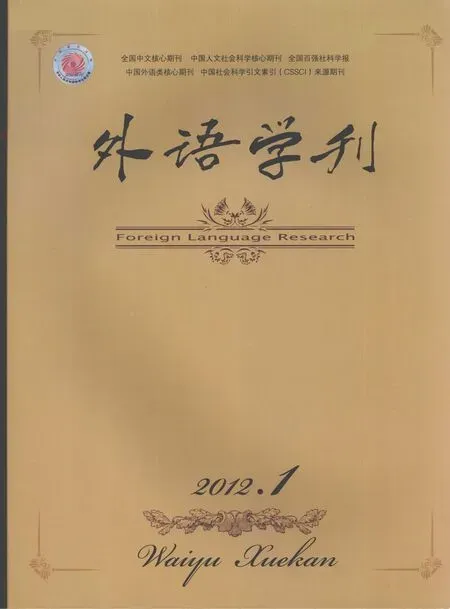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俄狄浦斯王》在宗教外衣下的政治内涵
马骁远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1 英雄与先知:宗教启蒙的政治污染
虽然目前保存的希腊文学完全是世俗的,但社会历史表明,希腊人“非常敬神”。(吉尔伯特·默雷 2007:45)当雅典要向克尔索奈苏斯殖民时,他们难以在大量人选中推举出一位将领,只好去请示并根据皮提亚的神谕,选择了米太雅德。地米斯托克利在雅典生死存亡的关头主张人民撤离城市,到军舰上去。他利用了德尔斐的神谕:“用木墙保卫自己”。极力劝说木墙就是指军舰,终于赢得了对波斯的海战。马其顿的腓力为了取得中部希腊的控制权,借口保护德尔斐圣地,参与了神圣战争,并组织皮提亚运动会,最终达到了目的。可以看出,德尔斐的宗教势力在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俄狄浦斯王》中,阿波罗也起着主导作用。
雅典娜守护的是实实在在的城邦文明。而阿波罗发布预言,在精神上引导人们。正如品达在诗中写的:“勒托之子又让你们托天之福,使利比亚平原繁荣。你们获得听取正确意见的智慧,治理一个有黄金宝座的城邦。”(《古希腊抒情诗选》1988:211)
德尔斐曾是盖亚的圣地,阿波罗来到这里,斩杀巨蟒皮同,占有了这片圣地并发布神谕。这种变化显示了希腊民族形成过程中,信仰的转变。他们从远古的祈求丰收,敬畏死亡,转变到了一种新的精神认同。光明之神阿波罗,是希腊正面民族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一切使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特别是使之与周围的野蛮民族相区别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美,无论是艺术,音乐,诗歌还是年轻,明智,节制——统统汇聚在阿波罗身上。”(王晓朝1997:71)事实上,除了德尔斐,希腊没有正式的神职人员教导希腊人如何生活。(Beer,Josh 2004:8)从荷马时代开始,阿波罗取代赫利俄斯成为太阳神,将文明之光洒向每一个人。
索福克勒斯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著名悲剧作家,《俄狄浦斯王》是其代表作。讲述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成为忒拜国王后,发现自己没有逃脱神谕的命运,弑父娶母的故事。剧中的先知特瑞西阿斯对俄狄浦斯说:“我是洛克西阿斯的仆人,不是你的。”(《古希腊戏剧选》1998:192)一方面,先知代表的是阿波罗精神的宗教;另一方面,俄狄浦斯处于与之不同的阵营之中。二者形成了对立。索福克勒斯反映的这一对立关系,绝不是停留在宗教层面,而是有其政治内涵。
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很多自然哲学家一直通过类比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关于物理自然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论,也包括了关于人类道德自然的元素及其联系的类似结论——关于国家的元素,及其统一机制。”(厄奈斯特·巴克2003:64)所以很难区分他们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多大程度地论及了人类社会秩序。而这种朴素的观念也来源于当时希腊的神话宗教观。希腊人“把一个井然有序的希腊城邦国家制度投射到天上”(王晓朝1997:185),使形态各异的神和英雄组成了一个社会模板。如库朗热所说:“正是从宗教信念中,城邦获得了它的原则、准则、习俗、行政权。”(库朗热2006:3)所以说:“这种宗教奉献出一种秩序。”(让·皮埃尔·韦尔南2001:8)
这朴素的观念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向另一端发展。进一步的殖民活动使人们脱离传统社会,成长为更加自我的个体。历史学和游记散文的发展——以希罗多德﹑赫卡泰乌斯为代表——拓宽了希腊人的视野,非希腊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冲击着希腊人的传统观念。希波战争等对外战事的胜利刺激了思想自由,尤其在雅典,随着其文化地位的崛起,各种思想涌入。这些事实导致哲学——在智者们的带领下——与传统宗教社会分离,并迅速发展为相互排斥,甚至对抗的势力,成为一股启蒙思潮。
启蒙一般表现为“人类对知识的渴求与宗教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立”,给宗教带来“污染”(pollution)。悲剧常常对此进行描绘,其主人公“或是被神祇击败,或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刘小枫 陈少明2007:3)传统认为,俄狄浦斯是启蒙“污染”的典型代表,他以自己的知识挑战神的威严,与先知争吵时,“他一遇到猛烈的反驳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知识和洞察力”(刘小枫 陈少明2007:8),但是他忽略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当他认识到再强大的个体也难逃厄运——弑父娶母时,只得刺瞎双眼,向先知屈服。从整个社会来看,启蒙没有赢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只局限在少量政客与文化精英之间。文中带领乞援人的祭司对俄狄浦斯说:“人人都说,并且相信,你靠天神的帮助救了我们。”(《古希腊戏剧选》1998:180)可以看出,宗教传统在人民心中包括索福克勒斯本人依然有很高的地位,而且人民并不信任启蒙的理性。雅典也采取了一些针对启蒙的措施。他们放逐了哲学家,颁布法律控告不信神和传播天文学渎神的人。(刘小枫陈少明2007:11)
启蒙污染不仅是对神权的挑战,它进入了政治领域,背离了城邦秩序。当安宇图斯为了雅典的自由而亡命国外,浴血奋战的时候,他的儿子却跟随苏格拉底,和一群品质不好的贵族青年混在一起,沦为不可救药的酒徒,不愿继承父亲的家业。(吉尔伯特·默雷2007:135)作为城邦的战士,安宇图斯控告苏格拉底。
索福克勒斯使用了“tyrannos(僭主)”一词来表示“王”,“tyrannos”在古希腊悲剧中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像在其它文学形式中那样带有贬义。(D.M.Carter 2007:9)但诗人在作品中有一些表明了意图的暗示。拉伊奥斯是俄狄浦斯之前的“tyrannos”,作为合法的王被杀害。俄狄浦斯在成为“tyrannos”之后陷入了恐惧。一方面害怕杀害拉伊奥斯的人会杀害自己,另一方面又怀疑克瑞昂觊觎自己的王位。(Beer,Josh 2004:103)这种心理很像雅典早期刺杀僭主行为的后遗症,而雅典早期的僭主在政治上是被强烈攻击的目标。另外,俄狄浦斯的统治并非依靠强力,也不是依靠宗教势力。他通过破解斯芬克斯之谜被推举为国王,而且作品中显示,在他将城邦治理得风调雨顺的十几年中,他从未请示过神谕。所以,俄狄浦斯的君临(tyrannical rule)是纯粹反传统的理性的统治。(Ahrensdorf,Peter J 2009:19)
综上可以断定,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与宗教传统相背离,是启蒙的“政治污染”。诗人以这样的人物形象,试图影射雅典政治家,揭露雅典当时的政治现实。
2 俄狄浦斯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的政治讽谏
关于《俄狄浦斯王》写作的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大致定位于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25年之间。我们认为写作时间在伯里克利临死前的一两年之内。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的是怎样的时代。
首先是作品中的瘟疫能够多大程度地影响年代的判定。“污染-瘟疫-涤罪”是古希腊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模式。早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就曾将瘟疫带给希腊联军,阿伽门农要通过归还祭司的女儿平息阿波罗的愤怒。有观点认为《俄狄浦斯王》中的描写很像雅典在公元前427/6年的瘟疫情景。(Vickers,Michael 2008:36)但是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忽略诗人与散文史家之间互相借鉴到什么程度。其次是作品直接反映的现实环境是否是伯里克利执政末期。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25年之间,雅典有三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伯里克利﹑克里昂(Cleon)﹑阿尔西巴德。有观点认为,《俄狄浦斯王》反映了阿尔西巴德年轻的放纵,也预示了他未来的发展。(Vickers,Michael 2008:41)但是,阿尔西巴德的年纪显然比俄狄浦斯小,而且,诗人为什么要用一个30岁左右(俄狄浦斯年纪最小的估计也应在30左右)就被逐出城邦的人来反映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政治军事新星呢?至于克里昂等人的形象,如果与伯里克利比较的话,与俄狄浦斯更接近的显然是伯里克利。所以,《俄狄浦斯王》直接反映的应是伯里克利执政末期的时代。
伯里克利从哲学家处学到了诡辩和演讲,如芝诺﹑阿那克萨戈拉,使他“披上庄严的外衣”,“讲话比别的政客更有力量,并把他的威望提得很高”。(普鲁塔克1990:465)另外,在伯里克利的年代,德尔斐也成为了政治争夺的工具。公元前448年,“斯巴达人把军队开进福基斯人占领着的德尔斐,把庙宇交还给德尔斐人。等斯巴达人一撤走,伯里克利就把军队开进去,恢复福基斯人的权利。斯巴达人已经从德尔斐人手中得到代替别人祈求神谕的权利,并把此事刻写在神殿里那只铜狼的额角上,伯里克利于是又为雅典人从福基斯人手中夺回这个崇高的特权,并在铜狼额角的右侧刻写了这件事。”(普鲁塔克1990:483)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曾试图以清除“库隆污染(Cylonian Pollution)”的名义赶走伯里克利。(Plutarch 1914-26:95)事实上,伯里克利的祖先确实与库隆的渎神案有关。如果索福克勒斯有意用俄狄浦斯的“污染”类比的话,《俄狄浦斯王》写作的年代应不早于公元前431年。不可否认,伯里克利与索福克勒斯是好友,然而零星的资料表明,二人存在着分歧。索福克勒斯“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维护已经确立的秩序”。“过分是一个不准在他面前提及的词,节制是他的专有的用词。”(伊迪丝·汉密尔顿1988:225-226)他笃信宗教,作为“得克西翁”和诗人,与阿波罗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伯里克利不喜欢索福克勒斯的艺术气质,并且多次指责或讥讽他不适合做将军。(Vickers,Michael 2008:15)二人的立场颇有不同。伯里克利在索福克勒斯眼里是一个受了启蒙影响的政客,而索福克勒斯则是阿波罗的信徒。
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俄狄浦斯在忒拜的地位是至尊无上的,他的政绩也必然超越了前任。这与伯里克利在雅典的地位极为相似。公元前442年,伯里克利将政敌修昔底德放逐之后,“把雅典以及雅典所拥有的一切都掌握到自己手中:贡赋﹑军队﹑军舰﹑岛屿﹑大海。从希腊和外国得到的广大权利,以及由许多臣服的民族﹑友好的国王﹑结盟的统治者做屏障的霸权。”(普鲁塔克1990:478)
俄狄浦斯在早期的史诗中,同样弑父娶母,但他却有着光荣的结局。他战死沙场,享受盛大的葬礼。(王以欣2006:第五章)索福克勒斯并没有采用这样的素材,他的俄狄浦斯有着悲惨的结局。这也正是全剧的重要疑点。
俄狄浦斯与伊奥卡斯特共同生活了十几年,难道双方从来没问过以前的事?(Vickers,Michael 2008:40)为什么所有谜团都是在最后解开的。忒拜人民或王室能信任一位不知底细的国王吗?然而,根据索福克勒斯的意图,在这场瘟疫之前,这一切确是不为人知的。也就是说,剧中的俄狄浦斯根本没有弑父娶母,而是阿波罗强加了一个这样的命运。“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是阿波罗著名的箴言。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家也必将认清自己的局限。俄狄浦斯希望通过理性实现崇高不朽的理想,但阿波罗的法术使他陷入混乱的家庭关系之中,对崇高不朽的愿望使他不得不求助于神灵,放弃理性。他请示神谕,询问先知。而这一放弃又导致了他的失败。(Ahrensdorf,Peter J 2009:25)俄狄浦斯的认识活动告诉我们,人类终究不是神灵,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变得崇高不朽。索福克勒斯认为:宗教虔诚对于稳定的政治社会是必要的。(Ahrensdorf,Peter J 2009:46)
索福克勒斯在启蒙的浪潮中告诫好友伯里克利,希望他遵照阿波罗的训诫,及时隐退。于是作品中伊奥卡斯特在俄狄浦斯不断地追查,事件就要水落石出的时候说:“现在别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为什么问他所说的是谁?不必理会这事。不要记住他的话。”“如果你关心自己的性命,就不要再追问了;我自己的苦闷已经够了。”直到后来哀求俄狄浦斯:“我求你听我的话,不要这样。”(《古希腊戏剧选》1998:213-214)以这样的方式,诗人为好友提出了建议。
索福克勒斯也许看到了伯里克利在最后瘟疫中的屈服,伯里克利失去了大量亲人,“这些不幸都没有使他丧失他的崇高精神,无论在葬礼中,在亲人的墓前,都没有人看见他哭泣过,除了他失去最后剩下的唯一一个嫡出的儿子帕拉洛斯时,他才哭了。这次的打击使他低了头,他却还想尽量维持他一贯的风格,保持他崇高的气概,可是当他向遗体献花的时候,一看那光景,悲哀就把他打倒了,他失声痛哭,流下了滚滚热泪,这在他一生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普鲁塔克1990:498)这正是发生在伯里克利最后的日子里。索福克勒斯也许感受到了这些才将俄狄浦斯的悲剧写得如此传神,或者只是预见到了这些。
3 政治瘟疫与人民领袖:索福克勒斯的预见与局限
“我给人民以恰好满足的权利,所得不短少也不加多。有权势有令人羡慕的财产的人,我劝告他们不要过分,我手持大盾站稳,为双方挥舞,不让任何一方非法战胜。”(《古希腊抒情诗选》1988:83)这是梭伦的诗。万物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过犹不及”(Nothing in excess)是重要的。阿波罗将这种精神传遍希腊,其忠诚的信徒——品达、梭伦等人也都保持着这一作风。正如诗中反映的,梭伦希望营造中庸﹑和谐的社会环境。“阿提卡法律的仁慈反映了他温和而虔诚的气质。”(厄奈斯特·巴克 2003:59)然而,历史环境中这样的氛围并未持续多久,随着智者们的影响和宗教启蒙的不断深入,雅典的政制几经改动,这位阿波罗信徒的立法意图被篡改了。“雅典人把公民间的平等与所有人的平等小心地区别开来了。”(威廉·弗格森2005:21)最能表现这一点的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帝国统治。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把雅典说成“希腊人的学校”,认为“希腊人为他们所受的教育牺牲某些东西是正确的。”(威廉·弗格森2005:34)此时的雅典不再认为“有必要用漂亮的词汇粉饰丑恶的事实了。因为她认为这些事实不再是丑恶的了。”(伊迪丝·汉密尔顿1988:169)这一切都源自对权力的贪婪和野心。
阿波罗的信徒早已意识到这些,并采取了行动。早在希波战争的关键年头,也就是地米斯托克利忙于海战的时候,品达做出了“最无耻危害最大的抗拒行为”,“竟然侈谈什么和平与中立!”(吉尔伯特·默雷2007:84)这是阿波罗精神的预见。索福克勒斯也洞察到这些,在他的年轻时期,“雅典的前景无限光明,到了成年时期,战争和朋党争吵冲突,撕裂着整个城邦;到了晚年,美好、忍让、公平的交往以及雅典所倡导的一切都被践踏和抛弃了。”“他所经历的年代是对每一个人的品格的考验。”(伊迪丝·汉密尔顿1988:222-223)早在雅典全盛时期,他——阿波罗的另一信徒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国内,只有他与雅典城的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都有紧密的联系(刘小枫 陈少明2007:7)。
实际上,公民之间也并不平等。修昔底德这样写道:“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事实上权力正向第一公民手中集中。”他们(第一公民)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群众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威廉·弗格森2005:39-40)亚里士多德写道:“自克利俄丰以来,人民领袖不断地一线相承,尽是些最喜欢鲁莽从事的人,他们使多数人获得满意,目的在于求得当前的声望而已。”(亚里士多德1959:34)两人所论及的“第一公民”(Thucydides 1914-26:376)和“人民领袖”相似,都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能倡导某种政策路线,凭借影响力来统治。所以,克利俄丰之后的,以及伯里克利之前的米太雅德、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提得﹑厄婓阿尔特斯等人在本文中统称为“人民领袖”。在《俄狄浦斯王》全剧开篇,忒拜全城笼罩在瘟疫与恐慌之中。克瑞昂去请示神谕,俄狄浦斯出宫探视乞援的群众。他这样说:“我愿意尽力帮助你们,我要是不怜悯你们这样的乞援人,未免太狠心了。”群众中为首的祭司也答道:“我们把你当做天灾和人生祸患的救星”,“假如你还想像现在这样治理这国土,那么治理人民总比治理荒郊好;一个城堡或是一条船,要是空着没人和你同住,就毫无用处。”(《古希腊戏剧选》1998:179-180)这段话暗示了俄狄浦斯的身份。从全剧来看,俄狄浦斯的形象也可归纳为“人民领袖”。
综上所述,《俄狄浦斯王》实际上针对的是“人民领袖”——他们背离了传统的宗教社会秩序,在索福克勒斯的年代造成了可怕的政治倾向,事实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反映社会政治的悲剧。
然而,索福克勒斯反映了雅典内部怎样的政治现实?《俄狄浦斯王》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预言,由俄狄浦斯转述为:“他说我命中注定要玷污我母亲的床榻,生出一些使人不忍看的儿女,而且会成为杀死我的生身父亲的凶手。”(《古希腊戏剧选》1998:204)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暗示。俄狄浦斯通过武力和智慧夺走了拉伊奥斯的王位。在雅典,人民领袖通过党争取得领导地位是非常普遍的。地米斯托克利的功绩是战胜了米太雅德取得的。阿里斯提得、地米斯托克利以及客蒙也由于党争被放逐过。伯里克利也通过放逐修昔底德取得稳固地位。(普鲁塔克1990:495)
古希腊民主社会的重要观念与阿波罗教义相联系,“过犹不及”暗示了每个人的平庸。于是每个人分得等量的社会价值,公民之间平等地组成一个团队。使得他们的政治理念中,只有公民与城邦的统一,“而不知道它们之间也应该是相对立的,还没有公民是个体的概念。”(许耀桐2009:13)然而“在现实中他们还是倾向于使政治权力成为最强大阶级的战利品,而某个阶级一旦赢得政治权力,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利用它。”(厄奈斯特·巴克2003:16)理念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了雅典民主的一个重要缺陷。在这里,人民领袖的煽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带着启蒙的污染歪曲理念中的政治概念,利用公民的倾向党同伐异,造成了不同政治家的成败。
在开篇处,克瑞昂就说了“你得下驱逐令”(《古希腊戏剧选》1998:182)。后来,俄狄浦斯公开宣布:“在我做国王掌握大权的领土以内,我不许任何人接待那罪人——不论他是谁,不许同他交谈,也不许同他一起祈祷,祭神,或者是为他举行净罪礼;人人都得把他赶出门外,认清他是我们的污染,正像皮托的神示最近告诉我们的。”(《古希腊戏剧选》1998:186)俄狄浦斯绝没有想到自己下达的放逐令用在了自己的身上,于是他说道:“这诅咒不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而是我自己。”而且发问:“我不是个坏人吗?我不是肮脏不洁吗?”(《古希腊戏剧选》1998:205)这是索福克勒斯对民主缺陷的影射,他暗示了雅典的陶片放逐法,由人民领袖创制,遭到放逐的也往往是人民领袖。从《俄狄浦斯王》文本来看,俄狄浦斯努力成为贤明的君主,并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作为人民领袖——虽然这与政治理想不符,他们在雅典同样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希腊人也愿意把自己的风格气质归因于吕库尔古(Lycurgus)或梭伦之类的贤人。“希腊人极富灵活性的气质有时让他们极易适应某个治国之才的创造性活动,尽管这种适应可能并不持久”。(厄奈斯特·巴克2003:11)作为当时公民的一员,索福克勒斯在剧中强调“命运”、“平等”、“发言权”等,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模糊的名词有多大程度涉及了问题的核心,只能说诗人也在质问城邦:那些有功的领袖为何遭到放逐?
剧中忒拜出现了瘟疫,现实中的雅典也出现了瘟疫,如上所述,索福克勒斯在他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政治瘟疫”。《俄狄浦斯王》直接反映了伯里克利晚年的政局,实际上总结并预言了雅典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现实。在索福克勒斯看来,党争一直在继续,剧中的克瑞昂从德尔斐请求神示归来,戴着花冠,这与俄狄浦斯从外邦来到忒拜,成为国王的场景相似,预示了克瑞昂将取代俄狄浦斯的位置。(Beer,Josh 2004:102)而且,《俄狄浦斯王》没有交代在俄狄浦斯惩罚自己,离开忒拜之后,瘟疫是否得到了平息。
索福克勒斯的政治智慧有其对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的预见性,也有对当时的局限性。“在雅典盛行陶片放逐制的那些年代里,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可以通过促成放逐其对手来为自己赢得信任票;放逐制的价值也就在于,它把政策的方向交给一个受到信赖的顾问来把握,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当它在5世纪末销声匿迹后,人们就夹在了两个或更多相互竞争的'议院首领'中,一会儿跟随这个,一会儿听从那个,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厄奈斯特·巴克2003:50)背离阿波罗的宗教精神,持续的“人民领袖”党争,确实给雅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他的预见性。但陶片放逐法对当时政局稳定的掌控作用也是索福克勒斯没有看到的。
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戏剧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刘小枫陈少明.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罗念生水建馥.古希腊语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奈波斯.外族名将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皮埃尔·布吕莱.古希腊人和他们的世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2001.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水建馥.古希腊抒情诗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王以欣.神话与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许耀桐.西方政治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张竹明王焕生.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Z].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Ahrensdorf,Peter J.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Beer,Josh.Sophocles and the Tragedy of Athenian Democracy[M].Westport,Conn:Praeger Publishers,2004.
D.M.Carter.The Politics of Greek Tragedy[M].Bristol:Bristol Phoenix Press,2007.
Plutarch.Pericles:Plutarch LivesⅢ[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 -26.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 -26.
Vickers,Michael.Sophocles and Alcibiade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