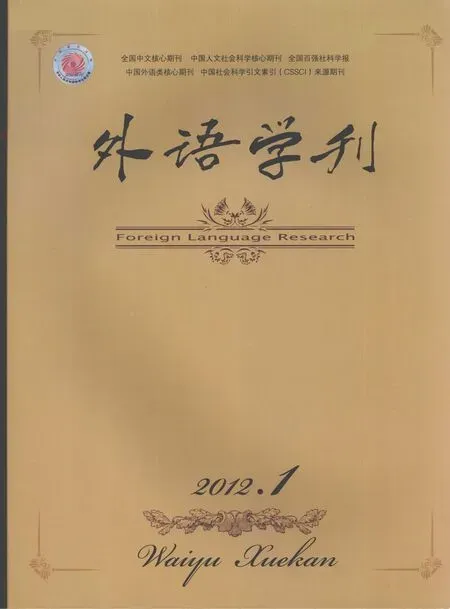奥尔巴赫《模仿》与德国文体学的黑格尔主义问题*
杜萌若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流亡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德国犹太裔学者艾里希·奥尔巴赫在极端艰苦的学术环境中写下了一部不朽巨著:《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多年以后,奥尔巴赫回忆起这段特殊的经历,仍有种百感交集的况味:“伊斯坦布尔没有对于欧洲研究来说资料完备的图书馆,国际交流被阻断了,我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的期刊和近期的研究成果……专业文献和期刊的缺乏或许可以解释本书为何没有注释。除文本以外,引文相当少,直接插入论述主体非常容易。另一方面,本书得以诞生,多半要归功于藏书丰富的专业化图书馆的缺乏。假设我能够获得众多领域的所有著作的话,恐怕永远不会产生写作的勇气了”(Erich Auerbach 1953:557)。奥尔巴赫的语气中流露着辛酸与伤痛,但更多的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庆幸和自得,战时的流亡背景反倒意外地使他得以摆脱学院式研究体制化的繁文缛节,拥有了自我表达的自由空间和直入核心问题的契机。
2
在《模仿》的“后记”里,奥尔巴赫清晰地阐释了他的主题和方法:“本书的主题是关于通过文学再现或‘模仿’对现实的解释……在研究欧洲文学中解释人类事件形形色色方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凝聚于一个焦点……对现实主义的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初衷,因为我的主导观念已经将其对象限定在一种非常专门的方式内来探讨。……在我看来,对‘严肃文体和严肃特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范畴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分析描述是不适宜的,从读者的角度来说,那样做会使他们一进入我的论题就不得不面对乏味的概念考察(甚至“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本身都是模糊含混的),更何况我也没有能力制造出一套简易便捷的术语体系。我采用的是这样的程序:为每个时期引用几段文体,把它们作为印证我的观念的个案,带着读者直入主题,使他在与任何理论性的东西触接之前先对具体的问题有一个实感”(Erich Auerbach 1953:554-556)。《模仿》的著述形式看起来简直朴素得惊人,全书围绕着从荷马到弗吉尼亚·吴尔夫两千多年西方文学史中的20篇文本选段展开解读和品评。根据奥尔巴赫本人的说法,“文本中的大部分都是任意选择的,选择时多半没有明确的意图,毋宁说大体上是出自兴来偶得和个人偏好”(Erich Auerbach 1953:556)。萨义德接受了奥尔巴赫的自我表白,认为“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从相互分离的片断出发开展研究实践”(爱德华.W.萨义德2006:118)。但法国批评家塔迪埃对此则有另一种看法:《模仿》形式上的随意性和片断性其实是一种假象,“确定20个章节之前已经存在一个总体结构,我们可以从20个章节的每一部分出发,复原这个结构”,“如果‘辩证’一词不会使人联想到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真想用‘意识的辩证性’一词来概括奥尔巴赫的思想”(让·伊夫·塔迪埃1998:58-60)。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暂时离开奥尔巴赫和他的《模仿》,去回顾一下他伟大的前辈布克哈特的思想及贡布里希对他的评价。在24岁时写给友人卡尔弗雷泽纽斯的一封信里,布克哈特谈到了他在历史研究上的宗旨和意向:“从天性上说,我是倾向于有形的、倾向于可见的现实和历史的,但我也决心不断地从并列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类似之处,由此独自成功地得出一些普遍原则,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原则上还存在着一条更高的普遍性原则,或许我将能达到那个水平……也许我的确无意中受了近来哲学思潮的影响,但是请允许我停留在这一谦卑的水平上,让我感觉历史触摸历史,而不要让我通过它的基本原则去理解历史”(E.H.贡布里希1989:45-46)。贡布里希敏锐地指出,强调有形事实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生动历史细节的布克哈特其实是个黑格尔主义者。贡布里希说:“要把布克哈特划为黑格尔派是骇人听闻的,因为他本人曾多次表示对黑格尔的哲学牌号的反感。他一贯强调自己不迷信体系而只相信事实,但我希望表明的是,布克哈特的情况证明了一条重要的方法论真理:正是那些心想抛弃所有‘先入之见’理论的人往往不知不觉地屈从了先验理论的威力……尽管布克哈特相信他是在归纳观察到的历史事实,然而他从史实中最终发现的正是他作为思辩的抽象之物而加以拒绝的黑格尔的世界精神”(E.H.贡布里希1989:46)。奥尔巴赫和他的前辈布克哈特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奥尔巴赫同样是一位披着反体系外衣的黑格尔主义者,塔迪埃的说法准确地洞悉了其思想潜意识的深层结构。
奥尔巴赫的同行和竞争对手库尔提乌斯把他和体现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德国思辨型理论家归为同类,这引起了奥尔巴赫的强烈不满,“在一篇义愤填膺的答辩中,他指出,《模仿》关注的是作家的实践而不是文体风格理论”。(René Wellek 1991:112)对这场“巨人之战”的公正裁决应该是:库尔提乌斯旁观者清,奥尔巴赫没能很好地履行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就像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沃尔夫林的文艺复兴式风格与巴洛克式风格、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奥尔巴赫也建构了一对德国式思辨气息浓郁的二元对立的正题和反题——古典的文体分用原则与犹太-基督教的文体混合原则。(施锐2011)《模仿》断片性札记的表象之下隐匿着一部展现对立面矛盾冲突、在不断的扬弃过程中辩证运动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现象学”。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荷马史诗之所以远远高明于同样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其他史诗,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其“整一性”的构成原则优越于其他史诗的“缀段性”,奥尔巴赫的《模仿》和库尔斯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均以语言学家对细节准确性的严格要求自律,也同样采用了“缀段性”的著述形式,而前者之所以比后者更受评论界好评,就在于它有意无意间展示了一种中世纪大教堂般的整一性空间构成之美,那境界犹如巴赫赋格曲秩序井然的旋律蕴含着主题间际交叉叠合的时间运动之美。
3
《模仿》的第一个片断“奥德修斯的伤疤”是这部批评史诗的导引,或者说,是这部批评交响乐的序曲。奥尔巴赫从《奥德修纪》中一个细节的解读出发,展开了荷马史诗与《圣经·旧约》的文体比较。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并不介意让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如洗脚这样的家庭生活场景——进入崇高和悲剧性的范畴,这和后来的古典文体分用原则中现实主义描写仅限于喜剧性或田园牧歌性范畴的情况有着不小的距离。不过,尽管如此,当荷马文体与《圣经》文体并置一处的时候,前者与古典文体分用原则的亲缘关系就会清晰地显示出来,“再现日常生活的家庭现实主义,在荷马那里保持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平和安宁的王国,而旧约故事的一开始,崇高的、悲剧式的、问题性的东西就实实在在地显现在家庭生活与日常琐事的场景之中”。(Erich Auerbach 1953:22)我们发现,《模仿》的主题所要求的黑格尔式二元对立的正题和反题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奥尔巴赫对文体本身的卓越鉴赏力和判断力本来使他洞察到了荷马文体的独特性,然而,先入为主的理论设定又在无形中推动他十分牵强地扭合荷马文体与古典文体分用原则的亲缘关系。奥尔巴赫对文体的选取绝不像他本人所描述的那样信手拈来,在意识的层面,他的确是要真诚地去感觉和触摸文本事实本身,然而,在潜意识的层面,理论结构莱布尼茨式的“预设和谐”已事先决定了每个文本单子的位置和形态,《模仿》的美在于这种深隐的“秩序感”,而它的问题也恰恰在于简洁优美的理论形式对文学史事实不可避免的扭曲和变形。
在比较荷马和《圣经》文体的过程中,奥尔巴赫抑扬分明的价值评判态度在近三百年来的文学史家中是极其罕见的:“在荷马那里,心灵活动的复杂性仅仅是通过各种情感的转移和转换来显现的,而犹太作家却能够表达意识的形形色色层面的共时性存在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冲突。……《旧约》中的伟大人物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展开得饱满许多、成长过程明晰许多、个性也远为鲜明……比起荷马世界中的人物来,亚伯拉罕、雅各乃至摩西都要更加具体真切、更加栩栩如生”。(Erich Auerbach 1953:13,17,20)毫无疑问,奥尔巴赫的评价对于荷马来说是极不公正的,希腊史诗沉雄深邃的人性深度表现在这里竟然被抹平了。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文学批评界对奥尔巴赫偏激而怪异的“两希”文学比较保持着出奇的沉默。奥尔巴赫犹太族裔的特殊身份以及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悲惨命运是否构成了这篇文学批评极端观点的意识形态背景呢?
从《模仿》的第二个片断“芙尔图娜塔”开始,这部批评史诗正式进行它地道的正题与反题对照:古典的文体分用原则与基督教的文体混合原则。奥尔巴赫给出的文本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一段文字以及新约对观福音书中彼得于耶稣被捕之后否认自己为其门徒的故事。在这里,奥尔巴赫强调指出古典现实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任何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寻常之事,均只能以喜剧的形式来处理,不容纳问题性的思考,结果自然是现实主义界域的狭窄化……古典文学做不到严肃地再现日常生活,亦即无法充分体悟日常生活的问题,看不到日常生活的历史背景。古典文学只能以低等文体再现日常生活,喜剧式的,甚至是田园牧歌式的,静止凝固,非历史化。这些不仅标示着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而且也标示着其历史意识的局限性”(Erich Auerbach 1953:31,33)。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在奥尔巴赫眼中,福音书中的彼得故事所反映的基督教现实主义要深刻得多:“表面看来,这里讲的是一次缉察行动及其后果,它完完全全地发生在芸芸男女众生之间,这类事情在古典术语中只会被设想为闹剧或喜剧。但为什么它既不是闹剧也不是喜剧?为什么它引起我们最严肃和最有意味的同情?……我们所目睹的是‘新心灵与新精神’的觉醒”(Erich Auerbach 1953:43)。在《模仿》的下一个片断解读中,奥尔巴赫通过对基督形象的分析,进一步确立基督教现实主义对古典文学的绝对优越性:“基督不是作为英雄和国王,而是作为社会最底层人物而出现的。他最初的门徒是渔夫和匠人,他在巴勒斯坦穷苦大众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活动……表现基督言行的文体几乎完全不具备古典意义上修辞文化的任何特征,它只是下里巴人的语言,然而,它感人至深,远比任何最崇高的修辞以及悲剧作品更加令人难忘”(Erich Auerbach 1953:72)。可见,奥尔巴赫关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与犹太-基督教文学的优劣裁断显然远不局限于文体学上的意义,而是具有整体文化抉择的更为重大的意义,奥尔巴赫坚定地站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一边,与德国文化界自温克尔曼、歌德直至尼采而达到最高潮的古典文化复兴、或曰异教文化复兴的主流泾渭分明。
4
从进入中世纪文学的探讨开始,奥尔马赫把眼光基本上集中到文学本身的问题之上。“现实的表现是奥尔巴赫的主题,因此,他必须作出判断,在哪里、在哪些文学作品里,它得到了最巧妙的表现”。(爱德华.W.萨义德2006:110)奥尔巴赫的专业是拉丁语系语言和文学,他在《模仿》中给予意大利、法国文学中的现实再现最重要的地位和最大的论述篇幅。在奥尔巴赫看来,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创作达到文学对日常生活现实再现的完善境界:“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成型于19世纪早期法国的现代现实主义特点突出,表现为对关于文学再现层次论的古典教义的彻底摆脱……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从与当代历史状况水乳交融的日常生活中任意提取人物形象,把他们塑造成严肃的问题性的乃至悲剧式再现的对象。……他们为现代现实主义开辟了道路,从此,现代现实主义与纷纭变幻、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现实保持同步,日益丰富其表现形式而发展壮大”(Erich Auerbach 1953:554)。在奥尔巴赫的文体学理论体系中,中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成为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完美合题,只不过,不同于一般的正题——反题——合题惯例,这个合题展示为一个辩证回返于反题的变体。
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施 锐.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文化[J].外语学刊,2011(2).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象——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Erich Auerbach.Mimesis:The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G.W.F.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and The Macmillan Company,1931.
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 ~1950[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