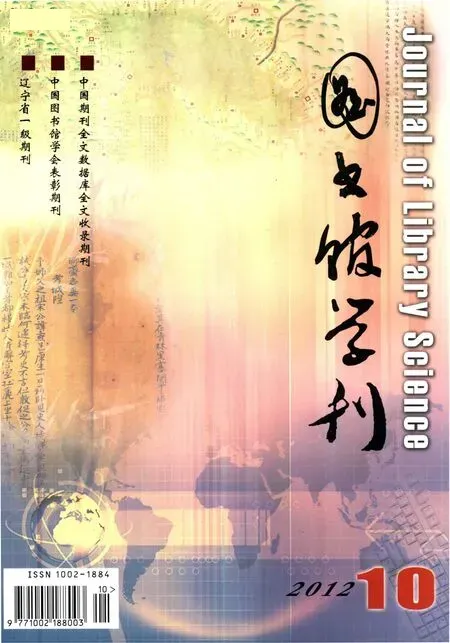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考略*
肖书铭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007)
肖书铭 男,1986年生。硕士,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整理。
官府从事刻书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发轫于五代,消止于清末,对保存和传播历代文献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福建古代刻书事业自宋代以来就见称于世,至明清两代更是瑧于鼎盛,与之相应,其官府刻书事业在这一时期亦得到长足的发展,刻书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超前代。
1 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的目的
官府刻书,其主体为官府,而其具体的经办人则是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故官刻本所体现的必然是各级官员的意志。作为官员,利用官资从事刻书事业,其目的大抵如下:
首先就是以刊刻书籍为手段,宣扬理学正统思想,从而达到崇扬正学,占领文化阵地的目的。明代建阳大儒书院刻有《道南源委录》,乃嘉靖年间福建巡抚李邦珍主持刊刻。对于刊刻本书之缘由,据该书序言云:“闽兵燹极矣,孔子所谓修文德,服远人,而疆理南海,卒归于矢,文德之颂,盖正学、明文教、张士修孝弟忠信,即干城函矢在人心矣。呜呼,闽学之士,不讲旧矣,矢德修文,其在兹録乎。”[1]可见其刊刻此书,乃因当时福建倭寇横行,兵连祸结,人心疲惫,无心向学,故欲刻此书,而以其理学之忠诚孝悌、怀德远人振奋士气。清末重臣左宗棠,其在宦闽期间,以张伯行所刊刻丛书《正谊堂全书》“扫异学之氛雺,入宋儒之堂奥”,[2]而刻板已不存于世,为使“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之遗绪”,[2]乃设立正谊书局,博求《正谊堂全书》之初版,并组织学者和儒生精雠细校,仅9个月就校刻完成《正谊堂全书》共63种,其中所包括之著作皆为宋代以来濂洛关闽学派之理学名著。
其次,明清时期福建官府致力于刻书还为了保存文化遗产,以推动文化传播。明嘉靖四十年建宁府刊刻王维桢所撰《王氏存笥稿》,该书初版乃刊刻于浙江姑苏,求之者甚众而传本稀少,“士大夫购之者恒虑弗获”,杨一鹗“获而诵之”,十分喜欢,在建宁府为官期间,他又结识了该书作者王维桢的弟子,时任建安县令的潘儯,于是趁职务之便将该书交由潘儯刊刻,以广其传播。[3]乾隆年间,徐景熹任福州知府,“相其圭臬,权厥钧黍,爰及志帙,讶其断脱”,感叹福州志书“自明万历至今,无起而续其记载者”,认为“兹事重大,亦无先于此者。夫书阙则疑不耀,事久积则苑而听益荧”,[4]为保证文化之传承,故决意重纂福州府志,并于乾隆十九年付梓刊刻。
第三,明清时期官府刻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舛正刻本之谬误,以正刻书风气。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本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条下录有明代福建官刻本《五经四书》卷首提刑按察司牒文,其中叙述该书刊刻之经过甚为详尽,该牒文载:
“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刬毁,决不轻贷。”[5]
从中可见,当时之地方政府为减少错讹,端正刻书风气,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著作,他们组织专门力量加以校正,刻成范本颁给建阳,作为其刻书的范本,并要求建阳书坊照式翻刻,不许另刻。
最后,明清福建官府也从实用目的出发刊刻了不少书籍,内容涉及医学、军事、行政等方面。刊刻这些文献的目的大多是满足实践的需要,或解决民生之问题,或为政府行政提供资鉴。如邢址就任邵武期间于郡斋所刊刻《心印绀珠经》一书,据该书卷首序言,述其刊刻之缘由甚详,序言首述其在闽之经历,“入闽邵武,万山众麓,风气蕴毒,未几病疸”,已而医生从该书中“检剂服之,遂而获痊”,自此深感“闽土气偏而病湿,民命殊脆”,而“该书世所罕见,而备诸方剂多合闽民之病”,故“刻之以济惠下民”,[6]从中可知其刊刻此书之目的在于解民生之困,除万民疾疫之苦。
2 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的经费来源
经费的筹措是刻书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官府刻书之经费出自官资,然刻书属文化事业,无关乎民生社稷,故惟官资有富余之时方才考虑,因此在政府财政开支的序列中,刻书多敬陪末座。嘉靖《建阳县志》卷四《贡赋》中曾对建阳县之开支有详细的叙述。当时,建阳县财政之主要收入为商税、田赋以及“派征正、杂二办纲银”,其支出主要用在春秋二祭、清明、七月、十月三祭和乡饮,以上开支之后,有剩余方用于“本县庆贺赆礼、刷书之用”。[7]清代书院刻书大兴,书院各项事务皆需经费,而刻书不属于急用,故其在经费的使用序列中仍是十分靠后。清代致用书院之经费,首先是用于书院的各项事务支出,剩下的经费首先还是要“留为山长盘费”,其后才是“递年修理添置器具、刊刻课艺等用”。[8]
除了正常的税收用于刻书外,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有其他的来源,如赎锾、厘金等,它们也常常被用于刻书。所谓赎锾,其缘起可追溯至上古之尧舜时代,《文献通考·刑考十》载“虞舜,金作赎刑”,[9]而其后的各个王朝也几乎都设有以钱赎罪的法律条款,可谓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这笔款项常被用于文化事业的建设,当然也包括刻书。明代福建一部重要方志《闽书》的刻印出版就有赖锾金的支持。万历四十四年,何乔远修成《闽书》,但书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乏人问津。崇祯元年,熊文灿出任福建巡抚后,以《闽书》“以师之志,不异乎圣人”,对其颇感兴趣,遂决定捐资刊刻,乃“捐赎锾数百金,为刻于闽省”。[10]
而所谓厘金,乃出现于清末的一种专取于商不取于农的新税法。各省所收取厘金的一部分被用于刻书,尤其是清晚期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热衷于兴办书局、刊刻典籍,其费用就常常取之于厘金。清末左宗棠于福州设立正谊书局,据《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卷二百零五所载:“所指以厘金充修脯一节,闽省鳌峰书院旧藏正谊堂板无存,左宗棠设局重刊。”[11]可见左宗棠乃以厘金充书局刻印人员之薪酬。
另据吴棠《闽省建设书院疏》载:“前督臣左宗棠重刊先哲遗书,开设正谊书局,录选举贡百余人,月给膏火,分班校拨,……以书局工程蒇,请设举贡书院,……呈经前兼署臣英桂批司议定章程,在于厘金下筹拨银五万两,发交殷实富商,每月完息一分一厘以资经费,将正谊书局改为正谊书院。”[12]从中可知,正谊书局除将所收厘金发给员工薪酬外,还特别拨出一笔款项交给殷实商人,坐收利息,并将每月之利充当书局经营之用。
3 明清时期福建官府刻书的校勘
校勘是书籍出版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其水平高低对于刻本质量之优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书籍校勘的水平高低又与参与校勘人员的素质密切相关。考诸文献,明清两代福建官刻本的校阅者无外乎3个群体。首先是官员。官员作为官府刻书的主体,大都是通过科举而晋身仕途,具备较深的文化功底,可以胜任书籍校勘的职责,故明清时期福建官刻本多有由官员校勘者。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刊刻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苏信所撰《重刊晦庵先生文集序》对其校雠之经过叙述甚详:“是集旧刻闽臬,岁旧刓阙,且简帙重大,人艰于蓄比,省约版纸者什四,方鸠工沐梨。而胡宪使岳至,躬总校雠之任,董学潘宪副潢佐之、罗宪副英、陆宪副铨、姜佥宪仪、刘佥宪案咸于有劳,信莅亟促其成。”[13]
弘治十五年,建阳知县区玉出知建阳县,在任内他“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缺板,悉令重刊,嘉惠四方学者”,[7]其间刊刻了宋人章汝愚的《群书考索》一书,当时参与该书校订工作的,就包括建阳县丞管韶、罗源知县徐珪、建宁府同知胡瑛等官员。正德十一年,邵豳出任建阳知县,在任内他“兴学校,增学田,奖进生徒”,[7]政绩颇著,期间他曾亲自校订刊刻了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
其次,学者也是明清时期福建地区负责官刻本校订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或隐居不仕,或任职于相关教育机构,受有关官员之委托而从事官刻本的校雠工作。由于明清时期学者多博通经史,学养深厚,于书籍之校雠亦颇有心得,故所校之书,质量亦较官员为好,其中更有不少刻本已成为中国古代刻书之精品。嘉靖年间,当时的福建巡按李元阳任职期间刊刻《十三经注疏》,是现今最早的一部十三经刻本,其校勘精审,影响深远,“在南北监本之先,今称闽本,较监本尤可贵”,[14]其主要的校订者就是当时福州两位著名学者高濲和傅汝舟。高、傅二先生作为当时之著名学者,其学术功底深厚,校勘细致,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成就了闽本《十三经注疏》的高品质。康熙年间,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建鳌峰书院,“取朱子语类、学的、文集、文略、遗书、二刻遗书、朱刘问答诸书及闽前哲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黄勉斋、陈北山、高东溪、真西山诸文集,尽刊布之,凡五十五种”,[15]刻成《正谊堂全书》,该丛书的校订者中就包括当时之名贤如蔡壁、蔡世远、蓝鼎元、郑亦邹等人,皆当时福建学术界之精英。时至清末,又有左宗棠重刊《正谊堂全书》,其选定的总校官亦为当时福州的著名学者杨浚。
第三,官学或书院的师生也是明清时期从事官刻本校勘工作的主力军。这一时期,福建官方刊刻了许多大部头的书籍,要对这些书籍进行校勘,其工作量十分庞大,仅仅依靠人数有限的官员和学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人数众多而又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学校学生就成了从事官刻本校勘工作的不二人选。崇祯年间漳州府儒学刊刻黄道周所撰《洪范明义》,该书原为黄道周奉命撰修之书,进呈后未誊抄副本,仅存草稿,但其任职之漳州府儒学的学生深恐该书不传,“咸云书经进呈,必须传播”,遂由该儒学之生员14人联合校订,将其刊行于世。[3]清末左宗棠重刻《正谊堂全书》时,曾发《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招聘儒生从事《正谊堂全书》的校勘工作,其中云:“近年科举频开,得举者多,谅不乏有志问学之士,其愿入局任分校之役者,各赴署报名,本月十六日取齐,定期十八日面试。”[2]对于面试通过并参与校雠工作者,“月致膏火银五两”,[2]给予了很高的物质奖励。在清代方志的校勘工作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官学或书院师生的身影。《乾隆福州府志》的参与校勘人员有教授王士鳌、附监生林玉衡和增生林擎天;《道光晋江县志》的校勘人员为晋江县廪膳生张培槚、林炜和泉州府学生陈鼎铭。
[1]朱衡.道南源委录.道南源委录后序.明嘉靖四十二年建宁大儒书院刻本.
[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长沙:岳麓书社,1987.
[3]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徐景熹修;鲁曾煜,等纂.福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福州府刻本.
[5]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
[6]李汤卿.心印绀珠经.刊心印绀珠经序.嘉靖二十一年邵武府刻本.
[7]冯继科修;朱凌纂.建阳县志.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8]王凯泰.致用堂志略.清同治十二年致用堂刻本.
[9]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转引自钱茂伟: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文史,2008.
[11]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吴棠.闽省建设书院疏.见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13]朱熹.重刊晦庵先生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序.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刻本.
[14]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见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5]游光绎.鳌峰书院志.清嘉庆十一年鳌峰书院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