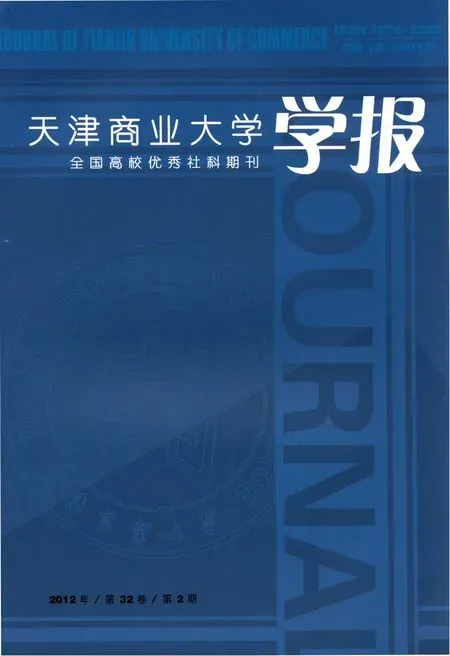经济学语境中的归纳问题
唐晓勇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都611130)
自哈奇森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一书中将证伪原则引入经济学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同证伪主义关于归纳问题的争论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归纳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难题。在逻辑实证主义似已销声匿迹、证伪主义日益衰落的今天,这场争论中凸显的矛盾、冲突仍然困扰着经济学家,传统归纳问题和“新归纳之谜”仍然是笼罩在经济学方法论之上的两片阴云。
1 传统归纳问题和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史中,曾经有两次关于归纳法和演绎法关系的著名争论,一次是18世纪初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争论,另一次是20世纪初期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论战。这两次争论的焦点可以追溯到与斯密同时的哲学家休谟提出的传统归纳问题。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将推理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之间关系的推理,即演绎推理;另一类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推理,即归纳推理。休谟认为,经验事实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不是必然联系,当一个种类中的一个事件在经验中时常伴随着另一个种类中的一个事件,心灵中就会形成一个习惯从第一类事件的观念通向第二类事件的观念。“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休谟的结论是:通常把以因果观念为基础的归纳当作具有必然联系的推理完全来自于主观印象,作为归纳结论的预测是与过去的规则性一致的那个预测,而这种规则性确立了“习惯”这一人生的伟大指南。这一结论实际上对归纳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果归纳推理的结论超出了前提断定的范围,那么,归纳结论在逻辑上可靠吗?归纳法在逻辑上合理吗?如果归纳法是扩展我们知识的主要手段,那么,我们的知识有合理根据吗?[1]
休谟的归纳问题是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挑战。如果归纳法的合理性得不到辩护,那么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科学就没有理由将从观察陈述中概括而来的理论陈述当作必然规律。为了维护归纳法在科学方法论中的地位,人们提出了各种归纳合理性辩护方案。其中,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表述的以“自然齐一性原则”为基础的论证是最著名的归纳辩护方案:“自然界中存在着平行这一类事情,过去曾经发生的,在具有足够的类似程度的条件下,将再次发生;并且不仅再次发生,而将经常随同相同的条件的出现而发生。”穆勒认为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源于自然现象之间的恒常联系,因果关系作为自然齐一性的一种形式,使我们能够从过去一事件的惯常发生推出将来该事物的发生。同自然齐一性原则一样,因果律也是普遍的、必然的经验性规律:“对于因果律来说,我们不仅不知道有任何反例,而且那些明显限制特殊规律的反例不仅不和普遍规律相冲突,反而认证普遍规律。”[2]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自然齐一性的可靠性?演绎法无法证明自然齐一性和因果律,因为作为结论的自然齐一性超过了作为前提的自然知识的范围;归纳法也无法证明自然齐一性和因果律,因为如果归纳法合理性的依据是自然齐一性,我们所作的只是无效的循环论证。穆勒否认这是循环论证,在他看来,自然齐一性和因果律的证明运用的是简单枚举法,而以自然齐一性和因果律为依据的归纳法的核心却是排除法,他称之为“实验研究的四种方法”。在《逻辑体系》一书中,穆勒实际上论述了五种排除归纳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剩余法、共变法。虽然这些方法不可能达到必然性而只能有或然性的结论,但却是探索因果关系的要点。就是在被研究现象的先行者中找出原因、从后继者中找到结果。因此,五种排除归纳法的基础就是因果关系的普遍性、恒常性、有序性,对它们的认识是科学研究中先行的、自发的归纳法的结果。
虽然穆勒不遗余力地为归纳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他并不认为归纳法在方法论意义上优于演绎法。而且,他对归纳法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强调自然齐一律是归纳法起作用的基础、了解现象的先行者或后继者是运用排除归纳五法的前提条件。正如“实验研究的四种方法”这一名称所表明的,穆勒总结的这些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活动,而不是对自然和社会研究一般方法的概括或建构。正是因为意识到经济社会现象的不可重复性,穆勒认为“自然齐一性原则”在经济学中是无效的,拒绝将归纳方法用于经济现象的分析。在穆勒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是演绎的公理系统,人性和理性行为的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基础。穆勒相信,在知道初始条件的情况下,从“相似的原因产生相似的结果”为前提,运用经济学定律可以对经济行为做出准确预测。作为经济学演绎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穆勒为古典经济学打上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烙印,他的方法论原则不仅直接影响了边际分析学派,而且被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奉为圭皋。
2 归纳问题与弗里德曼论点
将归纳法同概率论结合起来建立归纳概率逻辑的先行者是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凯恩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在抛弃了洛桑学派的物理主义之后,他针对市场体系不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缺陷,提出了借助特定的政策工具从外部使经济系统稳定化的建议。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方式。”凯恩斯学派对物理主义的线性平衡模型提出批评,转向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和经济分析的不确定性分析。
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与归纳法密切相关的认知不确定性是他的《概率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间的纽带。凯恩斯认为,演绎法的衍推关系可以扩展为归纳法的部分衍推关系,概率就是从前提到结论的部分衍推的程度,他称之为“合理信念度”。在运用无差别原则进行概率指派和比较时,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和悖论,这使得凯恩斯否定了概率赋值和比较的普遍可能性,并且将概率赋值能力当成了逻辑直觉。凯恩斯关于概率的逻辑解释是有明显缺陷的,例如,对于概率与人的认识、概率与统计规律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表述始终是含混不清的。凯恩斯试图通过承认认识的不确定性回避传统归纳问题,但对于规律性认识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的层次和产生机制缺少深透的分析,这使他的“合理信念度”和“逻辑直觉”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在凯恩斯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发展了概率的逻辑解释,并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归纳辩护的基础,他所提出的归纳确证概念引发了逻辑实证主义同证伪主义间的持续论战。
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要放弃了确定性真理目标就可以免受归纳合理性问题的困扰。在证伪主义的攻击下,他们不得不对其基本主张进行修正,从坚持“科学始于观察”转到承认“理论先于观察”,从相信经验事实能完全证实理论的真理性到放弃确定性真理目标转向较弱的确证度或归纳支持概念。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使用的“归纳支持”“确证”概念并不比“证实性”概念更容易避开归纳合理性问题。因为“归纳支持”不仅涉及证据对结论的蕴涵,也涉及已知证据对未知情况的预测,但这样的预测面临新的逻辑难题。
古德曼在休谟问题启发下构造出的“新归纳之谜”对归纳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相同的证据下,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几个预测,但没有任何先验的规则能够确定哪一个预测是恰当的,只能根据每个预测的“投射记录”归纳地评价它们的优劣。例如,从证据“这类宝石在时刻t之前是绿的”可以做出两个预测:“这类宝石在时刻t之后是绿的”和“这类宝石在时刻t之后是绿蓝的”,它们从证据得到的“归纳支持”并无差异,但却是相互冲突的。
“新归纳之谜”使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地位及证实与证伪方法之争论进一步升温,对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评价和选择理论的预测力标准:理论的建构基于对现实的抽象,评价理论的依据是能否做出成功的预测,无论这种抽象是否符合现实。弗里德曼将这个论点用于理性行为假设,在他看来,如果理性选择模型有很好的预测能力,经济行为主体是否真的是“理性人”就不重要,经济学家只需要假定经济主体“像理性人那样行动”。弗里德曼论点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除了在预测方面起作用之外,还应当具有解释性内容。也有人认为,弗里德曼论点“理论是用于预测的工具”是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混合物,是一种工具主义。
实际上,弗里德曼强调成功的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与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密切相关,他对预测问题的看法,与新实用主义者古德曼提出“新归纳之谜”的思想如出一辙。对古德曼而言,如果没有“投射记录”,“这类宝石在t之后是绿的”和“这类宝石在t之后是绿蓝的”这两个预测是同样恰当的。弗里德曼接受了古德曼的看法,认为区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济理论的标准不在于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和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功能,而在于是否具有实际的预测能力。弗里德曼以最低工资法为例解释这一看法:是否支持这一法案取决于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的预测,即关于它是否会产生大量失业的预期,而大量失业的后果与通过最低工资法保证最低收入水平是相互冲突的。在这个问题上,成功和不成功理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对失业的原因或工资的本质做出了正确的解释,而在于能否做出最低工资法后果的正确预测。弗里德曼支持理性选择模型的理由正是在于这一模型所具有的预测能力,虽然从理性选择模型的假设看,它是严重背离现实的,而从运用的角度看,这一模型有着很好的“投射记录”。
3 归纳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意义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化”的进程,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经济分析中是建构经济理论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经济学就不得不面对归纳和演绎关系这一方法论问题。如果说休谟的传统归纳问题是“科学的胜利哲学的耻辱”,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则矛头直指理论和规律的预测功能,对于科学的主要功能提出了质疑。“新归纳之谜”的重要性在于,即使是我们有能力解决休谟问题从而“证明”归纳结论的合理性,我们也无法在预测标准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区分真正的归纳预测和包含非正常谓词的假归纳预测。这样,归纳预测的可能性就失去了逻辑支持,只能诉诸于预测的实际结果。[3]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证伪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归纳问题和新归纳之谜无疑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挑战,不过,证伪主义的假说—演绎方法论也不能避开归纳问题的挑战而独善其身。实证主义重视新知识的获取,容忍归纳结论的概然性;证伪主义承认知识的可错性,同时要求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有必然性联系。前者强调知识的累积,因而推崇归纳法在科学中的作用;后者认为科学是一个猜想—反驳的非单调发展过程,因而信奉演绎在否证假说中的作用。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各执一端,要么排斥归纳要么贬低演绎,割裂了归纳和演绎的内在联系,歪曲了科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这也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都是将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对经济条件的具体观察,概括各种关系之间的变化规律,形成对经济趋势的预测;另一方面通过提出假设,理论演绎并运用观察资料检验假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菲利普斯为了找到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对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估计,提出了低失业率引致的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假设,并建立了体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4]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表明,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记住它们是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5]
[1]江天骥.归纳逻辑导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陈晓平.贝叶斯方法和科学合理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古德曼.事实、虚构和预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