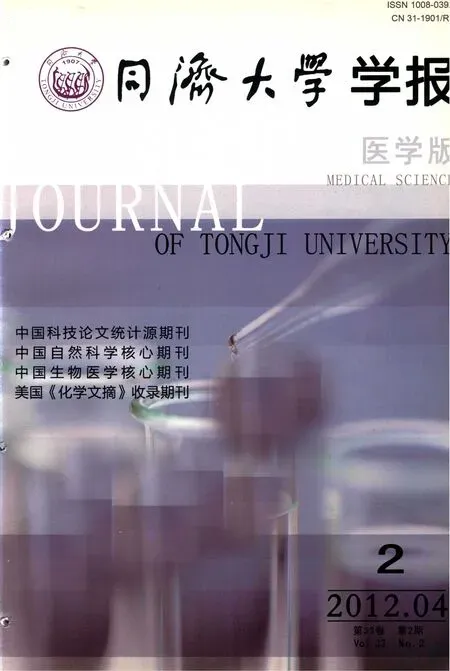从《正体类要》看石印玉教授治伤思路
石 瑛 综述,詹红生 审校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骨伤科,200021 上海)
石氏伤科是上海市著名的中医骨伤科流派。近年来,石氏伤科传人石印玉教授对骨关节疾病、腰腿痛、骨质疏松等骨伤科疾病有独特深入的研究。他非常推崇明代大医家薛己所著的《正体类要》,认为该书重视辨证施治,内容丰富生动。书中反映的学术思想和用药特点,对后世伤科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本研究从临床出发,综述石印玉教授的治伤思路。
1 整体疗伤,明辨虚实
整体疗伤的特点是《正体类要》的重要辨证思想。内经曰:“有诸内必形诸于外”。薛氏则反其道而论之,认为外在的损伤不但可以引起内在脏腑经络气血的病变,反过来脏腑功能变化,又可影响局部创伤的愈合进程。正如陆师道在序文中指出的“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1]。可见在外损的同时应认识到还有内伤的存在。例如从高处坠下,脊柱压缩性骨折的患者,往往会伴有腹胀、便秘等相应内脏的症状。中医伤科认为这不仅是外伤骨折,还伴有脏腑受损、气滞血瘀的内伤存在。这与现代医学认为创伤可引起心脏、肺、肾、脑等重要器官的功能变化,严重创伤可引起多系统、多脏器功能衰竭相一致[2]。这种强调创伤局部与脏腑相关联的病理观,是中医伤科辨证思想的一大进步,对后世内伤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石氏伤科在治疗的过程中还重视虚实的变化,正如《正体类要》中指出:“若肿不消,青不退,气血虚也”[1]。在临床上损伤后,单纯实证阶段的时间并不长,接着往往可有耗气伤血的趋向,其后病机渐渐由实挟虚,出现虚实夹杂的现象。老年人损伤后该现象更加明显,即使有实证表现,也多存在原有体质的虚弱或宿瘀的存在。因此在临诊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辨证论治,勘审虚实,或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或攻中寓补。用法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石筱山先生和石幼山先生都有治老人先理其虚,待虚损得复,始攻其瘀的经典案例,而不是按通常所说的三期治疗,先攻、继和、后补。即使是损伤积瘀,见诸肿胀疼痛瘀斑等实症,作为一个整体的“血”,一部分成“瘀”。整体自然就是“虚”,而且瘀积越重,虚亦越甚。只是在急性损伤早期,瘀积的征象为主,掩盖了虚损,待瘀去则虚象毕现。薛己也说过“余治百余人,其杖后血气不虚者,惟此一人耳”[1]。因此,三期治法中,后期是补,无虚不补,即要补必有虚。瘀既得去,虚象渐现,唯补为要,这也是全身整体观的体现。
中国逐渐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许多来中医就诊的患者都是老年患者,病种以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为主体,也有许多其它方面的疾病。相关研究曾对前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骨伤科就诊的60岁以上的患者做过一个不完全的调查,其中83.48%的患者都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其他科的疾病。其中主要是高血压、冠心病、胃病等。因此,辨证要广及全身而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伤病。治疗的方案方法也可从各科的经验中借鉴,变通化裁。因此,石印玉教授经常在临床上借用其他科室的制剂治疗骨伤疾病。例如,肝病科的补肾冲剂用于治疗肝肾亏损的退行性疾病,脾胃科的益胃颗粒用于伴有胃肠道病变的患者,中外科的小金丹活血软坚用于通络止痛等。
2 以气为主,以血为先
伤科疾病无论在脏腑、经络,或在皮肉筋骨,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气血。气血之于体内,无处不到。薛氏在《正体类要》中对损伤的认识是以气血为主,故在论治的过程中,多从气血入手。他认为:气血内伤,以气为帅,瘀阻络道则从化瘀为先。对于跌扑闪错而气滞血瘀者,多运用复元气散。方中以木香宽胸调气,青皮疏肝散滞,贝母肃肺降气,陈皮、茴香和胃畅中,并配白芷辛香通络,山甲走窜活血,漏芦疗伤调经脉,各药配合形乃复元。这就是以气为主的治疗方法。而对跌仆致伤瘀血停滞者,采用以血为先的治法,以复元活血汤主之,方中当归、桃红、山甲、大黄、花粉活血化瘀、疏通腑气,柴胡引升发之气,以舒肝经之瘀结,有直捣黄龙之功,再配合甘草缓急,共奏疏凿瘀滞,血活气行之功效。石氏伤科曾对此有评注认为,临床上的情况往往气滞血瘀并见,只是有所侧重不同,治疗原则也是如此[3]。
石印玉教授则有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内伤的治疗除此之外还因根据症状、部位的不同结合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如痛在胸,兼有咳呛、气促者,加入顺气肃肺的旋覆花、桔梗等;痛在胸胁,加疏肝胆之柴胡、郁金、玄胡、香附等;脘腹受伤,则肠胃运化失司,加入理气通腑的大腹皮、枳实、栝蒌等;少腹损伤、膀胱气化失司,加入疏肝下气的柴胡、青皮、及通利水道的车前子、通草等。总之以气血为总纲,结合全身辨证,明辨虚实,使气血运行于全身,周流不息,在外营养皮肉筋骨,在内灌溉五脏六腑。正是因为注意气血流通、全身调治的指导原则,临床上往往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3 筋骨并重,动静结合
伤科治疗的疾病中,很大部分是“筋”、“骨”方面的疾病,筋不离骨,骨不离筋,而筋骨与肉又不能分隔。所以祖国医学认为筋骨疾患与肝、脾、肾三脏最为密切相关。“肝主筋”,肝血充盈则“淫气于筋”,使筋有充分的濡养,才能“束骨而利机关”。凡损伤之证,不分所伤何经,皆以肝为主,所以薛氏在《正体类要》中提出,在疗伤青瘀时,应顾及肝脏,注意补养肝血,这样既防其克伐脾土,上犯肺金,又防止瘀血滞留,化为变证。在用药上实者祛瘀不忘调肝,调肝不忘补血;虚者补血不忘养肝,养肝谨防留瘀。方取小柴胡汤、逍遥散、当归导滞散等。可谓治肝祛瘀左右逢源,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肾主骨”、“藏精”、“生骨髓”,骨的生长、发育及至损伤以后的修复,都有赖于肾中精气的滋养。肾为先天之本,五脏阴阳,皆根于此。薛氏对素体虚弱、劳伤日久、元气亏损者,均以补益肾精为主。笔者依据此原则,对劳损而致的腰背部、四肢部劳损酸痛、动作乏力、甚或关节变形患者,采用补益肾精、气血兼顾的方法,将六味地黄汤、八味地黄汤、保元汤、龟鹿二仙汤、左归丸、右归丸等诸方化裁治之,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曾有1例陈旧性骨折患者,骨折半年后骨痂形成依旧不明显,追问病史有严重的肾精不足的临床表现,故而从益肾固精着手治疗,肾精充盈骨痂形成,久治不愈的陈旧性骨折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肝肾在骨伤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的病机与“筋”密切相关,薛己谓“筋骨作痛,肝肾之气伤也”[4]。以传统中医观来看,就是所谓的“筋出槽,骨错缝”[5]。手法是治疗“骨错缝、筋出槽”的首选方法。治疗时当先揉筋,轻轻搓摩,令其和软,将筋按捺归原处,再施以矫正关节类手法,使手法作用力深达骨关节部位,令骨缝对合,最终恢复“骨合筋舒”的正常状态。石教授认为药物与手法结合,一动一静,动静结合,往往能取得良好的疗效。目前,临床和动物试验[6-7]都证实,药物结合手法治疗膝骨关节炎有明显的疗效。
4 总 结
《正体类要》是薛己博采诸家之长,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而辑成的一本伤科专书。这本书对伤科内伤辨证治疗体系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治伤理论至今仍在伤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8]。
石印玉教授非常推崇《正体类要》,他在临床上的一些理论和用药方法都与之相关。他尤其推崇薛氏诸多著作中体现的“十三科一理贯之”的思想,认为虽寥寥数字,但意义深远,把中医内外结合的整体治疗观表述的十分清楚。外损不仅是外力对机体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影响气血、脏腑的功能,耗气伤血,虚实夹杂或由实及虚。脏腑则与肝、脾、肾的关系最为密切。临床上往往以气血为主,根据不同的症状、部位,辨明虚实,结合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9-11]。
[1]薛己.正体类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2]吴阶平,裘法祖.黄家驷外科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3]石印玉,陆品兰,石鉴玉,等.石筱山、石幼山治伤经验及验方选[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3.
[4]盛维忠.薛立斋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5]张明才,詹红生,石印玉,等.“骨错缝、筋出槽”理论梳理[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11):59-62
[6]曹月龙,郑昱新,石印玉,等.养血软坚胶囊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及安全性评价的随机对照试验[J].中国药物与临床,2004,4(6):423-427.
[7]庞坚,曹月龙,石印玉,等.软骨利胶囊对骨关节炎小鼠股四头肌收缩蛋白mRNA表达的影响[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9,13(11):2081-2085.
[8]曾清琼,韦以宗.《正体类要》对骨伤科的贡献[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1989,5(4):38-39.
[9]石印玉,石瑛,詹红生,等.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的优势与不足[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0(2):1-3.
[10]石瑛,石印玉.石印玉教授运用清热活血法治疗劳损性腰背痛病案一则[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3):11-12.
[11]石瑛,吴健康,徐震球,等.补肾活血法在骨质疏松性骨折早期运用的临床观察[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1(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