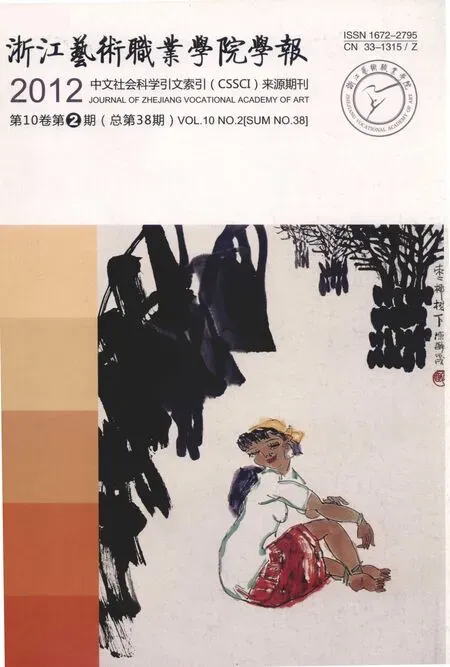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与现代悲剧意识
张 云
引 言
《金龙与蜉蝣》讲述上古时期,华夏某诸侯国境内叛乱,老王惨死,王子金龙出外狩猎,幸免于难。金龙归来,官尉牛牯将自己的盔甲卸下与金龙交换,掩护金龙出逃。金龙潜逃后在一小岛被渔女玉凤搭救,以牛牯为名与之成亲。三年后,生下一子,名为蜉蝣。金龙出走复国,二十年后,金龙重登王座,因怕牛牯抢夺王位而将其杀死。此时,蜉蝣在小岛娶玉蔷为妻并生有一子孑孓。蜉蝣为寻生父牛牯也离开小岛,误打误撞被抓进皇宫。由于惧怕报复,蜉蝣被误作牛牯之子而阉割,留作太监,八年后,金龙为生子强征玉蔷入宫,母亲玉凤携孙子也寻至宫中,夫妻、父子、爷孙……一起抵面,真相大白。《金龙与蜉蝣》是一出真正的震撼心灵的悲剧。它不再像传统中国戏剧那样的家长里短、帝王将相的因果报应,而是充满哲学与思辩色彩的黄钟大吕,金龙不知有子而日日盼子,认子后却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被自己阉割,媳妇被自己强占,处处为了祖先的基业的他却要受到先灵的谴责。这其中充满了对自己是什么、想做什么、要得到什么的思考;隐喻着对人性、对人生的更为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使得现代人被他所折服,用戏曲的魅力来感叹人生,我们几乎能从这出剧中听到麦克白的嘶吼、哈姆雷特的叹息。这出戏开启了地方戏曲都市化和传统戏曲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淮剧的发展就是和苦难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特殊的形成与发展环境,淮剧的观众群体最初被定位在最底层的百姓,淮剧演出的大多是观众所爱看的“哭”戏。“妻离子散”、“万里寻亲”都是淮剧最擅长表现的。所以淮剧的表演以“悲”见长,甚至把观众哭的程度作为评价演员的标尺。在传统的剧院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老观众会带着手帕进场,在看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片段时惯性地流下眼泪。所以,一提到淮剧,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苦戏。因此,也有些观众认为:《金龙与蜉蝣》在故事情节上是很“淮化”的,在上述那些让观众喜欢的“悲剧因子”在《金龙与蜉蝣》中一一体现出来,“金龙的亡国、玉凤与金龙的分离、蜉蝣的寻亲、玉凤的盼子”等等都能找到“老淮调”的影子。看《金龙与蜉蝣》时会让观众像看传统“苦戏”一样落泪;其实并不尽然,《金龙与蜉蝣》是体现着强烈现代悲剧意识而并非对传统苦戏之苦难情节简单因袭的淮剧作品。
一、苦戏和悲剧的区别
剧作家罗怀臻直接阐述了苦戏和悲剧的区别:“可以避免的不幸是偶然的不幸,不可避免的不幸是必然的不幸,苦戏与悲剧的区别正在于此。苦戏是由于道德的原因,利益的关系,可以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而悲剧的成因是观念、是社会、是历史、是宿命,无法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苦戏作用于人的感官,让你在现场流泪,观众居高临下地悲悯和同情剧中承受苦难的人。从这个定义来看,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大都可以认作苦戏。而西方的悲剧意识与我们不同,它的最高任务不是怜悯,不是同情,更不是廉价的泪水和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静穆、崇高,是让你在静穆与崇高的感受中灵魂得到净化,得到升华……”[1]我们可以看到淮剧传统剧目《秦香莲》就是一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苦戏。在《秦香莲》一剧中,由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使得陈世美丧失道德底线、从而抛妻弃子迎娶公主。秦香莲千里寻夫上京城,陈世美不但不接受宰相规劝,与家人相认团聚,并且为了摆脱这个威胁到他实际利益的麻烦,不惜以身试法,指使韩琪杀妻灭子。秦香莲的悲苦命运让观众同情,而陈世美的自私和残忍令观众感到愤慨。对秦香莲母子命运的同情更大程度上转化为对陈世美的愤慨和指责。所以,这出悲剧是可以追溯到具体的责任人的,如果没有陈世美因为利益的、道德的原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也就没有了观众对秦香莲母子悲苦命运的同情与怜悯。
我们再来看《金龙与蜉蝣》。这部悲剧作品是一部借鉴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精神和体裁、风格、手法的作品。古希腊悲剧精神中的命运的必然被该剧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这部作品中,命运的必然可以理解为:“是根源于我国古代宗法家长制的人性的异化。它在金龙、蜉蝣等剧中人物的心目中,当然是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命运。由宗法家长制所产生的家天下、王权至上,王位世袭,乃至其后派生的嫔妃制度、宦官制度等等,从人性的角度看,实际上都是人性异化的种种体现。只是这些人性异化的现象,在戏剧舞台上往往隐没在道德评判、历史评判的后面,不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借鉴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精神及其体裁、风格、手法就成为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了……”[2]
该剧的悲剧性是一个无责任人的不幸,是剧中人物命运的悲剧,父与子每人都在承担着并且推动着悲剧的发生。他们并不自知人性的一步步异化,是时代、历史和环境造成了对剧中人物人性的异化,他们在同命运抗争,然后命运却无情地把他们推向无底的深渊,无法解脱、无法救赎。“一位帝王需要延传他的血统,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至高无上的,因而他为此所做的一切就既合情又合理,可是他不幸走向了自己意志的反面,误阉了唯一的传人蜉蝣,于是一切合理都被推翻、被粉碎。这也是把绝对的家族血统置于族群的普遍生存权利之上所导致的必然的悲剧性结局,是一条不归之路。因此,悲剧就不仅仅是对剧中人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追究,更是对人权与人性的审美拷问。”[1]91
二、悲剧性的现代性
悲剧总是与人类的生存论问题紧紧相应。悲剧与现代人的自我生存领会,这正是悲剧的现代课题。也正因如此,现代悲剧承接着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而现代人更担负着把握悲剧传统,超越悲剧传统的责任。悲剧情感和悲剧直观是与一种文明的精神本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文明也是悲剧诞生的土壤。正是因为古希腊文明,悲剧才成为哲学、艺术和社会生活中一个常见的主题。而叔本华提出悲剧主义哲学观,认为悲剧的根源是原罪(生存本身的罪过),所以悲剧人物通过实际的人生苦难而摆脱求生意志。朱光潜先生认为“叔本华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真理”[3]。他对悲剧苦难的强调是天才的。他认为最好的悲剧是:“清清醒醒地睁着眼睛互相残害,却没有哪一个人完全不对。”[3]121以这个观点审视悲剧作品,更能发掘作品的现代悲剧性。这是对无责任人的不幸的一种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荆轲是一个悲剧。悲剧英雄荆轲并不具有西方“悲剧”式的效果,它并没有矛盾的发展和悬念,也不是在震撼人心的大毁灭中产生悲剧感。荆轲的悲剧是在易水河畔就完成了的:知道自己一去便不能再生还,知道自己必定在行动中毁灭,并且知道自己即使成功也不具有什么意义。荆轲的悲剧情感在萧萧的易水河畔就已经达到了高潮,对自己命运的悲怆理解和对命运奋力抗争的壮志情怀在易水河畔就完成了。相应地,秦廷上的流血只是一个情节结构的发展,而不是悲剧性本身的发展。那个情节高潮并不是悲剧情感的高潮。在希腊“悲剧”中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荆轲的悲剧中它们被有效地分开了。在鲁迅小说《药》中,悲剧英雄与其说是“悲剧”主人公夏瑜,不如说是他的救国精神。为了同胞的解放和振兴,夏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的奋斗的价值和意义被他为之献出生命的对象所否定:他们不但喝下了他的血,还把他的精神视作疯狂加以嘲弄。悲剧主人公夏瑜的全部奋斗和奋斗的全部意义被他为之奋斗的人们所否定。荆轲与夏瑜的悲剧是有别于古希腊悲剧中悲剧精神的,是对“悲剧”中的悲剧精神的外延,更契合现代人类社会的悲剧意识。
二、悲剧情感和悲剧冲突
悲剧情感产生于对世界的内在旋律的体验。在希腊文明和它的继承者——西方文明中,悲剧以一种戏剧形式“悲剧”(以下用引号表示作为戏剧的“悲剧”)集中地、凝缩地表现出来,使悲剧情感实现为表现品,但也使对悲剧的理解有了附加的成分。最著名同时也最纯粹的希腊“悲剧”英雄俄狄浦斯就是这样一个悲剧形象。这部悲剧主要表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与残酷的命运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认为:“戏剧所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神秘力量或者自然力量之间的斗争。”[4]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杀父娶母,于是他竭力想要逃脱这不幸的命运,但终于杀父娶母,陷入了冷酷命运的罗网。在剧本中,命运像一个巨大的魔影笼罩着俄狄浦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但是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表现命运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他着力表现的是俄狄浦斯和命运作斗争的行动。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这即是此剧的积极意义所在。
俄狄浦斯是个坚强勇敢的英雄,他凭借自己的才智破了人面狮身怪物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了危难中的忒拜城。他被拥立为国王后,又努力做一个正直贤明的君王,他爱护人民、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使城邦免于灾祸,他认真追查杀人凶手,即使追查的结果于他不利,他也要追查到底。俄狄浦斯从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将要杀父娶母的可怕预言后,便竭力想要逃脱这种厄运。他从神庙出来后,连家都不回了,马上远离他的父母,以此来摆脱命运的安排。然而可悲的是,他越是积极抵抗这可怕的命运,就越深陷入命运的罗网;他越是真诚地消除灾难,就越步步临近最终的毁灭。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了杀父娶母的过失——他终于没能在和命运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但是,《俄狄浦斯王》的主旨并不在于表现人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必然失败的痛苦和绝望,它想表现的人是有着坚强的意志的,他可能会被强大的外在势力打败,但精神却是永不屈服的。和古希腊其他悲剧一样,《俄狄浦斯王》着意于严肃,而不着意于悲惨。“如我们看曹禺的悲剧,看古希腊或者莎士比亚的悲剧,你都会产生一种崇高感、静穆感,是在仰视着剧中人的受难而无能为力。这种感受,使你离开剧场许久以后都不能释怀,它也有可能让你在一夜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认识,比如对某种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日常道理或现象忽然有了一种‘顿悟’的明了。这就是悲剧的力量。”[1]90它赋予人们的心理感受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更多的是悲壮和崇高之感。俄狄浦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是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地和命运抗争,抗拒命运为他安排的杀父娶母的厄运。当城邦遭受瘟疫时,他认真地查明事实的真相。他查寻杀人凶手的过程也是探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从第一步开始,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个结果可能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其实随时都可以宣布停止调查,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而是一步步地走向了那个最可怕的答案。他几乎是心惊肉跳地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于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贤明的君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罪犯。他在拯救了这个城邦的同时也走向了最终的毁灭。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俄狄浦斯没有丝毫的怯懦。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因为杀父娶母的行为都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做的,但他认为后果应由他来负担。他刺瞎了双眼,请求放逐。这种对自己的惩罚,无疑是非常严厉的。俄狄浦斯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他用血的代价换取了人格的独立,在痛苦的洗礼中,灵魂得到了升华。剧作家通过描写俄狄浦斯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冲突,塑造出了他理想中的人的形象:敢于和命运做斗争,敢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5]。赞扬俄狄浦斯的勇敢、慨叹他的无辜,可是最终无法逃脱“命运的必然”。这样的对比使得悲剧审美中的“同情”与“怜悯”的情感效果释放得更为纯粹更为彻底。俄狄浦斯的悲剧源自抗争命运的最终结果,是走向不可逆转的毁灭。他在奋力抗争命运、奋力创造自我之中将自己击得粉碎。他的甚至英雄的行为使得他完成了命运对他的安排。他自己的悲剧是由他自己的本质力量造成的。正如金龙和蜉蝣一样,他们的悲剧命运是由他们自己的本质力量造成。只不过他们不是为了避免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生存价值,这较之古希腊悲剧的悲剧英雄同命运抗争却一步一步走入命运的罗网一样,是具有净化心灵的震撼力的。
黑格尔认为:“戏剧诗是以目的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这种斗争的必然解决为中心。”[6]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麦克白》通过对麦克白性格中善与恶的斗争的表现,探讨了麦克白是怎样从一个英雄变成了罪人、怎样走向毁灭的过程。在该剧中,我们看出冲突的双方就是作为目的的“权欲和野心”与作为麦克白原本的“英雄”个性。个人野心使麦克白这样一个忠臣、有作为的将领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的。麦克白,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巨人”的苏格兰大将,最终被权欲和野心毁灭。权欲和野心,毁灭了人性,毁灭了很多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吞噬了麦克白天性中的好的东西。麦克白最后的堕落也就是美德的毁灭,恶的胜利,这是一场恶战胜善的悲剧,一场真正的悲剧。
我们再来看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莱特》中的悲剧冲突。一句话概括其主旨,是通过哈姆莱特的形象反映现实社会与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激烈矛盾。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是悲剧的基本冲突,这是进步的势力与落后、反动的势力的较量。莎士比亚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理想,都倾注在哈姆莱特的形象之中。哈姆莱特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他热情地赞美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理智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却屡屡遭到打击。被害的老哈姆莱特品德高尚,治国有方,是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君王,也是哈姆莱特心目中最完美的“人”。父亲的暴死和母亲的随即改嫁,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的理想开始破灭。叔父克劳狄斯的阴险奸诈又使得哈姆莱特在实现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时困难重重。他义愤填膺地指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世界是一所监狱,而丹麦是其中“最坏的囚室”。这一悲剧冲突的发展,充分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和英国在新旧交替时期的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悲剧中,哈姆莱特的内在冲突和外在冲突交织在一起,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
希腊和西方对悲剧结构和悲剧体验的分析是一种把它与戏剧结构和戏剧体验等同看待的。它们以“悲剧”代替了悲剧,把所有戏剧都具有的共同成分作为悲剧的要素。例如,它们把希腊式戏剧的结构、矛盾的发生、发展和高潮作为悲剧的结构;把戏剧高潮的一些心理因素当成了悲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的“悲剧”是从如何获得怜悯与恐惧的效果出发,来讨论情节该如何安排,是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还是顺境转入逆境之类的技巧完美的“悲剧”。虽然说《金龙与蜉蝣》也通过“突转”与“发现”这两个情节来获得完美的戏剧效果,但是《金龙与蜉蝣》一剧同时也蕴涵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悲剧情感。“悲剧中的怜悯绝不仅仅是‘同情的眼泪’或者多愁善感的妇人气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3]69金龙和蜉蝣面对的悲剧,同是生存的苦难,为了完成生存本身的意义:比如金龙,他生存的意义是复仇复国,于是他抛妻别雏;而蜉蝣生存的意义是寻找父亲,于是他也离母抛妻别雏。历史是一个轮回,惊人的相似,父子二人肩负着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的使命,如果不完成对使命的追求,父子二人将丧失立身为人的全部意义,所以他们追寻的脚步执着而坚毅,正是这种执着与坚毅让他们无可避免地铸成了生命的悲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悲剧中所体验到的情感不应该是简单的悲哀和壮烈,而是情感随着自我创造中达到自我否定这一结构而形成的自我矛盾的情结,是主体内部结构的自相冲突,是对悲剧结构的理解和体验。悲剧是一种群体体验,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体验,因此横跨国界而通贯古今。有时,人们愿意在剧场里通过审美触因来激发和完成这种体验,这就是戏剧观念范畴的“悲剧”。戏剧观念范畴的“悲剧”是悲剧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悲剧产生激情和自省。悲剧的激情和悲剧的自省是相互交糅的,最终是对人类生存本身的接受和体认,一种无法接受后的最终接受和难以体认后的深刻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悲剧也就是在至深层次上研究人类。研究人类就必须有现实关怀,于是才有了对悲剧意识的现代理解,这一点,《金龙与蜉蝣》做到了,它将“悲剧”技巧与悲剧自省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结 语
“文学意识弱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代意识与现代题材被混为一谈,经常用现代题材,现代剧场,掩饰其现代意识的缺失,现代意识不是西方意识,而是人类文明、中国文化积累到当下,人们运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人生,看待人的生理、看待人的情感、看待历史。题材的远近无关于作品意蕴开掘的深浅。有人以为越是现代题材越是有时代感,其实未必。”[7]《金龙与蜉蝣》这部戏中,它不仅在体裁、风格和精神上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精神,同时立足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土壤,自觉地寻找和表现现代悲剧意识。“悲剧作用于观众的不独是感官的刺激和煽情,它更重视作用观众的心灵和理智,重视唤醒观众的同步思索,让观众仰视剧中人,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1]79
《金龙与蜉蝣》虽然是一部古代题材的作品,但是全剧满溢着现代意识,以现代悲剧意识来阐释人文关怀,甚至可以说他以对人性和历史冷静的分析探讨,开启了古代题材戏剧糅入现代悲剧意识之先河,给中国戏剧创作以深远的启示力量。
[1]罗怀臻.罗怀臻戏剧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79.
[2]沈达人.《金龙与蜉蝣》的人文意义[G]//沈达人.戏曲的美学品格.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362.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23.
[4]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80.
[5]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3.
[6]黑格尔.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3.
[7]罗怀臻.中国戏曲在当代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