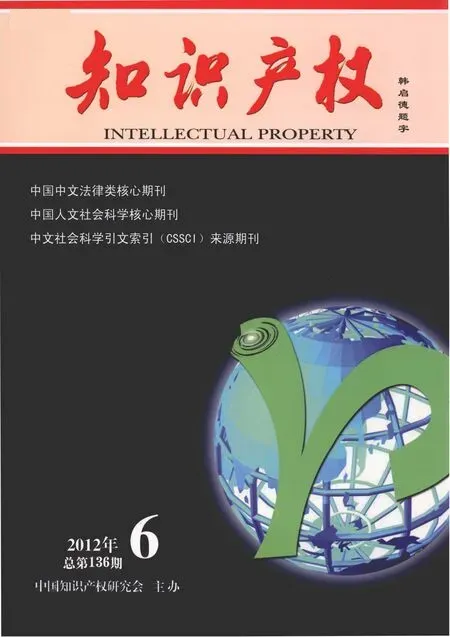“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法律论争的若干问题
王翠平 于立彪 曹正建
“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法律论争的若干问题
王翠平 于立彪 曹正建
《专利法》第33条规定了“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但如何理解和适用该原则,专利审查部门与实务界在此原则上存在分歧与争论。例如,关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之争;关于如何理解“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之争;关于修改原则与修改方式、修改时机之争;关于修改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关系之争等。从专利法的原理体系出发,针对上述法律论争做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业内全面探讨“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
《专利法》第33条 “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
目前的审查实践中,凡是遇到修改,审查员通常以“修改超范围”来反对。在上述杯子的方案中,假如说明书“一口气”写出了包含各种新技术、新材料的杯子,而不是分层次给出各个具体实施例,对于申请日以后提出修改的权利要求,例如申请人发现申请日前的现有技术中,还不曾有保温杯或磁化杯出现,更不用说说明书中所公开的更复杂的杯子了,但改写成保温杯或磁化杯的权利要求,常常被认为是“超范围”。
上述两种观点中,“形式缺陷论”对修改的理解有些机械。如果修改仅限于形式表达,那么又有何必要进行修改呢?换句话说,改与不改,没有本质差别。这样的修改“权利”实质上名存实亡。而对于“调整保护范围论”,反对者以“超范围”为由来反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就《专利法》第33条的理解与适用先后做出三份裁定,其中的“墨盒案”④即:关于“氨氯地平、厄贝沙坦复方制剂”的03150996.7号发明专利无效请求案的(2011)知行字第17号行政裁定书;关于“一种既可外用又可内服的矿物类中药”的第00113917.7号发明专利申请案的(2011)知行字第54号行政裁定书;关于“申请再审人郑亚俐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专利无效行政诉讼案”案最高法院(2010)知行字第53号裁定书。,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鉴于以申请日区分现有技术的规定的存在,专利申请人不能在确定申请日之后再将申请文件所载明的技术方案内容作出变化。”这实际上是假设了“技术内容作出变化就一定超范围”的前提。如果能证明这一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则可以证明“调整保护范围论”是体现《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的。
实务上,要求申请人一次性写出保护范围适当的权利要求,是不符合专利法原理的过分要求,这实际上涉及说明书与权利要求书之间的关系与分工。专利法原理对说明书的要求是“充分公开”到能够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来实现、满足这一要求的说明书,其撰写的正确性就是无可厚非的。而权利要求的作用是基于说明书的充分公开来界定保护范围,也即权利要求书要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因此,能够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权利要求,就是合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充分公开”的说明书支持的权利要求撰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是符合专利法要求的。故不管权利要求写成什么样子,只要是得到说明书支持并满足一定形式上要求的,都是《专利法》第33条赋予申请人的正当权利。在上述的杯子中,假设说明书给出的是最全面最复杂的实施例,就难以否认其包含了更多的简单实施例,体现多个较为简单技术方案的“集合”。申请人在提出申请后,根据其对现有技术的进一步掌握和判断,发现可以体现出多个稍简单些的技术方案,故通过修改权利要求重新调整保护范围,将原先“集合”的技术方案调整为“分立”的多个技术方案,这也是“技术内容的变化”。可见,“调整保护范围论”的本质是“权利说”,而“形式缺陷论”在表面上也允许申请人修改,但本质上却是“限制说”,即将修改限制在一些表面上的缺陷上。
二、如何理解“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争论
《专利法》第33条中“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的表述,正是“修改不得超范围”名称的由来。何谓“记载的范围”?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⑤见《专利审查指南》第2部分第8章5.2.1.1,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243页。,所谓“记载的范围”,是指“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和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⑥见注④的最高法院(2010)知行字第53号行政裁定书,第31页。:“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以文字或者图形等明确表达的内容;二是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综合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可以直接、明确推导出的内容。只要所推导出的内容对于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就可认定该内容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比较两种观点可以看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可“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以文字或者图形等明确表达的内容”属于“记载的内容”;而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根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才属于“记载的内容”,而后者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综合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可以直接、明确推导出的内容”也属于“记载的内容”。一个说法是“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一个说法是“直接、明确推导出”,两者之间的分歧很大。
上述两种观点,本文分别简称其为“确定论”和“导出论”。无论是“确定论”还是“导出论”,都认为其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墨盒案”中给出的说理是:“基于前述立法目的,对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该从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角度出发,以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公开的技术内容来确定。凡是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已经披露的技术内容,都应理解为属于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既要防止对记载的范围作过宽解释,乃至涵盖了申请人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未公开的技术内容,又要防止对记载的范围作过窄解释,对申请人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已披露的技术内容置之不顾。”
有文章⑦宋献涛、刘国伟:《关于专利文件修改超范围的法律思考》,http://allenemy.fyfz.cn/art/824943.htm。针对“记载的范围”,从立法解释的视角做了探讨。在1992年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其第43条第1款规定:“依照本细则第42条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日,享有优先权的,可以保留优先权日,但是不得超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 请注意,细则的表述是“不得超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而没有用“记载的范围”。与之配套的《审查指南(1993)》第2部分第6章中的3.2之(5)也重申了“修改不得超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
可见,在当时,认为“记载的范围”就是“公开的范围”,也就是说,与《专利法》第59条所规定的“保护范围”是一个性质的。其共同的关键词都是“范围”。但从“确定论”和“导出论”的论争看,“确定论”将重点放在了“记载”的解释上了,而“导出论”着眼于“范围”的大小上的解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个案中提出了“导出论”,但可以预见,“确定论”仍明确地写在了《专利审查指南》中,因此在实务上,“导出论”是否能替代“确定论”,尚需时日观察。
三、修改原则与修改时机、修改方式之争
作为一项总原则,对专利文件的任何修改,都应满足《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但在具体的修改原则上,针对专利申请和授权后的专利,还是有所区分的。
首先,在申请过程中,为使申请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可能会进行多次。理论上,对于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任何修改,似乎都应接受。但考虑到行政程序的效率,可对修改的时机或次数做适当限制。从修改的动机看,可分为主动修改与被动修改。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1条的规定,所谓主动修改,是指:申请人仅在下述两种情形下可对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主动修改:一是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二是在收到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的三个月内。所谓被动修改,是指为了克服审查意见中所指出的缺陷所做的修改。
其次,《专利审查指南》特别规定,在有些情况下,即使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不能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不予接受。更进一步地,即使修改的内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只要修改导致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扩大,也不予接受。因此,业内的争议主要在被动修改的规定上。
审查指南是从节约审查程序的角度规定了被动修改的限制。但业内对于何谓“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还是有不同解读。例如,由于审查意见认为原独立权利要求没有新颖性或创造性,申请人增加了在原权利要求书未出现的新独立权利要求,假设新独立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是否视为是“针对通知书所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对于《专利审查指南》明确规定的不得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业内的质疑理由是,这种做法与节约审查程序的初衷并不矛盾,为什么不予接受?这样的规定是否有超越《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之嫌。如果认为该条的立法目的以前述“权利说”为准,则有必要在今后的指南修改中予以考虑。
业界认为,在审查程序中,对于“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但修改导致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扩大”不予接受的做法,与专利授权后的修改原则也不协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68条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对于授权后的专利,其修改即使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也不允许扩大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这样的规定合理性在于,要保证授权专利保护范围的法律稳定性,不得损害公众对该权利要求的期待利益。举重明轻,在申请阶段,也如此严苛规定值得商榷,应根据具体情况,不能一律不接受新的权利要求或者扩大原请求保护的范围的权利要求。
此外,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关于《专利审查指南》规定的“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三种修改方式与修改原则的关系,通过“氨氯地平、厄贝沙坦复方制剂”的03150996.7号发明专利无效案⑧见注④中的最高法院(2011)知行字第17号行政裁定书。,也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该申请要求保护由两种活性成分(氨氯地平与厄贝沙坦)组成的复方制剂。原申请中,两种成分的重量比为氨氯地平:厄贝沙坦=1:10-50。实审中,申请人将上述比例修改为1:10-30。无效宣告程序中,为了应对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专利权人将上述比例修改为1:30。合议组认为其修改不属于审查指南规定的三种方式之一而对上述修改不予接受。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所述修改方式是允许的。首先,尽管原权利要求中1:10-30的技术方案不属于典型的并列技术方案,但鉴于1:30这一具体比值在原说明书中有明确记载,且是其推荐的最佳剂量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原说明书后会得出本专利包含1:30的技术方案这一结论,且本专利权利要求仅有该一个变量,此种修改使本专利保护范围更加明确,不会造成其他诸如有若干变量的情况下修改可能造成的保护范围模糊不清等不利后果,允许其进行修改更加公平。其次,《专利法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对无效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进行限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维护专利保护范围的稳定性,保证专利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另一方面在于防止专利权人通过事后修改的方式把申请日时尚未发现、至少从说明书中无法体现的技术方案纳入到本专利的权利要求中,从而为在后发明抢占一个在先的申请日。本案中显然不存在上述情况,1:30的比值是专利权人在原说明书中明确推荐的最佳剂量比,将权利要求修改为1:30既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更未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不属于相关法律对于修改进行限制所考虑的要避免的情况。再者,如果按照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观点,仅以不符合修改方式的要求而不允许此种修改,使得在本案中对修改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缺乏合理性。况且,《专利审查指南》规定在满足修改原则的前提下,修改方式一般情况下限于前述三种,并未绝对排除其他修改方式。
此案涉及修改原则与修改方式的关系,业界的质疑是:如果局限于审查指南规定的三种修改方式,则实际上是将修改方式上升为修改原则。或者说,满足修改原则下的任何修改方式,都应该被接受的话,那么,只要坚持修改原则就足够了。尽管审查指南中,规定了“一般限于”三种修改方式,但在实务中,被理解为“仅仅限于”三种修改方式。
四、修改与“禁止反悔”原则之争
禁止反悔原则(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与“等同原则”一样,属于法官造法的一个原则⑨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中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第247页。。禁止反悔原则是指,申请人在专利审查阶段,为了获取授权,对权利要求所做出了某种限制或让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的适用将这些限制或让步又重新“拾”⑩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用“recapture”一词来表示“重新拾起”的意思。回来,这样使得专利权人“两头得利”。最高人民法院也持相同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⑪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1日发布的法释〔2009〕21 号司法解释,此解释是目前关于专利侵权诉讼的最全面的司法解释。第6条中规定:“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通过对权利要求、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又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禁止反悔原则与“等同原则”如影相随,被业内公认为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发生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或者让步”的事实显然是在专利审批程序或确权程序中,而通过等同原则的适用将先前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或者让步”重新拾回则出现在专利侵权判定的过程中。而专利审批程序或确权程序与专利侵权程序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程序,两个程序需要“相互照应”,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专利权人“两头得利”的情况发生。
可见,禁止反悔原则通常是伴随着等同原则的适用而考虑的,其本身没有独立适用的价值。但实务中,仍有观点主张在判断修改是否超范围时,可以引入禁止反悔原则。有文章⑫崔峥、张鹏:《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立法本意与法律适用再探析》,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4期。认为,是以先申请原则和禁止反悔原则为逻辑基础的,……,结合修改时机和修改内容的判断,针对调整性修改,需要结合原始申请文件所体现的专利申请人的意思表示以及专利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书等方面体现出的意思表示,确定修改内容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反悔。
上述关于对修改的审查要引入禁止反悔原则的观点体现在“墨盒案”中。该案中,专利复审委员会称,精工爱普生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际上认为“半导体存储装置”和“存储装置”二者含义不同,而在无效程序中又主张两者含义相同,修改的过程反映出反悔的存在,应当认为将“半导体存储装置”修改为“存储装置”属于反悔,应予禁止。
作为回应,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禁止反悔原则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的适用并非是无条件的,其要受到自身适用条件的限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原则或者法律规定的限制。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应以行为人出尔反尔的行为损害第三人对其行为的信赖和预期为必要条件。同时,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其他同等重要的原则也限制着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专利授权程序中,相关法律已经赋予了申请人修改专利申请文件的权利,只要这种修改不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即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基于《专利法》第33条规定,其应该预见到申请人可能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其信赖的内容应该是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即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以文字或者图形等明确表达的内容和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综合原说明书及其附图和权利要求书可以直接、明确推导出的内容,而不是仅信赖原权利要求书记载的保护范围。因此,如果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禁止反悔原则在该修改范围内应无适用余地。
结 语
关于专利法“修改不得超范围”的法律适用之争,争议在于如何理解《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而对立法目的的理解与适用,应综合运用专利法基本原理来解读。从说明书与权利要求之间的关系与作用入手,是一个值得推崇的研究视角。在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基础上,任何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权利要求,都可以认为是满足《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在满足原说明书支持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存在着若干个符合《专利法》第33条规定的可能的技术方案,申请人在合适的修改时机下,有权决定其请求保护的范围。然而对于当前仍存在的种种分歧与争论,仍会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着,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因此,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仍应继续保持下去。
Article 33 of Patent Law gives the principle of “amendments shall not go beyond original scope.” However, Examination Department and Practical Circle diverge greatly on how to correctly comprehend and properly apply this principle. Especially, the diverges are abou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Article 3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the manner and opportunity for amendment and the relation of amendment with“estoppel” principle and so 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above diverges, and desires that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mendments shall not go beyond original scope” should be studied in an all-round manner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and system of the Patent Law.
article 33 of Patent Law; “amendments shall not go beyond original scope” principle;“estoppel” principle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修改等多种情况。这种观点可称为“调整保护范围论”。例如,一项关于杯子的发明,说明书给出的技术方案涉及多种新技术新材料的利用,包括保温材料、加热元件、磁化原件、中空结构等。但如何撰写出保护范围适当的权利要求书,在“先申请制”下,申请人为抢先提出申请,无暇仔细撰写权利要求,此时,如果说明书给出的技术方案满足专利法规定的“充分公开”,又不存在“用词不够严谨表达不够准确等缺陷”,就难以用修改是为了克服“形式缺陷”来解释。
一、《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之争
王翠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审查员
于立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审查员
曹正建,北京信慧永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人
《专利法》第33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业内称之为“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①我国自1984年3月12日开始实施专利制度以来,专利法经历了三次修改,即1992年、2000年和2008年的修改。但《专利法》第33条的几乎没有做实质修改,只是在个别措辞上的调整。。根据《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修改申请文件,但修改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专利申请文件递交后,申请人为什么要修改?专利法为什么也允许修改?这其实是专利法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折射出对《专利法》原理的不同理解。关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如《新专利法详解》一书认为②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著:《新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28页。:“之所以规定可以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是因为在撰写申请文件过程中,难免存在用词不够严谨、表达不够准确等缺陷,对这类缺陷如果不加以修改,就可能影响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切性,影响公众对专利信息的利用……”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形式缺陷论”③另有关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的见解认为:“设立《专利法》第33条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防止申请人以未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并在申请日以后通过修改专利申请文件来完成发明创造,从而获得不正当的利益;第二是防止申请人不重视申请文件的撰写,使得公众不能清楚准确地理解发明。众所周知,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应当为在申请日之前已经完成的发明创造;一项发明尚未完成就申请专利,要求较早的申请日来获得专利保护,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不利于鼓励真正的发明创造 。” 见崔峥、张鹏:《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立法本意与法律适用再探析》,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4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并非仅限于上述的“形式缺陷”,还应包括涉及保护范围的重新界定或随着现有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