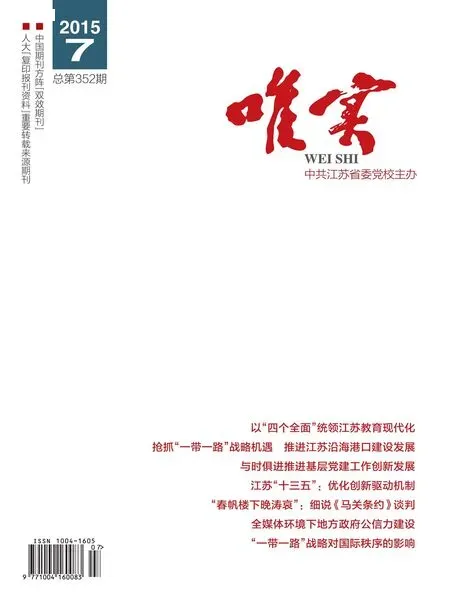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权浅析
王建富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权浅析
王建富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在当前高校管理纠纷解决模式不足的情形下,参与权由此兴起。民主、正义、平衡是高校学生参与权的理论基础。高校学生参与权不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参与权,而是发源于受教育权;学生参与权在实践中表现为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权、高校具体事项管理参与权和处分参与权三项内容。
高校管理;纠纷解决;学生参与权
一、参与权的兴起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成倍增长,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但学生管理模式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伴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学校权力和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诉讼案件时有发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1.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
我国已经有相对完备的高等教育基本法律体系,规定了现行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中申诉(校内和教育行政机关申诉)、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三种救济途径:
一是申诉。《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这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学生申诉的权利。教育部2005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条、62条、63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了申诉的两个具体步骤:一是学生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二是学生对于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复查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二是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学生可以对于申诉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处理提起行政复议。如果该机关对学生的申诉没有及时处理,则存在行政不作为的嫌疑,该行为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没有履行保护受教育权的法定职责”,学生可以申请复议。
三是诉讼。《教育法》第42条:“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对于学校处分、教育行政机关对申诉的处理、教育行政机关复议不服的都可以提起诉讼。
2.当前纠纷解决机制评析
这三种解决纠纷途径似乎已经涵盖我国现有的所有可能的救济手段,整个救济体系看似齐备。但从法律规定分析,这几种救济方式重叠和层次不明确,规定不清。从实际效果来看,救济不能和效率低下始终存在。
第一,申诉与行政复议定位不清。首先,在申诉范围上,现行规定中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只受理学校对于学生作出的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而对学校的其他决定是否可以进行申诉,法律的规定并不清楚,保护的程度还很有限;其次,对于申诉和行政复议的适用顺序没有明确,进一步缩小了学生权利救济的范围;最后,申诉制度的法律性质如何,申诉的主体资格、申述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如何,在法律中没有规定。而申诉和复议都集中在教育行政机关,设计申诉和复议并存的两套程序存在着重复。
第二,实际效果有限。首先,很多高校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校内申诉制度,自然无法给学生提供救济。而且在学校作为行政主导的前提下,这种内部纠正机制的“中立性”不明显,难以做到保障学生权益;其次,按照《行政复议法》对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规定,可以申请复议的事项是“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履行保护受教育权,而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的”。因此,只有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学生的申诉不予处理,学生才可以继续申请复议,这样就无形中限制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最后就诉讼而言,自“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后,我国司法机已经逐渐开启对于学校的诉讼之门,但随着司法介入的深化,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学校的主体定位模糊不清,这导致诉讼的界限难以把握。从司法实践看,目前法院受理的案件多跟学位的颁发有关,而纪律处分、课程评分等问题是否可以诉讼,法院司法审查和大学自主权界限如何认定,学生遭受的损害是否可以得到赔偿等诸多实际问题困扰法院,使法院不得不选择“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驳回诉讼请求”的回避之策。这种“司法不能”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对学生的“救济不能”。
3.参与权的提出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以事后救济为主,这种事后救济不但存在着救济范围有限、救济不能的问题,而且由于事后救济的消极性、被动性,决定了学生只有在其权利受到实质侵害的情况下才能寻求这种救济。基于此,从高校管理现状入手,寻找一种有效的事前防范和化解纠纷之道也就成了高校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方向。2005年教育部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1条指出:“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该规定不仅明确赋予了大学生对高校管理的参与权,而且也对高等学校设定了支持、帮助和保障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义务。在高等学校管理过程中,引入并发动教师、学生及相关主体的广泛参与,既符合大学自治的基本理念,也有助于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因此,学界也开始了对高校学生参与权的理论探讨,并对学生参与权的内涵、价值、实现路径和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层探讨。
二、参与权的基础论
高校学生参与权,指高校学生作为学校的成员依法享有通过一定方式对学校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决策的权利。[1]参与权具有多种涵义,在宪法意义上,公民的参与权也可称之为参政权。所谓参政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权行使的权利,公民的参与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它应当且已经被物化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与制度,表现在立法领域、行政领域、司法领域等,[2]体现在教育行政领域,即教育领域的行政参与权。
我国学者研究高校学生的参与权也基于这种逻辑分析。如认为大学生作为一特殊群体,其政治参与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研究与探讨高校学生的政治参与,应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参与自我服务”这一基本议题之上。[3]此种观点认为学生高校参与权属于政治参与的表现。也有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本质上为行政法律关系,因而学生参与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参与权。[4]
不可否认,教育领域确实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例如通说理论认为《教育法》第28条规定可以成为高校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律根据,高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该规定虽未明确区分“权力”、“权利”的性质,但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都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因而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力,学校属于授权性的行政主体。但是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却不可一概论之。有民事法律关系说、行政法律关系说、内部管理关系说、多重法律关系说、高校决定论等多种学说。但不论民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都不足以概括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因此,将参与权局限于行政领域参与权研究,相对狭窄,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益。
高校学生参与权不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参与权,而是发源于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除了具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稳定的固有特性之外,还在于它具有繁衍其它权利的“母体性”,它可以派生出各种“子权利”。[5]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也同样具有这种“母体性”,可以派生出各种受教育的“子权利”。
有学者认为教育权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公民要求国家作一定行为的权利,即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权利。受教育权利是人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接受教育的能力和资格。[6]学者多注重受教育权的平等性研究,而对受高等教育权的研究较少,但是“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是面向广大民众开放的一种权利”[7],《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民接受高等教育这项权利。
根据《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和《教育法》第9条、第42条的规定,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权所包含的内容应表现为: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措施、设备、图书资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学位证书、学业证书;对学校给予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据此,学者一般将受教育权的内容表述为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公正评价权(受教育成功权)。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学生参与权也包含在法律规定中。前三项内容中,受教育机会权是接受任何等级教育的起点、资格或身份;受教育条件权是国家及相关部门提供相应教育条件的配备;受教育成功权指教育过程结束时的获得公正评价权和获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但是,这些权利都是静态性权利,学生参与权是动态性权利,具有联动性,能够保障以上三项权利的实施。教育部“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规定,首次明确赋予了大学生对高校管理的参与权,就将学生参与权引入到实际操作规程当中。
将高校学生参与权认定为受教育权的范畴,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首先,受教育权可以合理的界定学生参与的事项范围,在学校事务中只有与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相关的事宜才属于学生参与范围,而不是学校的整体全部事务;其次,可以回避学校主体地位、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争议,根据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属性,确认高校学生参与权属于行政权利性质,使其具有可诉性,以有利于保障权利行使;第三,参与权具有可诉性,将司法审查引入到高校教育事务中,可以防止学校规章制度制定时的权力滥用。
三、参与权的权利范围
关于学生参与权的内容,我国学者鲜有论及,美国学者麦奎坎认为学校改进中需要给学生赋权,包括三个维度:学习维度、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8]这三个方面中社会维度的赋权已经被教育教学设施利用权所包含,真正属于参与权内容的仅仅是政治维度,即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但是在具体范围和内容上,还是语焉不详。笔者认为高校学生参与权主要包括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权、高校具体事项管理参与权和处分参与权三项内容。
1.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权
《高等教育法》规定了校长制定学校规章制度的权利。在规章制定的过程中,管理者总认为学生是学校改革的可能受益者,而很少把他们看作是学校变革过程中或者学校组织生活的参与者,[9]因此,在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中一直没有学生的参与。而现实中影响学生权益,导致高校纠纷的处分大多是基于学校规章。
根据学校规则条例的内容不同,学校规章制定权的范围包括法律授权与法律保留两种来源。法律授权依据“法阶层理论”,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也即法律优位原则。高等学校规章制定权是法律授予的,违反国家法律的学校规章当然无效。因此,经过授权制定的学校规章条例的内容不得超出法律法规的范围,不能高于法律法规的要求,也不得突破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根据《高等教育法》第58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品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准予毕业。”但实际上,高校在国家设立的学业证书颁发条件之外自行设定了许多条件,如规定受处分者不得授予学位,规定以发表学术论文、通过国家英语考试四级等作为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等,都违背了法律优位原则。
现行学校规章条例中主要问题是过多涉及到法律保留的事项。根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对私人领域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对行政机关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仍有大量涉及到学生道德行为的条款,为学校留下充足的处罚学生的依据空间。现实中也有很多学校根据以上规定,制定多项规章约束学生的道德行为。这些规范都是关于学生私人生活的,应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而哪些行为对学校的公共秩序造成影响,既属于学校自治的领域,则应该有学校自治主体(管理者、教师、学生)共同制定,而不是由专断的学校规章直接调整。
2.高校具体事项管理参与权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政治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所有与学生有重要关系的决策都应该征求学生意见。[10]一般认为,在图书馆、学生宿舍、餐厅等场所为学生参与高校事务的具体管理提供充分的机会,基本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教学性事项学生是否具有参与权仍存在着争议。
美国的大学最早允许学生参与教育评估,后来其他国家的学校纷纷效仿。该制度对教学的作用显而易见,但这种机制是否会导致“学生绑架教师”有过疑问。法国就曾经发生过要求取消学生参与教学评估的案件,法最高行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学生对教学成果的评估不会对教师的职业造成影响,因此并不违反教师享有独立地位的原则。[11]在我国教育管理中,一些学校已经实施与评教相关的规定,学生评教甚至部分改变了高校内部利益配置机制。但是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应限制在何种范围之内,还没有明确的界定。
3.处分参与权
现行学生处分在法律层面的规定,原则性的表述多,程序性规范少,具体操作难,可诉性不强。校规作为内部管理规范,是一种自治规则,在合法的前提下,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但是现行的高校学生管理中充斥着过多的学校规章,甚至出现了以多种非规范性的形式,如“通知”、“决定”、“意见”等来规定处分。在“田永案”中,北科大的“068号通知”第1条内容就是“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在关于学生处分的规定中,学校规章还普遍存在着越权现象。
前文所述,学生的参与权来源于受教育权,面对学生的处分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受教育权的限制。在五种纪律处分中,开除学籍是最严厉的纪律处分,在现实国情下,它对学生及其家庭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关系到受教育者一生的命运,因为身份的剥夺意味着与学生身份相连的权利和利益将无可挽回地受到限制和剥夺。[12]有学者认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受教育者与学校的内部关系中形成的权利,而是已经涉及到了剥夺公民的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已经超过了处分的性质所决定的应有限度,理应属于行政处罚。[13]不可否认,开除学籍的处罚程度实质上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不仅具有行政性,还涉及到行政利益。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语境下,剥夺学生身份处分权行为可称之为准行政处罚行为(或类行政处罚行为)。[14]
因此,在学生处分的程序中保障参与权应该按照行政处罚的规定来设置。首先,在相关申诉程序中,保障学生参与。新的《管理规定》第60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要求各个学校建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中应当包括学生代表;其次,在学生处分中引入听证程序。“根据正当程序要求,在学生因其不轨行为而被公共学校开除以前,必须给其通知并给其审训(即听证)的机会,……法院一致确认,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共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生的决定。”[15]例如2000年,华东政法学院首次把处分听证移植到学生管理中,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16]□
[1]韩兵.完善我国高校学生参与权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6).
[2]马青红,张慧平.公民参与权的理论检视[J].理论探索,2001(6).
[3]孙勇,刘庆丰.扩大学生有序参与反映学生利益诉求[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4]李沫.试论行政法视野下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权[J].现代大学教育,2010(3).
[5]徐显明.基本权利析[J].中国法学,1991(6).
[6]李凤堂.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保护[J].天津教科院学报,2002(1).
[7]陈学飞,秦惠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5.
[8]卢乃桂,张佳伟.学校改进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7(4B).
[9]Michael Fullan.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M.Toronto:OISE Press,1991.151.
[10]吴殿朝,崔英楠.国外高等教育法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3.
[11]王敬波.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D].中国政法学大学,2005.
[12]刘育喆.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二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72.
[13]刘元峰.对学校‘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处分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EB/OL].http://chhs.chinaren.com/r -143514017-11424.
[14]董立山.高等学校学生身份处分权问题研究[D].湘潭大学,2006.
[15]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泽.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218.
[16]徐静.华东政法学院处理学生先听证[N].中国青年报,2000-05-09.
责任编辑:钱国华
D922.16
A
1004-1605(2012)07-0075-04
本文为江苏省2010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参与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10B_015R;本文亦为南京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资助项目。
王建富(1976-),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