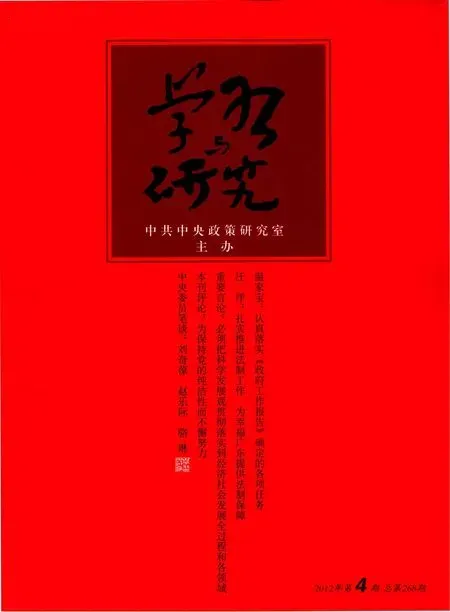叶适对《春秋公羊》学的评说
黄开国
(四川师范大学 政教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在《习学记言》中,叶适对经学的经典及其经学学派都有所评说,这部分评说是叶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叶适的评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叶适是通过经学的经典来为自己的思想寻求理论的支持,这是经学时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不得不然;另一方面,叶适则是用自己的思想来训解经学的经典,评说经典及其经学派别的得失,以“六经注我”的形式,借助经学的经典来建立自己的思想。在这两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后一方面,因为这一方面才是叶适思想的特质所在。叶适的经学评说内容丰富,本文仅就他对《春秋公羊》学的评说做一探讨。
一、《春秋》为孔子所修
《春秋公羊》学是经学中训解《春秋》的一个学派,《春秋公羊传》是其典籍的依据。按照龚自珍的看法,经与传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尽管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已经有《春秋公羊传》的经学博士,但《春秋公羊传》根本够不上经的资格,只能算是传。叶适虽然没有像龚自珍那样明确区分经传,但他对《春秋公羊传》的评说,是以是否合于《春秋》为标准的。
对《春秋》的认识,自孟子以来,尤其是经过《春秋公羊》学的抬高夸大,《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为天子之事。叶适特别反对此说:
孟子曰:《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诛赏。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去孔子才百余岁,见闻未远,固学者所取信而不疑也。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则《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且善恶所在,无间贵尊,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则《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意者以是书接禹、周公,有大功于世,其道卓越,又欲掲而异之乎?虽然考索必归于至实,然后能使学者有守而不夸。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底丽者,小则以《公》、《榖》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
《春秋》是古已有之的史书,并不是孔子著作后才有的。古代的史书,有著作的书法,也就是写作的规则,同时,书法有是非的表现,并不是如《春秋公羊》学所说只有孔子所著的《春秋》才有书法、是非。只是古代《春秋》的书法有不完全合于道的地方,其是非也不完全合于义,所以,孔子对其有所修正,而不是完全重作,也就是所谓“修而不作”。这就是叶适对《春秋》的基本认识。这与经学界以往关于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观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人们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有两种基本认识:一是今文经学的观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一是古文经学的观念,认为《春秋》是述而不作,只是孔子对原有史书的传述。叶适的观念是对这两种观念的折中,一句“修而正之”,不仅肯定了孔子与史记《春秋》的联系,也说明了孔子《春秋》与未修《春秋》的重大差别。所以,就孔子与未修《春秋》的联系而论,无论是孔子以前的《春秋》,还是孔子所修的《春秋》都有书法、是非,二者的差别只是完善与不完善而已。这实际上是将孔子所修的《春秋》视为史书,只不过孔子的史书较史官的史书更加符合道义,否认了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以孔子的《春秋》为经,以未修《春秋》为史的观念。
叶适提出的人主“以功罪为赏罚”,史官“以善恶为是非”,二者并行不悖,完全是针对孟子与《春秋公羊》学而发。孟子首倡《春秋》为天子之事,乱臣贼子惧之说,其后《春秋公羊》学将《春秋》视为素王改制之书,认为《春秋》是一王大法,董仲舒说:“《春秋》采善不遗小,掇恶不遗大,讳而不隐,罪而不忽,明察以是非,正理以褒贬,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②何休《公羊解诂》说:“《春秋》褒贬,皆以功过相除计。”③范宁《春秋榖梁传序》说:“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巿朝之挞。”④刘勰说:“昔者夫子……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⑤。这些说法都是将《春秋》视为一部赏善罚恶的著作,而不仅仅是判断是非得失的书,在叶适看来,这就混淆了人主与史官的职权,将只是史官的职权误作人主的职权,是侵人主之权,这在根本上是完全错误的。故叶适将孟子之说讥讽为“卓越之论”,而将《春秋公羊》学与《春秋榖梁》学指斥为“浮妄之说”,并将《春秋》一直得不到正确认识的原因,归于孟子尤其是《春秋公羊》学。
二,《春秋公羊传》为《春秋》之蠧
依据《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西汉时,传《春秋》有公羊、榖梁、与邹氏、夹氏四家:“《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尽管《艺文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与《左氏微》二篇,但在叙说传《春秋》的各家时,没有提及《左传》,而只提到其余四家。不知这一处理是出自刘向,还是出于班固,但不可能出自刘歆,这是可以肯定的。两汉只有《公羊传》一直被列为学官,影响最大,《榖梁传》只是在汉宣帝时一度被列为学官,影响不大,《左传》则一直未被列入学官,但到东汉开始兴盛。后来流行的主要是这三部传《春秋》之书。
但《公羊传》一直排斥其余二传,尤其是力诋《左传》。三传优劣得失,一直是经学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叶适以对《春秋》的认识为出发点,认为三传中只有《左传》才是《春秋》正传,而《公羊传》只是《春秋》之蠧。他有两段话评说三传的得失:
《公》、《榖》按汉人以为末世口说,流行之学,见于其书者,又有尸子、鲁子、子文子之流。自经术讲于师傅,而训诂之说行,《书》以义,《诗》以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训诂之类也,口授指画以浅传,浅而《春秋》必欲因事明义,故其浮妄尤甚,害实最大,然则所谓口说流行者,乃是书之蠧也。至汉为学官,后世相师,空张虚义,虽有聪明之士,终不能髣髴,而以科举腐余之说,为圣人作经之极致矣,哀哉!⑥
左氏未出之前,学者惟《公》、《榖》之听,《春秋》盖芜塞矣。孟子虽曰天子之事,司马迁闻之董生,虽曰礼义之大宗,然本末未究,而设义以行,吾惧褒贬之滥及也。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简书具存,实事不没,虽学者或未之从,而大义有归矣。故读《春秋》者,不可以无左氏,二百四十二年明若画一,无讹缺者,舍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见其好异也……夫《春秋》非《诗》、《书》比也。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今将以实事诏后世,而学者无征焉,顾使《公》、《榖》浮妄之说,宛转于其间乎。故征于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无舛,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如影响之不违也。嗟乎不降其心难矣哉!⑦
所谓口传一说出自西汉《春秋公羊》学,本是《春秋公羊》学抬高其学的理论。但叶适认为口传之说肤浅,必陷入浮妄,这一浮妄之说完全是不合事实的虚文。而《春秋》为记事之史,记事必有某日、某月、某事、某人之实,只有《左传》对此有详明的叙述,《公羊传》与《榖梁传》以发挥所谓微言大义为主,所谓微言大义不过是“空张虚义”,所以,叶适认为三传中只有《左传》是对《春秋》的确解,二者的关系如身与影、声与响,至于《公羊传》、《榖梁传》皆为浮妄之说,只能是《春秋》之蠧。
叶适在三传高低的评说中,贯穿着一个标准,就是以实事与空虚为判。叶适肯定的是实事,对空虚则是坚决反对的。所以,他在上述二段话中,一再将实事与空虚对立为说。为此,叶适提出对《春秋》训解的正确路径,在于“以事明义”,而不是如《公羊传》不据实事的浮妄之说。而“以事明义”,就离不开《左传》。《春秋公羊》学贬斥《左传》,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所谓《左传》只讲史事,而没有对孔子微言大义的发明,以至西汉就出现了所谓“《左传》不传《春秋》”之说。叶适对《春秋公羊》学此说是完全反对的。在他看来,《左传》并非不讲义理、不传《春秋》,而且只有通过《左传》的实事,才可能以事明义,正确的知晓《春秋》之义。可见,叶适的评说三传高低与批评《春秋公羊》学,其实是以重事、重实的观念为根本的⑧,而这正是叶适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叶适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将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这就是将《左传》与《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上升到“以道为书”,还是“以书为道”的问题:
学者所患因书而为道,书异而道异,故书虽精于道,犹离也,以道为书,书异而道同,折衷其然与不然而后道可合也。然则世之言《春秋》者,因书而为道者也。⑨
叶适所说的“道”,是从事物、实事中所得出的,而不是脱离客观事物的,所以,所谓“以道为书”,是指文字表述的著作应该源于客观实际、合于客观实际,也就是一客观事物为第一位,以客观事物为对象。客观事物的“道”只有一个,对“道”的表述书可以各不相同,但只要是以“道”为第一位的书,不管如何不同,都是“道”的表述,这就是“书异道同”;“以书为道”则是今天所说的教条主义、书本主义,以书为第一位,而不顾客观实际,这样的书无论说得如何玄妙精深,也与道是偏离的。他批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春秋》学都是“以书为道”,明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董仲舒乱《春秋》
《春秋公羊》学最兴盛的时代在两汉,两汉分别出了两位最著名的大师,一位是西汉的董仲舒,他第一次对《公羊传》作出的全面发挥;一位是东汉末年的何休,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作出系统的论述。叶适对《春秋公羊》学的批评,也离不开对《公羊》大师的批评,但他对何休几乎无所论及,而重点批评了董仲舒。
董仲舒在两汉与后世的影响,都超过何休。两汉《春秋》经学博士,皆出于董仲舒之门。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⑩刘歆说: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班固更将董仲舒的治《春秋公羊传》与文王的演《易》、孔子作《春秋》相继为说,许其“为儒者宗。”“为世纯儒”。后世对董仲舒在经学上的成就与地位也评价极高。宋代的胡安国说:“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义,所对切中当世之病,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功不在孟子下。”朱熹说:“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但是,叶适认为董仲舒不仅对《春秋》无功,反而有害,是《春秋》的罪魁祸首。他说:
《汉晋春秋》载,钟离意治孔子庙室,有古文书,言乱吾书董仲舒。事既怪,学者所不道。而别《传》又言修吾书董仲舒。语参错不能明也。然自汉以来,仲舒首为推明孔氏,后世咸从之,宜若修其业者。然而以《春秋》为宗,以《公羊》为师,以刻薄为义,以操切为法,颠错伦纪,迷惑统绪,学者莫之或正,是则乱孔氏之书亦不无也。嗟夫,尊圣人而不足以知其道,若之何可哉?
所谓“董仲舒乱我书”,最早出自汉代的谶书;“修吾书董仲舒”,出自《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钟离意《别传》。东汉对“董仲舒乱我书”就有三种解释:一是以“治理”训“乱”,这是《春秋公羊》学的观念;一是以“烦乱”训“乱”,是与《春秋公羊》学相对立的观念;一是王充的以“完成”训“乱”,以董仲舒为孔子学说的最终完成者。通行的是第一种观念,而且到宋代时,这几乎是经学界的公论,这从宋代经学家对董仲舒的高度评价中,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但叶适认为董仲舒根本不明《春秋》,相反,对《春秋》多曲解,而且对《春秋》学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从《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史说,叶适有一段著名的评说:
昔孔氏之门不许夏以知道《春秋》笔削,传者又谓其不能措一辞,然后世显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为《春秋》悖谬更甚,分门专业者,竞于枝叶之末,流益远益讹,而自周衰以文字为敎者,既已有训诂笺注之渐矣,是先王之道至于汉儒,非独秦火能晦蚀之,盖亦其势也。且烧书六年,而秦遽亡,师友源流,耳目睹记,岂不尚在?俗师相授,屋壁独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辞华,而汉儒所闻,又词华之分散零落者。
人们普遍认为经学之厄,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密切关系,叶适则认为这是儒学传经的弊端所造成。就《春秋》而言,主要是《公羊传》的悖谬所造成,孔门高足子游、子夏尚且不知《春秋》之道,汉儒更是不得其门径。所以,他的结论是:七十子只是得《春秋》之辞华,而汉儒更下,仅得辞华的分散零落。叶适此说,否认经学上有一个从孔子、七十子到孟子的所谓道统,这是对程朱以道统继承者自居从根源上的否定。
叶适所指责的汉儒,主要是针对董仲舒而言。他说:
《春秋》甫脱稿,遽为陋儒迷执不置,孔子既死,又驾说以诬之,虽孟子不能辨也。故汉兴最先行,而董仲舒自任以推明孔氏,尊奉一经,盖抹诸书,故学者习用最深,而其道蔽最甚。
最蒙蔽圣人之道的不是别的,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叶适认为关于《春秋》的种种误说,多由于董仲舒之故:“特以董仲舒师授《公羊》,其语方烂漫于世,故不暇考详也。”又如:“以类例为义,始于《公羊》,董仲舒师之,于是经生空言主断,而古史法没不见矣。”认为经生以空言说经,董仲舒的影响最大。所谓以类例为义,即从书法以发明微言大义,《公羊传》虽然已发其端,但将其形成一套理论,并对后世治《公羊》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推董仲舒。叶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书法以发明微言大义,正是《春秋公羊》学的优点之一,就理论的发展而言,这在经学时代无疑是思想家们借以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最适宜方法,不宜完全否定。
叶适还通过将董仲舒与他人对比的评说,来批评董仲舒。他说:“盖汉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颇见古人本末,而叔孙通以刓方希世为儒者所贬,然岂知通于暴秦胜羽中,以其所学绵蕝自立之为难也,儒术赖以粗传,真叔孙通陆贾之力。”这是就经学传承的贡献言,董仲舒不如叔孙通。较之河间献王,董仲舒更是不值一提:
河间献王得《周官》、《尚书》、《仪礼》、《礼记》、《孟子》、《老子》、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诗》、左氏博士,先王孔子之道赖以复传于今,其功大矣。贾谊,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当时陋儒莫识其意,已得之书,不能讲明,使再有散失,讹缺甚多,尤可痛惜。班固言王答诏三十余事,推道术而对,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此亦过谊仲舒之流远矣。
董仲舒在经学上的贡献,甚至连河间献王的十分之一也不到;而河间献王得对策,深得道术之意,也远远胜过董仲舒。叶适此说是对宋儒程朱等人极力称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间接批评。叶适甚至还将董仲舒贬斥为连少年经生终军都不如的人:“终军诘徐偃,虽少年刻薄,然异乎汉经生,言《春秋》者,董仲舒不能及也。”叶适所说的终军诘徐偃事,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出使行风俗,在胶东、鲁国矫制鼓铸盐铁的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徐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终军诘偃说:“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结果是“偃穷诎,服罪当死。”其实,终军的理论正是汉代《春秋公羊》学的通行理论,而这一理论是出自董仲舒的。所以,叶适的批评董仲舒连终军也不如,显然是有些偏颇。而以董仲舒的不如河间献王的十分之一,虽然说得过分,却是叶适重《左传》的理论导向所致。
[注释]
②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5~1076页。
③④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233页,第2359页。
⑤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⑧《四库全书》收录叶适的《习学记言》与《水心集》两书,言事达三千八百多处,言实达八百多处,实事或事实连用也不绝于书。
⑩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