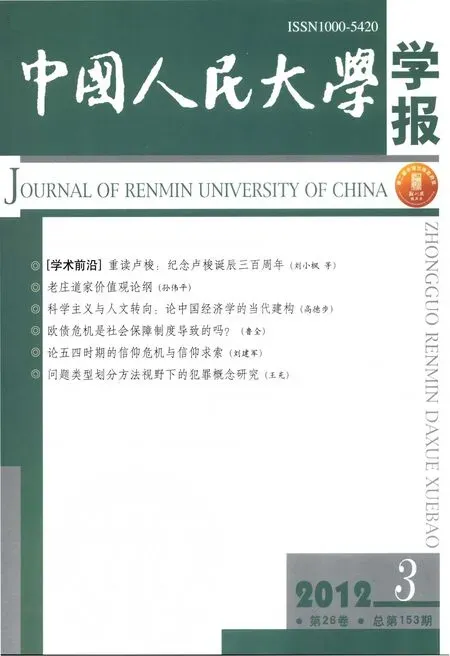卢梭与启蒙自由派*
刘小枫
1751年,卢梭发表应征文 《论科学和文艺》①何兆武译本 《论科学与艺术》长期是唯一的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59/1962/1997),晚近有李平沤译本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中译本都不能支撑研究性的阅读。本稿引文均出自笔者自己的译文,以蓬卡迪 (Francois Bonchardy)的考订注释本 (Rousseau,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Paris:Gallimard,1998/2002/2010)为底本,参考古热维奇 (Victor Gourevitch)英译本 (见Rousseau,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Uni.Of Cambridge,1986/199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和里特 (Henning Ritter)德译本 (见Jean-Jacques Rousseau Schriften,Band I,München,1978,Frankfurt am Main 1988/1995)。,一夜之间成了整个欧洲的 “文化名人”。随后,卢梭写下一系列如今已成为西方经典的政治哲学作品,引发没有停歇的争议,留下迄今学界没有获得共识的理解困惑,比如,《社会契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格言式的话L'homme est n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有争议。必须承认,尽管这句话流传极广,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含义似乎谁都能懂,其实这句话非常含混,颇令人费解。
要获得对卢梭笔下含糊修辞的正解,唯有让卢梭本人进行解释。卢梭说过,《论科学和文艺》是他全部著述的基石。如果这话诚实,我们就应该可以从 《论科学和文艺》中得到理解《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含混格言的线索。
在 《论科学和文艺》正文之前,卢梭引了一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为题辞:“我们被表面上的正确欺骗”,出自贺拉斯的诗体 《书简》卷五 (也就是著名的 《诗艺》)的25行。卢梭用的是拉丁语原文,后来的编者把这句题辞中的拉丁文specie recti译作par apparence du bien[表面上的善]并不准确,因为recti的意思不是“善”,而是 “正确”(如 《诗艺》英译笺注本译作by the appearance of what is right)。贺拉斯是有学养的诗人,早年曾留学雅典,这段诗文谈的是写作风格问题:文学写作要讲究风格,但风格是一种外表,任何表面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因此,要掌握文辞的外表并不容易,好的作家必须得有品鉴力,或者说必须善于运用风格;反过来说,好的读者也必须学会善于辨识作为写作策略的表面风格。卢梭用这句诗作为全文起头的题辞,暗示了全文的题旨:同时代的自由智识人用科学和文艺搞启蒙仅仅是 “表面上正确”,实质上并不正确。随后我们就读到论文的开头:
复兴科学和文艺有助纯化还是败坏道德风尚呢?这的确是必须审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站在哪一方?当然是适合一个正直的人那方,先生们,虽然他一无所知,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就不怎么样。[1](P29)
对 “复兴科学和文艺”有助纯化还是败坏“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卢梭用了 “必须审查”(il s'agit d'examiner)的修辞,“审查”是苏格拉底在讨论问题时喜欢用的语词;不仅如此,卢梭实际上修改了原题,加上了 “败坏”一词。卢梭紧接着就把是与否的选择回答与选择是否与 “一个正直的人”为伍联系起来,他说自己选择的“一方”“适合一个正直的人”(qui convientàun honnête homme)。这无异于说,搞启蒙不适合“一个正直的人”,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立场。显然,与 “一个正直的人”相反的“一方”指的就是当时搞启蒙的启蒙智识人。
接下来,卢梭就用嘲讽的笔法纠弹启蒙智识人心目中的 “文艺复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卢梭却说,文艺复兴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古老的 “写作的艺术”和 “思考的艺术”的堕落。卢梭说,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文学的复兴,随后才是科学的复兴。为什么卢梭要强调这个顺序?卢梭解释说,所谓 “文艺复兴”,指的是当时的人们发现了文学的社会功用:
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搞交易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让人们更富于社会性,得靠值得人们互相欣赏的作品来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2](P30)
“社会性” (sociables)这个词与société (社会)这个词相关,虽然在我们听来这个语词实在太过耳熟,却未必清楚其含义。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社会”堪称 “现代”的重大标志之一,换言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都没有 “社会”。卢梭后来写下著名的Du 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论》),探讨的就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人和现代人过的都是群体生活,两者的差异何在?为什么古人的群体生活不称为 “社会”?因为,“社会”生活基于 “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en leur inspirant le désir de se plaire les uns aux autres),而古代政制的生活方式并不以此为基础。文艺复兴的文学与古人的 “写作艺术”不同,人们写的是 “值得人们相互欣赏的作品”。因此,卢梭说,所谓 “文艺复兴”的实质其实是,“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做买卖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古代也有人做买卖,但这类人很少,而且不大被人看得起,属于品质最低的一类人;现代的标志则是:商人才牛。可以确切地说,卢梭的这段话不仅为我们解释了现代 “社会”的词源就是 “激发欲望”,而且指明了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 “商业”文明的诞生,如果没有 “商业”性质,文艺就很难存活。
卢梭的说法推翻了关于文艺复兴的两个流行观点:首先,文艺复兴所谓的复兴古代文明并非了不起的创举,而是直接受惠于所谓 “野蛮”的中世纪时代;第二,如今的启蒙智识人十分得意的让文艺具有社会作用的观点,其实是在 “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这无异于告诉启蒙智识人,无论搞文学还是做学问在古代都是少数人自我认识的艺术。文艺复兴把这种自我沉浸的艺术变成了相互取悦、激发欲望的艺术,无异于说文艺复兴的真实含义是古老的文学和科学的堕落。
接下来,卢梭说了一段关于统治和法律、专制和自由的话,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卢梭后来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写下的传世名言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的首次表述:
精神有自己的需要,身体同样如此。身体的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的需要则是愉悦。统治和法律为群体的人们提供安全和安利;种种科学、文学和艺术不那么专制,从而也许更有权力,它们把花环缠绕在让人们背负的枷锁上,窒息人们对原初自由的情感,人们似乎是为此而生的——使他们爱上自己的受束缚状态,把他们型塑成所谓的开化人民。需要树立起王权宝座,科学和文艺加固王权宝座。地上的权力们啊,爱惜才华们吧,保护那些栽培才华的人物吧。[3](P30-31)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颇有些让人费解,必须小心识读。首先出现的是 “需要”(besoins)这个语词,与前文刚刚说到的 “欲望” (le désir)形成对比。显然,人的 “需要”不等于 “欲望”。如果我们记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关于城邦形成的说法:“在言辞中咱们从头来打造一个城邦吧,打造这城邦的,看来是咱们的需要”(参见柏拉图 《王制》卷二开头369c9—372d5),那么可以说,“欲望”是过分的 “需要”。卢梭把精神与身体分开,他没有说身体需要精神或精神需要身体,而是说精神和身体各有自己的 “需要”:精神的需要是 “愉悦”(l'agrément),身体的需要是 “社会的基础” (les fondements de la société),但身体的需要是什么,卢梭却语焉不详,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外乎吃、住、穿。卢梭强调的是,社会以身体的需要为基础,而非以精神的需要为基础。这无异于说,相互取悦、激发欲望本来并非社会的基础,如果它们成了社会的基础,不过是文艺复兴的智识分子人为制造出来的。
卢梭话头一转,马上说到 “统治和法律”或者政治制度,可以说,与社会的基础平行对举的是 “统治和法律”,与精神的 “愉悦”平行对举的是 “科学、文学和艺术”。换言之,统治和法律就是社会的基础,这是身体所需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来恰当地管制人的 “需要”,“需要”就会变成 “欲望”。但卢梭没有这样说,而是说 “统治和法律”为 “群体的人们”(hommes assemblés)提供 “安全和安利”。卢梭同样没有说的是,“统治和法律”以王者的存在为前提。事实上,人们很难设想没有王者的 “统治和法律”或政制,即便民主政体也预设的是全体或部分人民为君王。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二节中说:“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里,人民在某些方面是君主,在某些方面是臣民。”[4](P8)如 果 “统 治 和 法 律” 是 身 体 的 “需要”,那么暗含的意思就是:君王也是 “社会的基础”,或者说君王是群体的人们的身体需要产生出来的。
精神的需要是 “愉悦”,由此产生的是科学(学问)和文艺。我们自然会期待卢梭接下来说明精神的需要与身体的需要的关系,卢梭接下来果然说的是这两者的关系。可是,卢梭的表述却突然显得像在唱自由民主共和分子的高调:“统治和法律”是 “让人们背负的枷锁”(les chaînes de fer),甚至等于 “专制”(despotique),科学和文艺则是装饰枷锁的 “花环”(des guirlandes de fleurs),帮助 “枷锁”束缚人们 “对原初自由的情感”(le sentiment de cette libertéoriginelle)。在这样说之前,卢梭用了一个插入句:科学和文艺 “更少专制,而也许更有权力”,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和文艺成了专制枷锁的装饰。卢梭在这里并没有区分封建的君主制和专制,或者说,没有区分封建制与专制。按照孟德斯鸠的划分,两者的差别在于:封建君主制是君主依法而治,封建专制则是君主凭个人意志而治。我们可以说,卢梭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但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难道他连孟德斯鸠说的 “常识”都不懂吗?
这样一来,统治和法律与科学和文艺都分别多了两个描述性界定:统治和法律是 “专制”和“枷锁”——这两个引申说法的语义可以协调一致;科学和文艺是 “权力”和 “花环”——这两个引申说法的语义没法协调一致。可是,按照起初的逻辑,“统治和法律”作为社会的基础是身体的 “需要”,难道不能说,“人们背负的枷锁”是身体的 “需要”?甚至难道不能说,“专制”是“集体的人们”的身体需要?倘若如此,卢梭也就不能说,集体的人们有 “原初的自由”,更不能说,集体的人们是 “为此自由而生的”。换言之,当卢梭在这里突然采用反 “专制”的启蒙修辞把 “统治和法律”说成 “人们背负的枷锁”时,隐含着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从字面上还看到,当卢梭说到 “原初自由”时还补充说,人们 “似乎是为此而生的”(pour laquelle ils semblaientêtre nés),他用了 “似乎”这个含糊词语。显然,如果 “统治和法律”是身体的需要、“社会的基础”,那么对人来说,何来 “原初自由”、何以能说人 “是为此而生的”?
一旦意识到这话在逻辑上的蹊跷,读卢梭接下来的叙述就更得加倍小心。他说,“需要树立起王权宝座 (les trônes),科学和文艺加固王权宝座”。仔细体会的话,语气似乎又与前一句相反:既然 “王权宝座”是 “统治和法律”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人的身体的需要,即便它是 “专制”,专制君王用 “科学和文艺加固王权宝座”,也无异于满足人们的身体需要。换言之,前一句话听起来明显有反对 “专制”的味道,似乎科学和文艺与统治和法律一样,都是专制王权的工具,目的是让人们 “爱上自己的受奴役”(aimer leur esclavage),把他们型塑成 “开化的人民(peuples policés)”,现在则说, “王权宝座”不过是依人的需要树立起来的,这无异于说,刚刚说的人们的 “原初的自由”完全是子虚乌有。
如果承接上文关于文艺复兴的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卢梭在这里所说的王权与文艺的关系,指的是封建专制王权及其统治下的文艺。因此,卢梭随之分别对 “地上的权力”和 “开化的人民”发出 “爱惜才华们 (les talents)吧”的呼吁,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反讽。 “地上的权力”(Puissances de la terre)的 “权力”与前面说科学和文艺 “更少专制,而也许更有权力”中的“权力”是同一个语词,我们显然没法把这个呼吁译作 “地上的力量”。
这里我们看到三种人:“地上的权力”亦即君王、 “开化的人民”和有文艺 “才华”的人。显然,任何时候,君王和有文艺才华的人都一样地少,更多的是广大人民。值得我们设想的是,有文艺 “才华”的人的需要是什么呢?或者说,在统治者 (“地上的权力”)与被统治者 (人民)之间,文艺 “才华们”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说到这里,卢梭做了一个注释:
君主们总乐意看到,迎合人心的艺术的趣味和对白白大把花钱的多余之物的趣味在自己的臣民们中蔓生。因为,且不说这些能培养臣民们的卑微心态,以适应奴隶身份,君主们知道得很清楚,人民带给自己的所有这些需要,都无异于在添加自己所背负的枷锁。亚历山大要食鱼族依附于自己,就强迫他们放弃捕鱼,和别的民族一样种植普通食物;美洲野人光着身子到处走,仅靠猎获为生,从来没谁能让他们臣服。的确,对于什么都不需要的人们,谁能加以羁轭呢?[5](P31)
卢梭在这个注释中说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与正文一样仍然在说道理,后一部分则是举例。注释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说 “君主们”(Les princes),直接说穿了正文中 “地上的权力”的比喻修辞,与此对应的是 “他们的臣民们”(leurs sujets),也就是正文中所说的 “开化的人民”。这段话的字面含义很清楚:封建专制君主对文艺复兴很满意,因为臣民们身上滋生出“对迎合人心的艺术的趣味和对白白大把花钱的多余之物的趣味” (le goût des arts agréables et des superfluités)大大有利于自己的专制统治。无论是 “君主”还是 “臣民”,这两个语词都没有出现在正文中,换言之,卢梭在正文中没有突显封建专制的特点,注释的修辞则彰显了封建专制。与此同时,卢梭在正文中没有说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是启蒙的需要,在注释中却说人民有了这种需要。卢梭显然知道,这样的 “需要”是有文艺才华的少数人制造出来的,但卢梭却说是“人民带给自己的”(tous les besoins que le peuple se donne)。这无异于说,人民产生出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是启蒙的结果。倘若如此,这段说法就隐含着两种政制——封建专制与自由民主政治的混杂或连接。
卢梭在第二次说到 “君主”时用的是代词ils savent très bien(他们清楚知道),“君主”的语义没有变。但在第二次说到 “臣民”时,卢梭用的是le peuple(人民),难道我们能说 “臣民”与 “人民”的语义相同吗?或者,难道卢梭不知道这两个语词的语义的巨大差异吗?答案毋庸置疑是否定的,因为卢梭明明说,“臣民”的身份是 “奴隶”(la servitude),有 “卑微心态”(petitesse d'âme),显然不能说——卢梭事实上也没有说, “人民”的身份是 “奴隶”,有 “卑微心态”。毋宁说,“臣民”和 “人民”指涉的都是正文中所说的 “群体的人们”,但 “群体的人们”这个说法显然并不清楚,还没有赋予政体的规定性。我们都清楚,卢梭自己当然更清楚:“群体的人们”在封建君主制下是 “臣民”,在自由民主制下是 “人民”。两者的差异关键在于 “群体的人们”的品质不同: “人民”不是而 “臣民”是 “奴隶”,“人民”没有而 “臣民”有 “卑微心态”。不仅如此,“臣民”没有但 “人民”有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我们记得,卢梭在正文一开头就说, “群体的人们”需要的是 “安全和安利”,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并非 “群体的人们”天生的 “需要”,因此,“臣民”变成 “人民”的重大标志是,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成了自己天生的 “需要”。
卢梭的这段话让我们想到两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首先,民主政治的趣味是专制君主自己培育出来的。专制君主以为,鼓励文艺复兴有助于自己的专制统治——给专制枷锁缠上柔软的花环,没想到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 “在自己的臣民们中蔓生”(s'étendre parmi leurs sujets)之后,臣民们必然要求自己成为君主。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最终起来推翻了专制君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民主政治是专制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专制君主直到自己灭亡时都没有搞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二个问题同样十分有趣: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本来是少数有文艺天赋的人的 “需要”,他们在专制下的臣民中普及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甚至对思辨的趣味,就是所谓 “启蒙”。专制君主鼓励、奖掖这些有特殊趣味的智识人或艺人,无异于鼓励、奖掖 “启蒙”——如卢梭在正文中的说法,把臣民型塑成 “开化的人民”。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最终革掉了专制政体的命,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启蒙运动是专制君主自己扶植起来的。如果说专制君主鼓励、奖掖启蒙却不知道个中的厉害,有特殊趣味的智识人是否也不知道呢?
卢梭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历史真相:革掉专制制度的命的启蒙运动是专制君主与有特殊趣味的智识人联手上演的历史戏剧。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让我们看到,启蒙智识人的特殊趣味就是对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的趣味。因此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有自由民主趣味的智识人与专制君主结合的结果。的确,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科学院、法兰西学院、柏林科学院……哪个不是在专制君主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呢?卢梭说,“君主们知道得很清楚”,人民有这样的趣味无异于让自己背负更为沉重的枷锁,但人民自己并不知道这点。由此看来,卢梭在正文中呼吁 “地上的权力们”爱惜才子们是反讽,因为,注释中的说法表明,专制君王培育文艺才华让人民具有对文艺和奢侈品的趣味是个大阴谋,目的是让他们安于奴隶身份。
正文的这个段落一开始说的是 “群体的人们”的身体需要 “安全和安利”,从而需要 “统治和法律”。不用说,专制政体与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具有不同的 “统治和法律”。当智识人告诉臣民,他们在统治者统治下是 “奴隶”时,“臣民们”必然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设想,臣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是统治者的奴隶后必然会起来造反,争取自己的权利。按照卢梭在这里的说法,所谓 “开化的人民”,除了有不再是奴隶的权利,还有对艺术和奢侈的趣味的权利。不用说,为了保障这两种权利,就得建立新的“统治和法律”。
注释过后,卢梭在正文中接着呼吁人民也要培育 “才华们”……
开化的人民们啊,培育他们吧:幸福的奴隶们哦,你们赖以炫耀自己的那种纤巧而又精制的趣味得归功于他们;还有温软性情以及城市化道德,这些使得你们之间的社交既何其得心应手又何其熨帖;总之,你们才显得具有根本就没有的任何德性。[6](P31)
“开化的人民”这一表达式在注释之前已经出现过,我们已经知道,“开化的人民”是现代的专制君主和启蒙智识人共同 “型塑” (en forment)出来的,相比之下,古代君王的臣民就不是 “开化”的人民。卢梭随后用了同位语 “幸福的奴隶们”(heureux esclaves)来称呼 “开化的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讽,虽然意味深长,却并不显眼:人民即便开化了,无论怎样因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而幸福得很,仍然是 “奴隶”,作为被统治者的实质并没有变。倘若如此,前文说人民们 “似乎生来就有”、“原初的自由”就是佯谬。卢梭的意思实际上是:人民生来就没有 “原初的自由”。严格来讲,他们 “赖以炫耀自己的那种纤巧而又精制的趣味”意味着一种权力——市民的权力。的确,卢梭在这里并没有用到 “市民”这个语词,但他随之对 “纤巧而又精制的趣味”(ce goût délicat et fin)作了进一步解释。我们看到,这种 “趣味”体现为 “温软性情”(douceur de caractère)和 “城市化道德”(urbanite de moeurs)。①“温软性情”的译法比较接近德译本diese sanfte Geschmüsart。“城市化道德”德译本译作diese Höflichkeit der Sitte,不及英译urbane morals或urbanity of habits贴切。urbanite源于拉丁语urbane(按城市方式、彬彬有礼、城市人机巧地)(副词)-urbanitas(城市生活、精致有礼)-urbanus(城市的、市民的、有城市教养的),意思如今天所谓 “城市人的礼貌”。普及科学和文艺所启蒙型塑的 “开化的人民”就是现代的市民,也就是卢梭以及很多启蒙智识人一再讨论的所谓 “市民社会”。我们回想起,卢梭在注释之前说过:科学和文艺 “更少专制,而也许更有权力”。在这个语境中,卢梭实际上说到两种 “地上的权力”:一种是封建君王的权力,“幸福的奴隶们”其实天生需要这种权力的统治,即科学和文艺所带有的 “权力”。复兴科学和文艺让 “奴隶们”有了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无异于说,让 “臣民”有了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他们由 “奴隶”成为 “开化的人民”。所以,卢梭说,他们应该感谢普及科学和文艺的启蒙智识人。
不过,卢梭的重点并非嘲讽 “开化的人民”,而是尖锐地指责自由民主的启蒙智识人。卢梭的修辞在这里对 “开化的人民”用了第二人称 “你们”,似乎这话是直接对 “幸福的奴隶们”讲的。但我们可以设想,那时还没有普及识字,人民们即便想看也没法看卢梭的文章。显然,卢梭的这番话是说给启蒙才子们听的:启蒙智识人自以为在做型塑 “开化的人民”的伟大事业,改变人性,实际上不过是在让被统治者忘记自己始终是被统治者。不仅如此,自由民主智识人以为搞启蒙可以让人民在道德上有很大的进步,卢梭用坚定的口吻说:“开化的人民”不会有自己天生“根本就没有的任何德性”(toutes les vertus)—— “德性”这个古老的语词,与 “温软性情”和 “城市化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立。卢梭的意思不是说,人民根本没有任何德性,从论文中可以清楚看到,卢梭当然知道,“群体的人们”自有其德性,但他也知道,他们天生没有什么德性。启蒙智识人要型塑人民 “根本就没有的任何德性”,结果型塑出的是 “温软性情”和 “城市化道德”而已。自由派智识人不懂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德性”,可谓不懂得政治生活的根本,却自以为最懂政治,进而要重建 “统治和法律”,结果只会型塑出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
卢梭在文中分别向专制君王和 “开化的人民”发出培养文艺天才的呼吁,明显是反讽口吻,注释恰好加在不同的两个呼吁对象之间,从而切割了连贯的呼吁。其实,注释本身的文义也分为两段,让我们继续看注释的后半段。卢梭接下来说到三种类型的人,并以举例方式说明前两种类型的人,对第三种类型的人则没有举例。他首先说,亚历山大 (Alexandre)帝王要本来靠食鱼为生的人族放弃捕鱼,转而靠 “普通食物”(des aliments communs)为生。亚历山大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食鱼人族成为自己的 “臣民”,显然,这得凭靠一套 “统治和法律”,从而,改变食鱼人族的生活习俗是一种政制举措。亚历山大不仅是古代的君王,也是最早的 “文艺复兴”的标志或象征。然而,卢梭说亚历山大强制食鱼人族放弃捕鱼转而靠 “普通食物”为生,却没有说他要让食鱼人族滋生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换言之,在亚历山大帝国治下有 “文艺复兴”,但没有启蒙运动。毕竟,“普通食物”是身体的需要,对艺术和奢侈品的趣味则不是。可以说,卢梭的行文对两种不同的君王的说法有别,通过例举亚历山大,卢梭不动声色地在对比两类君王:古代的君王和现代的专制君王。
第二个例子是 “美洲的野人”(les sauvages de l'Amérique),他们没有遇到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仍然是 “野人”,因此也就没有成为 “臣民”,因此,第二个例子说的是 “群体的人们”类型。食鱼人族和美洲野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生活 “需要”,要么靠捕鱼为生,要么靠狩猎为生。美洲野人虽然光着身子到处走,毕竟还要靠猎获为生,可以叫做食猎获物的人族。何况,“美洲的野人”如果要获得 “安全和安利”,就得建立自己的政制,有自己的 “统治和法律”,否则最终会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殖民。与此不同,第三种人 “什么都不需要”(des hommes qui n'ont besoin de rien)。这里出现的 “需要”(besoin)一词紧接食鱼人族和美洲野人而言,当指的是 “身体有自己的需要”。换言之,这里所谓 “什么都不需要”指的是没有身体方面的需要,而非没有精神方面的需要。什么人没有身体方面的需要?以精神愉悦为生的人会把自己身体方面的需要保持在最低限度 (参见柏拉图 《泰阿泰德》)。对于这种人,卢梭用修辞性问句的语式说,“谁能加以羁轭呢”(quel joug imposerait-on àdes hommes),这无异于说,在身体方面 “什么都不需要”的 “人们”才有与生俱来的 “原初自由”。这种人既非臣民,也非美洲野人,而是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与奴役不是社会状态的区分,而是人的天性的区分。
卢梭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他施展双重修辞的本领,这并非体现于正文与注释的对比,而是体现为具体的修辞策略:在展示启蒙的基本要点的同时揭露启蒙的欺骗性。卢梭以启蒙智识人的口吻说,专制君主的统治和法律 (专制)压制了人民的 “原初自由”,实际上是在告诉启蒙智识人,他们表面看来是在启蒙人民,实质上是在欺骗人民。更坏的是,启蒙还让人民具有了自己的天性并不具有的 “德性”。《论科学和文艺》的篇首题辞 “我们被表面上的正确欺骗”在此得到了解释。
再回头看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开头的著名说法——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会有何感想?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 “人们”(hommes)。倘若把 “人”理解为在身体方面 “什么都不需要”的 “人们”,这话的含义就是一种苏格拉底问题的表述:哲人固然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或某种政治制度之中,从而,哲人必须考虑与 “枷锁”的关系。若把 “人们”理解为全国人民,这话就具有火山熔浆般的革命煽动性……
[1][2][3][5][6]Francois Bonchardy.Rousseau,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Paris:Gallimard,2010.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