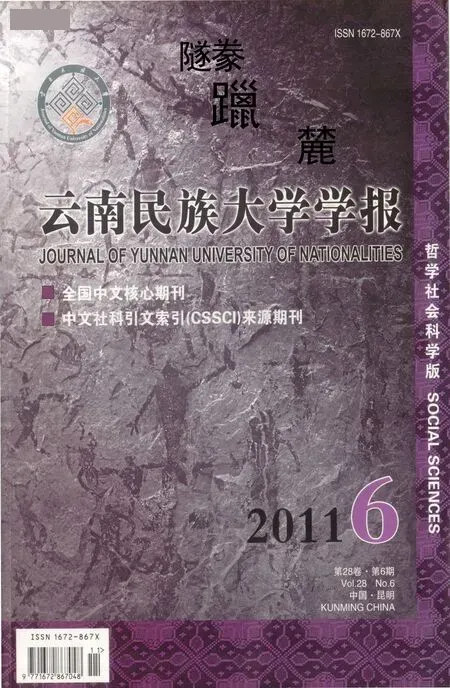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意义与教学实践
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流。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近30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他们带着“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他们又将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的新局面。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办学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民族。1980年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夐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 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教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村落调查;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着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田野调查(fieldwork)被誉为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中国人类学秉承了这一传统并贯穿于学生的培养之中。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人类学8个学分,考古学12学分),也是硕士(硕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3个月)、博士(博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10个月)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国内各兄弟院校大多也有田野调查的规定。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论如何深刻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到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为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上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民族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他谈到其在学社会学的过程中,就明白了必须联系实际到社会实践中去观察、分析、思考,因为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他认真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1](P175)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的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2]人类学往往从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的公开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得来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3](P8)。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由点到线到面的研究。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明白的语言表白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再到族群与区域研究、泛文化比较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积累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介入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老实实经历各个阶段的训练。
二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的实证社会科学,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培养博士、硕士、本科生三个层次的人才,对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更强调他们对于理论的深度掌握,即在田野实践的基础上参与人类学学术领域的理论论争,并借助理论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对本科生的培养,则将重点放在田野实践基础上创新能力的训练,以使他们在应对非人类学学术领域的工作时,能借助人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审视角度来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力。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一)田野实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田野”是与课堂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在课堂中,学生更多的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吸收书本中早已归纳、总结的文字,这培养的是接受和理解能力;在田野中,学生需要面队一切或简单或复杂,或熟悉或陌生的现象,他们必须将思维从书本中释放出来,必须将在课堂中接受的文字创造为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途径,这培养的是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包括社会思维方式的创造,社会问题审视角度的转化,书本知识的融会贯通以及社会现象解决方式的创新等。
(二)田野实习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
“精诚合作”被视为成功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形式,但独立操作能力却是个人得以加入合作团队的基本前提。田野实习提供给学生的便是一块需他们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的天地,无论是民族学的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文献整理、问卷访问,还是考古学的地层发掘、器物整理、测量、分析,每一环节都需学生亲自尝试,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从摸索中获得体验。人类学田野实习的独立操作,亦塑模了学生应对任何问题时沉着、冷静、严肃、认真的性格。
(三)田野实习有助于学生加深专业知识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书本上的专业知识提供给学生的只是一种记忆,而身体力行的田野实践则将这记忆转化为能力。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时间长了会淡忘,经过田野实习后,学生们头脑中处于表层的专业知识自然而然地形成为深层知识结构。特别是考古学,它本身就是一门非常强调经验性和实践性的学科,若非亲自参加田野发掘,其书本上的文字总显得艰涩而枯燥,因此,每一次考古田野发掘都会增强学生对考古学理论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从而巩固、加深学生的专业知识。
(四)田野实习增加了学生的就业机会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培养的学生具有极强的社会感知力、文化分析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田野实习给了学生们充分展示这些特有能力的机会,让有关单位的专家、领导认识并肯定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的能力,这使他们乐于选择该系的学生就业。同时,该系与业务单位的合作,使本科生有机会参与到他们的工作中,学生表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以及精诚敬业精神往往会赢得挂钩业务单位的青睐。另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学生的社会问题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意见,这也增加了他们去政府职能部门就业的机会。因此,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论,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三
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更好地发挥本身的应用价值。费孝通先生从广西大瑶山民族调查到江村调查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沿边开放、民族关系等研究的轨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的典范。21世纪的中国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古老中国的变迁虽然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制度与法治的健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为我们认识社会、反思文化、在实践中发展应用性研究,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那么,触目惊心的贪污腐化、丧尽天良的坑蒙拐骗、惨不忍睹的黄尘浊流、伤痕累累的青山绿水更让每一个学者觉得肩头责任之重大!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人类的迷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正为人类学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拿什么奉献给我们身处的时代?奉献给古老而又焕发青春风采的国家?奉献给异常复杂多元而又充满希望的社会?如果我们从人类学的“整体观”、斯图尔德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等视角去看待,去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或许可以获得不少解决问题的灵感。
[1]张冠生.费孝通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2]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