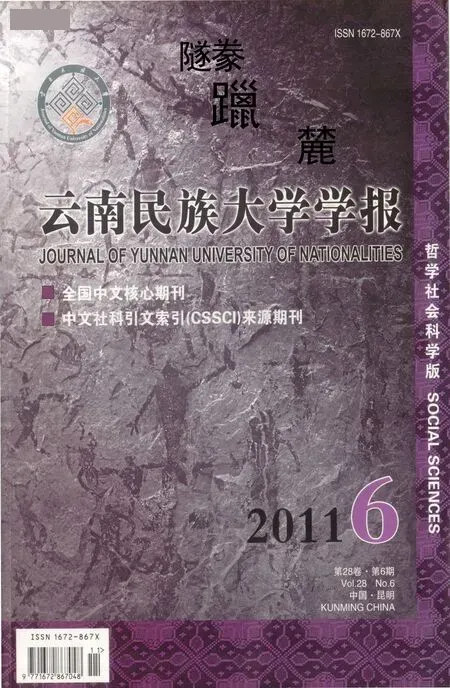近六十年我国民族识别研究述评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涪陵 408100)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它是我国一项理论性、科学性和政策性很强的而又相当复杂的重要工作,也是我国民族学界一项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科学研究工作。[1](P2)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民族识别研究也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识别研究的相关内容予以梳理,有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化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
一、我国民族识别研究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者几乎“全民参与”了民族识别这项重大工程,他们利用自身所学的知识和参与民族识别的经历,从民族理论、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角度展开探讨,而且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空前的。近60年来,民族学研究者和民族识别工作者深刻分析和深入探讨民族识别相关的问题,并不断对民族识别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总结,或撰写成专著出版,或撰写成论文发表。从总的来讲,我国民族识别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3方面。
(一)专著类
1.专门研究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我国专门研究民族识别问题的专著仅有两部,一是黄光学和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二是王文光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2]前者的内容主要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就和意义”、“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有关几个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探讨”;后者以历史顺序为经,以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为纬论述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识别。
2.直接或间接涉及民族识别研究的著作。这类著作较多,论述的视角和内容各不相同:王建民等学者的《中国民族学史》(下册),第四章“中国各民族身份的认定”,主要包括“民族识别的初衷”、“关于识别原则的认识”、“识别的复杂性与最初成果”[3](P106-129)等内容,可谓经典之作。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概论》,在“民族识别”内容方面阐述了“民族识别是我国新时代提出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和“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4](P247-250)等理论问题。张有隽的《中国民族政策通论》中涉及“民族识别政策”的有两节,即“民族识别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和“民族识别政策的基本内容”[5](P257-268)。王希恩的《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一书中安排有“民族识别与民族意识”的相关内容[6](P363)。林耀华在《民族学通论》中有“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7](P185-197)专节。图道多吉的《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同样有“民族识别工作”[8](P157-164)一节内容。王红曼的《新中国民族政策概论》有专门探讨“民族识别政策”[9](P97-117)的专章。周光大主编的《现代民族学》(上卷)第一册有“民族识别与民族识别意义”[10](P222-242)一章的内容。此外,杨堃在《民族学调查方法》书中有“民族识别的调查方法”[11](P38)的相关内容。
3.民族识别研究论文集。施联朱的《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12]中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专题,重点是通过具体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突出民族识别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的民族实践中去,使马列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辩证地相结合。
(二)史料类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调查是民族识别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族识别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和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历史资料。《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是其代表,该套丛书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上世纪50-8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编辑出版了许多民族识别资料集,如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辑《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1955年),其中包括《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和《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民族识别初步总结》等内容;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识别办公室编辑《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1-7集)》,其中第5集有《木佬人族别问题调查报告》等内容。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撰的《广东民族识别调查资料汇编》,由《怀集县“标话”集团调查资料》和《龙门蓝田瑶族调查》两部分组成,包括其历史来源、生产生活、语言风俗、民间信仰、传说歌谣等内容,是民族研究工作者了解怀集县“标话”集团和龙门蓝田瑶族最权威的资料。
(三)论文类
据笔者以“民族识别”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超星数字资源等系统下载的127篇论文统计显示,民族识别研究工作逐渐呈快速发展趋势。“文革”之前发表的论文有傅乐焕的《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费孝通和林耀华的《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南川的《也谈族别问题》、思明的《识别民族成份应该根据的主要原则》及杨堃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等5篇;1979-1999年21年的时间里发表论文57篇,2000-2010年11年间里发表论文65篇,其中包括7篇与民族识别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是就民族识别的意义、理论依据、实践标准、成就与过程、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民族识别研究的问题与建议、我国与国外民族识别的比较等问题,或就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民族识别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过程中,或采用传统的实证法,或运用史籍文献,或翻检地方志书,或通过实地调查材料进行论证,很多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二、我国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研究
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为国家安定团结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理论体系,三是通过民族学实地调查研究,为民族识别提供了科学依据,四是重视多学科的密切合作与配合,五是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民族学学科的发展。[1](P118-122)这项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民族工作者加强民族理论的学习和坚持民族识别的标准。
(一)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
我国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唯物和辩证的科学运用。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既不能搬运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13]。将民族共同语言、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既遵照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又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故能比较准确地辨明不同的族体。[14]黄光学、[15]王红曼、[9]周光大[10](P225-228)等专家学者均持这种观点。林耀华则认为,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除了这四大民族特征之外,还应将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民间传说等结合起来,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16]王希恩在《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一文中认为,200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民族概念的总结(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是现阶段进行民族识别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17]也就是说,民族识别必须将民族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及宗教等作为理论依据。
(二)“共同心理素质”的讨论
由于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给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所以,费孝通、黄淑娉等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证实了斯大林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已名存实亡。[18]因此,对于是否将“民族共同心理”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理论依据,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如前所述,除黄光学、王红曼、周光大之外,李绍明、[19]、熊锡元[20-22]顾学津[23]等专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众多的民族识别工作者并没有将“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理论依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当时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林耀华、杨毓才、安荣、黄淑娉、王辅仁、王良志、宛文涛等学者撰写的相关县民族识别小结,基本上是按民族名称、人口与迁徙、语言、区域、经济、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识别和撰写小结的,[24]这说明他们对“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持保留态度,这在他们后来的学术论文中也有所体现。[16]费孝通认为,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认同的意识。民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25]对“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识别理论依据持否定态度最坚决的莫过于韩忠太,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论述在理论上极为模糊,要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非常困难;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共同心理素质”标准已名存实亡;“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心理标志;我国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心理学界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对“共同心理素质”问题作深入研究后,至今仍得不出切实可信的结论。因此,“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他特别强调,今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必须根据我国民族实际,由我国的民族学家研究确定新的识别标准。[18]
(三)民族识别的理论构建
祁进玉在《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认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支撑一方面是基于前苏联民族工作的经验并借鉴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另一方面是根据当时的国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法。民族识别的构成要素包括民族构成、民族自称与他称、民族族源与历史记忆、民族语言与文字、民族文化。[26]
三、民族识别实践标准的研究
(一)一分法
周光大的《现代民族学》中主要将“民族特征”作为实践标准[10](P228-229),并强调“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其核心是对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来源、语言、经济生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心理素质等予以考察,确定民族成份。
(二)两分法
黄光学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将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确定为“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他认为,民族识别的最后决定必须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这是识别民族成份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原则, “民族意愿”包括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1](P81-103)图道多吉在《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同样将“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确定为我国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8](P159)
(三)三分法
李绍明认为,民族识别除了“民族特征”之外,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各民族的名称与历史渊源。他认为,各民族的自称与他称均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其来龙去脉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认定。此外,还应从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文献记载及各民族民间传说中,弄清他们的历史渊源。二是注重各民族的意愿。因为民族意愿是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的具体体现,在民族识别中必须加以尊重。他特别强调民族识别工作中的“名从主人”原则。[19]祁进玉提出,民族识别工作中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重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这是识别民族成分的客观的科学依据;二是“名从主人”,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重视有关民族的意见;三是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国化。[26]
(四)四分法
王红曼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中坚持民族识别有民族特征、民族意愿、历史依据和就近认同等四个实践标准。[14]她认为,这些标准是党和政府在领导具体的民族识别工作时,坚持科学理论和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符合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的民族识别标准。
四、我国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27]对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王兰永认为,我国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民族识别是强势的、占支配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族群认同是日常的、民间的、非正式层面上的。两者有时重合,有时相悖,但认同上的相悖并未影响民族成份的划定,相反,这种民族成份的划定却有着影响族群认同变迁的能力。[28]明跃玲提出,我国的民族识别客观上使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具有了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以户籍登记中的“民族成分”而体现,它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自己所具有的“民族成分”与族群差别,而与“民族成分”相关的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会在客观上固化人们的族群认同。[29]覃乃昌以广西历史上形成的12个各自具有共同历史来源、文化上各具特点并内部认同的族群为例,指出:通过民族识别,这些人们共同体的族群身份同时又具备了民族的身份,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但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30]龚平在作硕士学位论文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内两个村庄中的一个宗族为调查对象,从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的交互视角对调查点的同宗异“族”现象研究后认为:津头村一支的族群性、民族性表现出主观认同与族源根基性并行不悖的特点;在平乐村一支,其族群性表现出主观认同与客观文化特征、工具性相背离,与根源性相一致的特点。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历史上长期杂居通婚,平乐村的确有着一些和壮族一致的文化习俗,而国家“民族”识别时将其确认为壮族;二是主观认同与族源传说承续是其族群性的显著特点。就时间上看,越是以前,主观认同在族群认同和区分中的作用越重要;越是晚近,文化特征在族群性中占有更多比重,工具性表现出的民族身份认同则呈现出逐渐淡化的趋势。[31]
(二)民族识别对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
林宏杰认为,我国民族识别及民族身份的恢复与改正,均是把客观文化特征及主观族群认同的结合作为指导原则。当民族身份的更改成为客观事实之后,它对当地乡民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以江西金竹乡于2002年通过申请更改部分汉族民族成分的方式,获得成立畲族乡所需要的30%的畲族人口数量,进而成功申请成立了畲族乡为案例,分析了对族群认同影响的三个方面:一是没有更改民族成分的汉民,在面对畲民所获得的某些照顾时,心理上可能产生一定的失落感,但他们会因此而更强调自身的汉族身份,以虚幻的汉族优越感来获得自我的心理安慰与平衡;二是本属于汉族但出于利益的考量而更改为畲族的人,可能造成族群认同上的错位;三是畲族身份的确认,强化了畲民本已淡薄的民族意识。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是:利益与民族成分的挂钩,使不同族群因为民族成分的差别而在利益分配中获得不同的份额,由此引发不同族群间新的矛盾和争议。这种族群关系变化,在不同民族间或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利益群体间均有表现。[32]
五、我国古代、近现代民族识别研究
(一)我国古代民族识别研究
对我国古代民族识别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莫过于王文光。他在《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一书中强调,如果说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自觉的,那么,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便是不自觉的和自发的。他认为,从民族识别的角度看,我国的二十五史各民族史传大多讲述了民族成分、分布区域、文化习俗、语言特点,包含着许多民族识别的原则与方法。尽管有的民族史传中对许多问题混淆不清,存在许多不足,但为我国当代的民族识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基本的民族识别根据。清代以前的民族识别与分类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民族识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第二,民族识别的思想观念是“华夷之别”和“华夏中心论”,表现的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带有民族不平等的民族观;第三,民族识别的基本标准是以文化为标准,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以降至清末均得到史家的继承和发扬。[2](P4-5)王文光结合秦汉时期东北肃慎集团等三个民族集团的实际,提出古代民族识别的标准问题:“中原汉族史家把若干语言文化习俗相近的人们共同体视为一个民族集团”[33],这个观点很有建树。刘仲华认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诸夏与夷、狄、戎、蛮等少数民族的区分,并不是地域和血缘上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利益上的冲突和文化生活上的区别。这种以文化礼仪来区分民族的方法,在实质上承认了文化的进步、流动和传播特征。[34]
(二)我国近现代民族识别研究
近现代阶段是我国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阶段。王文光认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民族问题时,除依靠历史文献外,在理论上大量采用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十分看重田野调查,这对民族识别实际工作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均有着重要影响。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怀抱着实现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理想,但民国政府希望逐步实现各少数民族向汉族的同化,因而,当时的民族识别只是“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35](P6)的权宜之计。[36]朱映占认为,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分类,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来的民族分类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近代西方学者建立在语言学、民族学基础上的分类方法的影响。当时,民国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虽然先后对西南各省的民族情况进行了调查,但对西南民族究竟有多少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与当时国人的民族思想和国家观念密切相关。[37]
六、我国民族识别存在相关问题的研究
经过民族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民族识别已基本结束,这项工作已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毋庸置疑,民族识别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问题
王建民认为,我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将理论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二是个别地区对本民族意愿重视不够,三是个别地区存在着过分强调族源和血统。[3](P127-128)
(二)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
黄光学认为,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族体虽已进行过识别调查,并已有了初步的结论,但尚未最后落实,个别的尚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待识别族体因条件限制,尚未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P292)如僜人、白马人、台湾高山族等族属识别问题。费孝通认为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是有的人们共同体提出要求识别,如四川平武藏人,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及南部定结县、定日县的夏尔巴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苦聪人等。[13]
(三)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
黄泽在《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一文中指出,云南克木人、莽人、拉基人、普标人、老缅人、苦聪人、阿克人、浦满人、他留人、摩梭人等当时“族属状况不清的群体”未能在民族识别中得到识别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论是在地域范围、文化区、族际社会中,还是在历史文化、群体特色等),都被周围强势的群体所遮蔽、淹没,加上他们大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无法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从而成为了“我国民族识别中的难点、死角或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与学者们的视野以及政策导向的因素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民族识别是在弄清民族成分,划分民族归属,进而落实民族平等和优惠政策的紧迫“政治任务”下进行的。目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生活方式进入这些群体,民族主义意识、族群认同意识在这些群体中都有所表现”,这些群体的相关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故而也是摆在今天的民族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应该“对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理论作再认识”,对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充分认识和反思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指出了方向。[38]
[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3]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4]宋蜀华.中国民族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5]张有隽.中国民族政策通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6]王希恩.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7]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8]图道多吉.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9]王红曼.新中国民族政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10]周光大.现代民族学(上卷·第一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11]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施联朱.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3]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0,(1).
[14]王红曼.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3).
[15]黄光学.我国的民族识别[A].新时期民族问题探索[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16]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17]王希恩.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 [J].民族研究,2010,(5).
[18]韩忠太.“共同心理素质”不能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J].民族研究,1996,(6).
[19]李绍明.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J].思想战线,1998,(1).
[20]熊锡元.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问题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1981,(4).
[21]熊锡元.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持久因素[J].思想战线,1982,(1).
[22]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23]顾学津.民族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 [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1).
[24]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内部资料)[Z].昆明: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1955.
[25]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7,(2).
[26]祁进玉.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2).
[27]明跃玲.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J].云南社会科学,2008,(2).
[28]王兰永.“民族识别”的两个问题刍议[J].江苏社会科学(增刊),2007,(1).
[29]明跃玲.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 [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6).
[30]覃乃昌.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J].广西民族研究,2009,(3).
[31]龚平.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平乐村、津头村龚氏宗族个案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07.
[32]林宏杰.民族身份确认与族群认同 [D].厦门大学,2007.
[33]王文光.秦汉时期东北的民族识别[J].思想战线,1995,(6).
[34]刘仲华.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3).
[3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C].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
[36]王文光.1950年以前对云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2).
[37]朱映占.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J].思想战线,2010,(2).
[38]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