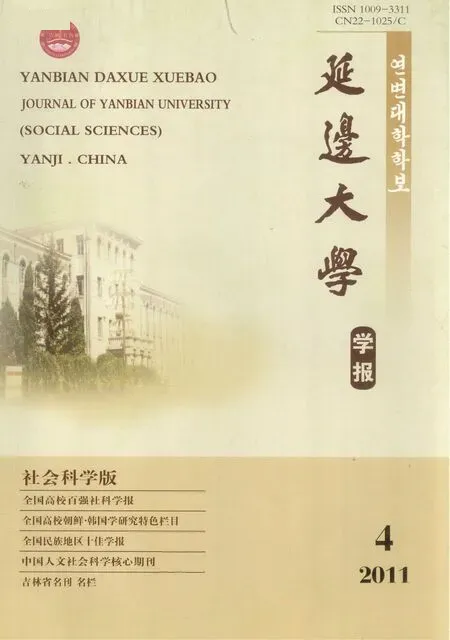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
谢 桂 娟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吉林延吉133002)
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关系
谢 桂 娟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吉林延吉133002)
与欧洲、北美及东南亚相比,有着深厚经济合作基础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却进展缓慢。从深层次文化根源来分析,该区域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淡漠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使得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建构主义有了充分的解释空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只有建构集体身份才能保证持续的、真实的合作。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呈双向互动关系,集体身份的建构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有重要的影响,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能够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
建构主义;集体身份;东北亚区域合作;互动实践
历史上的东北亚,曾经存在文化统一、政治上相互承认的身份认同。步入近代,自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以来,东北亚各国的地区认同意识却越来越淡漠,而对民族或国家认同却越来越强。这种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过分依赖,使得该区域国家的地区认同观念普遍较弱,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严重缺失。①这使得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建构主义有了充分的解释空间。基于建构主义集体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笔者尝试论证集体身份建构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即集体身份的建构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有重要的影响,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能够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
一、集体身份的建构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
在温特看来,“集体身份是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1]由此可见,集体身份即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具体指认同主导规范和因之确定的相互身份。温特提出了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通常,国际关系学界强调这些变量是怎样在利己者之间促成合作的”,“这些变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能够减弱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1]在一个情景中四个变量可能都会存在,其存在程度越高,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其中的一个因素即自我约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所谓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是指东北亚区域内的成员国认知和接受自己作为东北亚区域一员的观念,并在行为中体现出东北亚这一地区身份;同时,东北亚集体身份也包括主导国之间建立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把本国的利益与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集体身份是各行为体(即国家)形成共同认知架构的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包含建构、维系与改变的过程,其中集体身份建构至关重要。所谓集体身份建构,是指“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建构一个‘共同的自群体身份’(ingroup identity)或是称为‘群体意识’”。[1]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要求东北亚区域各主要行为体要转变认同观念,超越民族主义,淡化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树立地区意识至上的观念,建构东北亚地区身份认同。当然,超越民族主义对东北亚各国来说是个相当遥远的议程,但却是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首要条件。下面我们来分析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情况,及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
(一)东北亚各国普遍存在国家至上的观念,地区整体意识不强,极大地干扰了东北亚区域的正常合作
在理念层面,东北亚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至上的观念,东北亚地区认同意识不强。在东北亚各国,普遍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主要表现为狭隘排他的共同特性,国家至上意识和自民族中心主义。例如,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日韩两国心态比较复杂,日本担忧动摇其在东亚的领头雁地位,在韩国也唤起了曾经作为中国附庸国的历史记忆。另外,从目前的东北亚区域来看,强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比其他民族国家优越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性存在着上升的趋势。“虽然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但东北亚地区政治还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主权观念强烈,各国对于弱化和让渡主权的区域合作尚没有形成统一认知”。[2]也就是说,在身份认同方面,东北亚各国仍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民族)认同层面,地区集体身份认同远没有形成。由于过分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相对受益而不是绝对受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过分固守,没有意识到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密切联系,因此不利于国家对外做出妥协以产生合作,不利于地区整体意识的培养。在一定意义上,民族认同与东北亚集体身份所强调的地区认同是背道而驰的。地区认同的核心价值和本质是“地区至上”,因此可以说,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较量的过程。这对于民族主义对立情绪极为浓厚的东北亚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在现实层面,东北亚地区是二战以来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包括日俄之间关于“北方四岛”归属的问题,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日韩之间关于“竹岛”(韩国称“独岛”)归属的问题,以及中日和中韩之间关于领海线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界限划分的问题等。另外,日本政府经常否认历史侵略战争的言行也引起了东亚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些都说明东北亚地区缺乏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
无论从理念层面上来看,还是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东北亚各国的地区认同与归属感都很弱,极大地干扰了东北亚区域的正常合作。
(二)目前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竞争性洛克文化环境,使得东北亚区域合作难以摆脱自助性质
国际政治中集体身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文化环境决定了国家间合作关系的性质,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身份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出现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
目前的东北亚区域处于洛克文化状态。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竞争对手期望相互行为的基础是承认主权,不会试图征服或者统治对方,但竞争可能会涉及领土变动,有时这种竞争会导致暴力行为,只是预期国家使用暴力的程度会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之内。[1]这种“共存共生”的洛克文化虽然减弱了国家的自助倾向,但是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因此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
竞争性洛克文化环境造就了东北亚国家间积极和消极身份认同并存的状态,如中日间身份认同就处于这种积极和消极身份并存的状态。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使双方建构了积极的身份认同。这种积极的身份认同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合作,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民间交流增多,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些良性互动支撑和再造了中日间积极的身份认同。但这种积极身份认同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消极身份认同,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仍悬而未决。这说明中日之间初步建立起来的积极身份认同远没有真正内化到中日的战略思维当中去,双方没有从深层次上认同这种角色身份。中日之间的积极身份认同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暂时缓和中日关系的一种手段。与积极身份认同能够促进双方合作不同,消极的身份认同却阻碍了中日之间的合作进展,如中日之间合作的“政冷经热”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东北亚,积极和消极身份认同并存不仅仅存在于中日之间,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间消极的身份认同是常态,积极的身份认同背后仍然隐藏着消极身份认同。因此,处于洛克文化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始终难以摆脱自助性质,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过度竞争也延缓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
(三)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的最终确立
中日韩同为东北亚地区重要国家,也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决于区域内的中日韩三边框架。目前,“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正不断完善,中日韩三边外长会谈框架也在确立之中。但这主要是以东盟为主导的日渐成熟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东北亚,中日韩合作步伐进展缓慢,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制度框架远没有形成。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中日韩三国仍然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在地区合作方面,中国一贯主张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以平等、互利、互谅、互助的精神处理相互的关系,主张共赢而不是单赢。而日本在与东北亚国家合作中,考虑自己的利益(单赢)比较多,考虑共赢比较少。例如,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上,日本几乎是不择手段地把中俄已经谈好的合同抢走了。如果今后日本在东北亚合作中还是采取这种态度,那么东北亚合作很难顺利地发展。[3]韩国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很难突破这一框架。2007年4月,韩国置中国、日本于不顾,与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结成FTA(自由贸易协定),一定程度上,美韩 FTA将有可能使东北亚区域合作陷入混乱局面,扰乱其原有的合作进程。
其次,缺乏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在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都不想在区域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都想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发挥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作用,而且中国、日本、韩国都有主导东北亚事务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至今该地区仍然缺乏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中国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大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但由于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不但使中国很难在东北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而且也使得中国在融入东北亚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主动性不强。而经济强国日本,具备组织和引导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优势条件,也一直在与中国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但由于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治精英对二战期间对外侵略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思,因此难以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认同。加之,日本“出于政治考虑,对周边国家的技术转让持保守态度,热衷于自己所主导的‘雁型模式’,通过经济地位扩张政治影响,同时日本的对外关系不可能超越日美关系”,[2]因此日本无法独自在东北亚发挥作用。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表现积极,但由于其本身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都严重依赖美国,所以它先天地缺乏组织和引导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优势条件。
在区域合作中,共有知识是制度化的基础,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主导国之间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共赢的共有知识,缺乏核心国家主导作用,因此类似《东南亚友好互助条约》这样的规范性文件难以出台。由于缺乏共同遵守的规范,东北亚区域合作在整体上,仍然停留在缺乏约束力的政府对话和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东北亚区域合作尤其是政治合作缺乏稳定性。东北亚需要的长期合作的制度框架始终难以最终确立。
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能够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
关于区域合作或区域主义,国内外学者有诸多论述。赫里尔把区域主义分为五个范畴来解释,即区域化——区域意识和认同——区域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形成区域的内聚性。[4]国内有学者认为,区域主义是“同一地区内的各种行为体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总称”。[5]庞中英认为,区域主义是指在地缘上接近的、彼此间有着复杂关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联合、合作进而一体化的过程,是国家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进而达到调节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与政策。简言之,区域主义就是以形成一个区域国际体系的广泛的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运动。[6]这些关于区域合作或区域主义的论说可以作为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
笔者比较赞同“五范畴”说,这五个范畴可以被看做是区域合作的五个阶段,其中区域意识和认同相当于集体身份的建构,是区域国家间合作的前提基础。而区域合作是推动区域一体化,进而形成区域内聚力的桥梁。区域内聚力的形成意味着集体身份的形成。可见,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东北亚区域国家间的合作是集体身份建构与形成的一个纽带。
从历史上看,早在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时期,东北亚各国间就开始了互动的历史,但由于体系成员间是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东北亚缺乏平等主体间进行合作的传统。不论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朝贡体系时期,还是日本主导的东北亚霸权秩序阶段,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后开始形成的“亚洲太平洋圈”和80年代开始形成的东南亚“雁行模式”,都是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追随中心国家的不平等模式。直到冷战结束,随着朝韩加入联合国,国家间正常关系确立,东北亚地区才真正进入了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这意味着东北亚区域国家间的平等合作真正开始。因此,“历史地看,东北亚区域合作目前正处在初期阶段,只相当于二战之前的欧洲(当然不是在大国合作支配地区性事务的意义上而言的)”。[7]可见,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真正的平等主体间的合作起步较晚。尽管如此,东北亚国家间平等主体的合作,却是集体身份形成的最基本条件。下面从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来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是如何促进集体身份形成的。
(一)冷战后东北亚多边经济合作促使东北亚地区相互依存程度提高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随之瓦解,东北亚的政治生态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1990年9月,前苏联与韩国建交。1991年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2年5月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至此,除朝鲜与韩国仍处于敌对状态,朝鲜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外,东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大大改观,这为该地区由双边经济合作到多边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加之东北亚地区各国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上都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促使东北亚地区出现多边经济合作的势头。
东北亚区域既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梯次明显,资源条件也各具特色,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东北亚成为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北亚区域的 GDP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5。中日韩三国的 GDP总量占亚洲 GDP总量的73%。虽然曾经受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东北亚至今仍然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目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诸如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危机预防和处理机制、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等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互动和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地区不断加强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密切的跨边境经济往来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和地区组织的实践,东北亚区域在物质层面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使东北亚各国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会逐步培养出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因素。
(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促使东北亚国家共同命运感增强
从理论上讲,共同命运感来自于安全上的共同的外来威胁,而东北亚地区国家缺乏共同的外来威胁,因此共同命运感一向较弱。但在全球化时代,东北亚地区国家面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无疑是东北亚各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和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能源危机越发显现;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东北亚地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安全。因此,冷战时期形成的仅以军事手段来维护国家自身安全的做法无法应对诸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地区性问题层出不穷,单靠某一个国家甚至少数几个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贩毒、核武器扩散、艾滋病控制等)正是地区集体认同形成的潜在领域。”[8]目前,中日韩已经加入了讨论非传统安全和反恐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日、中韩、日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逐步展开,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间互动实践会导致角色对自身进行再界定(redefinition),使角色通过认知和学习而变得具有顾他性(other-regarding)和合作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增强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互信,促进了东北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同时也促进了东北亚国家共同命运感的增强。
(三)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使原本就有着文化亲缘关系的东北亚同质性程度的增强
东北亚地区同质性(或称相似性)较低。东北亚各国不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而且该地区民族众多、语系复杂,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存在明显的区别。但该地区历史上的文化亲缘关系是不容否定的。东北亚地区地缘相近,文脉相通,拥有较多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记忆,中日韩等国家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渊源,有着共同的儒教文化基础,各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节日安排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为东北亚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东北亚各国在文化交流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如人员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增进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进一步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民众改变对邻国的陈旧观念,加深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实践证明,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是化解矛盾、改善东北亚各国关系,维护与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地区合作不仅是经济合作、政治合作的过程,也是整合不同民族文化,共建地区共同文化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是地区内成员国对地区合作形成跨文化认同的过程。”[9]就是说,东北亚区域合作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而且更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整合。东北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使该地区同质性程度的增强。
(四)随着东北亚各国互动实践的加强,东北亚国家出现了自我约束的征兆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间的互动实践,能够创造新的观念性国际关系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帮助角色之间克服集体性行动的困难和彼此间的不信任”。[10]这种新的观念性国际关系结构就是康德文化,康德文化的角色结构是友谊,它有两个要素,即非暴力原则与互助原则。目前,洛克文化为东北亚和平提供了规范性条件,即对主权规范的尊重,不使用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这已经成为东北亚国家的共识,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尚无关于非暴力原则的正式承诺,朝鲜更是未对地区国家做出明确的非暴力承诺。这说明,东北亚国家对非暴力原则的承诺非常脆弱。与对非暴力原则的承诺相比,目前东北亚多数国家之间缺乏安全互助的承诺。这充分表明,东北亚地区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结构的转化困难重重,必须改变国家利己的特性。为达到此目的,东北亚各大国必须要自我约束。
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大潮的趋势下,随着东北亚共同命运感的增强,东北亚国家也出现了自我约束的征兆。这主要体现为,中国倡导的睦邻友好政策与“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90-1992年间的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不要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争夺领导权,不要勉强承担中国无法担负的责任,这实质是在强调一种“自我克制”的理念。[11]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是更为积极的自我约束。东北亚国家自我约束的不确定因素使朝鲜游离于地区规范体系之外,这容易导致区内国家对它的意图认知发生偏差。因此,为改善区域内国家与朝鲜的认同关系,为了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区域内国家应该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国家间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基本条件,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三、结语
东北亚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建构的共生关系。集体身份的建构是维系东北亚各国进行合作的信念力量。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互动实践是集体身份形成的物质推动力量。集体身份是地区内行为体之间不断学习的过程,是在各国的合作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因此,集体身份的形成过程应该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同步进行。东北亚集体身份建构的过程,就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从初级到高级不断升级的过程。
注释:
①关于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详见拙文《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缺失及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 5期 ,第 205-209页。
[1][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24,331,329,274.
[2]巩村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12):11-13.
[3]沈骥如.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障碍与希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1):48-59.
[4]Andrew 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A].Fawcett and Hurrell.ed.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997.39-45.
[5]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
[6]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J].欧洲,1999,(2);俞新天.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165.
[7]陈玉刚.欧洲的经验与东亚的合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5):21-25.
[8]郭树勇.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道路——兼论东亚共识的制度化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5).
[9]刘昌明,宋超.区域合作中文化因素的建构主义分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79.
[10]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0-12.
[11]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6):9.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XIE Gui-juan
(Dept.of Political Science,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Yanbian University,Yanji,Jilin,133002,China)
Though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solid,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s still stepping forward slowly comparing to those of in Europe,North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The analysis of deep-leveled subculture shows that nations’indifference to collective identity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and it holds back the cooperation in this region.Thus constructivism can make full play of its power to interpret such problems as it focuses on both cultures and identification and proposes that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a sustainable and actual cooperation.There is an interactive and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the former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the latter,while the latter can progress the formation of the former.
constructivism;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interactive practice
G05;D81
A
1009-3311(2011)04-0048-06
2011-05-01
谢桂娟(1966—),女,吉林农安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责任编校:张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