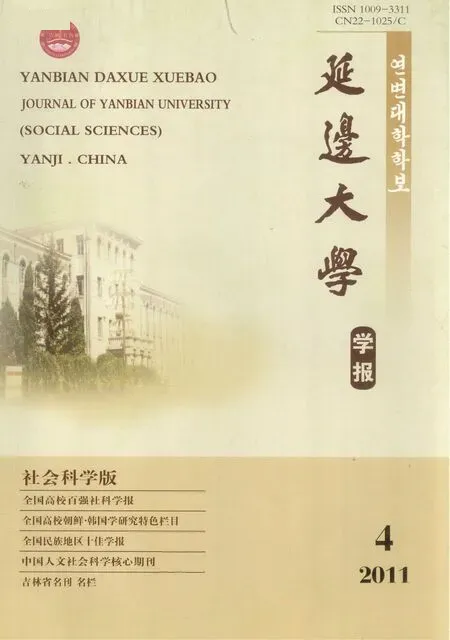“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
汪 长 明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上海200030)
“两个民族”理论(Two Nation Theory)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各异,是独立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实体,从而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应以此为基础,分别建立起独立的印度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这一理论由赛义德·阿赫默德汗(al—Sayyid Ahmad Khan)于1883年首次提出,后经旁遮普的诗人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Shaikh Mohammed Iqbal)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发展和集成。在实践上,“两个民族”理论与建立起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的社会运动——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相结合,成为巴基斯坦的立国之基和印巴分治的推动力量,从而导致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终结,最终导致了印度次大陆地缘政治版图的构造性断裂。巴基斯坦的建立,“是这一漫长穆斯林遗产的顶点”。[1]
一、“两个民族”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阿赫默德汗:“穆斯林民族论”
阿赫默德汗出身于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曾在殖民政府中任法官,他1870年退休后全力以赴从事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先驱。①他最先提出了伊斯兰教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和社会文化单位、穆斯林是区别于印度教徒的“穆斯林民族论”,对19世纪上半叶印度印、穆两大教派的关系和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阿赫默德汗的早期民族学说是“一个民族论”,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一个民族”。但是,在英国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推动下,印度社会的教派矛盾日趋激化,阿赫默德汗逐渐认识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前进了”。[2]1867年的贝拿勒斯论战使阿赫默德汗意识到,印度教徒同穆斯林不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向前发展,迟早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②他指出:“我现在认为这两个社团决不能通力合作完成任何事情。过去,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会因知识分子的鼓动而日益加深”。[3]
阿赫默德汗通过深入研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特点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指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各不相同,各自构成单独的实体,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他曾说:“我是一个穆斯林,一个印度的居民但属于阿拉伯种族。”[4]1868年,阿赫默德汗宣布,“建立‘印度穆斯林’的身份意识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后裔着想,必须巩固他们‘印度穆斯林’的身份”。[4]1882年,他在卢迪亚的一次集会上说:“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一起构成一个穆斯林民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5]1883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穆斯林民族论”的观点:“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所有英国人都离开印度,谁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两个民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平起平坐共享权力吗?肯定不能。必然是一个征服另一个,一个把另一个踢到一边”。“既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不能坐在一个宝座上,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分开?”[6]于是阿赫默德汗于1888年建立了印度爱国者联合会,又于1893年和英国人一起成立了穆斯林英印防卫协会,号召印度广大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划清界线,与国大党脱离干系。
阿赫默德汗是第一个发现并陈述了如下事实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并且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常常是冲突的。他一方面提出穆斯林是个单独的民族,有自己单独的利益;另一方面反对文官考试制度,主张行政人员由官方任命,并向英国政府请求任命时照顾穆斯林,给予他们更多的公职位置,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7]阿赫默德汗的“穆斯林民族论”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的理论先导。由于阿赫默德汗“是第一个预见到次大陆要分裂的穆斯林”,后人将他视为“巴基斯坦运动之父”。[8]
实践上,阿赫默德汗在印度次大陆发起了现代主义运动(或称“阿里加尔运动”,Aligarh movement),通过改进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使穆斯林摆脱在印度社会的不利处境。他的最大贡献是1877年在阿里加尔创立了穆斯林英语——东方语大学(即著名的阿里加尔大学)。这所大学培养了大批具有民族文化、伊斯兰复兴意识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干部,不少人后来成为反抗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领袖。阿里加尔大学的建立“被视为建立巴基斯坦这一要求的强力发动机”。[1]1870年,他创办了乌尔都语杂志《情感与道德醇化》(T ahdhibui Akhlaq),在印度特别是穆斯林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886年,阿赫默德汗创立了与国大党相对立的“全印穆斯林教育会议”,促进了穆斯林教育事业的发展。
阿赫默德汗提出“穆斯林民族论”的背景在于:(1)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失败,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政治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穆斯林恢复昔日莫卧儿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失落感和危机感成了印度穆斯林的集体意识。(2)穆斯林社会和印度教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差距的加大,使穆斯林上层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因而要利用宗教建立人为的壁垒,以维护其经济利益。(3)英国殖民者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导致印度社会印、穆两大教派发展不平衡,促使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往往以各自宗教信仰而不是集体身份来界定彼此利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不断扩大化、尖锐化。这三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印度社会教派利益的失衡和教派矛盾的加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穆斯林民族论”便因势而成、应运而生了。
阿赫默德汗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最先表达伊斯兰教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和社会文化单位思想的穆斯林。随着印度政治形势的发展,他的“穆斯林民族论”思想逐渐在印度社会传播开来并被广大穆斯林接受,最终发展成为印度穆斯林振兴的理论基础,对促进广大穆斯林的政治觉醒,促进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代现代主义权威法兹勒·拉赫曼(Fazlur Rahman)认为,“最先提出现代主义思想的人,很可能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9]伊克巴尔也称他为“第一个感受到伊斯兰教新取向的需求并努力付诸实施的现代穆斯林”。[10]
(二)伊克巴尔:“穆斯林国家论”
伊克巴尔是伊斯兰教现代改革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第一个提出穆斯林单独建国的穆斯林领袖。伊克巴尔进一步阐述了阿赫默德汗关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单独民族和文化实体的理论,提出建立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即“穆斯林国家论”。这一思想成为巴基斯坦的立国之本,伊克巴尔因此被称做巴基斯坦的“精神之父”。
伊克巴尔的社会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印度内部的问题是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频繁地爆发教派冲突,而国大党漠视穆斯林的事业。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确保印度和平的唯一出路是依据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亲和力重新划分这个国家”。(2)穆斯林要改变自己,必须依靠伊斯兰文化。“没有一个自由的穆斯林国家或者联邦,沙里亚伊斯兰法的实施和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多年来真诚的信念,而且我仍然相信这将是唯一的方法”。[11](3)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拥有民族自决权。[12]伊克巴尔说:“我们有七千万同胞,比印度的任何其他民众都更富有同质性。实际上,印度的穆斯林是唯一可以被恰当地称做现代民族的印度民族”。[13]“为什么印度西北部和孟加拉的穆斯林不能像印度的其它民族和印度之外的民族一样被认为应该拥有民族自决权呢?”[14]伊克巴尔感到印度穆斯林“需要获得主权以作为知识和文化重生的先导”。他的目标是通过民族自决,依据文化亲和力重新划分印度次大陆,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民族建立单一的穆斯林国家。
1930年12月,穆斯林联盟年会在阿拉巴拉德召开,伊克巴尔作为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讲话,集中阐述了他的“穆斯林国家论”思想,对印度穆斯林的未来政治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致词中强调,伊斯兰教不光是信仰体系和伦理道德准则,而且还是一种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他在对印度社会的宗教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后,认为印度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教塑造了印度穆斯林,印度穆斯林应该拥有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事实上,印度穆斯林是印度人民中唯一够得上在现代意义上被称做民族的人民。印度教徒,虽然几乎各方面发展都在我们之前,但还是没能取得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的同一性。”[15]他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要想实现社会的宗教(精神)和谐是不可能的。他强烈地驳斥了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的观念,认为那会使印度各民族人民的固有文化趋于湮没。他指出,“如果从单一民族这个概念出发来制订印度宪法,或者以英国式民主作为印度实施的原则,那无疑是在印度制造一场内战”。他明确提出,应在印度穆斯林聚居区建立一个“统一的穆斯林国家”,以保留穆斯林的认同及生活方式。他的最终目标是,“要使旁遮普、西北边境省、信德和俾路支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我看来,建立一个巩固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无论在不列颠帝国之内进行自治也好,或者脱离帝国自治也好,将是穆斯林奋斗的最终目标,至少对于西北印度的穆斯林应是如此”。[16]相对于阿赫默德汗的“穆斯林民族论”而言,伊克巴尔所构想的穆斯林国家具有了作为国家要素的领土属性,标志着巴基斯坦运动的正式形成。由于这次演讲,伊克巴尔因此被尊为“巴基斯坦国家的设计师”。[17]
1937年6月21日,伊克巴尔在给印度穆斯林“最伟大的领导者”真纳的信中说:“我以为,新宪法要把印度组成单一联邦的想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只有把穆斯林诸省组成为一个单独联邦……,才是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和平的印度,并把穆斯林从非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的唯一道路。西北印度和孟加拉的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像印度内外的其他民族一样,也能享有自决权呢?”[18]这时,穆斯林联盟不仅在舆论上而且在理论上已经为印巴分治做了充分的准备,行动上也加快了分治的步伐。1937年10月,穆盟领导人在勒克瑙会议上首次宣布穆盟“赞成印度完全的民族和民主自治”,对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给予明确支持。
伊克巴尔对巴基斯坦建国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他最早提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并论证了其合理性和可能性;他说服真纳接受把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作为政治目标;他的“穆斯林国家论”成为巴基斯坦建国理论——“两个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来源。关于伊克巴尔的理论贡献,《巴基斯坦简史》是这样评价的:“他比任何其他穆斯林政治领袖都看得远些”,“他给穆斯林指明了新的前景,为他们的信仰提出了理论基础。他的理想是按照伊斯兰教义的真谛来建立一个社会”。[18]
(三)真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论
真纳是19世纪上半叶印度穆斯林独立运动的领袖,他接受并继承了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思想,并集成了自巴基斯坦立国运动以来的穆斯林独立运动思想,创立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政治学说。从1915年起,真纳任穆斯林联盟常任主席,领导该组织为在印度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努力。真纳对于巴基斯坦的贡献在于,他把作为观念形态的“穆斯林民族”经由公共的想象共同体变成了社会实体,领导次大陆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走向成功——亲手缔造了巴基斯坦,被称为“巴基斯坦之父”。
伊克巴尔在1937年3月至10月间多次给真纳写信,提出“为了穆斯林印度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必须重新划分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并暗示“实现这一要求的时刻已经到来”。[5]真纳在伊克巴尔的思想和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中,发现了伊斯兰认同,构建了一种伊斯兰的使命和骄傲。他通过对“印度宪政问题的小心实践和研究”,最终接受伊克巴尔的“结论”,[14]并将伊克巴尔当做自己的导师。在1938年4月伊克巴尔辞世时,真纳致词指出:“对我而言,他是一位私人朋友,一位哲学家和导师,是我灵感的源泉和主要的精神支柱”。[16]
1940年,随着穆斯林各地方组织相继加入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穆斯林中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巩固,真纳审时度势,正式提出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论,主要内容包括:(1)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真纳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属于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和概念上的两种不同文明,他们生活的各方面都是不同的”。[19]他于1940年1月在伦敦的《时代与潮流》杂志上刊文指出:“必须制订一部承认‘两个民族’的宪法,这两个民族必须分享对于自己共同的祖国的管理权”。[20]1940年3月,他在穆斯林联盟的拉合尔会议上发表的主席致词中特别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不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们并不是宗教,而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能永远在一个共同的国家中发展那是梦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哲学、社会习俗、文学……把两个这样的民族束缚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中,一个占少数,另一个占大多数,一定会导致日益增长的不满和为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所可能建成的任何机构的最后毁灭”。[21](2)西方议会民主制不适合印度。真纳认为,“印度有许多的民族……它们的起源、传统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三分之二的居民信奉各种形式的印度教,七千七百多万人是穆斯林。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狭义的宗教方面,而且也包括法律和文化方面”。这种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体制,产生的是多数派印度教徒的统治。因此,以单一民族的国家概念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体制完全不适合印度,而且它是强加在印度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疾病”。[22]真纳认为,印度的政治前途是走宪政道路,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制度。(3)穆斯林要求民族自决权,应该建立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片领土”,[23]“印度穆斯林有无可否认的民族自决权”。[24]他认为,“无论根据何种民族理论,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家园,必须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给予其主要的民族单独建国,把印度划分为几个自治的民族国家。这样,这些民族国家之间就没有必要相互为敌了”。[22]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说:“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
实际上,真纳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段渐进式的发展历程,他最初的政治倾向是“坚持印度的统一、平等和独立高于他们的民族和宗教身份”,[1]主张通过民族团结(印穆联合)实现在英帝国范围内谋求自治,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色彩和浪漫主义的政治情怀。他曾断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随着印度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圆桌会议的失败,真纳逐渐放弃了寄希望于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自觉上,他转而致力于通过开展合法斗争争取实现穆斯林自治。随着印度社会印、穆矛盾的不断加剧,真纳在借鉴伊克巴尔等人的穆斯林国家学说的基础上,终于放弃了早期的政治理想,走上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道路,并最终成长为一位穆斯林民族主义者。③他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理论是这一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二、“两个民族”理论的政治实践——印巴分治
1906年 12月 30日,代表穆斯林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成立,标志着印度穆斯林开始以集体身份进入印度政治的主流。穆盟“被认为是1940年前在英印领导穆斯林利益运动的组织,由它开始倡导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在伊克巴尔和真纳等领导人的推动下,穆斯林联盟“在南亚穆斯林政治化过程中充当了先锋角色”,[1]特别是1937年举行的省议会选举,导致穆盟与国大党彻底决裂。从此,南亚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道扬镳、各分东西的时代正式到来,穆斯林国家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指日可待。
(一)“巴基斯坦决议”
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举行年会。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联盟领导人声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存在巨大而尖锐的分歧,要使他们继续统一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就会危机四伏。真纳在1940年3月22日的即席演讲中指出:“印度存在的问题不是教派之间的问题,而显然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也只能按此来解决”。“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印度划分为自治的民族国家,让两大民族各有自己的祖国”。1940年3月23日,A·K·法兹勒—乌勒—哈克提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历史上称这个决议为“拉合尔决议”(Lahore Resolution)或“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 Resolution)。④决议宣称:“任何宪法方案在这个国家都无法实施,也不会为穆斯林所接受,除非它是按照下述基本原则来制订的:地理上毗连的诸单位划分为若干区域,这些地区的划分应作必要的领土调整,俾使穆斯林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地区,如印度的西北地带和东部地带,能够组合成为独立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各组成单位将实行自治并拥有主权”。[18]如果说这个决议还没有明白地说明即将设计的分离政体巴基斯坦的范围,那么,1942年初,真纳对康帕兰德教授的那段谈话说得就清楚明白了。他说,巴基斯坦必须是“一个穆斯林邦或者几个邦:在印度的一边,由西北边省、旁遮普和信德组成,另一边是孟加拉”。[21]
巴基斯坦决议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它已经不再满足于提印度全体穆斯林的特殊国籍问题,而是通过了关于把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划分出来建立一个特殊的国家的决议。当时的媒体和人们普遍认为,巴基斯坦决议“等同于要求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1]从此,“穆盟在单独建国问题上走上了不归之路”。[25]在拉合尔会议以后,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们声明,为建立巴基斯坦而斗争是它的主要目的。这是由分治思想向分裂行动跨出的最为至关重要的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对立就发展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分裂的推进器已经启动,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它停止下来。
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巴基斯坦的问题,从此,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不再是少数政治活动家头脑中的模糊概念,而成为穆斯林奋斗的目标。会议后,真纳(这时已被穆斯林称为“伟大领袖”)对当时孟加拉首席部长说:“伊克巴尔现在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他还活着,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正是他要我们做的事,他一定会觉得高兴”。[26]他在一次讲演中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巴基斯坦的建立”,表明了穆斯林为建立巴基斯坦的勇气和决心。
至此,穆斯林联盟已经把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孟加拉东部,穆斯林联盟地方组织的成员已经增加到几十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有反帝情绪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以前认为联盟的领导不为独立而斗争,所以没有参加联盟,自从联盟公开发出为独立的巴基斯坦而斗争的声明后,这些人都参加这个政治组织,联盟的声势无疑大大地增强了。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巴基斯坦的思想已经不再是早期穆斯林学者停留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梦想了,它在穆斯林当中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二)“八月建议”
自二战开始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希望得到印度各族人民的合作,以便赢得这场战争。刚开始,欧洲战局的发展令人忧虑,德国长驱直入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以及法国投降的残酷现实都向印度资产阶级发出一种警报:法西斯的危险很快将波及印度。1940年7月,在浦那举行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国大党大多数领袖表达了支持英国政府参战、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立场。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大党准备在英国发表战后给予印度独立和成立负责的国民政府的宣言以后,就立刻和英国当局合作。[27]为了取得印度各派势力的合作,总督林立兹哥爵士(Lord Linlithgow,1887-1952年)于1940年7月放风说战后将移交政权,但又在1940年8月8日的答复(即“八月建议”)中宣布:“英国政府不会考虑把他们目前对印度的和平和福利所负的责任移交给任何一个其体制为印度国民中多数有势力人物所直接否认的政府”。[18]拒绝对国大党作任何让步。但是这个答复中对以穆斯林联盟为代表的少数党派的要求却作出了承诺,保证“没有他们的同意,不草拟宪法”。
“八月建议”不仅像圣雄甘地所指出的那样:“扩大了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裂痕”,[21]而且加深了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之间业已形成的隔阂。穆斯林联盟对于未来宪法的制订和执行必须得到它的同意和赞同这个保证感到满意。它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明白宣称:“印巴的分治是解决未来印度宪法最大难题的惟一途径”。[18]
国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主要原因是英国拒绝宣布“印度的完全独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局对人数较少的教派作了保证”。1940年10月,甘地宣布开始公民不合作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有2500—3000名国大党人被殖民政府逮捕,并以违犯“印度国防法”的罪名交付法庭审判,国大党几乎全部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到1941年底,国大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已经明显削弱了。[28]从此,次大陆以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为主要政治力量的两大政党在领导各自所代表民族解放运动、分裂印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印巴分治已经不可避免。
(三)英国撤出印度与印巴分治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预感到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将难以为继,决定撤出印度。1945年,总督韦维尔爵士(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与国大党以及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谈判,未能就英国撤离的时间表和此后的印度政治地图达成共识。1946年的一系列选举,进一步强化了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的政治地位,刺激了两党的政治话语权争夺。随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极分化增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化也在加剧,英国人试图劝说他们达成某些都能接受的框架。印度事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勋爵(Pethick Lawrence)率领的英国议会代表团,努力让印度领导人在印度联邦制式的独立基础上团结在一起,允许各省享有高度自治权,自己决定他们最终的政治前途。1946年5月16日,艾德礼(Clement Attlee)政府公布了解决印度问题的“内阁使团方案”(the British Cabinet Mission Plan),方案设计了一个中央权力比较微弱而各省享有较大自治权的联邦体制,希望既能维护印度的统一,又能满足穆斯林的自治要求。虽然两党早期都接受了这些建议,但后来都加以抵制。英国工党政府意识到,继续留在印度是不可能的。1947年2月20日,首相艾德礼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决心采取必要措施,最迟不晚于1948年6月把政权移交给印度人。英国已经江山不保,所以着手实施“撤出印度”方案。
为了让撤离更加顺利,1947年3月,艾德礼提名蒙巴顿爵士(Louis Mountbatten)担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到任后,发现次大陆的政治危机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他在同印度各政党领导人进行斡旋和谈判后,深感局势比预计的危急得多,于是决定提前移交政权。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史称《蒙巴顿方案》(the Mountbatten Plan),主要内容为:(1)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英国分别向二者移交政权。(2)在新成立的两个国家的国界未作最后确定前,先就孟加拉、旁遮普的划分及其归属以及信德、西北边境省和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县的归属问题分别进行投票。(3)投票结束后,将印度制宪会议分为印度制宪会议和巴基斯坦制宪会议两部分,由它们分别决定两个国家的未来地位。(4)授予各土邦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的权利。如果不愿意加入,可以保持与英国的旧关系,但得不到自治领的权利。(5)1947年8月15日为移交政权的日期。[29]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然一开始对《蒙巴顿方案》不满意,但最终都正式通过决议,宣布接受这个方案。[30]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方案》,规定在同年8月15日前结束对印度的统治,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在完成分治的相关法律手续后,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真纳在他的故乡卡拉奇宣誓就任巴基斯坦自治领首任总督;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尼赫鲁成为印度首任总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建立,标志着英国在印度长达19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巴基斯坦的建国理念——“两个民族”理论实现了从早期穆斯林学者的一种政治理想到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现实转变。
三、“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的相关性
“两个民族”理论是英国殖民统治背景下教派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衍生品”。本来,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应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政治任务,需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教派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二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从合作走向了反目,并最终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两个民族”理论是否具有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普适性,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除了英国一以贯之推行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外,国大党的教派主义色彩及采取的排他性政策,是导致印度社会两大政党和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不断激化,并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地步的关键因素。首先,国大党在指导思想和实践方面存在偏差和失误。早期国大党领导人多数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他们对印度社会情况了解得不够透彻,对两大教派矛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虽然国大党强调自己奉行的是世俗主义原则,代表的是印度全体人民的利益,但事实是,该党是以印度教徒为主体成分的党派,在政策执行上不可避免地首先维护的是印度教徒的利益,对广大穆斯林的特殊性不够重视或重视不够,因而难以摆脱印度教本位主义色彩。其次,由于印度教徒占人口的“压倒多数”(3/4),国大党在执行政策时,为了获取足够的“政治选票”,必然首先要争取广大印度教徒的支持,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而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忽视穆斯林的利益和诉求,使得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最终演变成印度教的复兴运动。国大党最终发展成了集形式上的世俗主义与实质上的教派主义、形式上宣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与实质上扮演的是印度教复兴运动的代表相结合的“奇异复合体”。对此,《今日印度》是这样评论的:“在整个近代民族斗争的任何时候,甘地都可以把国大党的政策转为印度教的革新运动(如在1932—1933年斗争的危机中),也可以把后者变为前者。因此,国大党精选的领袖和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要代表,始终是以印度教复兴的积极领袖的姿态出现的”。国大党的日趋去世俗化、印度教化,是穆斯林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并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重要动因。如果说“不合作”运动是印度教的,那么,巴基斯坦运动就是伊斯兰教的。⑤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民族”理论的诞生与国大党推行的教派化政治路线息息相关。
由于民族是一种“对他而自觉为我”的社会分群形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是被想象成范围有限、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1]因而,民族建构过程中具有“指标意义”的应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共同体被想象的方式”。作为民族的信条,民族主义的内涵包括:一种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建立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意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超越其他任何对象。[32]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建国进程、一种理论信念、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共同体认同。具体到“两个民族”理论上,应该认识到,印巴分治是两种——而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阿赫默德汗、伊克巴尔和真纳等早期印度穆斯林学者,同时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主张和政治学说对穆斯林民族塑造,推动巴基斯坦立国运动从一种理想信念走向政治实践,进而最终建立起穆斯林民族国家——巴基斯坦而言,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印巴分治至今已有60多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两个国家存在的事实已经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无论是按照世俗主义原则建立“大印度联邦”的设想,还是依据“两个民族”理论在次大陆建立单一的穆斯林民族国家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历史证明,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计划”从来就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能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其本人最终都对这一设想进行了自我纠偏。随着印巴分治、次大陆分裂,这个以印度文化圈为基础、以印度民族为主体的“大印度联邦计划”彻底破产。事实是,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未实现过统一,莫卧儿王朝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是统治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而次大陆历史上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意识”。正如马克思在《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1853)一文中所指出的:“印度社会完全没有历史,至少没有被公认的历史”。⑥“印度失掉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的世界”。[33]
关于“两个民族”理论的合理性,毋庸置疑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理论对巴基斯坦国家建构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对南亚穆斯林(至少对巴基斯坦穆斯林)身份的塑造和穆斯林共同体(乌玛,Ummah)的形成提供了观念上的能量供给,有利于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建构。“巴基斯坦的建立本身就是承认次大陆穆斯林是一个独立民族的结果”。[34]在此意义上,“两个民族”理论成为了巴基斯坦国家的生命线,是其立国之基。这一理论还是印巴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的症结所在。克什米尔问题是检验巴基斯坦国家生存的合法性和印度世俗主义建国原则及其建国理念——“一个民族”理论的试验场,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
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功能性缺陷。首先,根据宗教信仰来划分民族,并以此为依据成立国家,这在理论上是不合逻辑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彻底的。即便仅从宗教的因素界定,巴基斯坦虽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人口主体的国家,但事实是,如今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比巴基斯坦全国的人口还要多。再次回溯到印巴分治,审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由于民族迁徙引起的教派仇杀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无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背井离乡离开自己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迁移到对方国家。次大陆两种民族理论、两种建国理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破坏了次大陆历史形成的宗教分布格局,割裂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地理构造、资源分布和经济联系。其次,“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同质性。“民族—国家”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国家的单一民族性。考察当今世界的国家形态,不难发现,是多民族国家而非所谓的“单质化国家”(单一民族国家)构成国家结构的主体。实际上,民族与国家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性。民族是一个文化、心理和社会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联系,而国家则是法律和制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以及基于该权力政治上的主权原则。海斯指出:“国家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民族却主要是文化性的”。如将二者统一在一起,势必导致民族主义对国家结构体系的冲击,极易催发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因此,这一理论缺乏合理性的一面,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普适性。否则,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以多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将发生结构性重组,这无疑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地震。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南亚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巴继续保持政治对立、军事对峙、外交对抗,并不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继续围绕建国理念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多的现实政治意义,和平、发展与合作应该成为印巴之间的首要利益和共同政策取向。
注释:
①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最主要的人物除北印度的阿赫默德汗外,还包括孟加拉的阿布杜尔·拉蒂夫和赛义德·阿米尔·阿里。这几位早期穆斯林学者都提出过“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属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学说,其中以阿赫默德汗的“两个民族论”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②这一年,贝拿勒斯(Benares)一些著名的印度教徒发起运动,要求废除在法庭使用波斯书写体的乌尔都语,代之以天城书写体的印地语。他们认为,乌尔都语源于穆斯林,代表的是伊斯兰文化而非印度文化。印度教徒以印地语代替乌尔都语实际上是拒绝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语言之争对阿赫默德汗触动很大,因为他一直将乌尔都语看做联系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的文化纽带。
③促成真纳政治思想转变的直接原因,一是1937年大选中获胜的国大党采取了排他性的政策,加剧了印穆矛盾;二是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理念在印度广大穆斯林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同。
④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巴基斯坦日。
⑤两大政党在斗争策略上有根本分歧,印度教徒的政治代表甘地主张“非暴力”,而穆斯林则主张“圣战”。
⑥马克思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是一部神话史;其次,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是一部殖民史;再次,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印度,它的历史是一部分裂史。
[1] [巴基]伊夫提哈尔·H·马里克.巴基斯坦史[M].张文涛,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17,114,131,129,11.
[2] R.Symonds.The Making of Pakistan[M].London:Faber and Faber,1951.31.
[3] Sheikh Muhammad Ikram.Modern Muslim India and the Birth of Pakistan(1858-1951)[M].Lahore:Shaikh Muhammad Ashraf,1970.32.
[4] Mohamed Abdulla Pasha.Sir Syed Ahmed Khan:His Life and Times[M].Karachi:Ferozsons(Pvt)Ltd,1998.126,153.
[5] [巴基]G·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M].袁维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50-251,223.
[6] 张玉兰.论真纳的立国与治国思想[J].南亚研究,1992,(2):52.
[7] 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77.
[8] B.M.Chengappa.Pakista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olitical Evolution[J].Strategic Analysis,Vol.26,No.12,2001.
[9] Fazlur Rahman.Islam&Modernity:Transform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50.
[10] Muhammad Iqbal.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of Iqbal[M].Lahore:Shaikh Muhammad Ashraf,1964.277.
[11] Sandhya Chavdhri.Gandhi and the Partition of India[M].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rivate Ltd.,1986.49.
[12] Manzooruddin Ahmad.Iqbal’s Theory of Muslim Community and Ialamic Universalism[EB/OL].http://www.allamaiqbal.com/publications/journals/review/oct82/9.htm.
[13] F.K.Khan Durrani.The Meaning of Pakistan[M].Lahore:Shaikh Muhammad Ashraf,1946.150-167.
[14] Akbar S.Ahme.Jinnah,Paksitan and Islamic Identity——The Search for Saladin[M].New York:Routledge,1997.74,76.
[15]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theall-India Muslim League 29thDecember,1930.”Speeches,Writings and statement of Iqbal.Latif Ahmed Sherwani.Lahore:Iqbal Academy Pakistan,1995.26.
[16] Richard Bonney.Three Giants of South Asia:Gandhi,Ambedkar and Jinnah on Self-Determination[M].Delhi:Media House,2004.82-83,84.
[17] S.A.Vahid.Introduction to Iqbal[M].Karachi:Pakistan Publishing House,1954.40.
[18] [巴基]M.A.拉希姆,等.外国统治和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兴起[A].I.H.库雷希.巴基斯坦简史:第4卷[M].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353,340-341,354,35,358-359.
[19] V.P.Mahajan.A History of India,Vol.3[M].Delhi:S.Chand&Company Ltd,1980.318-319.
[20] [英]赫克托·博莱索.真纳传[M].袁维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32.
[21] [印]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印度通史:第4册[M].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1071,1073,1069-1070.
[22] Jamil-ud-din Ahmad.Some Recent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Mr.Jinnah,Vol.1[M].Lahore:Shaikh Muhammad Ashraf,1952.129-131,177-180.
[23] David Gilmartin.Partition,Pakistan,and South Asian History:In Search of a Narrative[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4,1998.1068-1095.
[24] R.J.Moore.Jinnah and the Pakistan Demand[J].Modern Asian Studies,Vol.17,No.4,1983.529-561.
[25] 程瑞声.南亚的热点——克什米尔[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43.
[26] Iqba.New Dimensions——A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and Rare Iqbalian Studies[M].Lahore Milestone Publishing House,2003.410.
[27] [苏]巴拉布舍维奇,季雅科夫.印度现代史(上册)[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三联书店,1972.646.
[28] D.G.Tendulkar.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6[M].Bombay:Popular Prakashan,1953.1-20.
[29] V.P.Menon.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M].Hyderabad:Orient Longman Limited,1957.371-402.
[30] V.D.Mahajan.History of Modern India,1919-1982,Vol.1[M].New Delhi:S.Chand,1983.350.
[3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6.
[32] Carl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
[33]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5.
[34] [巴基]赛义德·穆罕默德·德基.陆水林,译.巴基斯坦民族[J].民族译丛,198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