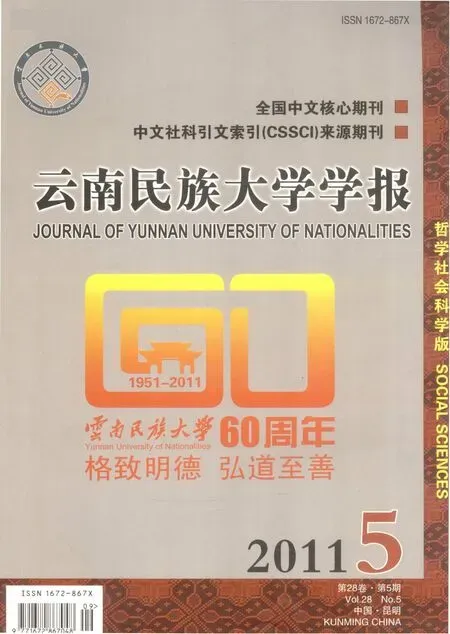道家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忧思
张尚仁
(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哲学作为人类存在方式及其价值的反思,所思考的首要问题是人类生存的问题。道家哲学认为,人类生存存在深沉的危机,这一危机深藏于人的自然本性与人为生存而人为的内在矛盾之中。自人类产生以来,这一矛盾使人类历史呈现“失道”过程,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道家哲学的使命,就是要人类正视危机,找出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化解危机的途径,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理论。
一、人性堕落导致人类生存的危机
按道家哲学,人来自自然,因而人本性自然。但自然产生的人,在其生存的过程中,却一再以人为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同时又改变其它事物的自然本性。结果,人和万物都离道越来越远,从而导致人类生存的危机。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悲叹:“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39章说:“万物得一以生”,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得到唯一的道的作用才产生和生存。如果背离道,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1](第39章)也就是失道必然导致灭亡。所以,“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1](第23章)任何事物的生存必须同于道和德,失去了道和德,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存危机。得道生、失道亡,这是必然的,人类也不例外。人类要同道而生,只能自然无为;但人要取得生存条件,又要人为。人为的结果是失道,失道的结果是灭亡。这样一来,人也就为生存而走向灭亡了。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人类循道而生之后,其生存的历史却是一个失道的过程。“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1](第17章)这里将把历史按领袖和民众的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当于现在说的早期氏族社会。按老子的观点,越是符合自然状态就越与道相合的,原始时代最接近自然,因此这个时代是最好的。第二个阶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部落时期,即中国上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汤、禹时代。这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的区别在于:在第一个阶段百姓只知道有一个头领,头领和百姓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在第二个阶段,头领成了百姓的治理者。虽然如此,但他们和百姓的关系,就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一样。头版对百姓是“亲之”;百姓对头版是“誉之”。对这个阶段,老子也是赞美的。第三个阶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进入阶级对抗的社会。对于这个阶段,老子从统治者在经济上压榨、政治上胡作非为、生活上奢侈淫欲揭露了“民”与“上”的尖锐矛盾。第四个阶段说的是老子生活的时代。其时,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1](第53章)那时的统治者,宫殿外表十分辉煌,然而,里面却极其腐败,农田己荒芜,仓库已空虚,官服却很华丽,官员佩带锋利宝剑,美食也已食厌,个人财产多得用不完。此类人只能称为盗魁贼首!这都是违背道造成的恶果啊!这样下去,结果确实堪忧。
对老子描述的历史发展阶段,庄子作了更细致的剖析。在《缮性》篇中,他将从古到今人逐步丧失自然本性的过程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2]那个时代,人没有自己的作为而随顺自然。第二个阶段,人开始有自己的追求, “是故顺而不一。”天下虽然和顺,但已不那么纯粹了。第三个阶段,社会开始有了争斗,以武力平息争斗后,一方服从另一方,那是“安而不顺”了。第四个阶段,用人为规范去治理天下,民心舍弃自然本性而由欲望驱使,“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天下不能安定了。第五个阶段,“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统治者用花言巧语来粉饰,用旁征博引企图增益。到最后一个阶段,“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百姓开始迷乱,已经无法回归到纯朴自然的本性了。对此,庄子深为忧虑:“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他看到,从古到今,世风日下,现在是正道受阻,伪道盛行,一代不如一代。
在《庚桑楚》篇中,庄子写道:“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3]人人逐利心切,为此儿子杀死父亲,臣子杀害君主,光天白日抢劫,正午挖墙行窃。乱世的根源,必定发端于尧舜时代,其危害要延续到千年之后。千年之后,世上必定会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庄子的这一预言,读之使人有振聋发聩之感!
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认为,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离道越来越远,人类的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由此看来,历史是倒退的。
对于历史的总体趋势是进步的还是倒退?其实是历史研究中远未定论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的争论更趋尖锐。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口膨胀和人类平均寿命延长的今天,人类将面临灭亡的预言却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而是被更多研究者认为是现实的危险。例如,《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认为,现代化是人类通向灭亡的“单程车票”。据西班牙《阿贝赛报》2010年6月29日报导,澳大利亚著名科学家弗兰克·芬纳在《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指出,受人口过剩、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将在一个世纪内消亡,人类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出补救。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0年10月13日亦报道说,20年后人类需要两个地球才够用。如果科技进步的最后结果是人类的消亡,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大倒退呢?道家在古代即提出人类要注意历史倒退的警告,对我们警惕历史倒退的危险无疑是有益的。
二、人类陷入生存危机的内在根源
按道家哲学,道生万物,万物循道而动,形成井然有序的世界。人也是道运行的产物,那么人也应是循道而动的。为什么道产生的各种事物都服从于道,而在人的世界中又会产生“失道”和“不道”呢?从道家经典看,道家是认识到这个难题并作出了回答的。
老子看到,天地的生存、万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有所不同的。“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第7章)天地因不必依靠自身活动来维持生存,所以能“天长地久”。天地中的万物则必须依靠其它事物提供的条件才能生存,如果不能提供生存条件,自然界中的事物也会灭亡。人与万物相比,其生存方式更有特性。人不像其它事物能现成地利用自然物而生存,还必须用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事物,这就是“人为”。人的生存是“有身”;以人为去改变自然获得的财物是“货”;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名”。这样一来,“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1](第44章)得到“名”和“货”是“身”即生存所必须的,但过分地追求却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孰亲”、“熟多”、“孰病”三个疑问,表明处理这几对矛盾的度是难于把握的。结果,人就处在既要服从自然又要以人为去改变自然的固有矛盾之中。这个固有的矛盾解决得不好,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这些概念表明的都是对人“身”即人的生存的伤害。如果这种伤害不严重,自然和人靠自身的能力还可以修复,人类也就可以持续生存;如果这种“祸患”越来越严重,成了“大患”,自然和人靠自身的能力无法修复,那么人类的结局只能是“无身”,也就是人类的灭亡。道家哲学对人类的生存表现出深沉的忧虑。
《道德经》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第13章)人为什么会有“大患”?根源在“有身”,就是有生命,能生存。如果无身,不需要维持生命,当然也就不存在危机了。有身有命,是人的存在,为了自身存在,必然地要以“人为”去改变自然。以人为改变自然,又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不符合道的准则。这样,人要“有身”即生存,就需要“货”和“名”;追求“货”和“名”,必然有“患”,即有“亡”的危险。“患”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做的只能是使“患”不致酿成“大患”,如果是“大患”,那就“无身”即灭亡了。这就是在人身上永远存在的道、自然和人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的永恒之“患”的根源。既要“有身”,又要限制“患”,使之不至发展成“大患”,也就成了道家哲学要破解的难题。
人所必然具有的“身”与“患”的矛盾之所以难于解决,甚至越来越向“大患”发展,原因在于人为维持“有身”所需要的“货”和“名”而产生的和“欲”和“智”。
人的生存离不开“货”和“名”,从而产生了人对“货”和“名”的追求。这就是人的“欲”。“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1](第46章)就是认为罪过没有比填不满的欲望更大的了,祸害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的了,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了。“欲”是酿成“大患”的罪魁祸首。“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第12章)正是这种“难得之货”、“金玉满堂”、“财货有余”、“欲上民”等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如不加以限制,势必造成人类“无身”即灭亡。
自然不能现成地提供人生存所需的“货”和“名”。人要靠“为”才能得到, “为”就要用“智”。对于“智”,道家是加以贬斥的。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1](第18章)伴随智慧而来的,只能是极为严重的弄虚作假。智慧危害天下,所以“绝圣弃智,民利百倍”。[1](第19章)《庄子·人间世》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4]认为道德的丧失,是由于追求名利;知识的显露,是出于争强好胜。名利,是相互倾轧的原因;知识,是争强好胜的利器。这两样都是凶器,不能无止境地大行其道。
道家贬“智”,是因为道生万物并规定万物的运行都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用不着事先用“智”去规划安排。人则不同,因欲得“货”和“名”而要用“智”。“货”和“名”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人就以为用自己的“智”去安排的事物才是最好的。可是,世上的事情本来就错综复杂,人的“智”并不可能认清事物的所有联系和长远发展,加上各人用来判断是非好坏的标准又是不同甚至相反的。“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5]如果根据个人的认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谁没有自己的标准呢?各人有各人的标准而导致没有公认的标准,各人都以为自己的安排是最好的却导致一团乱麻。由此看来,人人都用“智”,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去用“智”, “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5]
“智”的反面是“愚”。《庄子·天地》中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6]就是说,知道自己愚的,不是大愚蠢;知道自己惑的,不是大迷惑。大迷惑,终身不能理解;大愚蠢,终身不能觉悟。在《骈拇》中,庄子又说: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认为小的迷惑使人方向不清,大的迷惑使人本性错乱。愚和惑本来有不知不觉的意思,而自知自觉到自己愚和惑,本身就已经不愚不惑了;要是不能自知自觉到自己愚和惑,那才是“大愚”和“大惑”。
《庄子·逍遥游》说“小知不及大知”,《齐物论》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5]意思是小知识比不上大知识,大知识广博通达,小知识最多只能做到精细分明。小知小智追求的是“形而下”的片断知识,大智追求的是领悟“形而上”的大道。不专注于小知而专注大道,在小知面前看似“愚”,这样的“愚”从领悟大道来说正是大知识大智慧。只有小知识小智慧看似不愚,而从导致违背大道甚至最后使自身灭亡来说其实是大愚。着眼于大知而不羁于小知,看似愚,其实是大智。在这里,不去用智,并不是不要思想,不要任何知识,而是不炫耀智慧,不随意地按人的设想去改变外在世界,而要潜心探求事物的本来面目,顺应自然,不用人为去破坏自然。挖空心思去破坏自然的本来面目,从自然去攫取人所追求的享受,就是道家所贬的“智”。这样的“智”,实则“虽智大迷”。[1](第27章)
局限于“形而下”的“智”有可能是“大迷”,就是智中有迷。超越“形而下”的“智”而能达到的“大知”,是“形而上”之知,亦即哲学的领域。“形而下”的知,只是世俗的片断知识。世俗的知识虽然也是智,但只是“小知”。“小知”在一定领域中是有用的,但如果背离了“大知”,不仅不具有真理性,而且可能蜕变为“大伪”。道家的愚智论,确立了哲学是“大知”的领域。“大知”是探求人类生存这个最大的问题之“知”。这里隐含着哲学是探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理论的思想。
三、人类摆脱生存危机必须重新确立价值准则
道家哲学屡屡强调人为与自然对立造成的危害,虽然流露出对此无可奈何的感叹,但从全面的论述看,指出人远离本性,正是为了实现人性的复归,即实现“配天”、“同于初”或“人与天一”。
在《天地》篇中,庄子认为,宇宙的初始是混沌状态,万物因道而生成。生成的物有形体,形体内含精神,便各有各的特性和规则。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6]通过“性修反德”而“同于初”就是“复归”。“复归”是“道”的复归,指人世在运行过程中偏离大道之后再回复到符合大道的要求上来。
为了实现人性的复归,首先要求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要确立道的主宰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处理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物质世界的关系。《庄子·天运》中说到,孔子51岁时还不懂什么是道,就去请教老子。老子说:“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一个主宰,外界的影响就不会在你心中产生共鸣;如果你想作用的对象没有正直的品质,你想推行的主张在外界也行不通。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的精神世界中必须有一个“主”,这个“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核心价值准则。如果心中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就没有辨别对错、善恶、是非、美丑、好坏的标准。那么,在我们的心中应确立什么样的主宰或准则呢?毫无疑问,就是“道法自然”[1](第25章)的准则。也就是一切要以是否符合自然本性为判断的标准。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违背了这个准则,人类势必灭绝。
在精神世界中把握“道法自然”的准则,本来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道产生的,道也自然地存在于人和一切事物之中,道产生的人的精神其实是也就是道自身包含的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因而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本来就存在道的准则。“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彼固使彼。”[7]造物者所赋予人的,不是赋予人注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赋予自然的本性。人有哪方面的本性,就会往哪方面发展。“彼固使彼”指后天人为的事情,有自然的本性作为依据。
为了回复人的自然本性,确立人心中的“主”,现在的人必须认真进行修养。修什么?养什么?庄子都作了说明。“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庄子·徐无鬼》)修养内心的真诚,以顺应天地的实际情况。 “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庄子·让王》)修养心志的人会忘记形体,修养形体的人会忘记利益,追求大道的人会忘记心机。修养达到这个境界,就有望回复到人的本性。然而,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要人在精神世界中忘记形体、利益和心机,回复到顺应天地的真情,几乎是异想天开。世俗人遵循的违反自然本性的价值准则已中毒太深,面对这样的现实,庄子只能感叹:“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庄子·则阳》)人只知道尊重他们已经知道的知识,而不知道要弄清已经知道的知识中所包含的还不知道的知识,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这不是很大的迷惑吗!“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庄子·胠箧》)天下人都知道要追求他所不知道的,却不知道要探究他已经知道的;都知道要非议他所认为不善的,却不知道要非议他所认为善的,因此才会造成天下大乱。“求其所已知者”和“非其所已善者”,就是要对现实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从其源头上重新考察其是否正确,将颠倒的是非标准重新颠倒过来,这才是挽救人类的出路。
《庄子·庚桑楚》篇说:“夫外缚者不可繁而捉,将内闭;内缚者不可缪而捉,将外闭;内外闭者,道德不能持”。[3]在被外物牵累时,不应因为繁杂而紧张,而要心神内守;在内心被心事纠缠时,不应因为纠缠不清而烦燥,而要排除外来的干扰。如果内心和外界都受牵累而不能排除,就是有道和德的人也不能坚守自恃了。这就是说,人之所以失去本性,根本原因在于受到外物和内心的束缚。要复归本性,其途径是“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铲除志向的羁绊,解开心思的束缚,抛却德性的牵累,扫清大道的障碍。
四、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现实路径
实现人性的复归,精神世界要重新确立“主”,行动上总的要求则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第19章)在道家看来,“欲”虽然是“身之患”的根源,但欲又是“有身”即有生命所决定的,要有身有生命,就必然有欲。但“私”和“欲”都必须在“见素抱朴”的指导下加以控制,也就是不能超出维持生存的“道”的准则。因此,道家既不主张“无私”,也不主张“禁欲”。老子不仅不主张“无私”,而且认为要“成其私”。[1](第7章)“成其私”就是保存自我,成就自我。但人要“成其私”却不能损害其它事物“成其私”,因此人要“少私”。保存和成就自我本身是“欲”,所以道家不禁欲,而是要求“寡欲”。“寡欲”不是禁欲,而是不能纵欲。如果纵欲,超出“道”的准则, “患”就将成“大患”,结果是“无身”。对个人来说必然带来祸患,对人类来说则可能是灭绝。因此,欲望必须有节制。为此,“私”和“欲”都要设定一个限度,这就是“知止”。“知止不殆,长久可以”。[1](第44章)人类要摆脱危机长久生存下去,“知止”是唯一的现实途径。
人类怎样才能做到“知止”和“少私寡欲”?围绕这个问题,道家哲学提出一系列践行的途径。主要有:
一是“上善若水”。
摆脱危机,在思想意识上必须确立“道”这个“主”。但“道”太抽象,难于成为人的行动指导。因此,老子以水喻道,提出人必须具备的品格。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忧。”[1](第8章)这一章说水“几于道”,意为水的品性和道几乎相同。接着连续用了七个“善”,这七个“善”又和以水喻道相关联。将每一句都和水性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水甘愿安居卑下地位而与万物无争,人像水那样也就具有了谦让的德性;水的中心地能自然地聚集成深渊,人像水那样也能得到天下的归顺;水泽及万物从不分亲疏,人有也应像水那样对万物深怀仁爱之心;水在影照万物时总是如实地再现其形象,人也应像水那样表里如一忠信诚实;水是公平的象征,人处事也应像水那样坚持公平正义;水能在万物生长发育中发挥作用,人也应像水那样努力去成就各种事业;水顺应天时而来,人也应像水那样顺势而行动。水性与世无争,人像水那样与世无争,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这里说的“无忧”,也就是不必忧虑人类的灭亡。
二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以人为去创造“货”即生活资料。但人为又可能破坏自然,那是不是人在自然面前只能无所作为呢?道家哲学并不主张人在自然面前只能消极无为,而是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就是要求人只应遵循事物自然的趋势去辅助事物的发展,万万不可胡作非为。
道家哲学对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是有判断标准的。概括地说,顺自然之势的事是可为的;为人自身的目的而违反自然之事是不敢为的。有鉴于此,庄子在《马蹄》篇中,对伯乐相马驯马大加鞭笞,认为为马烙印、剪毛、削蹄、套上辔头、关进马棚,让马饿着、渴着、奔跑、列齐、鞭策等等,马被折腾得死了一大半。庄子在《应帝王》中讲了一个寓言:北海之帝忽和南海之帝倏到中央之帝混沌那里去作客,受到混沌的热情招待,北帝和南帝为了报答混沌的热情招待,说:“人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来给他凿出七窍来吧。”[3]他们为混沌每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混沌死了。这里寓意为,不以自然本性为标准而以人按自身要求为标准,尽管动机可能是好的,但造成的后果是事与愿违。
《淮南子·修务》对老子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帮五谷得遂长。”意为在认清水势东流,春华秋实的自然秩序的同时,人顺自然之势而为,才能使五谷丰登,人和自然得到充分的和谐。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观点,虽有限制科学技术发展之嫌,但对提醒世人注意技术的滥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确有先见之明。
三是“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
《道德经》强调:“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三宝”中,老子特别强调“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1](第67章)以慈为宗旨,人心和顺,团结一致,力量无穷,作战时进攻能取胜,防守能稳固。在“三宝”中特别突出“慈”,是因为“慈”属于人的内在的品德,和道的精神最为接近。慈并非专对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而是包括对世间一切事物都要施于慈爱。“慈”演化出许多优秀的品德,如仁慈、慈爱、慈祥、慈和、慈孝、慈悲、慈善等等。再扩展开去,还可推导出仁爱、祥和、和善、柔和、随和、和谐等。
第二项是“俭”。也就是勤俭节省,有爱惜、珍惜、保养、不浪费等含义。勤俭节省是一种美德,是我国传统的人生信条。这种美德,也是《道德经》十分强调:“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1](第59章)这里说的是:治理社会,包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要将爱惜和节俭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各种矛盾才能化解于萌芽状态。这本身就是重视按照德的要求治理国家的表现。这样,其它一切问题容易解决。其所产生的治国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国家也就能够存在。这一点,应该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国家也就可以长治久安。在这里,老子并不是将勤俭节省仅仅作为个人的一种美德,而是将它看做是治理国家,使国家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之一。
第三项是“不敢为天下先”。它有守柔、处下、谦让、不争等意思。 “不敢为天下先”与“慈”和“俭”是密切相联的。“慈”是对人对物都要有愛心和同情心,有了这样的爱心和同情心,也就不会去想和别人争斗。这本身就是不敢为天下先了。“俭”是节俭,少私寡欲,不奢侈,也就不必去与人争,即不必为天下先了。不敢为天下先是“示弱”,“示弱”的目的是“求强”。不敢为天下先不单纯是一种礼让,包括不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摆在众人前面的意思。这样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反而能成就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道德经》认为,现在的人很危险,“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发展下去,人类必然走向灭亡。
四是“去甚,去奢,去泰”。
《道德经》指出:“故物,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1](第29章)就是说,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前行后随也好、炎热寒冷也好、强壮羸弱也好、栽培损毁也好,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正因为圣人领悟到了万物自然的真理,所以总是努力去除过分的追求、奢望和享受。去除了过分的追求、奢望和享受,也就能“复归于朴”,也就是人性的复归。
道家哲学关于人类陷入生存危机的现状、根源、摆脱危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路径的论述,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一种基础理论。这一基础理论体现了哲学的根本价值,值得我们深思。
[1]老子.道德经[Z].
[2]庄子.缮性[Z].
[3]庄子.庚桑楚[Z].
[4]庄子.人世界[Z].
[5]庄子.齐物论[Z].
[6]庄子.天地[Z].
[7]庄子.列御寇[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