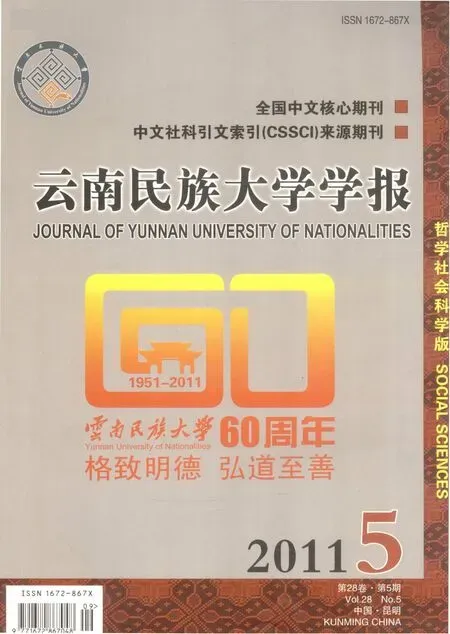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周竞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720)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了数千年封建王朝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国家理念在这一转型中受到强烈挑战,王朝国家的居民由臣民向国民的转变、王朝国家政治影响下的“王土”向主权国家领土的转变、王朝国家政治生活管理方式向主权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都成为王朝中国转型的表象。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进程中,主权国家时代的“中国”观和认同选择成为必然,中国国家形象也在西方社会自我形象的投射、在中国社会先觉者的焦虑中被模糊,并且不得不重构。
王朝中国的皇帝们一直将“天下共主”作为其追求的政治目标,皇帝手中之权属于特定的姓氏,皇帝对臣民称“朕即国家”,历代统一的中央王朝都承袭着“中国者,天下之中”的古老意识。在主权国家时代,王朝中国的“天下”成为一个边界不清晰的政治空间,传统的“华夷秩序”成为一个不具有清晰权利义务关系的秩序。于是,在王朝国家转型过程中,“华夷秩序”的“天下”观需要与“世界”观区别,并构建主权国家观。“……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 ‘天下’一身所兼之二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1]随着王朝国家转型的巨大变迁,传统的“华夷秩序”开始紊乱,“天下”二分,“世界”与“中国”界线分明起来,“中国”在“世界”中重新定位。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文称“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2]此论点破了“天朝上国”国家观念与对外关系的基本状况,其“中国”观显然还是局限于王朝中央国家观范畴。当王朝中国仍然沉浸于“华夷秩序”之中时,西方社会已将国家主权视为内外政治的关键和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当列强日益侵夺王朝国家权益使社会陷于危机之时,谋划构建具有独立地位的主权国家成为当时思想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华夷秩序”遭遇主权国家的时代,王朝中国开始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一、“中国”在世界地理空间的重新定位
“中国”在世界地理空间的再定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天下”观之下,“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在“世界”观之下, “中国”则是世界“万国”之一。“从利玛窦时代到乾隆时代,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古代中国对于异域 (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知识,已经从‘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3]。事实上,这种认识的转型到乾隆时代还仅只是一个开始,对“万国”政治格局的认知并未为全社会所把握,甚至可以说未真正落实到王朝国家管理的实际。从观念上来说,直到清末,大量的社会精英们仍然坚持着“天朝上国”的思想观念,只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畲、郭嵩焘和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开始在“国民国家”思想影响下发生转变。[4]沙俄对北方领土的侵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国家各种条约的签署,促成“中国”在“世界”中的重新定位实践日益深入。这种再定位进程中,西式的“国民国家”或“民族国家”观念开始日益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并很快占据思想之峰。于是,“中国”与“世界”通过条约签署、实力对决等多种方式,追求领土边界清晰化。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王朝中国的强邻沙俄在其向东扩张势力之时,就迫使王朝中国谋求双方边界清晰化,沙俄通过各种手段在双方边界清晰化过程中侵占王朝中国的领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俄于1689年签定的《尼布楚条约》视为“中国”在“世界”中边界清晰化行动之始,在这一条约之中规定了中俄双方的界河为乌伦穆河、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同时还明确了两国人民如何行旅等具体事宜。王朝中国边界清晰化的过程是其领土主权范围明确化的过程,也是王朝中国传统权益不断被强邻肢解的过程,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国家主权不断受到侵害,传统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性日益丧失。正因如此,到清末,“中国的维新派别无选择而只能想尽办法将清朝变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这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追求两方面的主权地位:一是对外主权:即国对国的对等权力;二是对内主权:即对既定领土的完全权力。而‘领土权 ‘(territoriality)则是决定这两者成立之关键所在。实际上,国力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一个无法掌控自身领土的国家是无法在国际间取得真正的主权地位。”[5]“中国”在世界地理空间的再定位过程,不仅需要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定位自身,而且需要确认领土主权,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着斗争、妥协、甚至交易,也带有极强的国家管理制度转型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王朝中国向主权中国转型进程中,对外关系由礼仪型向国际法型转变的过程。
二、“中国”人民的重新识别
人口是构成一切类型国家的根本要素,但是“人民”在主权国家条件下则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指向,涉及人们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中国”人民或国民的重新识别主要指王朝中国在处置其与欧洲各国关系进程中,日益涉及到与人民相关的权益问题,即“国籍”问题。最早与“国籍”相关的群体是华侨。20世纪初,南洋华侨经济力量的日益增强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引起荷属殖民当局的不满和恐慌,荷兰政府为此出台新的国籍法将整个爪哇华侨纳入荷兰籍,这一新法案的出台使数百万华侨被牵涉进来,一时演变为荷兰籍“中国人”与侨居爪哇的“中国”人民身份相关的重大问题。
在国籍意识确立和启蒙方面,留学生们贡献最大,他们纷纷著文,阐明公法、私法意义上的国籍法的区别,尤其对国际上出现的两种国籍法的原则:即出生地主义和血统主义的含义、区别以及各自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地宣传、介绍。还重点对各主要列强国家国籍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中国应早定国籍法的对策建议等,促使王朝末年的中国社会国籍意识日益提高和趋强,并开始认识国籍是国民身份的主要标志,是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主要依据。[6]1909年3月28日清王朝颁布《大清国籍条例》,详细规定了固有籍、出籍、入籍、复籍等原则,并配有实施细则。尽管《大清国籍条例》是针对荷属华侨而制定的,但对于国家转型进程中“人民”身份的重新识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帝国主义国家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王朝“中国”社会遇到了重大挑战,“华夷秩序”紊乱和王朝内部社会危机的频现,促使清王朝也在这一特定条件下开始以“大清国”、“中华帝国”、“中国”为他称。“天下”观被颠覆,王朝国家社会政治转型悄然发生,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启发下,王朝政治制度在走向终结过程中,提出了统一国家称谓问题。此外,王朝国家认同在保教保种氛围中被重构。1898年康有为就提出关于国家名称问题,“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皇上维新,尚统一而行大同……”[7]。王朝国家如何面对世界万国并称呼自己、形成认同,成为国家转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革命派“中国”认同的困境
正是在王朝中国转型中,革命派依据民族建国主义,寻找新的国家认同方向。1903年《游学泽编》10期刊出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提出:“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为了推翻清王朝政权,达成民族、民主目标,革命派也在国家名称上大做文章,在“排满”革命的形势下,他们宁认同于“支那”,而不认为于“中国”之称,“中国当蛮族入主之时,夷族劣而汉种优,故有亡国而无亡种;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亦唯有保同种、排异族而已。不能脱满清之羁绊,即无以免欧族之侵陵。居今日而筹保种之方,必先自汉族独立始。”[8]
革命者认同“支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将中国与“清国”相区别,“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诉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认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9]“太炎在东京创亡国会,日本警察询之曰:‘尔清国何省人?’答曰:‘我非清国人,支那人也。’是革命党人不承与清室有连甚显。此义扩充,影响到康梁一派。康为保国会于北京,先下一义曰:保中国不保大清,是康梁一派,亦欲别清于国也甚显。然则所谓国者安在乎?太炎自承支那人,为问支那国安在乎?如实考之,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葬支那,无所谓国,支那非清,复无所谓支那,然则国与支那,支那与清,走于一环,无能自脱,是直丐词而已。太炎所称支那人,特从权为之辞耳,支那固非其所愿依托也。于是持排满论者,谓欲亡满清,必先亡支那。”[10]循着民族建国主义的逻辑,有人对清王朝提出汉族主权,称“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为列祖列宗,讴歌而扬颂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而爱之?”[11][12]章太炎取“南明”永历皇帝被执之年为明朝亡国之年,又取崇祯帝自缢之日为明朝亡国之日,两相凑合,1902年在日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3]。1906年《同盟会军政府宣言》称: “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革命者不断宣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石敬搪、吴三桂之流,天下共击之。”[14]
在革命的话语条件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事实上指中国乃汉人的中国,革命派要光复的是汉人国家,因此,汉满关系在种族民族主义语境中被重塑,满人被视为汉人国家的侵略者。为了“排满”的需要,在革命者眼里满汉关系亲密度甚至不如日人,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一文中就称“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灿然要知。自国民言之,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棘羯,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湮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是日亲满疏,断可知也。”[15]因而多有驱逐满人至关外之议。
革命者既认为“中国”是汉人国家,那么汉满矛盾在革命者眼中被置于更关键的地位,似较之国际帝国主义的国家权益侵夺更为重要。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对此曾有透彻的说明:“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列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昔巴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痛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翦一长蛇,岂以为病?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6]
革命派民族建国的基本思路即“为救国,必须反帝;要反帝,必先反满,遂成为清末民初革命派民族思想的根本所在。”[17]虽然革命派大力宣传满汉对立,但是,当时的社会并非由汉满对立思想一统天下,满人御史贵秀就曾指出:“时至今日,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18]举人董芳三则称满蒙汉不过是同山诸峰、同水异流的关系:“盖亚洲之有黄种,若满洲,若汉人,洪荒虽难记载,族类殖等本支。如山之一系列峰也,水之同源异派也,禾之连根歧穗也,本之合株散枝也。一而数,数而一,既由分而合,讵能合而为分也。”[19]
有人亦撰文指出革命派民族建国理想的困境:“如曰中国不当无政府,因满人为异族,故当以汉人代满人,则此致尤谬。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民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仅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既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公理,故满人而欲满汉平等,实行大同主义,则当先覆爱新觉罗氏之君统;汉人而欲肮除虐政,诛戮满酋,当并禁汉人自设政府。使人人知革命以后,不设政府,无系毫权利之可图,而犹欲实行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否则人人到利己为心,即使满人可逐,岂非以暴易暴乎。”[20]
后人分析指出“对于以民族为基础,要求建国者,则称之为‘族国主义’,对于以国家为前提,要求境内人民相认同者,则称为‘国族主义’”[17]。若依此分析,在辛亥革命前,革命者将汉人打造成汉民族,主张族国主义,将汉人民族化的大范围认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似乎也借助了书写、印刷等技术,推动了汉族的想像,成功塑造并提升了汉民族的身份认同,重构了国家认同。虽然,这对动员革命力量有较显著的作用,同时,“五方之民”长期杂居共处的历史格局也挑战着民族建国主义理论,民族畛域的提出至少在特定地理区域和阶层,加深了社会的分裂,如武昌起义后,在满、汉民族关系上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地方出现仇满举动。例如陕西,在西安的革命党人有百分之八、九十都隶属哥老会,他们仇满情绪激烈,以至于同盟会无法控制局势。在商讨起事军名称时,同盟会主张为“秦陇革命军”,会党的人则主张称为“秦陇复汉军”,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循会党之意,定名为“秦陇复汉军”。这个名称本身就寓有很深的种族情绪。在武昌地区一度曾发生仇杀满人之举。一种是满族贵族和反动官吏在此环境下亦煽动满人仇汉。例如,福州将军朴寿把全体满人组织起来,凡旗人13岁以上男子,均给洋枪1支,子弹300颗,妇女则发给小刀1柄,以备与汉人决战,且于旗界内安设大炮,埋伏地雷,宣言必使全城汉民同归于尽。还有满人文楷者,组织杀汉党。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满汉之分,比如,辛亥革命后,花翎二品衔蒙古汉军八旗协领官前署建昌镇总兵清河、陆军粮饷局会办全川财政补用道泽宣等代表汉军八旗2万余人向中华民国汉军政府提出返旗归汉,原业归宗要求。[21]他们在满汉身份选择上更多受到社会政治氛围的直接影响。可以说革命派具有很强的汉文化优越感,主张以汉族同化诸族。在排满中动员、发展起来的是汉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在历经革命运动之后很大程度上成为华夏中心主义的替代物,为民初民族同化理论的形成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从历史事实来看,汉民族主义对底层社会的动员可能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普遍,据称黄花岗起义中,义军冲击督署衙门,义军与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时,有人便高呼: “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说完便中枪弹。[22]
四、结 语
革命派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推翻清王朝国家行动,借助民族建国理论发明和重构王朝时代的中国概念,将其仅仅限定于汉族,将清国与“排满”目标相联系,使用了清国、满族及汉族的压迫者的种族民族话语。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汉族的中国目标并未在革命后真正实现,而是受到传统“五方之民”格局的深刻影响,以至于民初不得不以“五族共和”来消弥社会分化的前景。因此,回到历史现场可知,革命派的中国观形成基于民族国家理论,但王朝国家的历史实际不断校正着其政治目标,使近代中国国家建构逐步符合“五方之民”数千年互动的历史现实。
[1]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梁启超.变法通议[A].饮冰室文集点校[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
[3]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建辉.从“中华”到“中国”——世界的转变到自我认识的形成[A].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多边文化研究:第1卷[C].北京: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1.
[5]刘擎.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6]许小青.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困境[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2).
[7]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A].康有为全集(第4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9]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满清的态度变迁[J].语丝,1924,(8).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11]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 [J].新民丛报,1903,(28).
[12]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0.
[13]耿云志.蓼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警告我汉族大军人[J].民报,1907,(16).
[15]章太炎.正仇满[J].国民报,1901,(4).
[16]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7]朱浤源.从族国到国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义[J].思与言,1992,30(2).
[18]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A].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A].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志达.保满与排满[J].天义报,1907,(3).
[2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57.
[22]王炯华.胡汉民评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