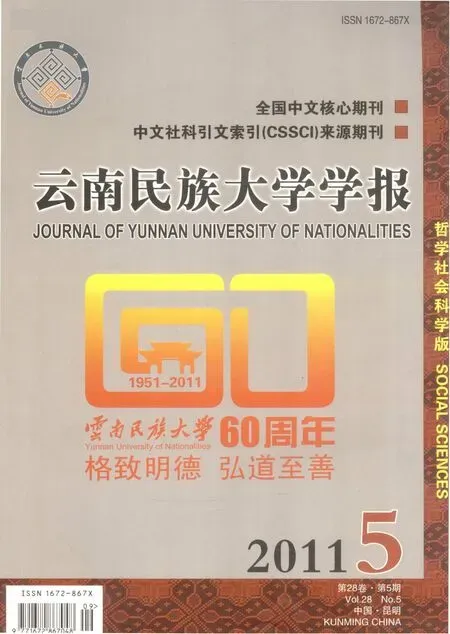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及其废置缘由考析
唐晓涛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和最终被裁撤的历史过程及政治经济背景,是明中期广西边疆地区局势变化,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以及官府和地方将领对狼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华南地区推广和变化。有明一代,广西西部的土司们与朝廷政治休戚相关,而由土司统领的数量庞大、极具战斗力的狼兵则是明朝廷最主要的军事凭依之一,在明朝的军事征伐史中,偏处广西中东部的大藤峡地区[1](P618,626)因为“猺乱”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东进狼兵最重要的集结地,在此地区建立的武靖州即是明朝在东部流官统治区设立的众多土官衙门中,级别最高的一个[2]。武靖州之设立、迁址以及最后的裁撤与明中期广西地方局势的变化、中央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密切相关,因此,对武靖州废立缘由的考析,可以展示出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华南地区推广和变化的重要侧面。
一、武靖州设立及迁址之缘由
明代,西江航道日益成为盐运及军事物资运输的枢纽,大藤峡地区因地处西江两大支流 (黔江与郁江)之交汇点而独具重要的财政及战略枢纽之地位,关连着明政府在两广的盐道及兵源、军饷运输通道之畅通问题。明朝国家对广西的治理是沿着西江及其支流而推展,西江及支流的沿山地带大量被称为“猺”(或“獞”)的土著,其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遂面临剧烈变动。在被迫与官府交集的过程中,山区土著把截江道索要日用品之类的活动被官府视为“动乱”,土著们也成为文献记载中的“猺贼”,此即文献记载中的“大藤峡猺乱”。成化元年 (1465年),朝廷命韩雍统率十六万大军前往大藤峡征剿,此举为“藤峡三征”之第一征。在军事行动之后,韩雍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将桂西的上隆土司州整体迁往大藤峡地区,将包括知州岑铎及其所部狼兵和家属“尽数发遣”,在浔州府这一流官统治区设置武靖土司州。武靖州的州址设于碧滩,碧滩地处大藤峡入峡口的献俘滩 (即驽滩)和出峡口的勒马滩之中,即正好位于峡江之中部。相对于两岸的峭壁悬崖,此地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坡地,所以韩雍建议在此设置土司衙门,筑立城堡,由狼兵专职垦田戍守,以把截道路,镇慑瑶人。由此可见,官府设置武靖州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利用狼兵及家属在当地屯耕,籍其力以防守峡江,从而保证峡江的畅通以便于官府对峡江的使用,一言以概之,即是为了控制大藤峡航道。
不过,狼兵事实上没有在碧滩长期驻扎,而是很快迁离了碧滩,嘉靖《广西通志》记载迁离的原因是在碧滩建州遏贼“不
果”[3](卷51《外志·土官属流沿革·武靖州》,P600)。即无法达到依靠狼兵屯耕以防御瑶人的目的。为什么不能达到目的?实地到大藤峡地区乘船沿峡向上逆行一趟,即可明白,碧滩的地理条件非常有限:碧滩周遭万仞壁立,层峦叠嶂,万山包围之中,碧滩面朝险急大江,背倚狭小坡地,且腹地纵深均为狭长高耸的山谷,并无多少田地可供开垦。后人测量据说是州城的遗址长仅136米,宽仅118米[4](P10),而以一家五口计算,岑铎带来的狼兵及家口约有万人之多,如此众多的人口很难局促于此一狭小的耕种空间。即是众多狼兵及家属无法在此安心屯耕。此其一。其二,还因为碧滩本为瑶人腹心地区,官军对瑶人作战时,瑶人散走群山,官府无论是设置营堡还是巡检司,还是武靖州衙门,在不能找到切实办法解决瑶人问题之前,数量极少的狼兵官军在如此险要的瑶人腹心地确实很难站稳脚跟。此前在其地所设之碧滩驿与思隆乡皆为瑶人所据,连衙门也不能建立[5](卷22韩雍《处置地方久经大计疏》,P244-5),嘉靖年间征大藤峡的将领翁万达和田汝成也称设置的营堡被瑶酋据用[1](P626)。
因此,武靖州治很快被移往他处。据嘉靖《广西通志》记载,武靖州先自碧滩移建于府城南之马流滩 (今桂平航运枢纽工程处)。浔州府地方志也沿用了此提法。从《殿粤要纂》的桂平县图看,此地为万历年间的军事据点马骝堡所在地。不过,顾祖禹对此说法存有疑问①刘茂真的《武靖州治考》(《广西地方志》2002第6期)一文对林富所言武靖州先后建在碧滩、犸骝滩、武靖村三地进行了考订,并得出由碧滩迁至马流滩的时间在成化十年,但他引顾祖禹所言以证明武靖州曾迁于马流滩则是误读了史料。[6](卷108《广西三·武靖废州》,P4885),在 《粤西文载》也没有州治设于马流滩的记载[7](卷12《左江土司志》,P651-2)。马流滩离府城太近并且地方也不够宽阔,既不利于控制瑶民也不便于狼兵屯驻,纵使曾经移至马流滩,时间也应是极为短暂。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武靖州治很快就迁至崇姜、大宣二里之间的黄绅岭,即今桂平市金田镇武靖村。林富记载迁移的时间是在成化十八年 (1482年)。田汝成在《断藤峡》中的记载及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考订,使我们可以对武靖州在此地的情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二人的记述如下:
昔韩公讨平藤峡,以碧滩盗贼充斥,乃筑营堡,开设州治,奏改岑铎部兵二千来任州事,寻复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间,为蓼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____岭、大冲诸山要路也,地广土沃,袤连大同、鹏化,可以控制诸蛮,藩卫郡治。[1](P627)
《城邑考》:州城,在府北渌江上。渌,亦作蓼。督臣韩雍委土知州岑铎所筑,有二门,周二里。又《土司考》:初,上隆州岑铎犯大辟下狱,韩雍建置武靖州,特请宥其罪,使迁部兵二千人世掌武靖州事,设流官吏目一员。……万历末州废为武靖镇,仍置兵戍守。[6](P4885)
蓼水即渌水,现称南木河,是浔江北岸最大支流。武靖州所驻地正处于蓼水中段,南可达驽滩,东可出大湟江,交通十分便利。而且正如田汝成所言,此一地区是通往紫荆、竹踏、梅领、大冲等大山的必经之路,向东北延伸即是大同和鹏化,这些山区正是瑶僮集结之地,故称其为“控制诸蛮”之要地。
武靖州治此次迁移后至最后被废,再也没有变动治所。据顾祖禹考订,州城周二里,有两门。时至今日,在武靖村仍然可见部分城墙旧基。笔者2006年10月在当地考察时,亲见村民正在为刚复建的城隍庙的开光庆典做准备。村中两位何姓老人称,因为武靖旧时是州城,所以才有城隍庙,一般的村是不会有的。何姓老人还告诉笔者称村南的南渌江边曾立有一根浮桥铁缆柱,此柱现存放于桂平公园中。笔者后来见到此缆柱,缆柱的洞口下方铸有如下铭文:
大明成化贰拾贰年岁次丙午五月朔日,创武靖州城池扵黄绅岭前,建浮桥,铸造缆柱。
钦差镇守两广司设监太监刘
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巡抚监察院右都御史宋
钦差镇守两广总兵官征浔州安远侯柳
□□□两广地方湖广按察使陶
□□□□□地方□□□□□
□□布政司左□□
浔州府知府马
广州右卫指挥使杨
浔州卫指挥佥事张
武靖州知州岑
由铭文可知,蓼水浮桥建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为沟通渌水南北两岸而建的浮桥,可以猜测建桥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军事需要,是作为从武靖州往南岸瑶人聚居的崇姜里派兵的通道。明朝经略华南地区的策略,在明初以抚为主,依靠当地土酋力量,到了明中期则转变为依靠狼兵进行剿杀,并依靠桂西土司的军事力量在当地戍守。为切实推行此策略,朝廷在梧州设立两广总督这一军事机构,并使其凌驾于两广行政机构之上。据《苍梧总督军门志》可以考知上述所记太监刘、总督宋、安远侯柳分别为刘倜、宋旻、柳景[3](卷1《历官》P19)。他们均为总督府的在任官员,武靖州之设置即是成化年间军事需要的结果,所以为军事目的建造的浮桥,其揽柱上全数刻上了这些军政长官的名字。表明武靖州事实上是处于两广总督军门的掌控之下,以防守大藤峡地区瑶人,特别是保证峡江之畅通为首务。
正因为如此,其时的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将武靖州作为桂东地区的狼兵大本营。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万祥在弘治十一年 (1498年)的一份奏疏中提出要将武靖州作为整个桂东地区的狼兵总部,规定桂东的土人,有愿为土兵者直接编隶于武靖州管辖之下,成为狼兵。[8](《明孝宗实录》卷139“弘治十一年七月壬戌”,P2421-2)可见,就明朝廷和广西地方官员而言,设立武靖州的最主要目的即是防止“猺乱”,所以武靖州的狼兵无论是守隘,还是守城,在这样的情境当中被赋予的角色非常明确——作为“猺獞”的对立面而存在,特别是狼兵驻守的隘口和营堡,事实上成为“民”与“猺(贼)”的分界点。
武靖州治迁至黄绅岭,事实上还落实了朝廷对狼兵的另一方面的使用意图。
由韩雍奏书可见,武靖州狼兵到达浔州后,朝廷要求地方官府给予狼兵及家属田地耕种,即如田汝成所言是“畀其地而资其兵”[1](P627),要凭借桂东地方的寥阔田地来换取土司狼兵的效力。事实上,奏书所言之“绝户田地”大部分是原为瑶人耕种而没有纳入官府征税范围的田地。那么,为什么要将瑶人的田地给予狼兵耕种?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朝廷和官府的眼中,武靖州这些移家世守的狼兵及家属之所以异于体制外的“猺獞”,在于“猺獞”是素不纳粮的,而狼兵狼民则向国家交粮纳税、具有“民”的社会身份,这是朝廷将武靖州的土司狼兵作为军事力量以维持桂东社会秩序之外,对其的另一种定位。前引韩雍的疏中已明确说明,迁至浔州府的狼兵及家属是需要向国家“报效粮米”的,表达了朝廷将狼兵作为国家的粮税来源之一的意图。事实上,在明朝中后期,大量狼兵东进,田地换兵的方式大规模使用,以致在后期,狼兵被直接称为“耕兵”。万历《广西通志》就将“耕兵”单独开列,详细登载了广西全省耕兵的数量及占田数、各府州县的耕兵及田数,而武靖州每年“实征粮米二千三百九十一石二斗五升有奇”,[9](P433-4,635)非常有力地表明了武靖州狼兵对朝廷的这一利用价值。
不过,朝廷对武靖州土司狼兵的利用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可克服的弊端,这些弊端的日益严重。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广西地方形势的变化,武靖州的狼兵被裁减,武靖土州也最终被纳入流官体系之内。
二、万历后期裁狼兵与武靖州改镇的缘由
武靖州作为土司狼兵的聚落,其管理制度移植自桂西土司制度,有着不同于流官地区的统治模式。首先,武靖州建立时狼兵是携家口而来,并被拔给所谓的“绝户田”耕种,属于“移家世守”类的屯戍方式,并且这些狼兵及家属并不与民户编于同一赋役黄册内,而是被地方官府另行编册。这些专门的狼兵狼民册规定: “册内狼丁,虽已物故,传之子孙,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1](P628)其次,武靖州的粮税之征典型地体现出不同于流官体制的特点。武靖州迁来之狼兵及家口是“依上隆州则例输纳报效粮米”,即不是按流官地区的方式,而是狼兵部民直接向土官交纳税粮,再由土官上缴。
武靖州的治理方式之下,特别是由土官征收税粮的方法,使得土官的意志可以直接左右征粮之事,当土官势力强大时,往往会拒绝这项负担,使税粮难于完纳。与此同时,土官强悍难控,往往依靠其掌控的狼兵大量侵占民户、民田,将原来流官管领的版籍、土地变成狼户、狼田。正德年间,两广地方官就向户部宣称浔州等府、武靖等州,出现了狼兵占籍占地之事,因此要求中央出面禁止和查处土司狼兵占据版籍田地的做法[8](《明武宗实录》卷164“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丙午”,P809)。因此,朝廷依靠土司狼兵防驻桂东的策略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是桂西土司力量的扩张使地方官府受制于土司,特别是大量民田变为狼田之后,既导致官府在桂东地区赋税收入的减少,也带来“民差日重”的后果。田汝成就认为狼兵在桂东地区人数众多,将私置田地混为狼田,而当地吏民又以逃亡产业招狼住种,或将原有田税诡寄狼名逃避差役,因而导致“民田日削,民差日重”的恶果[1](P628)。而“民差日重”又引致不少编民为避差役而逃离户籍的更严重后果。
本来官府调狼兵东进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地方社会秩序,但桂西土司发展的结果,反而导致民田减少、差役加重而使更多编民逃离户籍,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所以,对于这个策略,朝廷及地方官府一直都在争论和反思,也一直不乏反对派。嘉靖后期反对的声音逐渐居于主流,翁万达和田汝成即是其中的代表,万历年间的广西巡抚杨芳也极力反对对桂西土司的倚重。在此期间编纂的两部广西地方志《苍梧总督军门志》和《殿粤要纂》集中地反映了万历年间华南地方形势的变化以及广西地方官府反对土司狼兵扩张的态度和理念。
《苍梧总督军门志》一书是呼吁朝廷更多地依靠军门的力量来控制华南地方秩序,但此书其实正是两广总督权力被削弱,苍梧失去旧日地位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大体上看,明中期由侯伯挂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两广,开府梧州,再设副总兵一员驻劄桂平兼制柳庆,并于成化八年 (1472年)时设置分守左江参将驻劄浔州,以分守左江一道并梧州地方,参将的职责是“提调训练募兵及巡司土兵、官军、戍守军兵”[3](卷6《兵防二·武官》,P98-9)。其时华南地区的焦点是大藤峡地区,务在打通西江及其支流,剿杀沿江及交通要道的叛乱“猺 (獞)”。到了嘉靖中后期,西江主干道已基本畅通,古田大征、罗旁大征之后,府江流域及西江下游水道也基本肃清。因此,朝廷对大藤峡和府江地区的军事行动逐渐减少,而因为东部沿海的倭寇等问题,朝廷对华南地区经略的重点遂由西向东转移。因此,在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朝廷不再由侯伯挂征蛮将军印,而分别设置广西、广东镇守总兵官,广西总兵官移镇省城桂林,隆庆年间将军门由苍梧移驻肇庆,万历五年 (1577年),据总督侍郎凌云翼之议,左参将移驻岑溪县。总之,到万历年间,朝廷对华南的经略重点已移至广东沿海地区。而对广西的经略则由军事为主改为行政手段为主。当然,作为广西军队的将领,仍然希望维持军门对华南的控制,所以殷正茂、刘尧诲呼吁重新将军门移回梧州,并致力于编纂军门志,历数梧州军门的辉煌历史,表明其不可替代之重要地位。犹如落日余辉或挽歌一曲。
《殿粤要纂》一书可以看到广西由军事系统开始向行政系统的转变。此书的主编为杨芳,当时他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任广西巡抚兼理军务。此书编写时,先是由守巡兵备各道造报所属府州县图说上交杨芳,之后杨芳命人绘出统一的图式样本,与原先各州县的图说一并交与广西布政司,由广西布政司会同按都二司将这些图说再行校正,加以讨论,照式绘图,最后按照各道所属定稿成编。全书更强调“防”,而不是“剿”,从书中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如何布防的问题。对于桂西土司兵的使用上也有所改变,更多是将其作为“耕兵”来使用,即强调其为“民”,能交税的一面。而从书中的地图看,鲜明地表达了华夷格局、以“华”化“夷”的理念。杨芳认为南蛮不同于西北夷人,是可以化而为“华”,地方官府需要贯彻的策略是依靠地方军事力量加强防守,同时以文化力量使其化而为“华”。[9]体现这种理念的最典型例子是时人关于武靖州裁撤的议论。
翁、田在嘉靖年间平定大藤峡瑶乱之后,提出了处置大藤峡的善后七策,其中第四、五条涉及对武靖州的处置。第四条提出要将武靖州改为武靖千户所,以贤能军官 (即流官)为主管,只让邦佐之子担任协同管理的角色[3](卷29翁万达《处置藤峡事宜议》,P383-4)。事实上即是废除土司头目的军事控制权,而将狼家属尽编于保甲之中。不过,官方记载称此条措施在当时没有得到批准和执行[10](卷32《外夷志二·左江土官》,P635)。为什么地方督府此时不批准武靖州改制?因为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当时正要借助桂西岑氏土司以对付安南,惮于岑氏土司的叛服无常,所以没有轻易裁撤同出于岑氏衣钵的武靖州;另一方面当时大藤峡瑶乱刚刚平定,瑶民尚未完全向化,保留武靖土司和狼兵以维持足够的军事震慑力,还很有必要。故从《苍梧总督军门志》中仍然可见关于武靖州的记载。
不过,到了万历年间,广西官方反对武靖州存在的声音日渐高涨,万历《广西通志》就表达出这样的态度。在“武靖州”一条中,主纂苏浚所写的评论就提供了时人的看法:“武靖非诸土州比也。土酋等籍其幅员,归于公家,宜世世嗣不绝。武靖故中原地,第藉兵外夷为吾藩圉,今伍符空设而徒弃内地以资狼心,非设官之初意矣。且邦佐再传而绝,清宝一传而绝,天之所殄,不可兴也!翁田之 议,洞 若 观 火,时 哉 不 可 失矣。”[10](卷32《外夷志二·左江土官》,P635)武靖州的设立与桂西土司的设立目的本来就不同,是为了借助狼兵的力量来防守大藤峡地区的“猺贼”,到嘉靖中期翁、田大征并采取系列善后措施进行调整之后,可以说峡江地区的“猺乱”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因此,武靖州的军事价值已不再为广西地方督府所倚重,苏浚认为此时若还容许武靖州这一军事性质的机构存在,只是在平白地浪费中原的田地资源满足“外夷”土司的贪欲,已违背了设立武靖州的初衷。因此,如果说嘉靖年间因为“猺乱”刚刚平定还需要保留土司狼兵以震慑瑶人的话,那么,在大部分峡江瑶人已经进入里甲体系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必要。这样我们就看到督府对武靖州的态度在万历后期由保留到裁撤的转变。
据地方志记载,浔州府的狼兵在万历年间已经裁汰了三分之二[11](卷18《军政下·民壮·狼兵》,P4)。对比《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殿粤要纂》中所记驻于碧滩堡、驽滩堡的军队人数,前书编于万历七年(1579年),所记屯驻军队数为400名,后书成于万历三十年 (1602年),屯驻军队减少为88名,正好有一个数量上的大变化,由此可以推测裁减狼兵是在万历七年至三十年之间。又据万历《广西通志》“耕兵”条云:“土司兵故精劲每遇警辄征召,大者数千计,小者百计,原有定额。国家亦不靳名器金帛之锡以鼓舞其心,故趋檄者恐后。然行之久而兵日骄恣,民且苦兵矣。总督尚书王守仁以征调频数,人不堪命,因议更番戍守之法,……其制良善,然穷年外处,月饷无几,武夫悍卒多不乐役,第以老惫充数,到伍以后潜归相属,其名存其实亡,于是戍兵不足恃,而警报一闻,又不得不议征兵矣。万历十六年督府刘继文以地方宁谧,议减戍卒之数,但兵额既减而虚名如故也。”[10](卷32《外夷·土兵征戍》,P671)由此可见,万历十六年(1588年)确有广西省府采取实际行动统一裁减戍卒的举措,作为其时广西戍卒主力的狼兵应该就是因应此一政策而被大量裁减的。
为什么要在万历后期裁减狼兵?上引材料提到两个原因,一是广西地方趋于安静,正与前文分析华南局势变化的情况相一致。二是狼兵日益骄恣,百姓苦兵,即是官员们其时认为使用狼兵之弊甚于其利。对此苏浚有更深的讨论云:
昔之议者,率谓狼制獞,然仅计一时而不可长恃也。狼初利吾田,势必聚兵,戈戟如林,足制诸夷死命。二三年后,兵窜故乡,田归酋长,戍守无几,脆弱居半,獞人且寝处之矣。其甚也,獞人负租不敢问,稍恣睢,白挺随之,狼果可长恃耶?夫驭得其道,獞可作使,驭失其道,狼且作敌。圣人有金城,隐然虎豹在山,则自恃之道也[7](卷57苏浚《古田论》,P698)。
认为“狼不可恃”成为万历年间广西官府最主要的声音,极力反对再过度倚重土司狼兵,转而主张将瑶僮教化以为我所用,重心在于以夏变夷,极力反对重用土司“蛮夷”。大体上而言,总的趋势是结束武力剿杀或以夷制夷阶段,而进入到以“华”化“夷”阶段。
武靖州的改制发生在万历末期,《浔州府志》“武靖始末”条中有记述如下:“邦佐死,子崟嵛袭,崟死,绝。以族人清宝袭,清宝复死,绝。改为镇,以所领狼兵属本府通判。国朝因之,不设土官,后复裁镇,归入桂平县。”[12](卷26,《武靖始末》,P6)即是到清宝绝嗣后,武靖州才改为镇,并改由浔州府通判权知州事。
到了康熙年间,汪森编《粤西文载》,其中的《左江土司志》“武靖州”条在引述了上引苏浚所言后,加了一个按语称:“今邦佐之嗣已绝。浔州府通判权知州事,狼兵归之桂平、平南、贵县三县,俱如翁、田二公议。”[7](卷12,《左江土司志》,P652)《左江土司》为采集地方名胜志所写,所记当为明末或清初之事,表明到明末清初,至少在康熙年间汪森编书之前,已经完成了武靖州改制之事。
浔州府裁汰狼兵与将武靖州改为镇,将狼兵改隶府通判管辖,两者的意图是一致的。裁兵在前,改州为镇在后,也许正是官府大规模裁狼兵之时,清宝之绝嗣刚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明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武靖州采取行动。
翁、田善后七策的第五款是关于狼田的清理,即要重新丈量狼田,同时开始向狼田征收粮差,要求狼户与民一体,交纳相当于差役的米粮[3](卷29翁万达《处置藤峡事宜议》,P384-5)。按顾祖禹所言,万历末期,对武靖州的处置是“俱如翁田所议”,那么这一政策便也得到了实施,其实施的结果使得武靖州这一土司制度下的“狼”的开始进入流官治下的里甲体系。
此后,浔州府的狼兵狼民基本上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变。一是三分之一被保留的狼兵,他们被编置了保甲,仍保留在单独的狼丁册内,但武靖镇改由通判权知州事,意味着武靖镇真正成了流官直接治理的地方机构,后来,狼兵更是分归桂平、平南、贵县三县自管,直接归属流官。这些册内狼户主要的职能仍然是应兵役,继续承担着守城等军事职责[11](卷18《军政下·民壮·狼兵》,P3页)。桂平县一些村落直至乾隆年间编制保甲时仍然看到单独的“狼甲”[13](卷3,P445、439、443)。清朝至雍正时仍用狼民协防,可见这些人作为狼兵的身份一直保留。另一个方向是被裁撤的三分之二的狼兵,他们与民一体编户,不再编入单独的狼丁册内。因此,此部分狼兵被裁之后与其家属一道逐渐融入当地,消失了他们作为“狼”的身份。
据文献资料看来,武靖州的土司狼兵基本上是沿着第二个方向演变的。乾隆《桂平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桂平县编保甲的情况,武靖州所在的大宣里这个原来狼兵最集中的地区,所有村落均为民村,并没有狼甲编制的村落,桂平县被保留狼甲编制的村落基本上集中在浔江南岸沿河一带的赵里 (今桂平蒙圩镇)、武平里 (今桂平石龙镇)和甫里 (今桂平石龙镇)。[13](卷3,P445、439、443)随着武靖州狼兵其“狼”的身份的消失,当地的主要人群转而被称为“獞”,他们已经成为输粮纳税的国家编民。
三、小结
武靖土州在桂东流官管治区的设立、迁址和最终被裁撤,是明中期广西边疆地区局势变化,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以及官府和地方将领对狼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明代,西江航道日益成为盐运及军事物资运输的枢纽,大藤峡地区因控扼西江流域中段航道而引起朝廷的重视,当地被称为“猺”的土著群体成为官府管制的对象。明代中期以后,由地方到中央均以征“猺”为要务。而明王朝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桂西土司率领的狼兵,朝廷将进入桂东地区的狼兵以军事聚落的形式进行安置,拔给其田地使之屯耕防守,镇摄瑶人,保证江道畅通。这是武靖州设立的最重要缘由。武靖州址由碧滩迁往大宣里和崇姜里之间平旷的黄绅岭,盖因狭窄的碧滩无法安置众多狼兵家属,无法达到以田换兵之目的。而迁址之后同时也实现了朝廷对于狼兵的“耕兵”定位,使朝廷可以从这些耕兵中获得一定的粮税收入。嘉靖中后期到万历年间,在大藤峡地区的瑶乱基本平息之后,一因武靖州的土司管治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二因其时华南局势的重点转向广东沿海地区,所以,桂东地区的狼兵被大量裁减,武靖土司州也最终被裁撤。
[1][明]田汝成.炎徼纪闻 (四库全书第352册卷2《断藤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3][明]林富修,黄佐纂:广西通志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1,据明嘉靖刻蓝印本影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4]广西博物馆.明代大藤峡·八寨农民起义调查资料[Z].1975年油印稿.
[5][明]刘尧诲编.苍梧总督军门志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6][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7][清]汪森编.粤西文载 (四库全书第1465-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明]明实录[M].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本.
[9][明]杨芳编纂.殿粤要纂[M].范宏贵点校.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明]苏浚纂修.广西通志 (中国史学丛书15.明代方志选六.据万历二十七年刊刻本影印) [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11][清]胡南藩修,欧阳达纂.浔州府志[M].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12][清]魏笃修,王俊臣纂.浔州府志[M].同治十三年 (1874年)刻本.
[13][清]吴志绾修,黄国显纂.桂平县志[M].故宫珍本丛刊影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