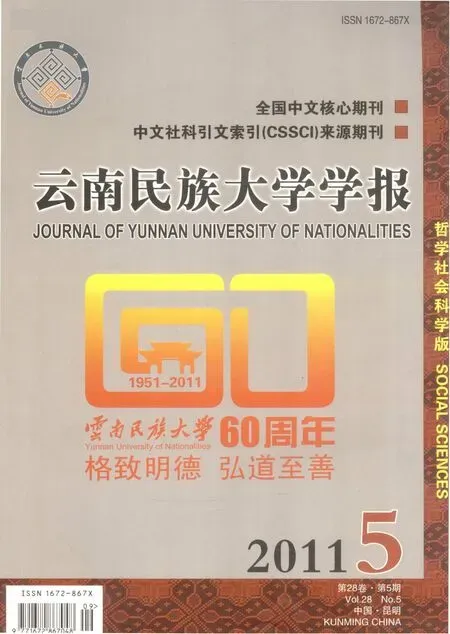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及其影响
段红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
明朝平定云南后,继承元代的行省制度和土司制度,在政府能直接控制、汉族人口较多且军户、民户较集中的地方设置府、州、县,而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则设置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据《明史·云南土司传》及《明史·地理志》载,[1]明代自洪武至永乐朝先后在云南极边地区设置了麓川宣慰使司(辖境在今德宏州及边外若干地区,1382年设)、木邦宣慰使司 (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兴威,1404年设)、孟养宣慰使司 (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江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1404年设)、缅甸宣慰司 (其地在木邦以西,孟养以南,今缅甸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1403年设)、底兀剌宣慰司 (在缅甸宣慰之南,旧蒲甘伊洛瓦底江以东即洞吾之地,1424年设)、大古剌宣慰司 (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之白古,即马革为得棱子地,1406年设)、底马撒宣慰司 (在萨尔温江入海,丹那悉林地带,南至土瓦,1406年设)、八百大甸宣慰使司 (其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1404年设)、老挝宣慰使司 (其地在今老挝境内,1403年设)、车里宣慰使司 (辖境相当于今我国云南西双版纳,1384年设)等十宣慰司,孟艮 (在今缅甸南掸邦景栋一带,1405年设)、孟定 (在南定河流域及以南地区,1382年设)二御夷府。[2][3]其统治范围包括今云南德宏、西双版纳及老挝、缅甸大部,以及泰国的一部分。
明代初期,统治者尚能通过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策略震慑当地土司,对诸土司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然而,明朝中后期以后,一方面腐败日渐突出,朝廷上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贿赂公行;地方上纪纲不振,荒淫怠政,玩忽职守,已经不能对边境上的土司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控制。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各地土司实力都有所提升,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内部纷争越演越烈。以麓川宣慰司思氏土司为代表的地方民族势力不断纷争,不仅造成了西南边疆的动荡,也对明朝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统治构成了新的威胁。
为加强对边境土司的控制,沐昂上奏朝廷,以“思任发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刀珍罕、土官早亨等相助为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齿,势甚猖獗”[1]为由,请求进讨思任发。于是,自正统四年 (公元1439年)至正统十四年 (公元1449年),明廷在太监王振、兵部尚书王骥等人的倡导下“三征麓川”,将麓川思氏的势力赶到了伊洛瓦底江以西,将思任发的孙子思命发发配“沿海登州卫安置,月给米二石”[1],摧毁了麓川割据称雄的野心。
在边境土司的纷争和明廷对麓川思氏的征伐过程中,缅甸宣慰司逐渐强大起来。缅甸土司莽瑞体不仅建立了洞吾王朝,还趁古喇兄弟争立之机“举众绝古喇粮道,杀其兄弟,尽夺其地”,后又借孟密土舍兄弟争立之机,纳其弟为女婿,“攻孟养及迤西诸蛮”[1]。从此,缅甸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与木邦、孟养、孟密等土司相争夺,造成了中国西南边疆更大的动荡和危机。
在缅甸洞吾王朝频繁的武力扩张面前,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止丢失西南边境更多的土地,便于万历二十二年 (公元1594年)在腾冲卫设立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距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八关。[3][4]八关的设置,意味着明朝主观上放弃了设置在八关以外的蛮莫、猛密、孟养、木邦、老挝、八百等地统治。
于是,明代初年在西南边疆所设的十宣慰司及二御夷府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缅甸洞吾王朝的扩张及当地土司的纷争中逐渐脱离明朝的统治而为缅甸所有。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载:“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慰,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5]今云南之边界,惟有麓川、车里二宣慰司及孟定府在我国境内,且已不完全。
二、明代中缅边疆变迁的原因
明初,在明朝政治统治和强大军事震慑面前,西南边疆“麓川、缅甸、车里、八百媳妇诸蛮皆遣使纳款内附”[6],明廷先后在西南边疆设置了十宣慰使司及二御夷府。明朝中后期以后,朝廷处置的失当,边境土司的纷争和缅甸的崛起,最终导致中国西南版图的大范围龟缩。
(一)明朝统治不力,处置失当
明初在云南边地所设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底兀剌、大古剌、底马撒、八百大甸、老挝、车里、孟艮、孟定等地,大多为元代才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元代以前,这些地区或为中央王朝的藩属国,或为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所控制,受中原汉文化及内地的政治统治制度影响较小。因此,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认同感不强,对中央王朝统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远远不足。明初之所以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主要是因为朱元璋、朱棣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励精图治,明廷国力强盛,对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在强大的明王朝面前,云南边地的各民族上层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遣使入贡,祈求“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为中央王朝“奔走惟命”,处理所属民族地区事务。[1]同时,明初中央王朝也能对不听节制,坐地扩张的麓川思氏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统治。因此,明代初年,各地土司朝贡不断,保持了一种良好的统治状态。
正统 (公元1436至1449年)以后,明王朝由盛转衰,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明初实行的军屯制度逐渐废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正德至万历年间,明王朝内忧外困,加上明王朝北有蒙古瓦剌部也先力图向中原扩张,东部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并试图进一步向中国扩张,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破坏,西南地区缅甸洞吾王朝向北扩张,土司纷争不断。面对众多的社会矛盾,明朝廷已经是有心无力,无法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控制。
就云南而言,明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及地方管理对地方土司纷争及缅甸的北扩处置失当。先是正统年间太监王振及兵部尚书王骥等人“三征麓川”,“发十五万,转饷半天下。大师三动,连兵十年,士死伤不算,仅以破克,而中国益耗病”[7];隆庆二年 (公元1568年),木邦土舍罕拔请求承袭,明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索贿不成便不上报,引起了罕拔的反抗,转而投靠缅甸东吁王朝。时有“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谣;[8]同年,缅甸莽瑞体遣使招降陇川土酋多士宁,多士宁不从,“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1],并向屯戍蛮哈的指挥使方谧报告了缅甸进攻中国的策略,无耐方谧不听,最后多士宁被养子岳凤毒死,投靠缅甸;万历四年 (公元公元1585年)缅甸攻打孟养,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让思个坚守待援,积极调兵至腾越准备进行支援。但因云南巡抚王凝不谙边防,急传罗汝芳不准发兵增援思个,导致土司思个被俘,不屈遇害;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缅甸焚掠施甸,进而又破顺宁、盏达。盏达土酋刀思廷求救不应,终因粮食耗尽而被攻破。
由于明廷统治不力,对边疆危机处置失当,“致使忠义之酋如陇川多士宁、干崖刀怕文、迤西思个,横罹惨难,极千古而冤不一伸”[6]。更为严重的是,明廷在边疆危机处理中的不作为,在缅甸进攻边地土司时,明朝政府没有积极组织救援,使得朝廷在土司中的公信力降到低点,“盖自麓川、孟养、盏达三不援救,而后诸夷确然知中国之不可恃,而甘心于臣缅矣”[6],纷纷投靠缅甸力图自保,这些地区后来沦为缅甸的属地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缅甸崛起,向外扩张
缅甸自汉代与中国开始正式官方往来,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保持着和平友好的交往。明永乐元年 (公元1403年),缅甸首领那罗塔派人入贡,于是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那罗塔担任宣慰使。而后,缅甸在明朝初期朝贡不断。在征麓川期间,明朝廷曾颁旨许诺“木邦、缅甸能效命擒任发献者,即以麓川地与之”[1],后来缅酋马哈省、以速剌等擒获思任发,并要求明朝兑现以麓川地换人的承诺。从此,缅甸与麓川、孟养等地结下仇怨。
嘉靖初年,孟养首领思陆发的儿子思伦发联合木邦及孟密攻破缅甸,杀死缅甸宣慰莽纪岁及家人,占领其地。莽纪岁的儿子莽瑞体投奔在洞吾的母亲家。长大之后,莽瑞体尽有洞吾之地,建立了洞吾王朝。而后,洞吾王朝先后于1539年灭了白古王朝,1555年灭了阿瓦王朝,再次实现了缅甸的统一。随着缅甸洞吾王朝的崛起,缅甸于嘉靖末年开始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在缅甸扩张的过程中,缅甸酋莽瑞体及其子莽应里“颇知用兵,尤计善狡猾,凡诸夷未服者,先声言攻取以挟其来,及既已来者,又重加赏赉,以快其欲”[9]。嘉靖三十九年 (公元1560年),孟密土酋思真及其子思汉相继死,引发了内部土司继承权的争夺。莽瑞体趁机招思汉次子思琢为女婿,以此操控对孟密的控制权;隆庆二年 (公元1568年)木邦土舍罕拔请求承袭遭到明地方官员拒绝时,莽瑞体立即给予援助,并于罕拔“约为父子”[8];隆庆六年 (公元1572年)陇川宣抚司目把岳凤杀多士宁投缅后, “乃赍重贿投拜瑞体为父”,导之内侵。而后,蛮莫头目思哲也投降缅甸,“瑞体纳为义子”[8]相反,对于激烈反抗的边地土司,在被缅甸攻破后,往往遭到残酷的迫害。如陇川土酋多士宁被岳凤杀后,“多氏族属,残灭殆尽”[8];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莽应里攻破施甸后,“焚掠施甸,剖孕妇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顺宁”[8]。
在缅甸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面前,明廷显得软弱无力,虽有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及万历十六年 (公元1588年)刘綎、邓子龙的反攻大捷,但也挽回不了明朝在交锋中的颓势。于是,缅甸越发骄横。万历三十年 (公元1602年),缅甸再次进攻蛮莫,“途观思政败奔内地,缅以重兵入滇索之,抚臣大惧,斩思政首畀之,缅乃益骄。”[5]万历三十四年 (公元1606年)木邦宣慰司为缅甸侵占后,“五宣慰司复尽为缅所陷,而庙堂置不问矣。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5]。
(三)土司纷争,叛服无常
明初,朝廷为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对“西南夷来归者”, “即用原官授之”[10],在边地设置了十宣慰司及二御夷府。其目的是通过土司制度笼络各地民族上层为其“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11]。
然而,纵观整个明代,云南边地土司之间的纷争就没有停止过。先是明初麓川宣慰司思伦发对景东、金齿卫、缅甸及马龙他郎甸的摩沙勒寨等周边地区的侵扰。明朝在挫败思伦发的扩张后,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其地“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1]。麓川宣慰司被分置后,一方面,麓川思氏企图恢复原来的势力范围,伺机扩张。另一方面,明廷虽然遏制了麓川思氏,却培育了孟养、木邦、孟密、陇川等大小不等的地方民族势力。这些民族上层羽翼丰满后,也加入了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当中,引发了边疆更大规模的土司纷争。见诸记载的有:宣德元年 (公元1425年), “麓川、木邦争界,各诉于朝”[1];宣德八年 (公元1433年), “木邦与麓川、缅甸各争地,诉于朝”[1];正统三年 (公元1438年),麓川侵孟定、南甸等处;弘治六年 (公元1493年),云南守臣奏孟密侵夺木邦,“兵连祸结,垂四十余年,屡抚屡叛,势愈猖肆”[1]。翻阅明代相关史籍,土司之间的纷争见诸记载者俯拾皆是。值得注意的是,麓川思氏被削弱后,西南边疆没有了独占优势的民族势力,各地土司在一种较为均势的状态下纷争不断,客观上为缅甸洞吾王朝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嘉靖年间缅甸向外扩张以后,木邦、孟养、车里、陇川等地土司面对缅甸强势的攻击和明廷统治的软弱无力,为保住已有的既得利益,在明朝和缅甸政权之间摇摆不定,叛服无常,甚至出现了双重的政治归属。万历元年 (公元1573年),缅甸攻入陇川后,岳凤杀死多士宁及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投靠缅甸莽瑞体抵抗中国。万历十二年 (公元1584年),刘綎、邓子龙取得攀枝花大捷,收复陇川、孟密后,岳凤自度无处可逃,遂“偕其妻子、弟侄及所统夷汉归命,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甲、刀枪、鞍马、蟒衣并伪给关防一颗”[5]。同样,木邦土舍罕拔因请袭职遭到地方官吏索贿后,怒而投缅。潞江安抚使线贵因为罕拔投缅后得到很多好处, “亦投瑞体,日津津泄中国之虚实,教以吞邻内侵”[8]。罕拔投靠缅甸后,还召干崖土司刀怕举的弟弟刀怕文“袭职以臣缅,且许以妹”[1]。
明朝政府在边境民族地区公信力的降低,使得边地土司在面对缅甸不断侵扰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就连后来英勇抗击缅甸的孟养土司思个,在万历四年 (公元1576年)缅甸大举进攻迤西时,不知是该投靠缅甸还是归附中国,“乃刻木二,一书天皇帝号,一书莽瑞体号,率众拜之,乃卜”,需要通过占卜的形式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因“天皇帝者卓立几上,莽瑞体倾坠于地,由是决意向中国”[8]。再者,嘉靖十一年 (公元1532年),车里宣慰使刀糯猛投靠缅甸,当时出现了“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的局面。[1]
边疆土司势力在明朝和缅甸政权之间叛服无常,甚至采取双重政治归属的做法是力求自保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明朝云南边疆版图大为龟缩的一大重要因素。这对我们今天处理民族地区事务,研究和解决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警示作用。
三、明代中缅边疆变迁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中缅边疆地区的纷争和动荡,一方面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另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大量内地军士进入边疆民族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的交往,并为中缅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雏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奠定了近现代中缅边界的基本雏形
云南自古蛮夷之地,远在荒外,汉武帝时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后蜀、晋、隋、唐“虽曰郡县其地,不过遥制以为羁縻而已”[12]。到了元代,忽必烈攻下大理后,元朝于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在云南设置了云南行省,其辖境除今滇及黔、川部分地外,南界还到了缅甸、泰国境内,并在边疆地区推行土司制度。
明代继承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和土司制度,明初几经调整后,中央王朝在云南行省设置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其辖境“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富州,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趾界”[13]。然而,明代中后期,随着缅甸的扩张,明初在边境地区所设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剌、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逐渐为缅甸控制,惟有麓川、车里二宣慰司及孟定府在我国境内。
明代西南边疆的大范围龟缩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朝建立后,在明代末年西南边疆变迁的基础上,清政府先后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普洱府、顺宁府、永昌府、腾越直隶厅等行政机构,清代云南省辖地“东至广西泗城;七百五十里。南至交阯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会理;四百里。西至天马关,接缅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14]显然,明代原属于中国的缅甸、老挝、孟养、木邦等地到清代已成外域之地。
从唐宋以来,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明代以前,无论是南诏、大理国,还是元代云南行省,其辖境都包括今天四川、贵州及越南、缅甸领土的一部分。明代边疆的大范围收缩后,清代云南省所辖地界已经和今天云南省所辖相差无几。后经近现代领土争端和未定区域的逐步确定,最终定格成今天中国和缅甸的边界。
(二)部分百夷、峨昌等民族沦为缅甸控制地区的居民,逐渐成为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明代,“自永昌出塞,南际大海,诸夷自相君长。本朝芟锄梁、段,以武临之,皆稽首而奉正朔。”[8]在云南永昌以外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以百夷为主,包括峨昌、野人、蒲人在内的众多民族群体,明廷先后在这些地区设置了车里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老挝宣慰司、里麻长官司 (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地带)、茶山长官司(小江流域地带)及孟定府、孟艮府等进行统治。
明朝中后期,随着木邦、孟养、八百、老挝、孟艮等地先后为缅甸所有,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百夷也就成为缅甸境内的居民。被缅甸封建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百夷,即今天的傣族,尽管依然自称为傣族,但是,缅甸的统治者一直把他们叫做掸族。后来,人们把他们控制下的傣族地区也统称为“掸族诸邦”(Shan States),简称“掸邦”[15]。此外,明代后期置八关将里麻、茶山长官司放弃之后,居住在其境内的峨昌,以及“在茶山、里麻之外,去腾越千余里”[8]的野人,即今天的景颇族,也成为了缅甸的居民。
可以说,云南今天傣、阿昌、景颇、佤等16个跨境民族的形成,虽然有些是清代或近现代逐渐迁徙出境的,但追根溯源,今天跨境民族的形成与明代西南边疆尤其是中缅边疆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中缅边境地区森林茂密,物产丰富,“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易麟介以冠裳”。然而,连年战乱,导致边民非死即逃,边地经济呈现出一片凋敝的景象,“三宣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16]。连年的战乱,导致边疆地区“饷费不貲,即转输米石,运价至十金”,以致“编氓鬻妻子,诸郡邑不支”[8],甚至祸及云南腹里地区的府州,出现“大理、鹤庆、蒙化、姚安、楚雄五郡,邑无遗村遗户,不死而徙耳”的凋零景象。[17]
此外,连年的战乱也使当地居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明神宗万历实录》载,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18]另据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缅甸土酋莽应里极其残暴, “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19]。
(四)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间的交流
明代边境地区的战乱虽然使当地各民族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手段和方式,战争起到了促进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明代从洪武年间起便开始在这一带广设卫所,大规模进行移民屯种。伴随着卫所设置,一批内地的汉族移民也进入了永昌、腾冲、金齿一带。至明末天启时,滇西腾、永5卫共辖45个千户所。按编制计算,所驻兵力占了全省三分之一,已成为一支庞大的外地移民队伍。[19]大量汉族军士进驻永昌、腾越一带,给当地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注入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基因,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边地民族文化的交融。据谢肇淛《滇略》记载,“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诸夷所产琥珀、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揍转贩,不胫而走四方,故其习尚渐趋华饰、饮食、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三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10]。另据光绪《腾越厅志》载,腾冲一带“自元明设卫分屯,用夏变夷,一时从戎驻牧者多江南人,遂沿有江南风俗”[20]。
随着各民族间交流的增加,明代很多汉族商人、军士还通过经商、流徙等形式到达今天缅甸境内,对当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明史·云南土司传》载,蛮莫一带因地处水陆会通之地,于是“蛮方器用咸自此出,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1]。另据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 “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16]。由于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汉族的生活和文化习俗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习俗的变迁。据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缅甸、木邦、孟养、孟密、蛮莫一带以百越为主的各民族在饮食方面“蒸、煮、炙、煿多与中国同”,“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漆器贮鲜肉,数日不作臭”。在婚姻方面,受汉文化影响,当地居民“婚姻不用财举以与之,先嫁由父母,后嫁听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别,近华故也”[16]。更有甚者,这一带的蒲人、僰人、阿昌等民族因“杂华而居,渐变于夏,间有读书登芹泮,纳粟为吏承者矣”[16]。可见,其经济文化生活已经受到汉族移民的影响。
此外,由于连年与缅甸作战,明朝中央政府尤其重视对缅甸的各项工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朝廷设置的四夷馆中增设缅甸通事。据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明初“四夷馆通事仅译外国,惟缅甸亦设数名,其后八百亦如之,盖二司与六慰中又加重焉”[5]。在地方上,由于战争中缅甸使用大象作战,“中华人马未经习练者,见象必惊怖辟易,彼得乘其乱也”[16],每遇象军来袭,则溃不成军,伤亡惨重。于是,万历年间刘纟廷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21],争取战场上取得主动。这也算是因战争而带来的双方军事上的交流和学习。
总而言之,在中国与缅甸交往的历程中,明代是中缅边疆变迁和关系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代乃至近现代中缅关系中的许多事件,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都与明代的变化息息相关。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曾总结到:“滇云一隅之地,著于唐虞,历于三代,通于秦、汉,乱于唐,弃于宋,启于元,盛于明。然亦困于明,极坏于明,不可收拾于明”[6]。而今观之,虽有些过激,但不无道理。
[1]明史·云南土司传 [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贺圣达.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及其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2).
[4]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缅甸盛衰始末[A].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1998.
[6][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六[M].李埏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7]傅维麟.明书:卷七四《边防志》 [M].商务印书馆,1937.
[8]天启.滇志·羁糜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9]吴宗尧.莽达剌事情节略[A].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1998.
[10]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A].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11]明史·职官五[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12]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3]明史·地理七[Z].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14]清史稿·地理二十一:卷七十四[M].
[15]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16]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A].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7]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卷218[Z].
[18]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卷153[Z].
[19]古永继.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
[20]光绪《腾越厅志》卷三《舆地志·风俗》 [Z].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21]明实录·神宗万实录:卷175[Z].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