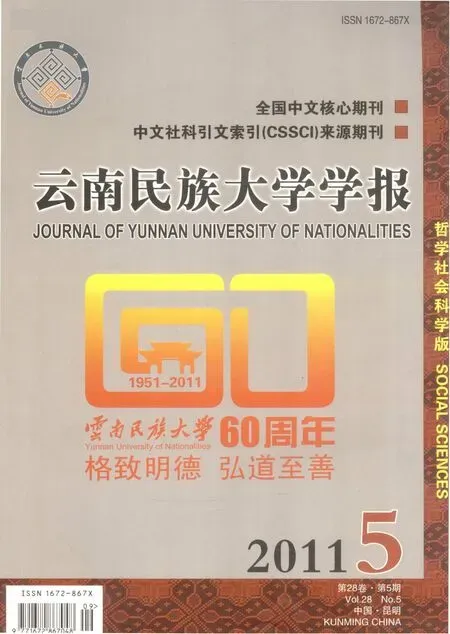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戴顺祥
(云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云南 昆明 650091)
通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大体而言,聚落形态下的城市与乡村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呈现出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一、先秦至隋代的城乡关系
(一)城市的起源与早期城乡关系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和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一部分富有者的财富,也为了保护氏族和部落的安全,人们开始在聚居地的核心区域建筑“城”:《淮南子》、《轩辕本纪》、《黄帝内经》、《世本》、《汉书》中都分别记载了黄帝、神农、鲧、禹在此时筑城的情况,《通志·都邑略》、《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则对古代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都城的地点,王国维也认可了此时所筑的都城。[1]以这些所筑的“城”为中心,在其周围地区分散聚居着该氏族和部族甚至是部落联盟的多数人口,形成一个人口居住稠密区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就在该“城” (聚落区域)周边进行。这样,这些“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了部落联盟的中心。” “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乡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也正是从筑城开始,有别于原先聚落主体“乡村”的“城”出现了,早期城市开始起源。
虽然说原始社会时期一直被看作是一个传说时代,但结合考古发现来看,“鲧作都城”[3]、“夏鲧作城”[4]、“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5],基本还是可信的。商代,以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城的考古发掘显示,商代的都城规模已明显大于早期“城堡”,城内有成片的住宅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这说明此时作为人类聚集地的“城”所容纳的人口更多,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又从《尚书》等有关文献和出土的大量玉、贝等具有货币价值物品来看,当时可能已经存在固定集市。
从夏商早期都城的建筑、布局、规模等可以看出,此时的都城已经具有一般城市形成的基本要素,即具有了行政、防御、商业、手工作坊和集中居住区等五大基本物质要素,和最初纯粹的聚落形态——村落 (或者乡村)比较而言,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从聚落 (城市)的中心建筑来看,完成了从最初简单的以供奉祖宗的宗庙为主到以君主居住的宫殿为主的转变;完成了部族聚落中城墙与城池由分设到合二为一的转变;商业交易地完成了向城市的集中转变;手工业作坊布局完成了从城郊到城缘的转变;基本确定了城市作为居住区的“内城外郭”地域结构。[6]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早期,在筑城的过程中,一个核心居住区从整个居住聚落区中脱颖而出,并且开始发挥行政中心或者是集市中心作用的时候,由此带来城与乡的分离和差别。
早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更多的居民是居住在城周边的乡村聚落中,只有遇到战事或者需要进行交换时才会迁往城中。因此,这个时期的城乡主要还是一种朴实的互相依存关系,乡村通过“贡”、“助”、“彻”等形式向城市君主缴纳或提供统治所需的物资和劳力,城市则为周边部落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二者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二者一体的关系。
(二)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城乡关系
周武王灭商后,开始实行“封邦建国”制,受“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5]的影响,各主要封国如鲁、齐、卫、晋、燕、宋等,为抵御外敌入侵和保护封地内的生命财产安全,均把建城作为立国的根本方略;同时,周王室也积极进行都城建设,先后建有岐邑、丰京、镐京、洛邑等,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周代城市的发展。此时,周代城市发展呈现出城市数量增加、分布范围广泛;形成了严格的城邑等级制度;城市建设具有较强的规划性;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有所发展等特点[7]。周代城市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等级性、规划性特点,突显出此时期的城市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事实上是早期夏商都城建设的延续与扩展。同样,周代的城市中也有专门的手工业区和商业交易区,并且在周政府“工商食官”管理模式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城市中的工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手工制品特别是青铜铸器发展到了一个顶峰。但这种“工商食官”制度将手工业发展限定在政府直管之下,民间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不高。此时的城市还是典型的以政治性为主导的城市。对于政治性城市之外的聚落乡村,周代实行了不同于城市管理的“乡鄙(野)制”,与城内(国)的管理相对应。这种规定国(城市)与鄙野(乡村)的不同管理体制,基本上类似于一种人口户籍管理制,事实上是第一次将城市形成发展以来出现的城乡分离作了相对较为明确的确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获得急剧发展,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城市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时期,由于“工商食官”局面的被打破,民间工商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综合性城市和工商业城市。城市数量空前增多,城市规模扩大。据《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达68次,除5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据今人统计,春秋战国时各种城邑数目已接近千余。[8]到战国时期,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人口也在急剧增长,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千家者。” “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9]城市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西周时期成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经济中心。
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确立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郡县制的推广,城市数量在原有基数上不断增多。据统计,西汉时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达到1600多个,到东汉时,虽然有所减少,但仍基本保持在1000多个以上规模。西汉经过休养生息以后,中国人口随即获得急速增长,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2年)人口规模达到6000万,城市人口也比前代有了大幅增长。 《汉书》记载:“平帝原始二年(2年),(长安)有户口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如果加上皇室、贵族、奴仆、军队,长安城的人口超过四五十万。东汉王符说“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表明洛阳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长,并且认为,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10]。同时,以首都为中心,这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国都—郡所—县所三级城市体系,城市建筑规模和人口规模基本与其政治地位高低相匹配。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带来了货币、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经济、商品贸易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通其所欲”。这些富商大贾或经营盐铁,或从事贸易,“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11]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获得急剧发展,一大批具有行政、商业职能为主的城市也随之兴起。
在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既与国家对地方管理体制的强化推广有关,又是伴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盛。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个时期城市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一些大的诸侯国 (秦汉时期则是长安、洛阳以及部分重要郡所)的都城发展较快,但更多的城市发展水平不高,规模不大。特别要注意的是,工商业城市在此阶段获得较大发展,但这些城市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都会,不是因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自然形成,更多是从政治中心、军事据点演变而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和经济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仍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和控制。在这个时期,国家在乡村一般实行的是乡里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从乡村中获取统治物资供给,包括粮食、人口赋税以及军事后备力量等。城市仍是作为统治中心,向周边乡村辐射进行统治,二者体现出乡村对城市的政治依从与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依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农业人口与工商业人口并不是绝对的乡村与城市人口的差别,城市中也有大量农业人口。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仍然联系紧密,但已经显示出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三)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的城乡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大动乱时代,南北分裂、战争频发、民族冲突与融合、社会经济发展滞缓是其主要特点。受战火、自然生态环境遭破坏的影响,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一改秦汉蓬勃发展的趋势转而为衰败,如长安、洛阳自东汉末年以来持续遭受战火侵袭焚毁,直到北魏前几乎就是北方动乱中各方势力角逐的主战场。洛阳自董卓撤离“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后,又多次遭战火焚毁,到三国时曹植感慨“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长安更悲惨,长安城西晋末年一度是一种“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2]状态。都城尤且如此,地方城市遭受兵火焚毁也多是大同小异。北方不少地区是“名城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1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4]。大量的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三国时期,总人口合计仅为1 129.9万,只是东汉灵帝年间人口总数 6000万的18.9%,减少了4870万人。[15]直到唐中期以后,人口才又重新达到东汉人口数水平。城市的衰败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态势。
西汉初年,在农业经济发展前提下,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且由于商业利润丰厚,刺激了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汉代城市快速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战火的影响,城市人口锐减,城市衰败,整个社会经济集体凋敝,大量聚居在乡村的人口及其社会生活重新突显出来,并以其自有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力量,工商业经济陷入发展低谷。这样,自秦汉以来城市与乡村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发生改变,重新回到了城乡不分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下。这既体现在这个时期商品交易由秦汉时的货币交换重新又回到以货币和布帛、粮食等并用的交易阶段,又体现在这个时期大量的坞、堡、壁、垒广泛发展起来。
由于战乱的影响,在乡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坞、堡、壁、垒。这些坞堡壁垒一般都是以一家豪人为中心加上他率有的人口组成,不能在战乱中自保的人都依附到这些坞堡壁垒中寻求保护。每一个坞堡壁垒都仿佛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他们的生产生活完全在坞堡周边内,实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些坞堡壁垒的兴起和城市的衰败相对应,事实显示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是以乡村为中心,秦汉以来城与乡的逐步分离趋势仿佛中断了,城乡关系在逐步淡化,城乡二者基本还原为一体了。
北魏建立后,直至隋统一全国,北方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而南方由于战乱较少,随着移民的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发展。这样,城市在南北朝后期直至隋代又开始逐步恢复与兴起,乡村则在战乱中随着移民浪潮和坞堡壁垒自给性经济的发展也获得较大发展,秦汉以来城乡分化趋势在社会经济获得发展的前提下又开始往前迈进。进入隋唐,特别是中唐入宋以后,城乡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二、唐宋时期城乡关系的转折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高峰时期,也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变革时期。中唐以后直至两宋,社会经济获得长足进步,农业、手工业生产力进步明显,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及其影响扩大,商人和商人资本的崛起,城市、中小型市镇经济异常繁荣。[16]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乡村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以往的“城乡一体”逐步走向“城乡分离”;与此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和协作不断加强,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交相生养”的新型经济关系。
(一)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
唐宋时期,“城”与“乡”开始在官方文书中出现:唐代政府对百姓不同的居住区实行“村(里)坊制”管理,将城居的“坊郭户”与乡居的“乡村户”相对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入宋以后,这种将城市与乡村作为对应概念描述的记载不断增多,且范围不再局限于对居住区域百姓的管理,已经扩大到更深更广的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层面。这些新情况表明:唐宋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已经分化,二者关系与以往时代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唐初,“武德七年 (624)始定律令: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居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17]这条法令规定了居住在城中与居住在乡村的不同命名方法——坊与村,这与西周时期的国野制命名有一定的类似,但二者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又有明显的差别。在这条法令中规定了“士农工商,四人各业”,这是一种从身份上进行的职业划分,并没有从中体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因为我们可以结合唐代的土地授受制度知道,不论居住于邑中,还是村中,并不影响人们从国家授受土地。居住在坊中的也可能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而居于村中也可能是士子、工商业人等。也就是说,武德七年法令虽然规定了根据居住区不同而予以不同命名的法令,但并没有从中体现出城乡的分离,它所重视的只是国家对民户的一种管理手段。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12年)敕:“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18]这条资料表明,在确定户等时,郭内 (城内)非商户百姓的郭外宅和郭外 (城外)非商户百姓的住宅,都不算作划分户等的依据。这既显示出政府对商户的歧视,也体现出政府已经将郭内、郭外百姓区别对待了。但仍然还难以体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分离。
到宪宗元和四年 (809年)有敕规定,“诸道州府应征留使、留州钱物色目,并带使州合送省钱,便充留州供用……如坊郭户配见 (现)钱须多,乡村户配见 (现)钱须少,即但都配定现钱。一州数,任刺史于数内看百姓稳便处置。”[19]这条资料是现在发现的有关“乡村户”和“坊郭户”的最早记载。它明确使用“乡村户”和“坊郭户”用语,与开元年间使用“郭内百姓”仅指居住区域的含义有了明显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坊郭户”和“乡村户”已经具有了与从事职业经济构成不同的区别。我们知道,建中元年 (780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改革,规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收税方式上区分出“居者”和“不居者”, “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20]两税法改革与之前租庸调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凡百役之费,一钱敛之”,加大了对货币征收的比重。而以“钱”作为征收对象,无疑对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百姓来说是件困难的事。因此,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的加大,以往并未对乡村民和城居民区分收税的方式逐渐不适应时势发展了。“坊郭户”城居者虽也有农民,但更多的是官员、军队、富室、商人以及手工业者。从前文所述可知,中唐以后社会商品经济交易发达,手工业者、商人数量增多,货币经济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兴盛,他们大多居住于城内,为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才有了元和年间规定的“坊郭户配现钱须多”和“乡村户配现钱须少”的条文区别。“坊郭户配现钱须多”也从侧面表明,“坊郭户”已成为城郭内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一个职业群体,这个群体已经为政府所认可,也就是私营手工业、工商业者的地位获得政府认可。因此中唐以后,随着国家财政需要的加剧,城市工商业者的地位也有所提升,这是城乡经济分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从这里开始,唐宋城乡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得以实现。
进入五代、两宋时期,“坊郭户”、“乡村户”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如五代晋少帝《收复青州大赦文》:“青州城市居人等,久经围闭,颇是凋残,……委本道以食粮赈恤。所有城内屋税,特放一年。”[21]宋代元丰二年(1079年)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产裁定免出之法。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三十千,并免输钱。续诏:乡村合随逐县民户家业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举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22]哲宗元祐二年 (1087年)臣僚上言: “兴复州县,若别无大利害,则惟坊郭近上(城)之户便之,乡村上户乃受其弊也……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此乡村上户所以受其弊也。”[23]又如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十一月:“以调度不足,诏诸路州县出卖户贴,令民具田宅之数而输其值。既而以苛扰稽缓,乃立价: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24]这些材料中,“坊郭户”多数都是和“乡村户”对应而出现,体现出在宋代,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已经被宋代统治者普遍认可了。“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的出现,是城市人口增长、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工商业队伍的壮大。
唐宋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不仅统治者这样认为,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现象也让诸多的官员、百姓认可了这种城乡差别的现实。比如在遇到灾荒救济年月, “诸处赈济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乡野,”[25]“乡村近者数里,远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籴则已居后”,以致“老稚愁叹”,为了避荒就熟不得不背井离乡。[26]在经济生活与思维习惯方面也体现出城乡差别,如唐末洪州 (今南昌)有一胡家,家境贫困,其小儿子偶然在一洞穴中捡到数百万钱,胡家因此大富,于是要迁往城中居住。[27]这表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城市已经成为富裕者居住之地,城市与乡村已经不一样了,城乡之间分离的意识除了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有所体现外,在思想观念中也已经成为当时人的一种普遍认识。
(二)“交相生养”新型城乡关系的出现
从上文可见,中唐以后,不论是在国家法令规定中,还是在士大夫、小民的自我意识中,都认为这个时期城市与乡村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城市已经从乡村中分离出来了。在城乡互相分离的同时,城乡经济联系和合作也日益加强,出现了“交相生养”新型城乡关系。
首先,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城乡经济关系耳目一新。唐末至两宋是古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在两宋形成了城市化的高潮,以至有学者认为唐宋时期出现了“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革命”。[28]唐宋时期 (主要是宋代)城市化的高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充实和外溢的特征。第二,由城镇的人口规模、经济职能、政权机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了一批经济城市,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第三,市镇和农村地区的经济、人口职业和社会生活都出现了非农业化。[29]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过程也是城乡关系调整的过程,是由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特征的城乡一体化走向城乡分离,再由城乡分离走向以城市社会为代表特征的城乡一体化运动。[30]唐宋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促进了城乡分工以及城乡之间在产业格局、人口构成方面的差异。应该指出的是,一般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将会使得城乡差别的程度逐渐减弱或消失,城乡融合度提升,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宋代城市化的水平仍然不高,城市化的范围和水平有限,宋代城乡关系依然呈现出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特点。
其次,市场的拓展为城乡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宋以前,城乡市场不甚发达。斯波义信认为,唐代以前“既没有进入地方贸易体系中的周期性集市,也没有发达的远距离贸易进入农民社会的生存空间”。[31]宋代以来,伴随着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纵向上看,联接城乡的市场等级体系已经形成。唐宋以前,乡村的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租税的形式而非市场的渠道进入城市,城乡之间的通过市场渠道而形成的经济联系较为薄弱。中晚唐以来,农村市场逐渐发育起来,市镇的发展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充当了良好的媒介;城市市场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经济对乡村的辐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村落小市场—县镇市场—中心市场这样的“以州府城市、县镇、草市各级中心地为序列的‘中心市场’等级网络”。[32]从横向上看,形成了涵盖城乡的市场流通圈。据斯波义信的研究,南宋时期的杭州已经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市场圈。第一层次市场圈是由杭州及其直属郊区组成的通商圈。第二层次市场圈是以杭州为中心的小范围腹地构成的商圈,是为满足杭州150万人口日常生活需要的直供商品和储备物资而形成的中距离商业运输圈。米谷、薪炭燃料、油脂、鱼肉、鲜活食品、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茶、盐等来自这一商圈而集聚于杭州,圈内的各种特产相互在地域内按行当分设营销设施。第三层次市场圈即以杭州为中心的最大腹地构成的远距离商业运输圈。[33]不仅杭州,宋代各个城市都存在这样覆盖城乡的市场圈。在市场圈内,通过城市消费的拉动以及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城乡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
在城市化和市场体系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与乡村间的经济互动逐渐频繁,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功能日益加强,乡村对城市的影响也渐趋突出,出现了新型的城乡关系。宋哲宗时殿中侍御史孙升说:“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郊,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34]这段话对于城市与乡村经济关系作了很好的归纳,他不是强调城乡的分离,而是强调城乡间的联系与合作,强调二者“交相生养”。这是对这个时期城乡经济关系很好的一个总结。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A].观堂集林 (第十)[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世本·作篇[Z].
[4]吕不韦.吕氏春秋·君守[M].
[5]赵晔.吴越春秋[M].
[6]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8]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9]刘向.战国策·赵策[M].
[10]王符.潜夫论·浮奢篇[M].
[11]司马迁.史记 (卷129《货殖列传》)[M].
[12]晋书 (卷5《愍帝纪》)[M].
[13]范晔.后汉书 (卷97《仲长统传》)[M].
[14]曹操.蒿里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23)[M].
[15]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漆侠.宋代经济史[M].中华书局,2008.
[17]刘昫.旧唐书 (卷48《食货上》)[M].
[18]杜佑.通典 (卷6《食货六·赋税下》)[M].
[19]王溥.唐会要 (卷58《户部尚书》)[M].
[20]刘昫.旧唐书 (卷118《杨炎传》)[M].
[21]全唐文 (卷 119,晋少帝《收复青州大赦文》)[M].
[22]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65之21)[M].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407)[M].元祐二年十二月丙申条。
[24]宋史 (卷174《食货上二·赋税》)[M].
[25]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上)[M].
[26]历代名臣奏议 (卷246《荒政》)[Z].
[27]胡我琨.钱通(卷17)[M].
[28]Mark Elvin(伊懋可):The Revolution in Market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See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1973,PP164—178.
[29]吴晓亮.宋代城市化问题研究[A].宋代经济史研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30]戴均良.中国市制[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
[31]Yoshinobu Shiba(斯波义信):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Market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See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J.W.eds.P41.
[32]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M].宋代城乡市场等级网络分析——以东南四路为例,宋代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33][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4]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394),元祐二年正月辛巳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