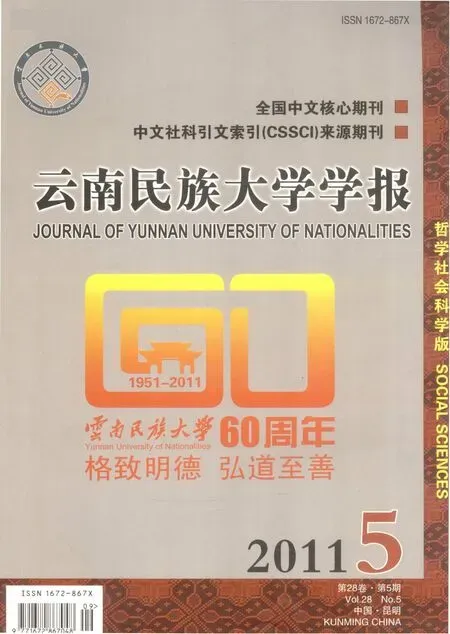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
尹绍亭,尹 仑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滇国的记载,但极为简略。今天人们认识滇国,主要依靠从滇王等墓葬中发掘出的多达15000余件青铜器所贮存的历史文化信息。滇国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独特,构思奇巧,制作精湛,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历来备受学界重视和推崇。考察滇国的青铜器,不难发现滇国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诸多明显差异,具有大量的动物形像,便是滇国青铜器有别于中原青铜器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对于此特征,云南考古学界张增祺先生等曾做过系统的研究。查阅相关的论述,可以看到考古和历史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大体相同,那就是将动物图像作为滇国的文化符号进行考察,借以解读滇人的社会和生活。这样的研究当然重要,把出土文物作为历史佐证的研究方法,历来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所沿用。不过,除了考古学、历史学之外,考古文物应该还具备多学科、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例如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审视滇国青铜器的动物图像,将它们视为“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媒介”,从而考察滇人认知、利用动物的知识体系,便是不落窠臼、另辟蹊径的视野。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之滇国
滇国为何称滇,有学者认为那是因为其时该地族群名为“滇人”之故;然而多数学者不同意此看法,而主张此名出自滇池(“滇”来源于“颠”,滇池出水口有似倒流,故名),因为滇国乃是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而建立的古国。
1.滇国是一个部落王国。《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从这三段话可知,西汉时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包括滇国在内的许多部落王国,它们经营农业,形成了聚落;滇国在西南夷中虽然算是较大的王国,然而其民众不过数万人,在大汉王朝的眼里不过是区区“小邑”,实为“小国寡民”。
2.滇国封闭,少与外界交通。《西南夷列传》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到来自中国西南的商品——蜀布和邛竹杖,回国后上奏天子,于是天子乃命使者出使西南夷,希望找到经西南去往身毒国的道路。滇王在接见汉朝使者时问道:“汉孰与我大?”滇王说此话,并非夜郎自大,而是因为滇国交通闭塞,与内地信息不通,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
3.滇国自然环境优越,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西南夷列传》载:庄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楚。”史家认为,“旁平地肥饶数千里”系指当时滇池区域及附近的大面积土地多被开发和利用,所谓“肥饶”当然是就农田而言的。[1]这样的看法与同传所说滇国“耕田、有邑聚”对应,是不错的。然而从地貌看,滇池地区不仅有盆地 (坝子),还有绵延起伏的山地,所以“旁平地肥饶数千里”除了指平地的农田之外,还应该包括山脉丘陵、广袤的森林和草原。《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鱼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显然,这里的“河土平敞”就不可单纯理解为“田鱼之饶”的农田水网,能“出鹦鹉、孔雀”的环境,自然是森林。就笔者生活过的地方而言,既有“田鱼之饶”,又“多出鹦鹉、孔雀”的地方,只有云南西南部的德宏和西双版纳。
二、青铜器上的“动物志”
自1955年至今,考古学者们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浦头三处滇国重要遗址进行了8次大规模发掘,期间还陆续发掘清理了昆明、呈贡、安宁、曲靖、东川、宜良、嵩明、富民、玉溪、路南、泸西、华宁、江川、新平、元江、个旧等地的许多滇文化墓葬和遗址,共获得以青铜器为主的滇文化文物15000余件,此外尚有100余件流失海外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2]滇国青铜文化兴盛于中原青铜文化衰落之际,而无论是从文化内涵还是从艺术风格来看,滇国与中原王朝的青铜器均迥然而异。中原青铜器充满着中原封建王朝的威仪和礼乐制度的丰富文化内涵,所以形制主要是礼器、乐器和兵器,装饰图案也多具相应的象征意义;滇国青铜器则表现出浓郁的部落社会特征,其青铜器中礼器较少,主要是生产、生活用具及兵器,其器物的装饰也朴实自然,极少抽象的图案,而多写实的图像。例如动物图像,在中原的青铜器上并不多见,而在滇国青铜器上却有众多灵动的动物,充分显示了部落社会与大自然共生、亲和的特点。滇国青铜器上的动物图像,计有虎、豹、熊、狼、兔、鹿、猴、野猪、狐狸、牛、羊、马、猪、狗、蛇、水獭、穿山甲、鳄、鹄、鹈鹕、凫、鸳鸯、鹰、鹞、燕、鹦鹉、鸡、乌鸦、麻雀、枭、雉、孔雀、凤凰、青蛙、鱼、虾、螺丝、鼠、蜥蜴、蜜蜂、甲虫等,多达40余种。[3]仅在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的青铜器里,便有各种动物图像296个;其中的一件铜臂甲,镌刻动物图像10余种,此臂甲因此被命名为“虫兽纹铜臂甲”。[1]
上述动物图像,自然不会是古代云南滇池地区动物种类的全部,然而如果把它们视为当时常见的动物种类,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滇国青铜器不仅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是十分宝贵的自然遗产,其塑造、刻画的数量众多的动物图像,可以称之为古代滇池地区的“动物志”。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图像,除了可以满足今人的审美需求之外,其蕴含的古代滇池地区的生态环境、生物、气候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信息,值得重视。
滇国青铜器多以动物为装饰的原因大概有以下4点:
1.滇国自然环境的反应。古代滇国具有十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此不赘。
2.滇人生计形态的反应。滇国青铜器中有铜锄、铜斧、铜铲、铜爪镰等生产工具,青铜贮备器图像里有“播种”、“上仓”图,说明农业已是滇人的主要生计。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最多的是牛,然而滇文化研究者们皆认为滇人“耕田”是“锄耕”而非“牛耕”,即农业尚未使用牛,那么滇国的牛就是畜牧业的主要对象了。除牛之外,滇人还饲养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家畜。大凡人烟稀少、森林茂盛的地方,就一定少不了狩猎。狩猎不仅是肉类食物获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男人们酷爱的充满惊险和刺激的活动。滇国得天独厚,坐拥“方三百里”的滇池,周边河流纵横,不仅有舟楫之利,还有渔捞之饶。畜牧、狩猎和渔捞,使人们成天和各种动物发生密切的关系,青铜器的动物图像便是生计和生计资源的形象表现。
3.滇人动物崇拜的反应。滇国境内多沼泽、湖泊 (如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杞麓湖、异龙湖等),又多茂密的原始森林,经常有大量野兽和毒蛇出没,对人们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滇人崇拜动物之神,尤其对人畜有伤害的虎、豹、毒蛇、鳄鱼等更加畏惧,由畏惧进而乞求、崇拜,将动物视为神灵供奉祭祀,祈望人畜平安。如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一件祭铜柱场面的贮贝器,柱的中段盘绕着两条大蛇,柱的顶端立一虎,下段横绕一条鳄鱼。铜柱边有四个待杀的人,显然是将人作为牺牲祭祀的场面。又如石寨山12号墓的一件祭祀贮贝器上也立有铜柱,柱上盘绕一条大蛇,蛇口中衔一人头,使人望而生畏。[1]
4.滇国冶金铸造技术达到较高水平的表现。任何金属的艺术造型,无论题材如何神奇,构思如何巧妙,如无制造和加工技术工艺的支持,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滇国青铜器的动物造型、雕刻复杂多变,精细入微,在两千多年前,滇国竟有如此发达的冶金铸造和雕塑的技艺,实在令人惊叹!
三、滇人对动物的认知
凡属能够充分享受大自然恩惠的人类社会,必有丰富的生态经验和知识的积淀。关于这一点,不要说古代,仅就笔者过去20多年对云南十余个山地民族的调查而言,便足以证明。那些一直被人们视为所谓“原始、落后”的民族,其对自然感知的敏感,对动植物特性的熟悉,就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非文明人、现代人能够望其项背。例如基诺族,几乎人人是“动植物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基诺族根据热带山地垂直变化的气候和土壤进行轮作、间作和混作的栽培植物还多达100多种,其中陆稻就有74种;雨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仓库,说起动植物人人如数家珍,他们常用的食用及药用野生植物近500种,狩猎的工具和手段形形色色,人与动物的关系竟然达到了相互熟悉对方的声音、气息和习性的程度。由于缺乏资料可考,我们已无法得知滇人对植物分类、利用的知识,而从滇人青铜器上塑造的动物众生像,却可以窥见滇人动物分类认知之一斑。李昆声教授曾从艺术史的视野把滇国的青铜动物图像分为下述四种艺术造型:
第一类为单独一件动物圆雕,一般表现家畜、家禽、飞禽和温顺的食草动物。
第二类为动物群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类动物作一组合,在一件高浮雕上表现出来,如群牛、几只孔雀等;另一种是表现动物搏斗题材。
第三类是人和动物的组合,有表现放牧、狩猎、剽牛祭祀等内容。
第四类是用立体动物雕塑来装饰在青铜器上,大量是装饰在兵器上。[3]
如果把李教授的艺术分类还原为滇人的认知分类,那么动物图象表现的就是生态系统中各种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系统内的各种关系,也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为各种动物的独立图像,例如牛、马、鹿、鸡、鱼、鸟、蛙、蛇、鹰等。此类图像反映的是滇人生境中与人类共生的常见的动物,显示了滇人对生境动物多样性的认知。
第二类是表现同类动物种群生态的图像,例如“二牛交合扣饰”、 “五牛线盒”、 “四牛头铜扣饰”、“三孔雀铜扣饰”、“鸡边组合扣饰”、“蛇边组合扣饰”、“猴边组合扣饰”、“狐边组合扣饰”等。此类图像表现了在生态系统中动物交配、繁衍、群聚生存的状态。
第三类是由两种动物生态关系构成的图像,例如滇国青铜器最具代表性的重器“牛虎铜案”以及“虎牛铜枕”、“八牛虎贮贝器”、“虎牛搏斗铜扣饰”、“虎噬牛啄”、“三虎噬牛铜扣饰”、“驯马虎贮贝器”、“二虎噬猪铜扣饰”、“二虎噬猪铜扣饰”、“虎熊搏斗铜戈”、“二豹噬猪铜扣饰”、“豹衔鼠铜戈”、“三狼噬羊铜扣饰”、“二狼噬鹿铜扣饰”、“水獭捕鱼铜戈”、 “三孔雀践蛇铜扣饰”、“鸟践蛇铜斧”、“鸟衔蛇杖头铜饰”、“水鸟捕鱼铜像”、“鱼鹰衔鱼铜啄”等。在此类图像中,均以两种动物结合造型,表现了动物界不同等级的肉食动物之间以及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的生态关系。
第四类是由数种动物生态关系构成的图像,如“虎豹噬牛铜扣饰”、“虎豹噬鹿铜扣饰”、“狼豹争鹿铜扣饰”、“虎牛鹿贮备器”、“桶形铜贮备器”等。此类图像动物多于前类,内容更丰富。例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桶形铜贮备器”,其器桶上有两只老虎,呲牙裂嘴、虎视眈眈欲扑向桶顶奔跑状的两只硕壮的黄牛,而在一牛腿之下又藏卧着一只猛虎,张着血盆大口两眼瞪着铜顶所立一棵树上的两只猴子和两只鸟,猴、鸟做惊恐状。此类图像或为几种动物捕食一种动物,或为一种动物捕食几种动物,表现了高级肉食动物捕食对象的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的激烈竞争。
第五类是多动物生态关系构成的图像,代表器物如李家山墓葬出土的“虫兽纹铜臂甲”。此臂甲为圆筒状,开口上大下小,高21.7厘米,上口径8.5厘米,下口径 6.6厘米,甲面刻画虎、豹、猴、熊、野猪、鸡、鱼、虾蜈蚣、蜜蜂、甲虫等10余种动物。中国古代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句,虽然比喻的是政治军事关系的危机四伏,然而无意中却揭示了自然界动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关系。相比之下,滇国“虫兽纹铜臂甲”上所刻画的各类动物相互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和精彩:一头老虎腾空而起,圆睁双眼,张开双爪,做凶猛捕食状,其下为慌忙逃亡的野鹿和猴子,还有不知祸之将至、迎面游来的鱼和虾;一头硕壮的野猪口里衔着一条蛇状的捕获物,不料另一头剽悍的豹子已然扑到了它的身上;一只公鸡正在得意地啄食蜥蜴,而其同伴却被狼咬住了脖颈,在狼的后面,又虎视眈眈地立着三只豹子;一只蜜蜂凌空飞翔,当遭遇危险时,它对任何动物都可蛰上一针,然而其蜂窝不管是深藏于土里还是高避于树上,都往往难逃厄运,道理不难明白,其蜂蛹乃是许多动物梦寐以求的美食。“虫兽纹铜臂甲”刻画的图像,可视为表现滇人认知动物的杰作。如果说上述三、四类图像表现的是较少动物种类之间的简单的生态关系、据之尚不能感知动物生态系统的面相和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结构的食物链的话,那么“虫兽纹铜臂甲”的图像可以说在这方面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将众多动物 (消费者)按食物关系进行组合,显示了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能量流动,滇人认知动物的水平在此图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四、滇人对动物的利用
上述“虫兽纹铜臂甲”可视为一个由多种动物的食物链构成的动物生态系统。然而如果把这个系统扩展开来,其食物链结构还可以进一步拉长:从下端走,可有各种虫类、小生物以及微生物;从上端走,顶级肉食动物之上还有更顶级的消费者,那就是人类。人类与动物是共生的系统,这可以说是滇人的切身感受,正因此如此,所以滇人在青铜器上展现其生态和生活的时候,不仅刻画塑造了各种动物结合的图像,而且还着意刻画塑造了一批人和动物组合的图像。赏析此类图像,可以看到在滇人的生态系统中,动物作为其结构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滇人把动物纳入其生态系统,不仅充分调动技术手段猎取作为生理需求的蛋白质的野生动物,而且还将动物作为文化的“媒介”和“载体”在精神需求的空间发挥特殊的功能。动物在滇人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可从生计、娱乐、宗教和艺术4个方面得以了解。
首先说生计。滇人生计中的动物利用,主要是狩猎渔捞和家畜饲养。
1.狩猎。在食物获取的活动中,人类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就像前述许多表现动物捕食的图像那样,动物捕食均为本能的行为,是简单、直接的捕捉、搏斗、撕咬、噬食,而人类就不是那样。请看滇人的狩猎,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获取食物,然而滇人狩猎的方式却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滇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例如铜矛、铜戈、铜斧、铜鉞、铜剑、铜刀、铜棒、铜叉、铜弩、铜剑、鱼钩、渔网鱼叉和鱼笼等;其次,滇人狩猎除了个人行动之外,更多的是集体协同操作,例如李家山出土的“八人猎虎铜扣饰”、“七人二犬猎豹铜扣饰”、“三人猎虎铜扣饰”和“三人猎豹铜扣饰”、“二人猎野猪铜扣饰”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第三,滇人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还发明了许多巧妙的狩猎方法,例如设置陷阱等,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铜矛,其套口部的上段有横杆、凹形的栏槛及绳索等物,栏槛中围困着一虎,此即为陷阱的表现;第四,滇人能够把某些动物作为狩猎和渔捞的工具加以利用,例如借助马力和猎犬追逐猎物,利用鱼鹰捕鱼等,这在石寨山出土的“骑马猎鹿铜扣饰”,李家山出土的两件“骑士猎鹿铜扣饰”和“三人猎虎铜扣饰”,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鱼鹰衔鱼铜扣饰、6号墓出土的鱼鹰衔鱼铜啄、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刻有鱼鹰逐鱼船纹的铜鼓中清晰可见。
2.畜牧业。狩猎是人类直接从大自然获取动物蛋白质的一种方式,畜牧业则是人类凭借其智慧和经验所进行的动物驯化、改良、生产和利用。从青铜器上的动物图像可知,诸如牛、马、狗、猪、羊、鸡等凡适宜作为家畜的动物,滇人均已驯化饲养。反映家畜饲养的青铜器有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楼下设置饲养牛、马、猪、狗、鸡的“干栏式房屋模型”、 “二人驯牛鎏金铜扣饰”、 “牧牛铜啄扣饰”、“斗牛场景扣饰”和“牧牛器盖”,还有李家山出土的“喂牛铜扣饰”、“驯马贮备器”、“牧羊图像”、“鸡形杖头饰”等。饲养家畜,首先可以按照人类的需要生产足够的肉类,其次可以进行畜产品的交换和贸易,第三可以使用畜力,第四是某些特殊场合的需要。滇国青铜器有表现武士骑马进行战斗和狩猎的场面,说明滇人驯马、用马的技术已臻完善。在滇国青铜器的动物图像中,牛的形象最多。以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为例,出土的青铜器上共有各种动物图像296个,其中牛为96头,约占总数的34%。[1]关于滇国的牛,笔者对前人的研究有两点不同的看法。其一是牛的种类,此前考古学者们均一致认为滇国青铜器表现的牛皆为黄牛而无水牛,此说值得斟酌。首先,云南自古便存在水牛和黄牛两个野牛种类,古代滇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完全适合两种野牛的生存,既然如此,滇人便没有道理只驯化黄牛而不驯化水牛;其次,从李家山墓葬出土的“叠鼓形铜贮备器”等器物上的牛的头、角造型来看,显然是水牛而非黄牛。其二,《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国“耕田,有邑聚”,对于《史记》所说的“耕田”,学者们一致认为此乃“锄耕”而非“牛耕”,因为“耕牛”二字迟至东汉才出现于相关文献,而且滇国青铜器上的牛均未穿鼻,也无犁耕图像,所以肯定其时尚未产生牛耕。对此笔者也有不同看法。所谓“牛耕”,除了当今所见所行的耕牛穿鼻拉犁的耕作方法之外,其实还有别的方法,例如“踏耕”或称“蹄耕”,即为另类的“牛耕”。 “踏耕”的方法,是驱赶牛群入田,往复踏泥,从而使土壤细碎熟化,达到耕作的目的。踏耕是分布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耕作方式。樊绰所著《蛮书》卷四载唐代滇西南的“茫蛮部落”“土俗养象以耕田”,一些学者不解其意,以为是记载出错,其实不然,《蛮书》所言之“象耕”并非是大象拉犁耕作,而是使象踏耕。西双版纳昔日便确有使象踏田之农法。牛之踏耕,目前在广西、云南等地已经绝迹,幸运的是,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红河地区调查时竟然偶然碰上了踏耕,其时激动兴奋之情无法形容,由于必须赶乘汽车,只好匆匆观察,拍下了几张珍贵照片。所以,从历史文献资料结合民族学田野资料来看,滇国的“耕田”很可能就是“踏耕”,这也就是滇国多牛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滇国畜牧业的状况,除了可从青铜器考证,文献亦有记载。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和韩说初开益州郡, “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汉书·西南夷传》说“昭帝始元五年 (公元前82年),汉将田广明用兵益州(郡),获畜十余万。”《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二十一年 (公元45年)刘尚击益州郡少数民族头人栋蚕,得“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从上述中原王朝几次从滇国所得牛、马、羊的数量看,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数量确实惊人,其畜牧业之发达可见一斑。
其次说娱乐。石寨山墓葬曾出土一件“斗牛铜扣饰”,呈长方形,小小扣饰表现的观赏斗牛场面颇似西班牙斗牛场风景:扣饰牌正中开一门,牛正从门口走出,门两边分列五人,头戴长角状装饰物,手中抱着圆形物体,应是为牛造势鼓气的队伍;门楣上蹲踞一人,为开门者;扣饰的上端紧密排列着11个人,显然是观众,表现了人们对观看斗牛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斗牛之风,即使在今天也十分盛行,它是中国西南彝族、苗族、瑶族等民族节日期间必不可少和休闲时经常举行的娱乐活动,滇国“斗牛铜扣饰”的发现说明,斗牛活动在云南已有悠久的历史。
再说宗教。石寨山墓葬出土了两件“干栏式房屋模型”,房屋底层有形态各异的牛等家畜,楼上的晒台和屋内有多个人物形象,其形状、结构与当代傣族等许多热带、亚热带民族的房屋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件房屋模型晒台的柱子上挂着一个牛头,十分显眼。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西南山地调查,对于景颇族、佤族村寨悬挂牛头的景象记忆犹新。那时凡到景颇族山寨,一进寨门,便可看到高挂牛头的木桩;凡进景颇人家,屋后粮仓的门上必然能见到悬挂的牛头;如果有幸遇到烧地和播种前进行的农耕仪式,观看惨烈的剽牛和把带血的牛头高悬到竹竿之上,那情景更令人难忘!景颇族为何尊崇牛头?那是因为他们认为牛头可以避邪驱鬼、防灾佑福之故。比较而言,悬挂牛头的习俗在佤族村寨更为盛行,而且更为壮观。景颇族在每个场所通常只悬挂单个牛头,而佤族却不同,各家悬挂数量不一,少者数个,多者十余个。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佤族不仅把牛头作为辟邪驱鬼、防灾佑福的吉祥物,而且还将其作为财富的象征,谁家牛头挂得多,便越显富裕和权势。观察滇国干栏式房屋模型,一看便知乃是富裕权势的贵族之家,房屋廊柱高悬牛头,自然如景颇和佤族有其象征的深意。在佤族、景颇族等山地民族中,剽牛是与牛头崇拜密切相关的仪式。在人们举行的农耕仪式和新年等节庆活动中,为了祭祀山神、神林、祖先、谷神等神灵,必定要剽牛。牛被剽杀之后,人们或争相抢食肉血,或每家每户平均分配。剽牛习俗,集娱乐、认同、信仰和具有生态学意义的蛋白质补充及平衡肉食分配功能为一身,千百年来经久不衰,而探索其源头,则可追溯到滇国的“剽牛祭祀铜扣饰”之上。
最后说艺术。滇国青铜器以众多动物图像为装饰,形成了有别于中原等地青铜器的突出的艺术特色。滇国青铜器为何偏爱动物图像的装饰?前文说过,原因可从滇人的生境、生计、动物崇拜及冶炼铸造技术4个方面去探寻。而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大凡看过滇国青铜器的观众,都会对其塑造的琳琅满目、栩栩如生的动物图像留下深刻的影响,引发震撼和感动,原因何在?那就是美的力量。对于滇人而言,动物是家里、田中、山林须臾不离的“伴侣”,是其物质和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从滇人的青铜图像不难看出,在滇人的眼里,动物简直就是美的化身。其不同的形态,多样的习性,时时发生于眼前的一幕幕追逐、搏斗、厮咬、噬食的情景;骑士勇猛战斗、逐鹿的场面,猎人伏虎降豹的景像,牧者悠然放牧的画面,无一不蕴含着浓郁的美感。这种由动物带来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生活之美,情感之美,深深嵌入滇人的心灵,融入他们的血脉。滇人对于动物美的强烈感受并由此创造的卓越的青铜动物造型艺术,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园地增添了瑰丽的奇葩。
结语
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滇国青铜器的动物图像,基本的着眼点,在于解读滇人对动物的认知和利用的知识和技术。而往深层思考,又能感悟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以下两点,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给人以强烈的人与动物“共生”的想象,它使我们感受到人与动物共生的多重含义:1.动物是自然界的大家族,人类也是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2.大自然赋予所有动物生存的权利,各种动物均充分彰显着大自然造化的各自的特性并充分享受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恩惠;3.在大自然中,所有的动物均处于特定的生态系统之中,具有特定的生态位;4.在生态系统中,各种动物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竞争的关系,是特定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的关系;5.人类在大自然中,也有自身特定的复杂的生态位,人类既是某些高级肉食动物可能伤害的“次级消费者”,同时又是大量动物的顶级消费者;6.在自然界中,人类受动物的恩惠最多,滇人如此,其它族群也同样,在人类300多万年漫长的狩猎采集时代,动物就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和主要的食物供给者;7.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感恩、敬畏动物,或视动物为图腾,或将动物作为神灵,顶礼膜拜。
其次,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可谓“有大美而不言”,而生态美却是其美之核心。滇人朴素、独特、浪漫、粗犷的生态审美情趣,令人陶醉、享受、激动。其生态审美融合着下述多种美的元素: 1.动物多样性丰富、绚丽的自然之美;2.动物形象、特性的造型之美;3.动物世界相生相克的共生之美;4.崇尚勇猛的野性、强悍、智慧之美; 5.敬畏、崇拜动物神灵的谦虚、虔诚之美等。
滇国的青铜器,历来被视为青铜文化的奇葩,面对其琳琅满目的器物,观赏者总不免要发出由衷的赞叹。对于其所具有的眼球的冲击力和心灵的震撼力,人们总是将其归结到它们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的造型之上。其实,其感人的力量并不完全外露于风格和造型,还在于风格和造型的象征,那就是人与动物共生的深远意蕴和生态审美的瑰丽意境。而这样的意蕴和意境,正是当下社会所严重缺失的。
[1]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2]蒋志龙,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李昆声.云南艺术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YIN Shao-ting,Ying 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