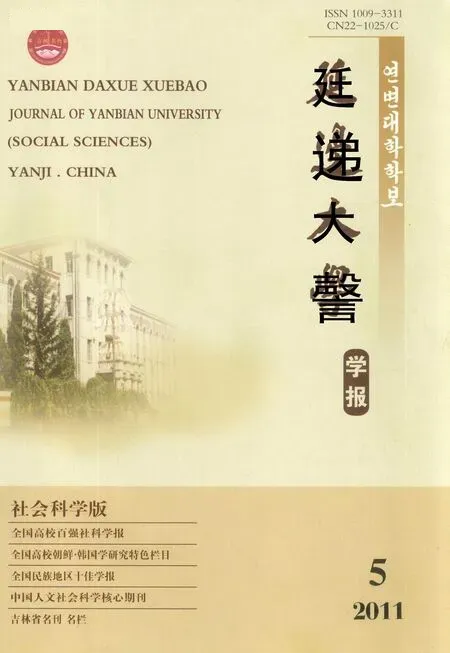士人批评的知识论特征解读
李 胜 清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411201)
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担纲着启蒙和教化的文化功能,他们主要是通过文学文化的生产、传播与阐释为整个社会提供着精神支撑与意义模式。士人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知识形态,在古典文学及其思想语境中,士人批评与古典文学史、古典文学理论处于一种知识共在的关系,它的知识领域既指涉着经验性的文学史层面,也关涉着理论性的古典诗学问题。作为一种以准理论性的形式而呈现出的接受美学次级形态,士人批评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意识形态义项,就基本构成元素而言,士人批评因为反映着现实的政治秩序与道德伦理等社会性诉求而呈现为某种教化性或实用性的知识形态;同时,士人批评也具有某种内指性,即从审美自律的角度对于文学文本自身所做的美学关切,这使得它呈现为某种审美性或非功利性的知识形态;此外,士人批评也是对于批评主体的某种反思与自我反思,它是古代批评家借以表达其对于自然万物、社会人生所做的形而上之思,因此它也呈现为一种诗性的或具有终极信仰意味的知识形态。在其现实性上,当人们从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来观照士人批评时,它的特征主要就表征为这样三个层面,三个层面的意义互动与视域融合规定着士人批评的复调知识论身份。
一、教化性的实用知识角色
从政治道德等教化角度来建构士人批评的思想身份是古代中国文论意义域的基本知识倾向与思维惯性。“文以载道”便是士人批评实施教化表意的基本立论基础与言说策略。在古代中国,士人批评从一开始就沾染着浓重的实用理性与经世致用的世俗意味。其意义表达的起点与终点设置都是基于某种现实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建构主义考量,通过批评以阐发封建王权政治与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构关系,确立王权政治秩序的历史合法性,调整社会关系与整饬社会规范,等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士人批评以封建秩序的代言人身份为当时的现实政治道德秩序提供了一种意义支撑与价值范式。
孔子和孟子以儒家思想奠基者的身份确立了古代士人批评的教化理路,“温柔敦厚”的诗教正是在孔孟时代被确立为士人批评的正统身份。孔子以中和之说建构了士人批评的基本教化内涵,对于《诗经》,孔子的评价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歌文本中的中和之美决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内置的形式装置,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介入性,其目的是为现实的政治秩序、君臣关系以及道德伦理关系提供示范性的意向,塑造“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总体性社会语境。建构符合儒家道统与封建王权政统的实用理性与实践规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拒绝或解构那种不利于正统秩序的所谓异端思想和行为,诗人批评在这一点上也显示了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论语》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凡是超出了儒家基本礼仪规范的思想和行为显然是不兼容于士人批评的教化取向的。应该说,儒家所确立的这种诗人批评的教化范式一直构成了文学史发展的正统,左丘明在继承这种教化精神的基础上更是放大了其所具有的道德启蒙与价值教化的意义,立意于对现实政治统治与道德伦理的改善,左丘明明确为《春秋》进行了教化性的定位,“《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上之人能使照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在左丘明的批评视野中,弘扬善行与惩戒恶德是《春秋》的基本主旨,它确立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问题域,也引导着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的思想风尚。两汉、魏晋、六朝祖述着诗人批评的教化传统。司马迁、扬雄、郑玄和刘勰等的言述就是在一种变化了的时代语境下对于教化性士人批评的新拓展。司马迁对于《国风》、《小雅》和《离骚》的批评继续体现着教化性的理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与政治判断架构着司马迁对于这些文学文本的评判,褒扬前两者而贬抑《离骚》正是一种政治实用理性意识的历史张扬。扬雄对于自己早年宏辞丽赋的深刻自责与悔悟,刘勰对于诗歌“持人性情”功能的强化都反映了士人批评教化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而到了唐宋时期,士人批评不但深化了文学教化的内涵,而且拓宽了士人批评的教化叙事范畴。将士人批评的教化意识课题化与自觉化是这一时期许多士人在进行批评时的主动选择,孔颖达将“温柔敦厚”的诗教作了进一步的内涵解析,“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3]而王安石则在一种明确的意义上直接推进了士人批评的教化性质,“上通乎道德,下止于礼仪”对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歌教化功能直接提供了实用性的注脚;韩驹则从士人批评的主体与诗歌教化功能的关系维度论述了这一点,“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谓‘思无邪’也。先具此质,却论工拙”。[4]它意味着,政治道德教化标准是诗歌文本的第一要务,士人批评在建构诗歌文本的意义世界时也必须先注意其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道德影响,至于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则是次要的了,很显然,这种着力强调士人批评的教化维度的极端做法已经步入了庸俗化的边缘,其观点也失之偏颇。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士人对批评教化维度的重视程度。时至元明清,士人批评依然高标着文学品评的教化功能,虞集、杨慎、陈子龙、魏禧、沈德潜等人关于诗歌所倡导的“微言大义”几乎都是按照道德教化的标准来进行命意的,激浊扬清、纯化民心、匡扶正义成为士人批评的基本历史承诺,而贯彻其核心的却仍然是孔孟确立的那种规范性的教化性文学观念。就此而言,士人批评的发展事实上就是一种连续性的道德启蒙与道德教化叙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士人批评被视为一种教化性的知识谱系显然也是符合古典诗学的基本价值立场的。
士人批评所具有的深刻教化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古典批评的民族性规定。在中国古典诗学语境中,道统与政统不但是道德与政治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是一种整个社会的意义框架与逻辑起点,它作为总体性的立法范式,不但规定着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边界与性质基调,而且更是以具体的方式参与到文化、审美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因此,士人批评在形成其知识形态时就会彰显一种鲜明的道德与政治因素,而其对于社会的文化观照也必然地会呈现出强烈的介入倾向与教化色彩。
二、体验性的审美形态
作为阐释审美文本的对象化形态,士人批评非常注重从文学文本自身的角度来探究其审美性的生成与存在。从审美形式和内在特质来看,文学文本主要体现为某种想象性与体验性的感性对象,在这方面,士人批评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究文学文本的美学风格、形式结构及其形成的规律与特点。也就是说,士人批评的阐释内容中也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相关美学感悟与审美体验感受,这一点就使得士人批评在其鉴赏判断中也呈现为一种具有理论意味的审美知识形态。
自从文学文本自身的审美特质成为某种相对独立的批评对象时起,士人批评就在传统的道德教化角度之外建构了文学批评的美学之维,即从相对独立的美学视角对于文学审美意识的开掘,就此而言,与道德教化性的知识形态并置并一同获得发展的还有一种体验性的审美知识形态在规定着士人批评的基本问题域。孔孟之说虽然侧重于文学批评的道德教化功能阐发,但是在其道德诗教的言述中也潜藏着丰富的关于文学想象与体验等纯粹审美方面的知识元素。“尽善尽美”与“文质彬彬”之说就显露了早期士人批评的审美化倾向,“兴观群怨”的“兴”实际上已经切入了文学审美想象与修辞的批评范畴,叶朗就此分析认为,“所谓‘兴’,即诗可使欣赏者的精神感动奋。这种精神的感发是和欣赏者的想象、联想活动不可分的,因而是和诗歌的审美形象不可分的”。[5]这说明当时的士人批评已经注意到了诗歌创造与接受的美学特征。而“诗缘情而绮靡”就直接论述了诗歌的情感性与形象性规定。沿着这种思维理路,后来的士人批评不断地深化着这种认识,并且在长期的审美批评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审美批评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旨在阐发文学审美情感、想象与体验特征的美学命题,也形成了相应的美学范畴系列。就文学文本的形成而言,士人批评认为古典文学特别是抒情性文类主要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审美效果,在具体的过程中,以自然美的意向来构建和类比性地书写主体的审美感受是古典文学审美形态生成的主要形式之一,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说法就是选取自然的意向以生成文学艺术的审美世界,审美性的想象、情感与体验正是驱动作者创造文学文本的基本动力与主要内容,因为正是自然美在形式感上与创作主体或接受主体内在审美结构的异质同构关系最终促成了文本审美价值的生成。很显然,士人批评的阐释内容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审美知识与美学判断,叶维廉认为士人批评的目的就在于“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发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6]再就文学的鉴赏批评而言,士人批评也遵循着一种审美的逻辑,刘勰的“披文入情”之说就是希望读者透过审美形式的外观而达入文本的审美内核,即内在的审美情感本身,而对于这些以审美意象与形象存在的情感,适合的批评鉴赏方式就是“味、涵泳、悟”等直觉性的方式,“澄怀味道”、“虚一而静”、“涤除玄览”、“澡雪精神”等等都是根据并适合于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的一些审美鉴赏方式,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典的士人批评也被称之为一种“寻美的批评”。与此相匹配的是,在士人批评的视域中也形成了诸多的具有纯粹审美意义的批评范畴,意境、传神、滋味、气韵、含蓄、婉约等在本质上都是士人批评对于文学文本内在审美特性与审美状态的揭示与评判;在审美风格上,士人批评也形成了丰富而鲜明的一系列美学范畴,典雅、绚丽、自然、疏放、清越、奇险、扑野、古拙、空灵、飘渺、雄劲、质朴、恬雅、浓丽、清淡、孤瘦、荒寒、幽邃、明净、野逸等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征,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古典士人批评所形成的论述也凸显了鲜明的审美性知识形态的倾向,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严羽的《沧浪诗话》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都是因为其自身的审美性批评理论身份而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的。
士人批评之所以会呈现为某种深具情感性、感悟性与体验性的审美知识形态,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形象思维特征与主体身份。从思维特征而言,中国古典的形象思维方式不但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主导逻辑,而且也是古代阐释学与古典批评的支配性逻辑构架,它以同一性的思维机制规定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方式,显示出这两者在知识谱系上的亲缘性与共在关系;在主体身份层面,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职业的作家队伍与批评队伍,这个队伍往往是处于一种身份叠加的状态,诗人与批评家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本质上却代表着相同的价值诉求,共同建构着文学文本的审美之维。
三、形而上的诗性知识形态
除却被建构为教化性与审美性的知识形态之外,士人批评作为知识形态的复调性特征还表现在它的主体性形而上之思方面。士人批评不但关乎文学文本与现实政治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乎文学文本自身的形式审美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人与人性的深度关怀。作为对于人本身及其主体存在的诗性思考与形而上的追问,士人批评也被建构为一种指涉人的存在意义的具有终极信仰意味的人文主义知识形态。
士人批评的基础问题与终极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性的某种深度提问,抑或是对于这种深度问题意识的终极解答。关注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索解文学文本自身形式审美的意义最终都是皈依人与人性的问题域,都是为了寻求对于人与人性的本体论认识,以期获得人生的终极意义承诺。作为士人批评原型创立者与典型代表的孔子曾经从存在论的角度提出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形而上命题,为世俗人们的人生意义提升提供了示范意向与应然维度。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理论意识同时获得自觉的历史时期,其中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显示了一种很强的形而上色彩,邓新华在其《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点评,“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普遍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格。作家、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寄寓着深层的思想意蕴和精神上的无限象征意义”。[7]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关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过往的历史文化镜像,并结合自己的人生际遇直接裸呈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其意义范围不但牵连着自我的人生慨叹,而且也抒发了对于宇宙洪荒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历史本相的喟叹,表达了一种形而上的人类学之思与存在论的生命观。魏晋南北朝关于人生苦短、生如夏花、命运无常等的思考也经常是士人批评所倚重的一个价值命题。艺术、美学、生命在士人批评的意义域中实际上就是异质同构的,中国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在“天人合一”理念的统摄下,中国人总是将生命意义艺术化与审美化,“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中国古人自然地用‘生’来观照天地万物,对待文学创作,把文学也视为与人一样的生气充盈、活力弥漫,乃至是血肉完整的生命实体”。[8]也就是说,在士人批评的阐释结构中,文学文本的诗性意向不但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审美反映,而且更是一种主体性的生命意识展示,它通过营构一种审美世界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地,也为人类那挥之不去的生命寻根行为提供了诗意的注释与合法性辩护。人类只有在诗歌所营造的审美乌托邦中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人,而只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才永远牵挂着那种诗歌建构的历史诗情与终极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其批评指向的形而上意味。士人是立法者与启蒙者,对于世俗社会的日常生活而言,士人不但要从技术层面提供可行性的现实法则,而且还要为整个社会的秩序、政治道德生活与文化传统提供价值支持与意义框架,士人批评的介入性品格规定了它不但要在私人层面解决好主体个人的道德皈依与生命有价问题,而且还要以公共话语的身份为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的文明演化提供最终的合法性依据与精神信仰。作为一种深具人文性的意义系统,士人批评基本而经常的使命就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拯救与规划,它因为拯救人生的无奈与虚无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同时,它又因为规划人生而彰显一种丰厚的生命底色与价值承诺。
士人批评具有三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扇面,但在现实性上,这三种知识形态处于一种视域融合的状态。从意义阐释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知识形态的基本内涵要得到全息性的绽放都必须获得其他两种知识形态的意义支持,否则,它的意义域就只能是一种残缺性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士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总体性,其基本的思想内涵就是,或者是探究教化性知识形态、审美性知识形态与形而上的诗性知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就是探究这三种元素所构筑的关系构架下的任何一种知识形态。
[1]刘宝楠.论语正义[Z].上海:上海书店,1986.294.
[2]王寿亨.本原·教化篇[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1.
[3]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2.
[4]王大鹏,张宝坤,田树生.中国历代诗话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5.493.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0.
[6]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2.9.
[7]邓新华.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9.
[8]黄霖,等.原人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