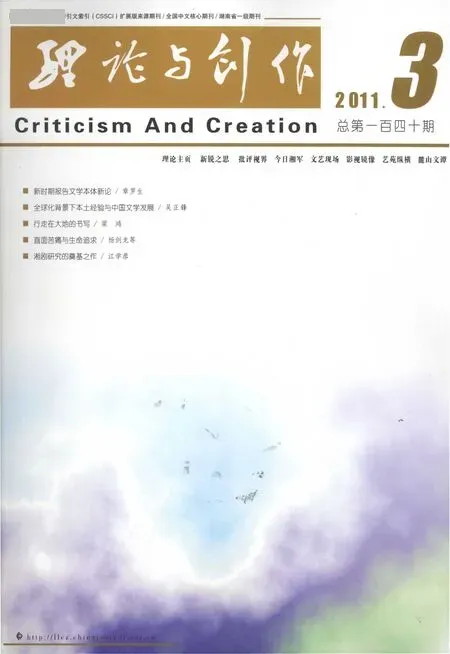张心平笔下老人形象的文化寓意
■向成国
张心平笔下老人形象的文化寓意
■向成国
张心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岁月之磨》、《草民》。收在这两个小说集中的有20多个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湘西酉水河沿岸土家百姓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反映了这一地区土家人民的生存面貌。其风格笃实、浪漫、深情、淡定、朴纳、丽质,像酉水河的河水一样,时而气色氤氲,时而清净透明,总是欢畅怡然;也像酉水河两岸的青山一样,有的雄奇伟岸,有的秀丽华美,总是庄谐自得。作品写人们相互间的矛盾,但这矛盾如同茶杯里的风波——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潮,却能揭示出生活的真谛;写民间的仇杀,这仇杀带着人身的血滴和余温,描摹着酉水河两岸土家百姓生存的历史;写底层的苦难,苦难的极限莫过于死亡,但就是在死亡面前,土家儿女大悲大痛常常被如常的生活取代,由此表现出的土家儿女生存的执著与坚韧,是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能改变的。那宁静的村舍,袅袅的炊烟,欢畅而永不停息流动的溪水,转角楼上、楼下、楼里、楼外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使你觉得张心平的小说就是画,就是诗!而读他的作品,你会很快沉入作品的意境中,被作品描写的生活所感染、所陶醉!
在张心平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塑造了一个老人形象系列。这些老人形象个个鲜明、生动,极其典型。这批老人负载着历史的艰难,常与痛苦和不幸为伴,然而他们生的欲望、生的热情、生的执著是那样的光彩熠熠。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所表现出的刚毅、坚强,善良、宽容把平凡的生活点缀得斑烂夺目!这些老人形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而通过老人系列形象,揭示出某种文化寓意,正是张心平的刻意追求。
一、人性本真的艺术展示
张心平的作品成功之处,就是通过老人形象的塑造,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本真,从本质上揭示和颂扬了人性的善良。
真诚是人性本真最直接的表现,真诚是老人们的心理结构,是他们生存的支点、基点,是他们人生的准则、人生价值判断的基本尺度。人性的真诚是张心平老人形象描写的一个亮点。在《岁月之磨》、《水塔与夕阳》、《火钳》、《翠屏怨》等作品中都以老人为中心,演绎着人间最为动人的、突显人性真诚的故事。
张心平把人性的善良置于小说创作的中心位置,用十分虔诚的态度去描写它。在那些老人身上,我们民族固有的善良宽容的本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首先表现在人们相互的关爱上,而这种关爱又常常以情义为联结,表现出人们相互间的友谊。短篇小说《夜雾,升起在河湾》的主人公小镇上的老理发匠寿祺老汉,有一个装理发工具的红色小木盒,是他的随身宝物。木盒是广木匠精心选取上好的竹叶楠做成的,是阳漆匠刷的漆,并用手掌打磨得像水晶一样透明,是修锁匠老通宝安的机关特殊的暗锁,里面装着的是王银匠为他琢成的一整套理发用的小家业。这个小小木盒把乡间这些手艺人——木匠、漆匠、锁匠、银匠、理发匠最精湛的手艺凝聚在一起,把他们的情义、相互关爱凝聚在一起。一个小小木盒成了一种精神凝聚,把乡下这批老人的关爱之情、善良之心物化成一种永恒,让人们在一小小的物件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因这种人性生出的人间的关爱的珍贵。这关爱也表现在临危不惧、勇担道义上。小说《花桥》中,年轻的外来养蜂人与寨中巧云姑娘真心相爱,年轻人被当作特务、巧云姑娘被当作包庇特务的坏人而遭公社郑部长带着不明真相的民兵搜山追捕,在走投无路的情急之中,寨中的岩包子大伯用绳索吊放他们从悬崖垭口逃走了。那一幕真情的描写把一位老人对两个年轻人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岩包子大伯人性善良的一面磊落皓皓,光明洁净。仅此一举,这位行不扰人、鸣不出声的老人形象是那样高大地矗立在读者面前。这关爱也表现在血缘亲情的真爱上。《草民过年》写农民工大量外出,农村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是近20多年来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于是这些空巢老人便承担起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多方面的历史责任。因此作品中的主人公清怀老汉成了一个多元结构的立体典型,所以本文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几次提到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清怀老汉的儿子、儿媳、女儿都在打工中不幸死去了。但清怀老汉并没有因此而倒下。他还有孙子。为了孙子的未来,他还得硬硬扎扎地料理未来的日子。小孙子是清怀老汉生活的新希望,也是那善良本性传承的希望。作者借这个巧妙设计的血缘亲情故事告诉读者,作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具有的那种善良的本性是不会中断的。人的生存可能存在着断代的偶然,而人的善良本性却能永远传承下去,这是一种必然!
其次这种善良表现在敬业上。张心平笔下的老人形象都是乡村或小镇上那些平平实实过日子的人。这些人信守“手艺一坝田”的古训,多数人从小就学习练就了一门手艺。他们学手艺不是欺世盗名、奸佞诈骗,而是把它当作生存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他们那里,有比手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性。他们第一讲究的是德性。何谓德性?德性就是正直、正派、诚信无私的品质,就是为他人设想、急人所急、帮人所需、救人于难的做人准则,就是舍己求义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德性在张心平笔下的老人身上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由此我们可看出张心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以德树人”的创作手法。正是运用了这一手法,所以他笔下的老人形象个个挺拔坚实,其典型意义和人文价值也就尤显突出。就说寿祺老汉吧,他十二岁跟一个老剃头匠学手艺。最初是打“空刀”,就是手执雪亮的小钢刀,摆好架势,运用手腕,朝着一个想象中的头空刮。接下去练剃冬瓜,在膀子上放一块砖头,后将砖头换作一碗水,一个冬瓜剃得溜光,水却不许洒出一滴,靠的全是手腕运动。就这样寿祺老汉做这头上动刀的营生五十年了。如今他剃头的手艺可说是炉火纯青。作品通过寿祺老汉的好友修锁匠老通宝的介绍,重点抓住三个细节,将寿祺老汉的理发技艺用语言演示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是修脸,又叫擀庞子,让你觉得干净舒服,那感受半月之后还留在心中。二是理发的提眉、端颈、松皮、掐寒经、掐嗝经的五把功夫,能把人熬夜伤神、失枕扭颈、风寒咳嗽、反胃停食等等病痛治好。三是干洗眼,把眼皮翻开,用锋利的小钢刀把内眼皮刮一遍,刮掉内翳,这干洗眼对治沙眼有特效。(《夜雾,升起在河湾》)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镇上普通的理发匠那种精于业、敬于业的精神风貌。
我们的文学要繁荣要发展,需要创造的就是极具人性、具有人性彻底性的形象。张心平努力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灵魂深处,竭力揭示人性的彻底性,表现人性的本真和善良,因此他笔下的老人,特别是那些乡间、小市镇上的老年手艺人,就显得特别突出和典型。他们带着酉水的神韵和湘西的风骨从历史中走来,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成为反观现代生活的鲜明的亮点。当我们面对当下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化时,从这些老人身上,见到了传统人性的纯洁和高尚,从而自觉地守住那不能失去的本来。从这点来说,张心平作品表现出的人性本真的内容,其价值是不能低估的。
二、回归自然的生存追求
在人类生存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关系。张心平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是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的,他的睿智也就在这里:通过老人形象系列的创造,表现了回归自然的人生追求,用形象注解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
首先是回归人生自然。人生自然是指人的自然生成状态,也即没有任何社会负荷的生命存在形式。这里又要提到《草民过年》。这是一篇自然化的小说。所谓自然化,就是指作品不加雕饰地按照生活的自然过程写出了清怀老汉的一生。但这篇小说又可以说是一篇哲理小说,因为清怀老汉他从人生的原点——活着出发,经历了种种苦难,最终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活着。然而活着就得好好地活着。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就有希望。人生就为活着而活着。这里的前一个活着是人生的自然态,也是人生存的目的。后一个活着是指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人的生存活动。人是具有双重性的,首先它是自然人,活着是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清怀老汉自来到这世界上,他就是作为自然人而存在着,活着是他的基本形态。但人又必然是社会的人,与社会构成种种关系。作为社会的人,清怀老汉从大跃进开始,一路走来,几十年风雨,他有了妻子,有了家庭,有了儿子、儿媳,有了女儿,有了人间的幸福温馨和满足。但天有不测风云,妻、儿、媳、女都先后死去了。这时的清怀老汉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大轮回,又回到了原初“活着”的自然人状态。回归人生自然,就是回归到人生的自然存在状态,它是人生的基本生存态,它是洗去了人生的苦难、净化了人的欲念、纯洁了人的灵魂、提升了人生价值观念全新的生存状态。经历了人生一个大轮回的清怀老汉,对活着有着全新的体认和理解。虽然“儿子走了,儿媳去了,女儿也走了,打工打去了整整一代人”,但他还有孙子,“还有根,根没有断,根还在”。因此他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硬硬扎扎料理“往后的日子”。这时的清怀老汉对人生有了透彻的理解、彻底的明悟,他在新的人生高度上,获得了全新的自由。
其次回归生态自然。这里所讲的生态自然,主要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质量,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一直是人类的自觉行为。在张心平作品中,对这一问题也有形象生动的描述。《黄昏,静悄悄》这个作品通过丁丁哥这个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腿上还带着弹片的退伍老兵的心理自述,写出了他对山林的热爱。他为护山保林,得罪了一些人,但山林保护下来了,因此人们获得了一个优美的生存环境。老人满足了。最后,老人拾起黄叶揉粹,卷成烟卷,深深地吸着,吸进的是山林之气,将山林之气融进自己的血肉里,在幸福的享受中安适地阖上双眼,静静地死去了。这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这个渺小、不起眼的护林员,永生在他保护的山林中。《老人·树》中的重喜爹爹从山上挖了一楠木树蔸,请人搬运回家,拒绝了一切高价收买或以物交换的外来客人,而请人将楠木掏空,做成棺材,睡在棺木中死去了。读着这个故事,你只觉得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在这里,重喜爹爹追求的、享受的只是死后与楠木合体。作品要表现的是,重喜爹爹是个知足常足、知乐常乐的生也幸福的人;同时以楠木为棺,死在楠木棺材里,是个死也幸福的人,因为他死在楠木棺材里,楠木的意趣、风骨、神韵便都浸漫在他的血肉里了。这是人以树木为生命的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表现了人们对优美的生存自然的环境的营造与追求。从这一层面上表现了回归自然的生存主题。
其三,人与自然景物的和谐。张心平对自然景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写作时,常能抓住自然景物中的宁静与充实,表现出生活中人的闲逸与安详,他常采用淡彩重笔、虚实相生的笔法,创造一幅幅水墨画式的作品,笔意朦胧、立意清晰的表现出人与自然景物浑然和谐的关系。如《黄昏,静悄悄》中:
正是烧夜火的时候。寨子上狗不吠、鸡不叫。女人们从地里回来,刚放下背篓,又换上围腰,在灶前灶后忙碌着。男人们……有鸟远远从霞光中飞来,飞过树顶,飞过竹林,飞过屋宇,飞进山里去了。哪家猪圈里的猪夹了脚,突然发出厉厉尖叫,那声音一下子惊忧了整个寨子。伏在地上的狗纵步跳出了灶屋;护卫着鸡群进笼的大公鸡,很英雄地扬起头左望望右望望,发出“咯—咯—”的警报……片刻过去,宁静又恢复了。
这里以动写静,充分表现了乡村的宁静。女人的动、男人的动、炊烟的飘动、落霞的变化、远鸟的归巢,都是写动,然而由于动的清晰,尤显静的安逸,只是一声猪崽厉厉的尖叫,引起了短暂的骚动,很快乡村又归于宁静。这一幅平和安适的图画,正是乡民百姓生存愿望的真实写照。而在《翠屏怨》中我们见到了另一种景象:
明月初上,象一面光洁而又古老的铜境,高高悬在天边,向着夜的千山万壑泻下无比柔和的清辉,古寺庭院里,月影绰约,晚风习习送来阵阵野花的芳香,使人感到舒适凉爽……
这里是以静写静,写出了环境深邃安谧和静中的古寺庭院弥漫着的空灵。在这空灵之中,活动着一位老禅师。老禅师经历坎坷,并精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佛家音乐。正是这空灵的环境才安放了这位禅师原本不安分的心,才使他在这空灵之中潜心理解佛家音乐的真谛,并矢志要传扬佛家音乐这人类的文明成果。
《花桥》“淡蓝淡蓝的炊烟”一节写泽车苦这个土家山寨的景色:转角的木楼、呢喃的小鸟、潭中跃出水面的鲤鱼、嗡嗡清唱的蜜蜂、欢快流淌的小河,花桥和花桥的爪角,青山、白云、天空,惊起的野雉,飞向天边的白鹤。这一切都自然天成。在这背景下,活动着老汉、老阿妈、男子汉、女人、少女等各色人物。这便构成了天人一统的场景。青年人望着这一切,眼睛里焕发出光辉,胸腔里涌动着心语。这里写景便上升到情景合一的境界。青年人面对这景致,飞快地描摹着,他要把眼前稍纵即逝的景色留在白纸上,变成永恒的艺术。这是写景中的景意结合。这里没有人为的故意造景,而是景色逼真的录制,它以淡远独特的风貌,让读者感受到这种自然天成的景色清丽与活泼、优雅与纯朴。作者就是这样以宁静、空灵、淡远的笔法写出了乡村美丽的自然景色,写出了人们与这种自然景色的和谐关系。
三、生命升华的另类表达
死亡,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文学家的笔下,死亡有各种形式和意义。张心平笔下多数是老人形象,因此也就较多地写到死亡。死亡现象是张心平作品中描写的一种基本现象。面对这一现象,张心平认真地思考过、提炼过,因此他写人的死亡,不只是把它写成人的一种自然生理现象,而主要地把它写成生命意义的升华。如果人在生的时候,他的生存意义还不突出的话,那么死亡,只有死亡,才会把它生的价值、生的意义充分地展示出来。所以死亡,成了张心平笔下的生命升华的另类表达。
《火钳》中八十岁的周四瓢老汉重病中,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他以一把铜火钳为信物,要他的妻子周婆婆每年给他上坟,连上二十五年,他就可以活过来,他们可以重新作夫妻。周婆婆承诺下来,怀着美好的愿望,年年为丈夫上坟。在这里夫妻恩爱并没有因死亡而结束,而是因死亡进入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永远思念、永存希望的境界,虽阴阳相隔,但这种思念和希望是隔不断的。对丈夫来说,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妻子,他死得放心;对妻子来说,他生活在丈夫重新活过来的希望中,她活得幸福。故事本身带有某种荒诞性,但因死亡而突显出来的人物的崇高思想境界却把这荒诞性给消解了!
死亡作为生命的升华最优美的篇章应为张心平的力作《血色织锦》:“这或许是从我们民族脉管发端的一头流淌过来的至今余温尚存的气息……”作者明确表示,他是在写我们民族脉管里流淌着的余温尚存的气息。这气息是什么?这气息就是《血色织锦》中写的人生的苦难和在历经苦难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作品用虚拟的荒诞作奇特的构思:土家织锦工艺大师玉妹在医院死了。她的魂魄却离开她僵硬沉重尸体飘向茫茫空中,寻找她的恋人和亲人。到了望乡台,要过奈何桥时,守桥判官不让她过桥到阴间,要她回到用自己八十年来心血打织的难舍难分的西兰卡普中去。这时,她骑上几百年前英雄老祖宗的座骑,一声雄壮的嘶鸣,风驰电掣般冲出了这混混沌沌阴阴沉沉的世界,迎来无限晴朗明亮的天空。作品以玉妹的魂魄作叙事主体,采用了双重叙事结构。一重是魂魄的阴间叙事,写玉妹魂魄到阴间的想望和活动,完全采用意识流的方法。这种叙述的时间和空间是模糊的、不定的、跳跃的。有时甚至是无时间空间叙事,如魂魄在冥冥中追逐一个朦胧的亮点,相信穿过那个亮点能看见她朝朝暮暮思念的五哥和先后死去的亲人。这种阴间叙事又错杂着、交织着倒叙、顺叙,呈现出主人公意识层和潜意识层的情感和思想活动。这种叙事将鬼魂集中的阴间写得扑朔迷离,有时也显得阴惨凄厉,然又总是浮现着渺茫的希望和主人公追寻希望的幸福。另一重是现实的生活叙事,这种叙事基本按玉妹生活的经历采用顺叙的叙述方式,时空清晰地叙述玉妹从生到死一生的经历。这两重叙事贯穿作品的始终,且每一章都将阴间叙事置于前,接着阴间叙事的余音展开现实生活的叙事。通过这双重的叙事,将阴间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作品便真实地显示出亦幻亦真、死生无界的艺术效果。就内容看,作品一是写苦难,写玉妹一生经历的苦难。苦难成长了玉妹,也成就了玉妹,她把苦难织进了西兰卡普,才使她织的西兰卡普美丽如彩霞,光彩映日明。二是写玉妹的悟性和精灵,写她勤劳地织锦,织锦成了她一生的事业和追求。她的织锦成了国宝,玉妹也因此被国家授予工艺大师称号。第三,作品写玉妹与五哥的爱情。她们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客观现实虽不能让他们成为夫妻,但他们共同地经受着世间的苦难,承受着祸害的折磨。他们对爱情的忠贞支撑着他们生的坚强。这个作品正是通过玉妹死亡后灵魂的飘升,写了苦难、织锦和爱情。是苦难成就了玉妹的织锦,织锦升华了玉妹与五哥的爱情。在这里,苦难、织锦与爱情都成为了永恒!这就是《血色织锦》写玉妹死亡的意义。
张心平是一位创作意趣极深的作家,他之所以要选择老人形象作为他向生活深处掘进的切入点,是有他鲜明的艺术追求的。这些老人形象可以说是代表着我们民族传统由远古走到今天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德性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传统品格与现代意识发生了冲突。如何面对这种冲突,这是当代人绕不开的难题。作为老人,他们的生存是有限的,死亡是自然生理的必然现象。但由老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磊落的品质,光明的德性却是我们民族在千百年实践中积淀的精华。一方面,它必须汇入现代生活,与现代意识结合,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现代意识只有融汇了传统的道德意识,才找到了根,才能更坚实,才能极大地丰富自身。因此这批老人,不仅他们的事业不朽、精神不朽,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由历史走向未来的桥梁。张心平所努力的,就是通过老人形象的塑造,在筑建我们民族发展中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
吉首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