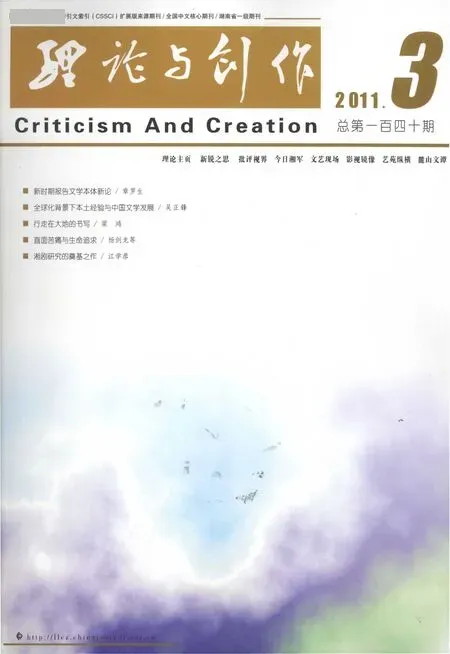大众传媒语境中小说创作的多元选择✳
■ 刘茂华
大众传媒语境中小说创作的多元选择✳
■ 刘茂华
人们生活在各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众传媒信息构筑的生活世界,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力,包括作家在内的许多人渐渐丧失了自我的感受力。为了对抗这种“镜像”的生活现状,重新挖掘生活感受力,近几年,不少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创作资源、创作方式、创作姿态等体现出有别于过去的多样化特点,走向“多元”选择的道路。
一、创作资源:作家选择的多样化
记者职业和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成为小说创作中重要的资源,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数量的作家曾从事过记者职业,美国的海明威、马克·吐温、欧·亨利等等。海明威曾深有体会地说:“新闻工作不会损害一位年轻的作家,如果他及时把它摆脱,这对他是有帮助的……可是过了一个特定的时刻,新闻工作对于一位严肃的有创造力的作家会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①海明威说的是新闻工作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和负面性,揭示了不同的创作资源对于作家创作成败的影响。
作家原本就与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须一瓜,既是一个作家又是在大众传媒时代具有天然优越性和特殊地位的“无冕之王”,记者的职业生涯不仅仅使须一瓜获得了一个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她的小说创作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须一瓜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她凭着新闻职业的敏感搜罗和汇聚千奇百怪的信息,为自己的小说创作积累下丰富的生活素材,这些创作素材充满了生动的人生体验。须一瓜的创作策略使得她的小说与其他作家的作品有着重大的差别,她也因此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须一瓜所看准的新闻性事件大多故事性强,具有非常广阔的再次建构和阐释空间,受众从中可以观察人性的秘密和复杂性。须一瓜叙述所采取的措施为:将作品中的人物置于人类生存情境的极端化状态,这样就能最为本真地凸显人性中最本真最为复杂的层面。《雨把烟打湿了》中,一个受他人尊重、受政府重视的青年才俊为什么会杀人?其中的原因显得错综复杂,让人难以理解。当然可以对蔡水清的杀人动机做出合乎犯罪心理学的解释——回家的急切、令人烦躁的雨夜、病痛的发作、与粗蛮司机的冲动等等。须一瓜并没有就此止步,她从事件的背后对杀人者进行了客观、细微的人性剖析,由此获得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来自于贫困乡村的蔡水清真诚地接受城市文明的改造,他所获得的只是一副人格的假面。蔡水清憎恨、压抑着那个野性的自我可又无法摆脱,很痛快地杀死了那个长相酷似自己的司机,其实他是想杀死那个隐蔽的自我。蔡水清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完成了“脱胎换骨”的仪式。小说中人性的悲哀暴露无遗,强烈冲击着读者的灵魂。须一瓜把小说没有单纯地进行外在描写,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内心的揭示和灵魂的解剖上,她的小说也由此确立了独立的审美地位。
余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过自己对生活经验的认识,大部分来源于报纸、网站的社会新闻或者朋友的道听途说,这些所谓的“二手现实”构成了余华小说的基础。②媒介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然而全球化趋势下的类型化、同质性、无深度等弊端也显露无遗,面对媒介传播环境,作家如何应对?
李洱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认为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面对媒介的强大冲击力量和全球化时代,小说家应该有适应新时代的应对方式。他敏感地意识到,小说创作的资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固定单一,而是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小说的资源应该深入到地方的角落里去寻找。
莫言的《檀香刑》,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1900年,猫腔戏班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美丽的女儿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牢,并给他施行一种残酷的死刑——檀香刑。行刑者赵甲是大清朝的头号刽子手、也是眉娘的公爹。赵甲把这次死刑视为他退休生涯中至高的荣誉,一心要让亲家死得“轰轰烈烈”。是什么触动莫言的创作灵感,小说的创作资源与莫言以前的作品有何不同,与媒介传播环境有何关系?
莫言回顾《檀香刑》的创作时说:“20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出现,使我经常地激动不安。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就是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高密无论大人孩子,都会哼唱那种婉转凄切的调子。通过《檀香刑》,我完成了童年记忆中关于火车和猫腔的一次丰美的想象。整部《檀香刑》犹如一出大戏,色彩浓重、主题鲜明。我称之为创作过程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面对当前高雅而温软的流行趣味,我突然唱起了土得掉渣儿的猫腔大戏《檀香刑》,目的就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③高密,一个山东省的小小县城,由于莫言的写作,这里成为一片近乎神秘的土地,并化为某种文学符号镶嵌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到底与这片土地有何牵连?高密与胶济铁路有着什么样纠缠不清的哀怨?莫言没有停留于书面的表面,而是花了较多的精力去当地实地考察获得了第一手的珍贵材料:100多年前,为了抵抗德国人修筑这条铁路,高密西乡108个村庄的农民,在孙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年多的斗争,斗争失败后孙文被处死。莫言在其长篇小说《檀香刑》的后记里说,早在清末民初,孙文抗德的故事就已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猫腔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莫言这部小说主人公孙丙的原型就是孙文。孙丙抗德失败后,被满清“酷刑艺术家”赵甲以檀香刑处死,据记载,行刑的具体步骤为削尖的檀木橛子从肛门里敲进身体,从肩膀里斜刺出来,小说为了让这个猫腔艺人能够歌唱至死,行刑者让檀木橛子稍稍偏离了方向,没有从他的嘴里穿出来。根据高密县志的记载,德国人在勘探和植标过程中,以低价收买农田,逼迫农民迁坟移舍,此举遭到了沿线农民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高密西乡,地势低洼,河水多南北走向,为修铁路阻塞水路,大水漫田,贻害无穷。1899年11月间,在孙文组织发动下,抗德队伍迅速扩大,波及108村,村村都有首领。抗争一直断断续续,山东巡抚袁世凯调兵镇压。1900年5月3日早晨,在绳、王两庄之间,孙文被逮捕。清政府后在高密城东门外大石桥以北将其杀害。“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者,为了感染他的听众,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再到后来,麻雀变成了凤凰,野兔变成了麒麟。我的小说大概也就是这类东西。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密东北乡、放在高粱地里。”④
二、创作方式:由新闻到小说的艺术转换
当代作家在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许多晚报都市报、电视中的探案节目,还有很多新闻故事,其故事性超过了小说情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作家创作什么样的小说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作家必须面对且采取相应的写作方式。
用文学的方式写作社会杂闻,代表作品有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神木》、北村的《愤怒》等小说。一批作家在新闻与小说之间做出了努力,如陈应松、刘庆邦、方方、须一瓜等,他们的小说反映的全部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场景,具有很强的亲历性,像新闻一样具有时效性。小说将笔触伸入特殊的群体他们集体和个人的生存状态,丝毫不回避现实的真实性、残酷性。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层,而是深入挖掘到底层,伴随着作家的艰苦思索,小说从而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陈应松、刘庆邦、方方、须一瓜就是非常典型的个案,本文以他们的小说创作来分析当前受到新闻化濡染的小说的特征、叙事角度及其负面效应。
第一,首要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很强的纪实性,新闻化小说像新闻一样特别关注生活热点或当下生存状态。方方善于描摹凡俗人生,这得益于她对于生活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她的小说直接逼近世相。方方常常走访一些特殊地方,如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等,像一个记者采访那样做详细的记录。小说《奔跑的火光》的创作原型就是得益于方方一次偶然的采访机会,她听到一个监狱女囚犯的倾诉,这位女子所叙述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用听来的故事作为创作素材,在小说中叙述了一个心比天高的乡下女孩的酸楚人生。《落日》借用一个公案故事,用客观冷静的叙事姿态透视社会人心。小说《乌泥湖年谱》以三峡为背景,记述了1957至1966年在乌泥湖的一批知识分子10年间的命运。方方采用“年谱”的形式写小说,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往事,成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这些小说都如同新闻一样关注人们真实的当下生存状态。
第二,用文学的手段将刚刚发生的社会杂闻进行艺术处理构成一篇好看的小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叙述了一件杀人劫物的流血案件,这是一个因贫富差距而引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望粮山》写的是,山里人因被城里人栽赃陷入无比愤怒和绝望,一念之差变成了杀人犯,《城市寓言》和《苍颜》叙说中国底层的生活中的悲欢,《金色夜叉》叙述的是一个“夺金”与恶势力不屈斗争的故事。刘庆邦的《走窑汉》、《玉米》、《平地风雷》等小说也将笔触进入底层社会,表现挣扎于民间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复仇故事。这类小说对于社会杂闻尤其是罪案故事进行文学性改造,像新闻播报那样及时、适时地追踪案件。须一瓜与陈应松、刘庆邦不同,她的笔下更多的是都市人因本身的人性弱点而诱发的犯罪。《雨把烟打湿了》的蔡水清杀害出租车司机而没有任何动机,人性的弱点和残忍性在小说中可见一斑。《淡绿色的月亮》是由入室抢劫案事件而衍生出的关于人性思考的故事。须一瓜善于透过社会杂闻思考人性的复杂。社会杂闻经过文学的加工而具有文学和美学的价值。须一瓜说她的创作方式就是用“手术刀”般的叙事策略解剖现实⑤。其实,须一瓜小说并非简单地对于现实的反映,还有相当的复杂性,小说的故事主线中会夹杂一连串其他的次级故事,《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瘫子就是一个陪衬性质的人物,与主要人物关系不是很大。很多时候,须一瓜小说中主要故事背后隐藏另外一些故事,与主要故事构成了表里关系,背后的故事便成了主要故事所要揭示的本来面貌。《蛇宫》所主要讲述的是“那人”与印秋、晓菌间的故事。与此同时,小说讲述了印秋和晓菌被关进蛇宫和她们之间因此发生的故事,小说还巧妙地通过“那人”的讲述,勾连出“那人”的婚姻与爱情以及他铤而走险抢劫银行的故事。不仅如此,“那人”还向晓菌讲述了一个表面看与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美国电影故事。这种故事之中套故事的手法使得故事之间充满了张力,其中的电影故事不仅与“那人”自身的经历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其所包含的人性意蕴又是对整个故事人性内涵的强化或补充。《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也是这样,故事的主线本来是粽子和老太婆的交往,但是叙事却一再地勾连出粽子和夭夭九的故事,还有席老太婆的革命经历和她的爱情及家庭故事,小说因此向更加开阔的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发展,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与意蕴。这样一来,众多的故事与人物都被叙述者有机地统一在同一个叙事整体中,各部分相映成趣,给整个叙事不断地补充意义、气氛或象征。无论是其故事性,还是其思想意蕴,整个叙事都比各个故事的简单相加更富有深意。
第三,小说中的叙事者以采访者的身份出现,具有亲历性。陈应松的小说大多与自己人生经历有关,如《黑鞘楼》、《寻找老鱤》,小说中的“我”既是叙事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刘庆邦的很多作品多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如《落英》、《远方诗意》和《家道》中的“我”都与刘庆邦本人的经历部分吻合。刘庆邦做过矿工,算是来自于最底层的一员,他总是自觉地站在平民的立场,从自身经历与情感出发,对农民和矿工的生存状态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和体验,如《灯》、《听戏》、《鞋》等书写人性美好,而多数作品描写的是河南矿坑里人们生存的残酷状态,还有一些命案的发生、暴力和死亡等等较为阴暗的社会的一面。小说《断层》和《神木》都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病态、人性扭曲和异化的状态。小说叙事者以采访者的形象出现,增强了小说的新闻化特征。须一瓜在《厦门晚报》担任法制战线的记者,她借助政法记者的独特视觉,以案例调查为写作素材,创作了一批高质量的小说,《第三棵树是和平》中叙事者直接参与了案件的调查。湖北作家陈应松曾在神农架地区挂职,说是挂职,其实完全是为了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的素材,以此寻找创作的突破口。他全身心投入神农架地区进行采访和体验,一组体现神农架人感性生活状态的作品先后问世。《松鸦为什么鸣叫》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和命运,《太平狗》展示了“人不如狗”的打工者程大种的种种厄运,结尾还直接用一则新闻:“这件事刊登在二○○×年十月的报上。报道说:狗的主人程大种(化名)音讯皆无,狗却千里迢迢地回家了”。
第四,充分利用文学的时尚化、快餐化与实用性特征满足读者的需求。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等均重复着她特定的叙述方式——以类似奇闻怪事的新闻报道作为小说的突破口。这样的小说应和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具有快餐化、时尚化的特征。新闻化小说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有一些开拓创新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注重现实感、体验感、亲历性。这种写作方式拉近了艺术与普通人的关系,使真实的东西从现实的遮蔽中脱离出来,让读者可以直接领略到艺术的审美性,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新的阅读快感。当然必须同时清醒意识到新闻化小说的弊端,新闻化叙事是对消费性文化做出的趋同性反映,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从而导致“对作品中的语言艺术、结构安排等其他成分的忽略”⑥。新闻所遵从的规律是信息的传播必须满足当前受众的趣味时尚,文学则需要超功利性、虚构性、艺术性。
第五,将一些富有传奇性的新闻故事挖掘出来,虚构和演绎为传奇的浪漫故事、冒险动作故事,或者神秘领域的故事等等。须一瓜就善于渲染新闻故事中的离奇、神秘、恐怖。《0:22,谁打出了电话》写了一个牵动警方视线的“鬼故事”,《淡绿色的月亮》由一桩入室抢劫案作为叙事的起点叙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雨把烟打湿了》写了一起让人难以理解而又合乎情理的杀人案。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须一瓜的作品具有了侦探小说、恐怖小说、警匪小说、志怪小说和新闻调查等等元素,她的小说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富于神秘色彩的情景。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须一瓜的作品吸引了一大批读者的眼球,把读者带入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中,充分发挥了小说的娱乐功能。
小说与新闻的相互影响,看来并非简单的结合。小说与新闻靠拢、相结合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媒介本身具有大众性,有新闻性因素的小说也比较容易地获得一种平民化的色彩。当前的许多小说产生出一种让读者宛如走进自己熟悉的乡村或者市井社会的感觉,小说叙述中处处洋溢着现代乡村或者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气息,传递着与现实生活中的多元经验,展现了具有某种流行色彩的事件,同时创造出一个信息迅速流动的公共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读者透过戏剧性故事去感知生活世界繁复多彩。小说还有了新闻即时播报的效果。传统的虚构小说恰恰缺乏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迅速回应的机制,在当下就面临着缺少聚集读者注意力的能力。
三、创作姿态:界限弥合的先锋性特征
大众传媒语境中,不仅仅新闻与小说很多时候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生活与文学、作家生活与写作活动也没有了截然分开的界限,呈现出界限弥合的先锋性特征。
文学身份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理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用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界定较为合适。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身份是指文学高于生活,具有超越生活的审美功能,文学与生活不能越界且具有艺术独立性,两者是各自独立的形态。晚生代小说的文学身份表现出去艺术化的倾向,或者说减少了文学的艺术因素,许多晚生代小说与生活同步,没有追求审美的超越性功能。晚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朱文接受访谈时就说过:“有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有的是在小说中发生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生活和小说是分不开的。你说我写小说时在导演戏剧也可以,也可以说我在导演我的生活。”⑦这种文学身份的生活化,使小说与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为生活和艺术的等同甚至可以相互替代,这也就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文艺学中所指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关于这个问题,19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的文艺理论界讨论较多,也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之一。陶东风说:“简单地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艺术与生活相互殖民的过程。进入1990年代以来,这种艺术与生活相互殖民、界限弥和的艺术实践与生活现象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频繁。”⑧这里所说的生活并不作为本源意义而存在的生活,而是作为被小说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现实生活中的片断和小说的世界可以互相调换,并非二元对立。这种创作观念颠覆了传统生活观,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感拉拢了,文学也不再对生活表象进行艺术与审美地提升,而是类似于一种原生态的记录。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审美活动呈现出超出纯文学艺术范围的倾向,审美活动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晚生代小说中最大的世俗生活就是当下的都市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正在进行时,并非虚拟的或者说艺术化的,是大家周围真真切切的现实生活。这种文艺观念改变了作家对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传统形象的塑造中,其“形象”与生活表象的关系具有有审美距离,晚生代的创作中,艺术形象与生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形象与“拟像”的关系。在“审美泛化”大势所趋之下,现实被“审美泛化”,在很多作家看来,“现实”已经没有了,有的就只是“超现实”,在“超现实”的语境中,一切“表象”都表现为“拟像”的存在形式。何谓“拟像”?波德里亚说,拟像“与任何现实都没有关系:它是它自身的纯粹拟像”。⑨波德利亚对“拟像”的看法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给出的,他的看法意在说明,现实与虚拟在很多时候是重合的,虚拟当然来自于现实,但比现实更像“现实”,人们习惯于把虚拟的形象当成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形象。
生活与文学艺术距离的消失,加之“拟像”形成了“超现实”,现实本身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一定程上可能摆脱了作家的意识控制。因而造成了创作上的一种趋势:作家的创作往往变成对生活的表面化反映,而不是深层意义的探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表面化的反映也会产生某种意义与可能性的,韩东曾经就此发表过意见:“写作就是一种发现,对情节的发现,对文字的发现,写作首先它是和未知打交道,不是和已知打交道。”⑩“后新时期”文学也因此有了文本主题的不确定性,有时候如同一段生活之流,没有主题,有时候就难以把握主题,甚至本身就是反主题的。在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作家的功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学观念中的作家具有神圣的意义,作家不仅仅要认识生活、解释生活,还要赋予创作某种意义和价值等等,做家务必将创作看作是一项肩负“人文精神”的神圣事业。而1990年代以后晚生代及其他一些流派的作家则不同,他们已经没有了创作行为中的神圣和庄严感,朱文就说:“写作,塑造了我,这是一个结果性的东西。”⑪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巴尔特所说的“作者之死”,不过,福柯认为这是“作者功能”的转化。他在《作者是什么》中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⑫作者当然不会死去,只是文本的意义已经与作者本人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外在形态上,“后新时期”的许多作家把写作看成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养家糊口”的工作,和其它职业别无二致。“后新时期”的许多作家成为“自由撰稿人”,写作成为一些作家的生存方式。一些作家谈起这些显得非常坦然:“我只能说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别无选择。”⑬对于传统作家身份神圣性的放弃,却使一些作家获得了一种世俗性的审美眼光,以亲和的姿态去表达生活。这些文学观念的演变有文学内部变革的逻辑推演,也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强势语境的推波助澜。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产生了“基因突变”,那就是网络空间的爆发,也是“80后”、“90后”走向写作的十年。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写作门槛低,让网络打破了传媒界限,给文学写作带来空前自由。毋庸置疑,大众传媒的介入所建构的特殊语境促使文学创作产生新变,1990年代至新世纪文学的进一步转型得以可能。其实,福楼拜一个世纪前就相信,“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⑭福楼拜的预言在新世纪已成为现实。
注 释
①乔治·普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②《余华的自信和难题》,《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9期。
③孙立海:《莫言细说〈檀香刑〉》,《羊城晚报》2001年6月26日。
④莫言:《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粱地里》,《齐鲁晚报》2005年6月23日。
⑤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
⑥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⑦⑩⑪⑬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第37页、第37页、第37页、第162页。
⑧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第1期。
⑨转引自金惠敏:《从形象到拟像》,《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⑫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⑭米·贝京著,任光宣译:《艺术与科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研计划项目《媒介制导下的“后新时期文学”》的成果之一。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