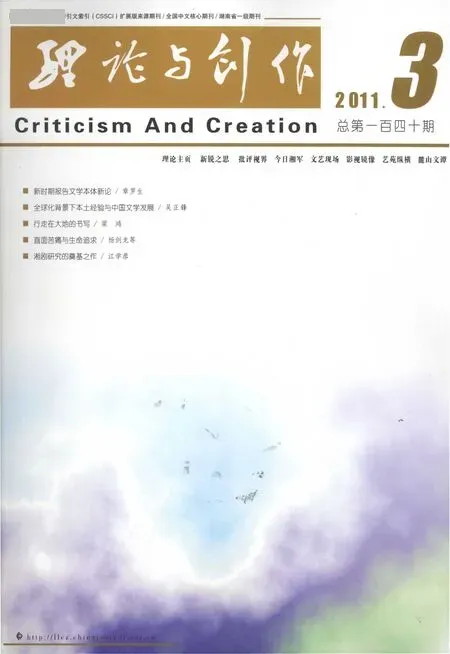行走在大地的书写——读《忆阿雅》和《曙光与暮色》
■梁鸿
行走在大地的书写
——读《忆阿雅》和《曙光与暮色》
■梁鸿
张炜《你在高原》是一种行走在大地上的书写,与沉默而广阔的中国生活对话,与仍在黑暗之中的中国精神对话。“行走”,“书写”,缓慢而沉着的书写,不仅仅是一种姿态,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我们时代的文学非常需要这种姿态和行为。这十卷本的《你在高原》花了张炜二十一年的时间,也是张炜行走大地、书写大地的二十一年。你可以抽出任何一本来读,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叙事,你可以从第一本读到第十本,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观照、相互阐释,构成一个庞大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世界和中国当代生活史、乡村发展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
《忆阿雅》讲什么呢?从最根本上的意义上,它是讲关于忠诚、背叛、牺牲与坚守的故事,它是人类命运的原型与隐喻。《忆阿雅》可以说是双重结构。一条是阿雅的故事,阿雅是一种美丽、纯洁的动物,一旦选定主人,就会奉献终生,并历尽千辛万苦为主人寻找财富,无论主人怎么误解、驱赶、殴打,它都不离不弃。这既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一种人类普遍向往的信念,关于忠诚与坚守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像金子一样,非常美好。同时,也暗含有儒家文化的模式在里面,一种君臣模式,忠贞,坚定,还有服从。与阿雅的故事相对应的是“父亲的故事”,它在小说中几乎是以“我”的叙事为基础出现的,和阿雅的故事形成一种互为观照的关系,对于“我”及整个家庭来说,父亲就是原罪,思考父亲,他与家庭、理想、政治的关系,就好像在重新思考阿雅的命运及其启示。另一条线索是“我”的不断流浪与城市的现实生活。“我”既是自我心灵的探询者,也是中国当代政治与当代生活的书写者和疑问者。作为一个五十年代生的人,正好生活在父辈命运所留下的阴影之中。在童年时代,因为要躲避“父亲”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不得不被抛弃在荒原之中,因为在荒原之中生存的可能性似乎比在有“父亲”的家里还更大一些,这种悖论一开始就在主人公的心灵中留下创伤。但是,即使是经过那么多年的流浪,他身上的罪并没有被洗脱掉,一旦重回文明社会,“父亲”的罪就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我”,无法摆脱。作者从五十年代出生人的命运切入,对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反复的考量与思索。五十年代出生人是共和国历史的遗产,是父辈与共和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见证者与承受者。所以,这种质疑与思考更为真切与深刻。在《忆阿雅》和《曙光与暮色》中,作者给我们勾画了五十年代出生人的一个精神群像,“我”,庄周,林渠,吕擎,都在不同层面被父辈所困。“我”对流浪的嗜好,林渠纯洁与欲望的多重生活,吕擎的犹疑与无为都来自于对父辈精神的怀疑,这种思索与怀疑造成一种疼痛与症结,使得他们无法安宁,同时也促使他们去不断寻找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与父辈的不断对话中,他们发现了历史与政治的很多黑暗,如吕擎对父亲学术事业的思考,借助于塑造这样一个泰斗,去“混淆大是大非”;如“我”对梅子父亲战斗历史和“老歪”政治历史的再追查,都是在澄清历史的本源,最后,被阉割了的臣服而慵懒的阿雅或者是父辈最终的一个侧面,被阉割,被伤害,被遗忘,那些最初的奔跑与忠贞,都转化为一种无奈而恐惧的等待。
作者试图在解决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如何思考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如何思考那些政治运动及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被驱逐的那一代人?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问题。这几乎成为一种原罪,一个肿瘤,只有把它切开,切除,才能够对自我的位置,对中国当代政治与人的关系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作者没有简单地控诉与揭露,而是把它放置于人类普遍命运的范畴中进行思考,这使得他的思考显得非常宽广,也使得许多对历史的疑问得到一种更为宽广的解释。父辈们为什么如此忠贞?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愚忠,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有修养,有理想与抱负,即使被冤屈、被折磨,被剥夺自由与尊严,遭受一切人类能想到和无法想到的屈辱,仍然坚持最初的理想。为什么?通过一层层的叙事,阿雅的忠诚,父亲的受难,外祖母与母亲的信念与等待,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忠诚与理想并不仅仅是对国家或某一个党的忠诚,在内心深处,也有对人类基本信念的遵守,那是一种承诺,对希望与美好的承诺,一旦认定,就终生追求。它超越具体的党派与历史阶段,超越战争与敌我或对错,就像父亲与叔伯爷爷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信仰并迎向自己的命运,这一恪守不能用对错来衡量。它是终极的。所以,从一种意义上讲,共和国初期的历史既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它包含着对具体的政治与历史的诘问与控诉,譬如它的多疑,它对生命与信念的蹂躏,及由此带来的对整个时代、民族的巨大伤害等等,反过来,这一受难史却也折射出人类精神的坚韧与美好,对信念与理想的坚守是超越于一切的,它神圣而优美。恰如阿雅。而小说的另一极,是作者对当代生活的批判。不再坚守信念,唯利是图,毁坏大地,毁坏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最为珍贵的东西。
有一个问题笔者一直在思考。张炜的小说中有非常清晰的大地的行走者的形象,行走者,共和国的第一批后代,由于历史的翻云覆雨,他们被迫成为流浪者,被放逐或自我放逐。那么,小说中的大地呢?是谁的大地?应该有一个界定,笔者认为《你在高原》的大地,是知识分子的大地,虽然它仍然是广阔的乡土大地,但与生存在那其中的农民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只有清楚这一点,才能明白《你在高原》中大地的隐喻与所指。大地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放逐地,热爱大地,意味着热爱自由,热爱自然的生命与生机,它的纹理、地层、土质,既具有地质学的真实,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投射。所以,大地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疗伤地,它是具体的自然界,在被破坏,被伤害,但同时又是抽象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象征地,是人文的大地。但它并不是农民的,虽然它也有对其中的生活,如“老孟”,如女房东,等等,但那都只是观察对象而已,只是象征的衍生物。但这也并不能看作是小说的缺点,一部小说必然有它最为核心的主题,如在《荒原纪事》中作者也试图写出当代“现代性发展思维”对乡村大地的破坏,对农民生存的破坏,它和知识分子精神生存的被破坏构成一体两面,充公展示了当代精神的颓败与大荒凉。只是,如果这些能够再强化或叙述更充分一些,或者“荒原”、“大地”在《你在高原》中的启发性会更深远,也更多义。
《你在高原》保持着张炜一贯的抒情与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抒情并不是空泛,而是建立在对扎实的叙述和对具体事物的叙事之上的,这里,一个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用呈现了出来,“大地”不只是作为地质地貌,作为知识,而是作为如韦勒克所言的“小说的肌理”而存在于小说之中,它的真实、缜密、专业性与抒情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独特密度的文体,增加了作品的精神厚度与层次。而对现实生活的细致和几乎反讽式的书写也增加了小说的密度。如《曙光与暮色》中对城市与“营养协会”中的黄科长的描写,《忆阿雅》中对阿蕴庄的书写,都很现实化,与小说中的象征与抒情构成一体两面。它们的荒诞恰恰在于它是一个极为真实的存在。作者采用第一和第二人称书写,如灵魂的呓语,有忏悔和往日时光的意味,还有随时而至的遐思,充满着某种哲理与情感。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两句诗,或对一棵李子树的思念,心灵直接坦露出来,让人一下子沉浸入一种情怀与意境之中,进入到作者,或者说“我”的思维之中,读者会被挟裹着一起进入到“我”的痛苦、怀疑与行走之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