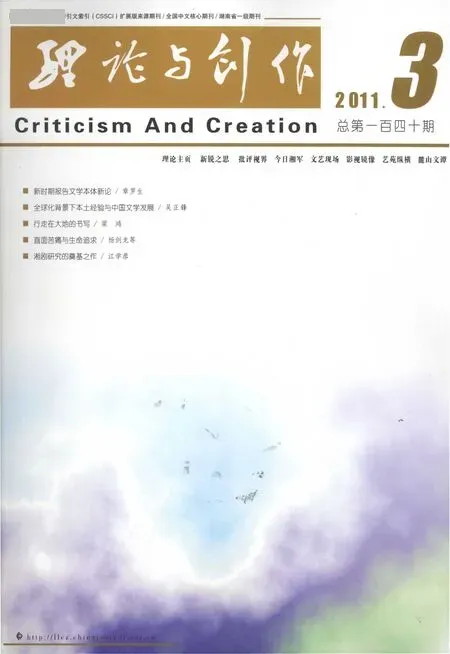复线的历史:遮蔽抑或还原?✳——1980年代以来“革命重述”的一个侧面
■赵牧
复线的历史:遮蔽抑或还原?✳
——1980年代以来“革命重述”的一个侧面
■赵牧
1980年代以来,凭借发展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为核心的现代化价值体系而重述革命,在权威的历史阐释之外寻求另外一种可能,终于演变为一种主导性叙事。我们知道,权威的革命叙事尽管形态各异,但根本上都坚持一种进化史观,通过批判黑暗而指向一个美好未来。但也正因此,它被认为删削了历史复杂性,将日常生活的多样景观纳入单一的阶级斗争图式,并以革命名义无情实施“叙述中的流血祭礼”,以致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图解”中变成了“人性彻底消失的冷文学”①。所以,“还原”被有意“遮蔽”的“真相”,构成了革命重述最强劲的原动力。宏大的历史线索被刻意回避,种种边缘化记忆浮上水面。个人悲欢,家族谱系,村落传说,地方传统,争先恐后进入叙事者的视野;情节的空白,故事的琐屑,结局的出乎意料,穿越时空的后设评价等,成为最受青睐的叙述方式。曾用来解释重大历史转折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如今不过一个背景,一个道具,一个时空坐标,而活跃在其中的,多为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人物,置身历史进程之外,过着庸碌的生活,搬演着几乎无事的传奇。也不排除个别身份多变和命运乖戾的大君子或伟丈夫,时而激情澎湃,时而静如处子,时而慷慨悲歌,时而意乱情迷,却不是在大历史中迷失自我,便是在小叙述中消失踪影,非但没能解放别人,反倒弄糟了自己的生活。如此等等,社会进化论的信仰被否定,启蒙现代性的逻辑被质疑,多样过去并不必然导出现在,而有关未来的一切,也不过一个荒诞的梦境:任何美好的愿望都可能带来猝不及防的灾难。理性设计未来的虚妄,人性自我放纵的灾难,就这样成为革命及其叙事的“总体性表述”。
但这一后革命时代的革命重述策略,本身却也是在建构另外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它的“整体性”就表现在为达到“去革命化”目的,以“人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或正是历史及其叙述的吊诡之处。福柯发现历史在前进过程中不断会有“散失”,②而在一本论述“中国民族主义话语起源”的书中,杜赞奇继承福柯“复数的历史”观,但认为有关历史连续性的表述不会消失,这些处于竞争之中的各类表述,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而“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③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叙事和“去革命化”叙事都是“利用性的话语”,它们“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并在“对历史事件的意义竞争中”建构各自的历史表述。
一、“真相”的“还原”
还原历史,这几乎是所有的历史学家真心或者假意地提出的一项历史书写原则,但事实上所有的历史书写却逃不脱想象与虚构的指责。相比之下,文学家对于历史的讲述似乎要坦诚的多,因为即使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中,想象与虚构都不曾受到无端贬抑。但自从“文革”结束后,以文学方式提供历史真实图景的说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尤其是对于革命历史题材而言,有心打破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的遮蔽的新锐作家,更是充满了打捞人性真实图景的冲动。我们知道,在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大致有三条主要的投身革命的路径:其一是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五四式知识分子自觉投入革命,其二是一批贫困交加的农民彻底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并逐渐汇拢到共产党人的周围,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其三是革命的感召力量,尤其是青年学生中间秘密传阅的革命书籍和圣地延安的象征意义,使得很多人放弃小资产阶级的幻觉而融入革命的集体。但在“还原历史真相”叙述中,这些革命路径都被改写了。在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中,父亲参加红军的动机竟然是因为一块嚼不动的生猪肉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小说就以父亲这个具体的生命个体对抗种种把革命神圣化的模式,将英雄主义还原为对人性真实的建构上,在农民、军人、英雄以及凡人等角色的转换中展开了人间苦难的探询。④在李洱的《1919年的魔术师》中,头上留有一根辫子的魔术师天宝因对辜鸿铭的辫子好奇,有一次跟踪他而迷了路,结果却混进了正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他正从学生领袖手中接过汽油桶往曹汝霖的卧室里倒时被闻讯赶过来的军警扭住,恰巧有个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拍下了这一情景,并在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下面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北大教授辜鸿铭先生,1919年5月4日在曹家楼前,受到警厅和步军统领衙门的当众羞辱”。事隔一天,这位记者又更正说受到“当众羞辱的”乃“辜鸿铭的高足”云云,但这恶搞般的误会却改变了天宝的一生,他成了风云人物,并随后在李大钊引领下成了一名革命党员。⑤而在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中,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及其亲友们投身革命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钱文之所以倾心于革命和激进的共产主义,首要的原因是他父母的吵架斗殴,“他恰恰是从他的父母的仇敌般的、野兽般的关系中得出旧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彻底砸烂,只有把旧的一切变成废墟,新生活才能在这样碎成粉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结论的”;洪嘉的继父朱振东是因为遇上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跟上了八路军;朱可发这个曾经在小镇子澡堂里当小二的人,他的革命经历更为可笑:因为窥视日本鬼子男女同浴被发现不得不出走投奔八路军;章婉婉由于学业成绩突出而引起了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的关注;郑仿因为反感絮絮叨叨的耶稣教义而转向了共产主义。⑥
难道如此人性化的细节就是原生态的历史真相吗?不可否认,原生态的历史的确是曾经存在过的,但却从来都在人们来不及把握与分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与诱惑的背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针对逝去的爱情而发的感慨,却给历史及其书写的一切动因提供了解释。人们正是为了在过去的事物中寻找有益于现在的意义,才有了叙述历史的冲动。而历史一旦进入叙述,无论是以实录的形式存在于文献的记载之中,还是以演义的形式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也还是以历史陈列馆里的文物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观摩与解说员的反复讲解之中,可以肯定地,都会不无例外地失去原生态的形貌。据杜赞奇说,玛瑞安·赫布森曾将作为遗迹或文献存在的历史比拟为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大体在其框架内对之作出答复,也就是,“我们怎样回电话,回电话时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别,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创造性”。⑦但吊诡的是,也只有通过如同打电话一般的记忆、转述、剪辑、整理、想象以及虚构等叙述形式,历史的意义才能得以生成。所以,离开了叙事就没有了所谓的历史,而在故事得以讲述之前,是没有所谓历史性的。
然而,历史性却有等级之分,不同的历史叙事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不同,决定了其历史性是受到压抑还是得以张扬。在强调革命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叙事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性格,都服务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凡是与这种规律相吻合的,都会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而凡是与之相违背的,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划分到反历史潮流的阵营中而受到鞑伐。所以,一旦林道静的革命性受到质疑的时候,作者杨沫就赶紧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版中加上她与工农接触的章节⑧,而断然不敢像邓一光或北村那样把革命动机与一块生猪肉或偷情的女人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以“人性化”或“人道主义”解释历史的观念已成为组织革命书写的指导。在这里,革命成了以所谓宏大的集体意志剥夺人性化吁求的借口。甚至在革命的名义下,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为了一己的私利或恩怨而残酷地戕害他人的生命与尊严,而即使有革命者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真诚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和忘却个人的得失,也被解读为革命对正当人性的异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把人性论看作检验任何其它叙事的元话语,凡与之相吻合的就得到肯定,凡相违背的就得到否定。这实际上采用了与革命叙事同样的逻辑,它们都坚信自身无可辩驳,且都把各自的价值强加在对方的头上,似乎唯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才符合历史真相,却假装不知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都是意识形态深度介入的产物。
结果在“人性化”的语法中,历史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而革命不过是残酷人性在别有用心的蛊惑下的发泄。《远离稼穑》中白军对红军根据地的清洗惨绝人寰,《战将》中红军对待地主老财的镇压也血腥残酷,所以在邓一光笔下,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被残暴人性所左右而全然分不出正义与邪恶。“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⑨这是毛泽东以革命语法对贫农的革命历史功绩所作的权威叙述,但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在格非的《大年》中,在周梅森的《英雄出世》中,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在李伯勇的《重轭》中,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以及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贫农出身的革命者却不但一个个残暴自私,而且都借着斗争阶级敌人的机会,把情色欲望发泄到地主小姐或姨太太或妓女的身上。
二、“历史”的“辩证”
这些重写的革命历史无疑都有潜在的仿写对象,而通过把仿写对象视作国家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历史合法性的文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相应地,仿写对象所描画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种宏大的有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自己所致力挖掘的历史细节就成了处于弱势和反抗者地位的小写的历史。李锐于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的题记就此种大小写历史的区分作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⑩
在这段富有文学修辞的文字中,李锐在强调历史文献不可靠的同时,决定把想象和书写的重心转向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一些感性故事。同一历史过程会留下不同的叙述,李锐所说的历史文献既然属于历史叙述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跳出特定的意义链条,它表现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至于所谓的“丧失信心”之语,则又是没能够从中获取到自己所需意义的心理反应。李锐对此也心知肚明。例如,在与《收获》编辑钟红明的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所谓历史理性的“深深的厌恶”,因为在他看来,“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而“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所以他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他“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⑪
李锐将他所认为的充满“谎言”的历史叙述命名为“大写的历史”,与此相应,他那些打捞生命的叙述,似可以被顺手牵羊地命名为“小写的历史”了。对此,钟红明有个更直截了当的判断:“我觉得就像你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⑫大写的历史是对历史的简化和缩写,大写的历史是有关伟人和大事件的历史,这种说法很显然针对的是以往的革命叙事。革命叙事似有很多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但小写的历史却自顾自提出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下的历史细节,关注被历史规律所省略的个体生命,并以悲悯的眼光打量历史洪流中的创伤、苦难、死亡、欺骗以及愚弄。历史的丰富性是容不得随意扼杀的,真实的体验是容不得随意篡改的,但这样斩钉截铁的声音却以“小”自比,显而易见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叙述策略,因为被称为“大”的东西只有被高高地举起,才有被随后的大撒手摔个粉身碎骨的可能。
既然执着于从理性的大写的历史潮流中打捞那些无情泯灭的生命,那么在处理革命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时,凡俗人生场景就成为精心描摹的对象。李锐的《银城故事》所书写的核心事件按理说应该是由留日归来的革命者和清政府的新军在银城组织的一场失败了的起义活动,但具体的情节却由多条线索展开,一则是银城的牛屎客旺财以及与旺财有关联的一帮银城主妇的琐屑生活;一则是银城大盐商刘三公的留日归来的儿子刘兰亭借办学之名秘密组织起义;一则是袍哥会首领组织灾民造反,从乡野小镇进攻银城;一则是刘三公的义子刘振武组织新兵从省城以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名义赶来支援起义。而所有这些几乎共时存在的情节都被欧阳朗云违反既定计划的刺杀知府袁雪门与临危授命的裁汰绿营千总聂琴轩缉拿凶手的事件若隐若现地串连起来。例如牛屎客旺财在银溪岸边发现的竹片是刘兰亭为向下游的革命党发出的取消起义的通知,他在进城向茶馆老板要帐的时候,看到聂琴轩为了逼迫刺杀知府的刺客现形而把包括茶馆老板在内的茶客绑在大街上的情形;刘振武奔赴银城的路上遭遇岳天义领导的乌合之众,而后当他被义父送上船准备流亡日本的时候,又被藏身船上的可能是他同跑兄弟的岳新年刺死。可以说,小说对各个枝蔓的描写都很细致和稳妥,无论盐井的生产情况、旺财制作牛屎饼的过程、刘三公中秋宴席上的退秋鲜鱼的制作过程、蔡六娘为女儿三妹的婚事以及自己将来所作的盘算,还是欧阳朗云自首前的内心冲突、秀山芳子为心爱的人的牵肠挂肚和愁肠百结、秀山次郎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对革命置身事外的心理,以及聂琴轩老辣独到的对付欧阳朗云的办法,都被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慢慢叙说着。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就这样被日常生活的场景肢解了。
历史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这也许是李锐通过把银城老百姓、革命者、裁汰绿营千总和大盐商并置的方式所刻意告诉我们的。在小说里,各色人物的被叙述的地位在银城几乎是相等的。即使刘三公为了中秋宴席上的一道菜而令数十名人员星夜兼程和不辞劳苦,但这一切无论在叙述者心目中还是在其间的人物的观念中都丝毫容不得质疑,而受质疑的却是革命者的盲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血腥行为,是他们破坏了银城尊卑有序的宁静的生活。他们的革命活动也似乎全然没有理由,不但富足的家庭给了他们留学的机会,国家也把他们安置在装备最为先进的新军中,哪怕不食国家俸禄如刘兰亭等,也都有自己引以为荣和周围的人们艳羡不已的事业。那个逞匹夫之勇的欧阳朗云投身革命的动机尤为可疑。他本是越南华侨富商的儿子,似乎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投身到革命队伍,并破坏起义计划而擅自刺杀了知府,最后又很小资味十足地自首,即使因为受不了聂统领的酷刑而供出革命同仁也没能逃脱一死。与此相对,旺财的欲望和需求,都非常个人化,跟历史——就是那种为作家所抛弃的历史文献叙述——无关,在他的眼中,所有身外之事,都是非自我的。他只关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桐江知府遇刺这样一件大事,旺财仅仅关心自己能否从作为嫌犯被聂统领关在笼子里的陈老板那里讨回欠款。旺财平凡、稳定而微小的幸福观构成了整个银城稳固生活的细小部分,而这部分因游离于革命的大潮之外,恰恰为李锐所竭力肯定。刘兰亭借银溪的水力向下游的革命党宣告起义取消的计划,结果因为岸边芦苇和杂草的纠葛而有许多竹片搁浅在岸边,而李锐所精心组织的这些相互纠葛的日常生活场景也使得一场虚妄的革命起义搁浅了。
与李锐以银城人琐屑平缓的日常生活消解血雨腥风的革命不同,李洱的《花腔》为追寻葛任生死真相而展开叙述,从而把关注点投向革命洪流中沉浮的个人的历史。小说不断变换切入视角,把各种直接或间接证据不断呈现和叠加,但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革命者究竟是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战斗还是死于川井之手却一直语焉不详。小说正文或副本以三位当事人立场各异深浅不同的叙述,像是从各个角度为葛任的故事拍摄的老照片,而一旦把这些照片相互对照以恢复事件全貌时,却不是彼此矛盾就是模糊不清了。整个小说就是在正史与野史、谎言与真实、文本与史料、现实与过去间穿插往返,无论哪方面都宣称忠实历史原貌,但哪方面的叙述都自相矛盾,他们对于葛任的说法似乎都与葛任本人无关,他们只不过是以或信仰或投机或反对革命及其历史的方式说着他们自己。在徐玉升看来,葛任的“才智不凡”;在毕尔牧师笔下,葛任的“眼眸有如露珠”;在田汗嘴里,葛任有不知审时度势的“诗人脾气”;而在黄炎的记忆里,葛任又是那个去国航行的途中出现在面前的文弱、羞怯、忧郁但不失豪爽的少年,这少年把引起恐惧联想的所有糖纸和瓶塞扔进了大海。所有这些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无一不是他们自己价值观的体现,也无一不是他们以自身的逻辑而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但无论真实的葛任还是真实的革命,依然在历史的迷雾中转身而去,留下的只是逐渐混沌不清的背影。“谁曾经是我/谁于暗中叮嘱我,/谁从人群中走向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⑬这似乎是葛任从二里岗逃生后回到大荒山白陂镇的时候发表在香港杂志上的诗歌的片断,它既是整个寻找葛任故事的开始契机,也是整个寻找的最后答案:“让一个我变成无数个我”。同样的,大写历史的因果链条被打碎,革命也从“解放”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一种讲述变成了无数个讲述。
三、“游戏”的“冲动”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这些寻求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讲述者进入历史时空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而成了一个被以往的革命叙事结构化了的符号。虽然对漏洞百出和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但李锐的“涨满性感的溪水”的银溪中,却仍然漂浮着许多历史文献的碎片。例如,李锐在前引题记中也有一个对时间的充满矛盾的表达。因为无论“大清宣统二年”还是“公元1910年”,都是历史文献而非庸常人生中所使用的,当时绝大多数的清朝子民还根本不知公元是怎么回事。这也许是李锐的刻意为之,正如他既可让“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又可让“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一样,以这似乎超脱时空束缚的视觉,让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中西二元对立的临界点上。然而这也再一次暴露李锐站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上重叙历史故事的动力并非源于摆脱理性控制的冲动。如果感性地再现银城人庸碌平常的日常生活,聂统领那种处于末世的悲凉感及其对满清行将就木的先知先觉就没有来由,而且当时日本人对于支那中国的模式化偏见也无从说起了。以往的革命叙事所提供的旧中国的社会图景依然在支配着他的银城想象。银城大盐商刘三公审时度势地送两个儿子留洋日本,并及时根据外边的机械化发展程度而改革传统的制盐产业,这不正是革命叙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翻版吗?所以说,革命记忆的前理解的存在,使得这些对革命历史的人性化还原都呈现出一种游戏于大小历史之中的态度,即使最为庸常的人生场景里也不难看到结构化的历史链条。所以,对于历史的叙述,不但隐含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奥妙交易系,而且暴露各种叙述结构都参与了对“散失的过去”的意义的竞争,并试图利用来为自己建构线性的历史。
当然,在有些聚焦家族或者村落历史变迁的书写之中,原来那种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扬眉吐气的新中国进而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等线性的革命信念,则又回到古老而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了。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几乎是重复了刘震云的马村故事,村名换成了符驮,两个家族的争斗换成了借助革命和阶级出身而当上村长的北存的长期专制统治。北存变着花样以革命名义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情色需求,而村民为了从他手里获得实惠,也不断地给他包括性在内的满足。他在革命叙事在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几乎成了符驮村中的土皇帝。“文革”后他从村长位上退下来后,儿子成了村里的一把手,权力似乎顺利世袭了,但他的性问题却遇到了麻烦,再没有村中的妇女愿意投怀送抱了。这时因为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的缘故,村中开始有了妓女,他最后拉开脸去了一次,结果却怎么也无法再展昔日雄风。⑭这种权力更迭的隐喻也正是历史循环论的另类表达,而在这里,革命似乎只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借以搬演的道具,大历史于是成了小历史的最为便捷的注脚。
所以,当这些作家们以人性化的名义、以道德化的姿态、以所谓个人体验的方式进入革命历史时,他们已经作为一个被结构化的符号,一方面存在着以往的革命叙事所留下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承载了“后革命氛围”中的解构革命神圣性的自觉义务。以往的革命叙事在新旧中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秩序,旧社会的一切所谓丑恶都是革命所斗争的对象,而通过革命斗争,为新的社会的发展指出光明的前途,然而如今的改写者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的翻旧出新,要么通过对人性化历史情景展开,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中所表现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追问,将那些高大全的英雄、绝对忠诚的信仰、苦大仇深的阶级对抗以及历史线性发展的逻辑,都别有用心地翻晒出来。
人们对过去的刻板印象经过人道主义的描述方法这么叙说一遍,却发现不但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粉碎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神话,而且革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反成了造成无数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但吊诡的是,这种人为制造人道主义与革命叙事不可通约的结果,不但无法找到除革命外还有什么更稳妥的改善社会黑暗和人性凶残的办法,而且他们既然承认人性如此不可救药,那么告别革命或认同现存秩序,难道是唯一的归宿?所以,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大举入侵,“八十年代”的“人性”的叙述虽仍被继承下来,但新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却使之对“资本”的考虑远大于对“政治”的服从。无论革命的初衷如何,最后都会造成灾难,这成为了被普遍接受和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所声称的“还原历史真相”,也丧失了站在权力之外发言的姿态,解构和消费革命于是成为娱乐文化生产的一大奇观,“红色共艳情一体,革命与恋爱齐飞”,游戏似成了其中唯一的态度。
注 释
①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7页。
②③⑦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第3页、第63页。
④邓一光:《父亲是个兵》,《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⑤李洱:《1919年的魔术师》,《午后的诗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350页。
⑥南帆:《后革命的转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⑧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⑩李锐:《银城故事·题记》,《收获》2002年第1期。
⑪⑫李锐、钟红明:《〈银城故事〉访谈》,李锐:《银城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第203页。
⑬李洱:《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⑭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关系研究》(编号:2010CWX008)阶段性成果。
河南大学文学院,许昌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