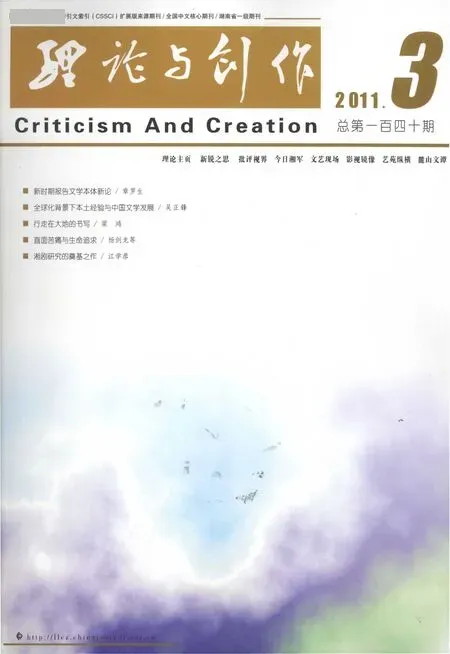新时期报告文学本体新论✳
■章罗生
新时期报告文学本体新论✳
■章罗生
我认为,当今的报告文学在观念和文体性质方面已发生根本变化,它不再只是“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相统一的“散体文章”,而是已发展、“扩张”为具有“新五性”特征的审美“文化复合体”①。其实,这主要是侧重于创作客体而言的,如果单就“主体创作”而言,我们还可作这样的补充,即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方式。
关于报告文学的主体创作问题,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中没有包括,人们也很少关注。即使偶尔论及,也没有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系统认识。这一点,在新时期以前的“过去”,也许情有可原。因为,在“过去”,与报告文学没有找到“自我”一样,我们也缺乏已找到“自我”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而且也缺乏成就显著、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大家”——即使如夏衍、刘白羽、穆青、魏巍、徐迟、黄宗英等名家,也要么以报告文学为“副业”,要么至新时期才奠定地位。而自新时期以来,其情况就得到了彻底改观:不仅涌现了几代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专业”作家,而且不少原以小说等其他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改行”至报告文学领域并取得突出成就——前者如徐迟、黄宗英、陈祖芬、乔迈、胡平、何建明、杨黎光、李鸣生、黄传会、一合等,后者如赵瑜、陈桂棣、肖复兴、叶永烈、张步真、王宏甲、孙晶岩等。同时,也仍有不少以小说等虚构文学名世的“大家”涉足报告文学创作,如王蒙、蒋子龙、李存葆、关仁山等。因此,以“主体研究”为核心的报告文学“作家论”就是当今研究者不应忽视也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了。事实也是如此:报告文学的“作家论”本是应放在第一位而首先加以重视的。因为,按照文学文化学的观点,“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②,“作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主体”③,而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又决定了其“创造主体”比其他作家更“特殊”。
就文体的“特殊”而言,与小说、诗歌等虚构文学不同,报告文学是一种“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甚至“主题先行”的文学。它不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存在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即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矫正其世界观的落后、偏狭,而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的思想高度也决定了作品的思想高度。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都以作家的所思所感为灵魂,唯独在报告文学中,作家的所思所感不仅作为贯穿全篇的灵魂,而且成为构成躯体的血肉和脉络”;“它可以直说,可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状态作最直接的评判,也可以向读者披肝沥胆,报告自己在特定情况下的真情实感”④;“若论‘干预生活’,无论是触及国计民生,揭露社会矛盾,还是抨击时弊或匡正世风,其他文学门类的可能性似乎都无法与报告文学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创作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渴求进步的正义感或使命意识,正如我们从不少优秀作品中感受到的,那是一种敢于向邪恶宣战的前沿品格,或一种独立思考的既吻合潮流又体现公众利益的社会文化精神”⑤。的确,就文体特性而言,由于报告文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必须经受历史和读者的检验,因而不是“崇高”人事进不了写作视野,不以“严肃”之态写不好崇高人事。尽管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当今报告文学中也存在媚俗、“拜金”等现象,但它毕竟不能像虚构文学那样,形成所谓“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废都意识”和“下半身写作”之类的颓废主义思潮,⑥相反,人们总是一再肯定其“说真话”、“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尤其是强调其“战斗性”、“批判性”与“忧患意识”、“启蒙精神”等等。如有人认为,“它的本性是抗争,是批判。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野文体。闲适与它无缘,拳头枕头与它无缘,风花雪月与它无缘”⑦;它“并不是因为需要低眉浅唱、吟风弄月才出现的轻浮文体,负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体使命”⑧。正是如此,虽然从当今的某些报告文学中也可找出与通俗文学相通的内容与作品,但总的来说,它只能是一种“严肃文学”,只能主要表现或追求“崇高美”。
与此紧密相联,报告文学作家也是更“特殊”的“创作主体”。其“特殊”之处在于:相对于小说等虚构文学而言,它对作家的素质要求更高,条件更苛刻。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倘若我们赋‘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以新的理解或含义,那便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列,关注现实而对社会进步倾注饱满的热情,无论是批判还是讴歌——它们是一个值得公众尊敬的‘作家部落’”⑨;“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和虚伪、谬误妥协;他崇尚正义的激情与鞭笞邪恶的精神力量一样强烈;他追求进步和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涉险,置身阴暗又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思想的先锋、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冲锋陷阵的尖兵”;“一部作家主体淡出的作品,非但不会有益于真实感的增强,反而会因主体不应有的缺席而弱化对于读者的召唤力。有分量的报告文学,必定是体现着主体激情和思想深度的作品⑩。”正是如此,可以说,“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⑪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从学理上说,“知识分子”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含意。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指一切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所谓“脑力劳动者”;就特殊意义而言,它是指西方人所谓的“代表社会良心”者——他们不只是一般的“有知识、有思想”,而是既有“庄严虔敬”的一面,也有“轻松活泼”的一面。⑫所谓“庄严虔敬”,是指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和敬意。他的目的不复限于用专业知识来谋生,而是要在他所选择的专业范围内严肃地追求真理。一切知识和思想——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或是人文科学的——都有客观的准则和内在的理路,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够横加干涉的”;其次,“一个敬业的知识分子必须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和节操”——他一定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尤其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奉持的精神。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或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句名言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一种最真切的写照。对知识和思想持这样庄严的态度的人也必然是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的人。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决不会是仅仅关怀一己利害的“自了汉”。相反地,从求真的精神上所发展出来的道德情操自然会引导他们去关怀文化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和公平。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其最重要的根据便在这里。⑬
综观中国的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可知,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报告文学作家的确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代表社会良心”的“特殊”知识分子,是最“值得公众尊敬的‘作家部落’”。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鲜明、突出的,主要也是其“庄严虔敬”。具体来说,这一点又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和节操”,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理性和公平”等“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关怀。也就是说,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为了“理性和公平”,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正如有人所说:“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⑭;“要有立场,就要有点胆量和拼劲,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即使‘打官司’也不怕”⑮;“报告文学作家不光要有智慧,还要有承担艰辛体力劳动的耐力和坚强的意志品格。报告文学作家有使命感、独立品格、忧患意识、牺牲精神,是那种‘周乎万物,道济天下’,努力‘经世致用’,对社会人生走向光明进步有着宗教般承当精神的人”;是“那些时常能够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把握社会生活矛盾的本质、用最文明和先进的思想观照现实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航船前进的瞭望者和引航人”⑯。的确,报告文学创作必须严守“真实性”,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因而被称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危险”不仅在于要承担“失实”的责任,随时准备对簿公堂,而且要冒因揭露内幕、触犯禁忌、鞭挞丑恶而被打击、关押甚至杀头的风险;作家为了充分获取丰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调查采访、搜集信息,甚至也要冒生命危险,深入洪灾、火灾、地震、战争、瘟疫第一线或异国他乡、毒品基地、高寒地带、“生命禁区”等特殊场域。如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愤怒的小秦岭》和《生死一瞬间》等作品,均是作者“历经数载,出生入死于荒蛮的山野和土匪、矿霸、山寨王等黑社会势力猖獗的矿区,以自己亲身经历、详尽生动地记述了野蛮抢窃掠夺国家矿产资源的那些当代新贵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惨无人道、荒淫无度、造孽后代的社会闹剧”⑰;如刘宾雁写《人妖之间》、张平写《法撼汾西》、赵瑜写《马家军调查》、何建明写《落泪是金》、卢跃刚写《大国寡民》等,都曾经历过因所谓“失实”而引起的官司;黄宗英写《小木屋》,在跟随主人公生活于藏西北森林中,曾因误食蘑菇而中毒;贾鲁生写《丐帮漂流记》,因化装乞丐体验生活而险被抓捕;邓贤写《流浪金三角》,因深入毒品基地而差点被杀;其他如写揭露官场腐败、黑社会集团以及有关艾滋病、麻疯病等题材,也都要冒一定的生命危险;有人甚至因此而舍弃了家庭、事业,改变了人生。
因此,要从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艰苦写作,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甘于清贫、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正如卢跃刚在《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想》一文中所说:“报告文学与小说家不同的是,它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胡平也认为,如果报告文学作家放弃文化批判的意识和文化先驱的使命,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转过身去,自己便与夜总会里浓妆艳抹的小姐别无大异,都失守了操守的孤域⑱。因此,他从上世纪的《中国的眸子》、《千年沉重》,到新世纪的《战争状态》等,一如既往地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陈桂棣之所以在1990年代从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是有感于“老百姓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坐下来去品味那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小说作品了,他们显然更欢迎直面人生、关注百姓疾苦的非虚构叙述形式的报告文学”,因此,尽管他“每完成一部作品身体都好像被掏空一样”,尽管“许多经不住这种文体写作磨难”的人“纷纷离去”,但他仍决心“继续用生命去写作”。⑲他的《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与《中国农民调查》等力作,即是其人格与思想的有力证明。这些,再次说明:“在全部文学创作的门类中,可能只有报告文学的理性色彩最重,并以独特的理性审视直接驾驭材料,诉诸文字而见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向报告文学提出了不同于小说和诗歌的审美要求。这些审美要求的第一条便是逼近社会,用它的方式揭示和透析社会,而且必须毫不躲闪,刀刀见血”⑳。
总之,报告文学作家所表现出的这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真理斗争的献身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之所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报告文学是一种最具知识分子品格的文学,是代表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主体人格、忧患意识、献身精神,应该是评价报告文学的首要标准;而“兼济天下”、“守望沉重”与“生命写作”,则可视为主体创作的三种境界。
其次,还须指出,为了“求真”,即为了保证作品的严肃、真实、可信,一般来说,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作家要付出比虚构文学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从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核实,因而其写作过程更长、更艰苦,其劳动也更令人尊敬。这一点,也进一步表现了创作主体的“庄严虔敬”。如何晓鲁、铁竹伟为了写“陈毅三部曲”,访问了许多当年和陈毅一起工作以及和他有过较多接触的党内外人士,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其中铁竹伟采访过的高层领导人多达224位,何晓鲁采访过的外交官、秘书、翻译和服务人员等也有60多位。同时,她们还读了几百万字的档案,查阅了几千万乃至成亿字的报纸(包括“文革”小报)、杂志和参考资料。即使是以作者亲属为主人公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分别用了六七年时间查找文献资料,还走访了众多的革命前辈;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非凡的年代》,既专注于从档案资料和父亲的自传、谈话及母亲的日记、回忆录中寻找可用的材料,又注意那些知情人与见证人的访谈和记录;不仅在北京满城跑,而且到老家四川南充搜集材料,并沿着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在雪山草地追寻先辈的脚迹。㉑还有,如黄传会、舟欲行的《中国海军三部曲》,其写作时间长达十年,期间除调查采访外,还大量阅读了清史、近代史、民国史、共和国史与世界海军史、造船工业史、海军兵器发展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同时研究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变迁,等等㉒,其准备之充分、态度之严肃、写作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其他如黄传会写《“希望工程”纪实》、叶永烈写“红色三部曲”等、孙晶岩写《山脊》与《女监档案》,陈桂棣、春桃写《中国农民调查》、卢一萍写《八千湘女上天山》和郝在今写《中国秘密战》与班忠义写《血泪“盖山西”》等,均在调查采访、资料搜集与考证乃至思想观点的锤炼方面,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以至健康与心血。在这方面,也许史家杰的感受和经验较有代表性。他谈到:几乎每一部作品的产生,大都需要经过“五子”的历练过程。即“采访的时候像骗子,构思的时候像傻子,写作的时候像疯子,发表了以后像儿子,没有发表像老子”。为了写《国葬》,作者“在历时十几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几千条的报刊资料,阅读了几百本的有关图书,积累了上百万字的采访笔记……那时就像是割包的小偷,军官证里总是夹着个小刀片,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时准备为无论所属谁人的报刊‘开天窗’”;因而他对蜡烛的认识是:“总是爱流着泪诉说奉献的痛苦”。㉓
除“庄严虔敬”外,知识分子还有“轻松活泼”的一面。这主要是指知识分子要“永远保持一种活泼开放的求新兴趣”,“在自己专业以外还要尽量培养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思想的广博趣味”——因此,正如有人所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永远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发展出他所必须具备的一些重要品质,例如不武断、容忍、有通识、超越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㉔这种“开放”的胸怀、“求新”的兴趣和“批判”的态度,在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点,实际与“求真”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庄严虔敬”相辅相成,也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息息相通。正是因为报告文学具有关注现实、注重题材开拓的特性,因而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求真”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他们不但追踪时代步伐,全方位地及时反映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而且在时空上,既掘进到了晚清以降的近现代历史,也深入到了青藏荒原、黄土高坡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人烟稀少之处。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种“求新”兴趣与“求真”、“超越”、“批判”精神融为一体,不仅表现出对“公平和理性”等“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关怀,而且表现出清醒、理性、独立的“思想家”特色。这一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愈到后来愈加鲜明、突出——我们只要从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查》,再到《革命百里洲》与《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从胡平的《世界大串连》、《中国的眸子》到《千年沉重》、《禅机》,再到《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从陈桂棣的《悲剧的诞生》、《民间包公》到《中国农民调查》;从邢军纪的《大沉浮》到《第一种危险》;以及从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到杨晓升的《只有1个孩子》,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到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等等,即可清楚看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不但表现了对“公平与理性”的坚守,而且其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的确“不是由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够横加干涉的”——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㉕。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与“痛苦”的追求,因而其作品就表现出沉重的反省、睿智的哲理与深邃的启蒙。因此,他们在反省“文革”这场民族浩劫时,就不只是简单批判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而是既思考民众与领袖、体制、路线之关系,也反省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应承担的历史与良心上的责任;认为离开法制的保护,思想自由便是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写在流水上的誓言(《中国的眸子》)。认为“地主制经济和中国一代代的地主,也嚼辛茹苦,披沙拣金,参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创造和推动”;决定社会性质与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除阶级斗争外,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战争状态》)。在探讨中国革命与“三农”问题时,他们认为灾荒是“革命”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也是紧紧抓住了灾荒这一大的“天时”;“三农”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不仅是共产党的问题,也是国民党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文化问题。总之,是中国社会、历史、革命的核心问题。(《革命百里洲》)在分析“张金柱案件”时,作者不是如以往那样,抓住张金柱这类所谓司法队伍中的“败类”,停留在揭露司法腐败、鞭挞封建特权的层面,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将张金柱的“交通肇事罪”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处以极刑,表面上看是顺应民心,实际上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因为,法律不能被舆论左右,不能被权力、“民愤”等“法律之外的东西”所干扰,“对于一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一种失去法律秩序的状态。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至于无法无天,草菅人命,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险,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种危险。”(《第一种危险》)而对于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等,他们也根据其“悲情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独立看法,认为应修订与调整“国策”,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第二胎。(《只有1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可知,在报告文学的本体构成中,“主体创作的庄严性”的确是其关键:正因为其“庄严虔敬”,才坚守“独立”、“痛苦”思考、“求真”“求新”,才表现出包括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和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等在内的“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也正因为其“求真”“求新”,才坚持“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也才向历史文化的深层掘进,表现出“文史复合的兼容性”。总之,才形成报告文学本体的有机系统,才从主客体两方面回答了什么叫“现在”的报告文学,即:从创作客体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从创作主体来说,它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
注 释
①报告文学的“新五性”是笔者近年提出的创新概念,包括“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参见拙文《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新五性”与报告文学之“文学”观念变革》,《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等。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③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④叶素青:《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统一——当代报告文学新“质”初探》,《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3期。
⑤⑨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自序:报告文学的创作品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⑥张器友等:《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范培松:《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序》,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⑪丁晓原:《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
⑩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思考》,《西南军事文学》2004年第 5、6期。
⑫⑬㉔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9页。
⑭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4页。
⑮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转引自梁多亮:《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⑯李炳银:《报告文学论》,《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2期。
⑰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内容提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⑱胡平:《千年沉重》,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4页。
⑲陈桂棣:《报告文学需要一种精神》,《报告文学》2001年第4期。
⑳卢跃刚:《报告文学面临新的问题》,《江南》1993年第2期。
㉑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3页。
㉒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对话〈百年海军〉作者》,《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㉓史家杰:《国葬·后记 死去活来》,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㉕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 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及其理论意义》(06BZW054)的成果之一。
湖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