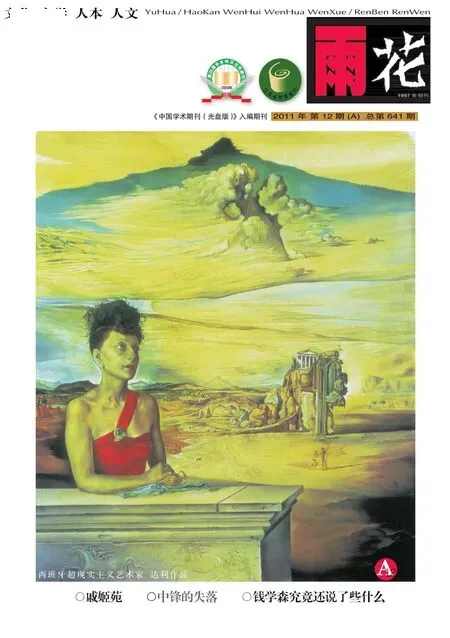象梳欹鬓月生云
● 靳 敏
我从来没有料到,会和这把牛角梳子相遇,相遇即欢喜。缘分是什么?女友千里迢迢带回送我,她送我的,除了这把梳,还有其他别的物件,可唯独这把梳子,一下对准了我的心思。
乡村长大的女子,幼时,情愿不情愿大都剃过一次或几次光头。也就在那一次,我才知道头发对女孩子有多重要,任凭好话说满箩筐,就是不答应剃。祖母哄:乖,剃掉再长的头发就缎子般黑亮,你看你现在,又软又黄,多难看。妈妈早不耐烦:少给她啰嗦,不剃也得剃!那时虽然小,也是怕人喊“黄毛丫头”的,终于含了泪让奶奶把头发剃光(不让妈妈碰),捂了整个冬天的棉帽子“焖”。乡间有个说法,剃光了“焖”出的头发就黑缎子一样顺滑。
果然,新长出的头发有黑缎子一样的光泽,只是依然卷曲。祖母拿把木梳,蘸水,往我的头发上抿,努力用红头绳在头顶捆绑出一个“鸡毛毽”。我持了一面小圆镜子看自己,也看奶奶:梳子斜插在祖母的鬓发里,像极了簪,祖母一点不像祖母,头发缎子一样黑,非常非常年轻。
我的发在祖母的梳理下长长,人也在祖母的梳理下长大,大到可以自己为自己扎辫子梳长发,心思也开始有了长发的长度,那把黑棕色木头梳子,每天无数次,从发根至发尾,慢慢走过。
我走出了祖母的视线,祖母在一场大病中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彩色精巧的塑料梳子代替了古朴的木梳来打理我的发,世界在我跨出家门离开祖母的刹那,如塑料梳子的色彩为我打开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我没有在出嫁时沿袭家乡为出嫁女梳头的习俗,我在外乡,是自己,上“轿”前慢慢地把长发绾成了发髻。我注重着头发的长长短短,注重着发型的随意或端庄,注重着发饰的色彩和美观,而没有重视过梳子,梳子于我,也就是一个必用的工具,直到我和这把牛角梳子相遇。
只一眼,就豁然明白,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场相遇。经过些世事,心已安静下来,需要这样一种工具成为最贴身最闺密的爱物。我握着这把牛角梳子,在发丝里挠挠,在发髻上梳梳,用眼睛、手、头发欣赏它爱抚它。无论经历多少世事,我都做不到看见心动的物什不欢喜。
几个小时前刚刚得到它。第一眼,莫名心动。我在两把任选其一的梳子里毫不犹豫拿起它,说:要这把。女友说,这把是老牛角的。
我把它装进我的包。想看它,又掏出,握在手心,细细看,越看越不舍。严格地讲,这不是一把精致的梳子,梳身好多处伤疤,梳齿也拙笨。可能恰恰是它的朴拙,暗合了我的心意。
整个梳体正是一只牛角的形状,也似一头牛的轮廓,背弯着,头弓着,梳身还莫名扭了一下,好像是斗架顶弯了角。所有的牛都有牛脾气,这肯定是一头更倔强的牛。无论如何放置,梳身都不是平面的。梳子的三分之一是把,握在手心恰恰好,润润的光滑,把的另一面,有鹅卵石纹样的纹理,这是一头牛年轻气盛的佐证。把伤疤磨砺成花纹,需要怎样长的时间和怎样钝的疼痛。
任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分钟,遇到什么物,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料到,会和这把牛角梳子相遇,相遇即欢喜。缘分是什么?女友千里迢迢带回送我,她送我的,除了这把梳,还有其他别的物件,可唯独这把梳子,一下对准了我的心思。在岁月的长河里,阳光,月色,暗夜的星,旅途的风,都将陪伴、见证我缓缓地抬起手臂,把梳齿插进发丝,轻缓地把寸寸青丝梳成白发。岁月的油润,会将这把梳子,浸润得越发润滑和乌亮。
没有送过别人梳子,但送过朋友篦子。我的那个女友,是以条理清晰著称的律师,但她却感性地在众多商品里,独独选了篦子要我送她。她说,祖母坐在太阳光里优雅地篦头发,已经成为她心里一幅越来越清晰的画。等她老了,她要坐在天井里,大太阳光下,边篦头边想我。
这一刻才明白,梳子为什么在古代像钻石一样承载了爱情的份量。
那首《木梳》,我还会背的,虽然是很久以前就读了的:我带上一把木梳去看你/在年少轻狂的南风里/去那个有你的省,那座东经118度北纬32度的城/我没有百宝箱,只有这把桃花心木梳子/梳理闲愁和微微的偏头疼/……我常常想就这样回到古代,进入水墨山水/过一种名叫沁园春或如梦令的幸福生活/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
这是送给爱人的诗,我转送我的女友。我所爱的,都能承担一把梳子的重量。这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