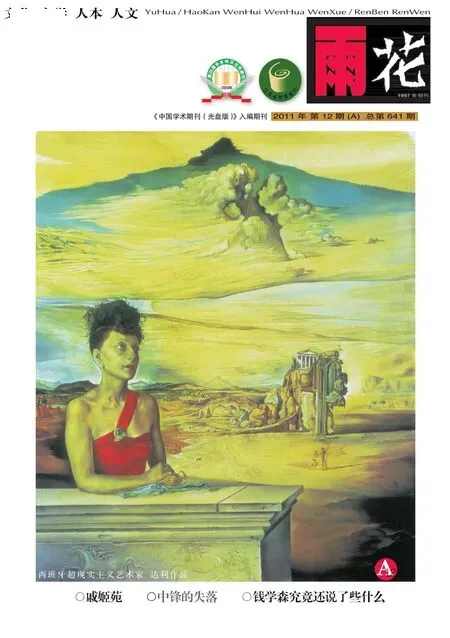一个女人的秋晨
● 董永红
秋晨的雾,如一位极度忧郁的老人。
太阳浸泡在雾气里,仿佛被淹得喘不上气来了。
雾气拖在天地间,如细密的鱼网,紧紧缠绕着村子。手触及的,脚触及的,脸触及的,呼吸到的……无不是阴冷的潮湿。潮湿,一点点儿浸湿衣服,浸透肌肤,浸入骨头,又一点点儿浸渗入人的心里……
时过中秋,着单衣已撑不住了。又是雾气弥漫的阴天,要是能在热烘烘的炕头上,美美睡一大觉,再吃一顿好饭,或者炒一盘豆子,边吃边和亲人闲谈,是最享受的事了!
女人醒来后才发现屋角漏雨了,有一缕泥水慢慢悠悠地从墙壁蠕动到炕角。炕角的被褥潮湿了。她不由紧锁眉头,把它们移到炕中间。心想,等忙回来,要赶紧上房顶收拾,要不然,大片漏雨,麻烦就大了。她记得小时候房子常常漏雨,有时漏得如筛子一样,外面大下,屋里小下,要是秋雨多了,家里的席子、毡子都吊在屋顶上,晚上也是没处睡觉。有时睡到半夜还会被雨水浇醒。只能顶着麻袋坐等天亮。那时候房顶上没有瓦,现在她家的房顶是有瓦的,可能是哪块瓦没有摆放好,才漏雨了。
女人给孩子喂足奶汁,把她抱在炕中间,用被子围好。拉紧门,就匆匆背起背兜向雾气中走去。路上她没有碰到一个女人。她碰到了两个男人。他们也是上山去打草的。他们经过她身边时,只是咳嗽了一声,也算是和她打招呼了。要是别的女人,他们可能还会开个玩笑,说几句话什么的。但是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有些不苟言笑的女人,很少有人拿她开玩笑。当然,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他们出门给牲口打草也是多么不情愿的事啊。说不定,他们刚才为打草的事与女人吵嘴了呢。看他们嘴唇撅得高高的,都能拴住一头牛。
她想,有个男人在家多好啊。要是男人在家,她一个女人家就不会这么早出门了。再说又来了那麻烦事,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天气潮湿,身体里也潮湿。禁不住浑身发抖。唉,她不由叹了口气。这些日子,不知为何,她总是由不得自己要叹气。有时还是一声接一声。当她发现,她自己都愣了。她想不明白,有事没事的,怎么就叹气呢?似乎是胸腔里被什么东西塞满着。叹口气就会释放些,感觉能轻松一点。
草上的露水一碰即落。镰刀收来的草潮湿极了。收在背兜里,水滴就顺着背兜往下滴嗒,很快,她的衣服和裤子就全潮湿了。秋田大半已收过,草有些不好寻觅。她跑遍几道地坎儿,膝头摔满了泥巴,厚厚的,如石膏一样渐渐僵硬。地坎很滑,走在上面不时打着趔趄。她看出眼前有几株很长的蒿草,心中一喜,要是割了它们,背兜就能满了。她就可以早点儿回家看孩子。也不知她醒来没有,要是醒来,一定又在哭。说不定尿了、拉了,她的小脚不停地乱蹬,把拉下的屎糊得到处都是……想到这里,她心急起来,赶紧向蒿草走去。
“叭嗒”一声响。
“妈哟……”
她滑倒在地。背兜从背上滚下地坎。盈满着奶水的胸脯狠狠地磕在地上。她觉得如破裂一样剧痛。奶水“哗”一下涌出来,胸前立时湿了一大片。她哪里能顾这些,镰刀碰在石头上,两根手指切进镰刀里,血顺着镰刀流出来,细细的,如一条虫子在刀刃上蠕动。她忍着痛,慌忙在内衣的破袖口上撕下一缕布缠在手指上。血很快从布条上渗出来。她急忙在田地里寻了些能止血的野草,放在嘴里咀嚼成泥,紧紧按在手指上。要是这回血还不停,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
好在过了会儿,血终于止了。手指却疼痛难忍。真是十指连心,每动一下指头都觉得心被人揪着。她忍受着,把那些蒿子割了,压在背兜里。背兜撑得圆鼓鼓的,但还没有到理想的程度。她只好继续寻觅。女人知道,牲口没有好夜草不行。天晴了,要忙着耕田地。地耕不好,明年的庄稼就没有指望。女人想,这雾气天正好给她和牲口放了假,看来一时晴不了。也好,停几天,牲口歇息好了,她的身子也歇清爽了。他们就能好好耕地了。
女人背着草往回走。雾气里的细水珠儿顺着她的头发梢往下滴。她不停地用湿漉漉的袖子擦拭着。鞋里全是水。每走一步,鞋子里的水就“沙咝,沙咝”作响。身后的背兜里也往下滴着水,她全身湿透了。似乎雨水渗满了她的身体,已实在无处盛下,又从她的身体里溢出来,一股股往外流,真是很难受。她想快些回家,趴在炕头上,把身子暖和一下。
她走得正急,不料脚下又一滑,背兜和人一起滚下地坎。
“咝……”的一声,裤腿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她低头一看,身体里流出的血早已浸染了裤子。血水正顺着腿慢慢往下流。受伤的手指触到地上,痛得她又叫了几声“妈哟”。好在这天气里没有几个人上山,要不这个样子,叫她如何走回去啊。
她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把裤子卷到半腿上,撕破的裤管走起路来就不会忽闪忽闪地叫人难堪了。这一摔,她浑身全是泥。她拉背兜,背兜很沉,死死地睡在地坎下,好像故意要耍赖。她越往上拉,它越往下滑,她使出了全身的劲,好不容易才把它拉上地坎,她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了,越是心急就越是觉得长。
女人的心里仿佛聚满了泪,真想哭一场。真的,美美哭一场,把它们全哭出来。放开嗓子哭。可是这不是叫别人听到了笑话她吗?唉,唉,唉,她只长长地,大大地,无奈地叹了几口气。
女人放下背兜,牲口已等不急了,直叫唤。羊儿叫,猪儿叫。鸡也叫,狗也叫。经过一夜消化,谁的胃里都空荡荡,都在等着女人回来给它们食物。她跑着,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一一喂养了。这当儿,孩子在炕头上不停地哭闹,她抽空进去哄几句,她还是哭个不停。她只能在院子里答应着哄她。可是,才三个月的孩子,如何听得懂她的话啊。她也是饿了,想吃妈妈的奶了。孩子哭,她就更急,恨不得飞着干。她来不急和好猪食。匆匆忙忙倒进槽子里,由它们自己和去吧。
女人终于跑进屋里。她用木棒死死顶上门。她快速脱去那些粘贴在身上的湿衣裳,她觉得它们缠在身上,叫她喘不过气来。裸露着身子,冷得她的上下牙齿之间磕碰得“咯咯”作响。她从暖瓶里倒了热水,把毛巾浸泡在水里,急忙开始擦拭。她的胸脯已胀得生痛,硬得像石头,手一碰,痛得她泪都要流出来。孩子哭得更紧了,她来不及细细擦拭全身,扔下毛巾,跳上炕头。抱起孩子,她那温暖的小嘴儿一下子扑上来,狠狠地吸吮着乳汁。她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慢慢降落在胸膛里,不是那么沉重了。
多么温暖的炕头,身子贴在上面,热气从她的身下慢慢蒸上来,散发到全身,真舒服啊。她把孩子的湿尿布移开,把孩子紧紧搂进怀里,这样,她的心不再那么紧缩,也不那么潮湿了。孩子吃过一阵奶,女人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那些胀满的东西,那些渗入的雨水,也一点点慢慢发散出来了。她觉得舒服了许多。
孩子均匀地呼吸着,女人端详着她的小脸。觉得如梦一般。她的父亲还没有见过她。要是他打工回来,看到这个小东西是不是要大笑了?女人想着,想着,眼前有些恍惚。她就这样躺着,搂着孩子昏昏沉沉睡着了。
很快,她就进入梦乡,她梦见男人回来了。他在院子里叫她。她推开门,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双新雨鞋,还有一件新雨衣。他正对着她笑呢。
突然,院子里狗狂叫起来,女人的梦被打破了。她惊恐地从炕头跳起来,急忙穿着衣裳。这时,来人已经径直走到了屋子门口,他推着门“咣咣”地响。“等,等,等会儿。”女人想,是谁呢?怎么也不叫一声就直冲屋子来了。
屋外的人见推不开门,说:“大白天的,把个门顶得严严实实,真像是过阴天哩,睡着不想起来了?”
“哥,你等一下。”女人听出是她娘家哥哥的声音。心中很高兴。
“哥,咱家里都好吗?妈的腿病再犯过吗?”女人接过哥哥肩头的行李问。
“还算平顺哩。两个老人想你想得不行,叫我来看你哩。天晴了,忙里忙外顾不上,今儿老天放了假,一大早,我想睡个懒觉,妈就催我起身了。你看我来了,你还睡懒觉呢。嘿嘿。”哥哥坐下笑着说。
女人赶紧给哥哥泡了一杯热茶,双手捧到他面前。她坐在哥哥对面,笑着说:“哪里还有睡懒觉的福气,我已经出门寻过一回草哩。这天气,把我冻得难受,回来在炕上暖着,就睡着了。”
“我还以为你睡着没有起来呢。嘿嘿。我想你也没有这么心闲。”哥哥说。
“不起来,长嘴的个个叫嚷得不行,哪个都要吃哩。”
“是哩,只要养着,哪个都要操心。”
兄妹俩拉着家常,时间过得真快。
哥哥说他还有事,坐一会儿就要走。女人硬是留下哥哥,叫他吃顿饭再走。孩子醒来了。女人给孩子吸饱了奶水,哥哥要抱小外甥,她就跑去做饭了。
秋雨来得没有预兆,打麦场上仅有的一些柴禾一夜间几乎被雨灌透了。能燃烧的就那么一点儿。
女人把柜子里的三只鸡蛋摸出来,小心翼翼地打进碗里,她要给哥哥做一顿好饭。哥哥一年四季来不了几回她家。她要把最好吃的拿出来给哥哥吃。她本想叫哥哥杀了那只老母鸡两人美美吃一顿,可他说什么也不让杀,他知道妹子家就这只下蛋的鸡,还要存着给娃娃吃鸡蛋呢。
菜炒好,水烧开,剩下的干柴不多了,女人想用这最后一把柴火把鸡蛋面做好。谁知打算没有变化快,面下到锅里,柴火快燃光了,却迟迟不见开锅。女人急了,跑出屋子,她寻遍院里的角角落落,双手在地上撒摸着,把那些风吹来的,避在角落里的干草叶拢到手中,跑回屋子,撒在火焰上,锅里发出“咝咝”的响声,她希望一下把锅烧开,但很快,响声就消下去了。眼看着火苗又黯淡下来,女人都快急死了。她又跑出屋子,又在角角落落开始撒摸柴草,这回她拣到得更少。她急急跑进屋子,把柴草撒在火苗上,锅里又发出一阵“咝咝”的响声,快开啊,快开啊,女人心里祈祷着。不能叫我的娘家哥吃半生不熟的饭呀。可是,就那点可怜的“咝咝”声随着火焰的再度黯淡而令人绝望地消失了……
糟了,这回面泡在锅里了。哥哥好不容易来一回,还给他端出了夹生饭。唉。女人的心都快急疯了。
她再次跑出屋子,院子的角角落落里已经寻不到能烧的柴草了。
她只好抓了一把有些潮气的柴草填进灶里,微弱的火苗这时加了潮柴全然熄了,只有雾样的白烟从里面涌出来。女人无奈地趴在灶火门口用嘴吹,浓烟一股股冲出来,呛得女人直咳嗽。顾不了这么多了,火再着不起来,饭就真泡得吃不成了,要是平日她一个人,她也就这样吃了,但今天有哥哥在家,哥哥是她最亲的亲人啊,咋能叫哥哥吃这种饭啊。女人心里反反复复念叨着,她越想越急,只能奋力吹着火,突然一股烟裹着火苗猛扑出来,女人一躲,仰卧在地上,受伤的手指触在地上,钻心的痛,包手指的旧布条再次被鲜血浸透了。其实她躲闪已经迟了,在一阵“咝咝”响声中,女人的眉毛和发梢被烧得结成疙瘩。女人用袖子擦了一下,袖口上粘着烧糊的眉发。这回叫我咋见人哩?女人摸索着脸颊。叫我咋能见人哩?叫哥哥看出来多难为情啊。
锅里的饭又一阵“咝咝”响,火焰过后,响声还是小下去。她急得都要哭了。
女人是在从地上往起翻身时,突然看到屋脊上的那把笤帚茵来。那是她夏天一根一根从地坎上寻着拔回来的。捆扎好能当笤帚用,这些年天旱,它们很难寻觅。女人专门花去两天时间,才寻觅到能够扎一把笤帚的草茵。女人看到它,如得到救星般地跳起来,她跳上炕头,从屋脊上抽出笤帚茵,跳下地,把它塞进灶膛里。“呼”火苗燃起来了,灶膛如一个得到意外之财的人,发出“烘烘”燃烧的欢笑声。她的心里一阵喜一阵痛,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锅里又开始“咝咝,咕咕……”响起来。很快锅里的饭终于开了大花。女人长长吐了一口气,她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脸上浮上笑容。
她把锅里的鸡蛋都盛到哥哥的大碗里端上去。
她从哥哥手中接过孩子,孩子把哥哥的裤子尿湿了。哥哥正在笑着怪嗔她呢。
看着哥哥吃得很香,女人很满意。她一边喂着孩子,一边和哥哥吃饭,一边拉着家常。
哥哥吃完了,抹了一把嘴,舒畅地吸着一支老旱烟棒子,望着妹子吃。他看着,看着,笑了。说:“你看你,都给娃娃当妈了,做一顿饭,还和小时候一样,叫锅黑把脸画得五麻六道哩。”女人这才突然想起她的脸,她耳根一热,脸发烧,心里涌上一片潮汐,泪珠差点落下来……她假装着去盛饭,跑到灶房里把泪抹掉了。
“你快些吃,吃罢了,你接瓦,我给你把房顶收拾一下,要是再连着下几天,你们娘俩连个睡的地方就没有了。”女人洗了脸返回去时,哥哥正仰面看她家的屋顶漏水处。
“我准备睡起来再上去看哩。正好你来了。我就不用愁了。”女人笑着说。
哥哥帮她收拾好屋顶,就匆忙起身回家。家里还有一大摊事等着他呢。女人目送哥哥走入雾气里。
哥哥的身影消失了很久,她还站在那里,呆着。她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一声,女人抬头望了望天空,雾气似乎正慢慢拢收着,天空有些亮堂了。她想,太阳到中午可能会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