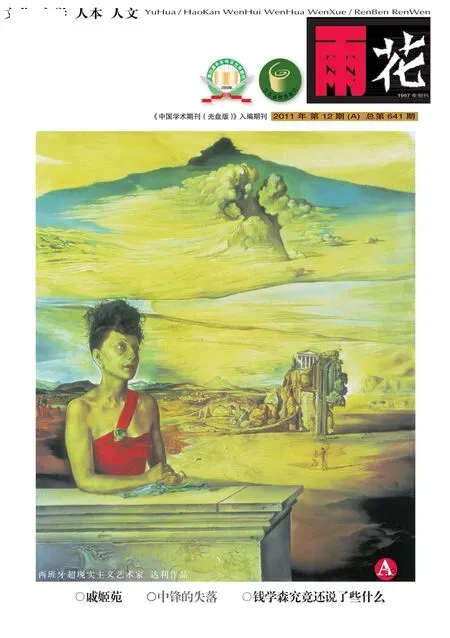苏桥的心事
● 郝炜华
苏桥呆住了,是那个男人,那个穿绿军装的年轻的将苏拾递到她手里的男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呀?他是从天上,从月亮上,从星星上,从空气里冒出来的吗?
十八岁的苏桥还在读高中,但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大姑娘了。她爸她妈不舍得叫她上山做活,叫她上学、考大学。苏桥的姑姑家在山的东边,一座不高不矮的山分开了苏桥家与姑姑家。妈妈有事情,比如送好吃的东西、比如过年走亲戚、比如将喝醉酒的爸爸叫回来之类,妈妈就叫苏桥翻过山到姑姑家去。这一次是因为表哥参军了,姑姑要苏桥送鸡蛋、面条和钱过去的。
表哥比苏桥大三岁,姑姑也想叫他考大学的,可是表哥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了两年还是没有考上。于是姑姑就叫表哥当兵。妈妈是不同意表哥当兵的,妈妈在村子里做妇女主任。她对姑姑说:“听说现在不太平,当兵有可能上战场,还是叫泉复读吧。”可是表哥不肯再复读,所以表哥就当兵了。
苏桥跟表哥的关系很好,每年寒暑假,表哥都在苏桥家呆上一段时间,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这样的,两个人一起写作业,一起到河里钓鱼,一起跟别的孩子打架,再到后来就一起说喜欢的男孩与喜欢的女孩子,所以苏桥听说表哥当兵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所以,妈妈让苏桥去送东西与钱的时候,苏桥早早就出门了。等到苏桥顺着山坡走去,看到姑姑家村口的那头石牛和乌黑、弯曲的老柳树时,太阳一下子蹦出来了。是多么大多么圆多么红多么柔软多么温柔的一个太阳呀,那么安静那么安详那么慈祥地挂在碧绿碧绿的树梢,直弄得人的心窝子都要软了都要柔了都要细了都要碎了。苏桥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十八岁的苏桥坐在山坡厚厚的绿草上呜呜呀呀地哭起来了。
远远的,路前头有一个人影,穿着绿色的衣服,远远地走过来了。是表哥吗?是穿着新军装的表哥来接她的吗?可是,看上去又不是表哥,那个人比表哥个子高,那个人步子也比表哥大。苏桥低下头,冲着那人走过去。走近了,才看到那是个穿着崭新军装的年轻人。苏桥的心一下子跳了,天呀,军装真绿呀,军帽下的这张脸真英俊,眼睛好大好亮呀。苏桥觉得心底里一层东西打开了,汪汪的水一下子冒了出来,她的脸红了。为什么又流泪了?十八岁了,为什么总要莫名其妙地流泪?
苏桥快步经过穿军装的男子身边,却听到他在身后喊她,“哎。”
苏桥回过身来,她看到穿军装的男子脸上灿烂的笑容,笑容里面包含着羞怯,包含着拘谨,他将手里一个天蓝色的包裹递给了苏桥。他说:“我参军了。现在就去城里的火车站。什么都来不及了。不过以后我会来找你。”说完,男子仔细地看了看苏桥的脸,仿佛要将苏桥记在心里。他甚至伸出手拍拍苏桥的手,又说:“等着我。”然后就掉头走了。
苏桥愣怔地看着那个碧绿的影子大步向前走着,很快就远得只剩下一个绿色的小点。那片汪出来的水已经将苏桥淹没了,苏桥感觉自己软得就像一团面,差不多要倒到地上,瘫到地上了。
这个时候,她手里的包裹突然动了一下,然后就爆发出响亮的哭声。苏桥吓了一跳,她这才去看包裹,那是个天蓝色的印着白花的小被子,小被子折成了粽子的形状,一端用红色的布带捆着。苏桥掀开折下的被角,一个端端正正的小孩子露在她的面前。
苏桥因此没有看到表哥。表哥一大早就坐着村里的汽车去城里报到了。
苏桥将面条、鸡蛋、钱还有包着孩子的小包裹放到了姑姑的炕上。姑姑正坐在炕上掉眼泪。可是她被苏桥的小包裹吓了一跳,因为那个小包裹又爆发出响亮的哭声,她一下子从炕上跳下来,说:“桥,你带来了什么?”苏桥说:“孩子,一个孩子。”“你妈妈叫你带来的?哪来的孩子?”苏桥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苏桥将经过说了说。姑姑一拍大腿说:“坏了,桥,是有人要丢孩子。”苏桥说:“可是,他要去当兵。”“当兵的人也会丢孩子。桥,你这个傻闺女呀。”
姑姑解开小包裹,一个赤裸的小婴儿出现在苏桥的面前,是个女孩,两条通红的小腿弯曲着,一下一下有力地蹬着被子,小脸上的五官跟随着腿的动作皱巴巴地挤到一起,嘴巴张得大大的,爆发出响亮的哭声。
姑姑说:“怪不得哭呢,拉屎了。”她找出一块布,温水湿了,很快地擦干净婴儿与被子的屎,然后又将婴儿紧紧地包裹起来。说:“要找着孩子的家人。这孩子给了咱们算什么事呀。”
姑姑带着苏桥去了城里,城里火车站的广场上坐着密密麻麻的新兵,他们像修剪整齐的青草一样,动作一致地坐在广场上。苏桥没有看到表哥,那些新兵看上去一模一样,似乎是一个模子里面扣出来的。姑姑指着那些新兵,着急地问:“看看,是哪个?看看,是哪个?”苏桥睁大了眼睛拼命地看,眼里除了汪汪的绿色,看不到别的颜色。苏桥找不到将包裹递给她的那个年轻男子。
姑姑着急起来,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她抱着孩子要去找带兵的军官,苏桥突然拉着姑姑的衣襟,“哇”地一声哭起来,她的哭声很大,一点不像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似乎她特意要哭给别人听,哭给别人看的。姑姑说:“你哭什么,哭什么呀。”可是苏桥还是哭,更大声地哭。姑姑急得跺脚,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她,因为怀抱里的那个小包裹也发出“哇哇”的哭声,姑姑急得跺脚,说:“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呀。”
这个时候,所有的新兵都站了起来,他们排着队就像整整齐齐的青草一样,进站了。然后,火车就开了。
妈妈与姑姑相对坐在炕上,为婴儿喂了奶粉。又一齐将目光投向苏桥:“怎么办?”苏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觉得她应该哭,可是她现在又哭不出来了。
妈妈与姑姑都认为孩子不是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的,一个即将远行的军人怎么会生养出一个婴儿呢?结了婚的男子是不能够当兵的。那么,可能就只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女人,没有结过婚却生了孩子,或是想生一个儿子却生了一个闺女的结了婚的女人偷偷将婴儿扔到路边,然后被穿军装的年轻男子捡到了。
是谁这样坏,这样作孽呢?妈妈与姑姑都叹气,她们决心到附近的村子找一找,将孩子丢到山上的肯定是附近村子里的人,她们决心到附近的村子里找一找,决心找到那个丢孩子的女人。
通过那座山能够到达的村子有四个,一个是苏桥家的村子,可是苏桥没有听说谁家的女儿怀孕,谁家生了孩子不要的。一个是姑姑家的村子,姑姑也没有听说谁家的女儿怀孕,谁家生了孩子不要的。另一个村子是山窝里的猴子沟。还有一个村子叫北汪。她们决定先去猴沟,在猴沟找不到那个女人时再去北汪找。
姑姑跟妈妈和苏桥告别,她的身子很快淹没在了山影里面。苏桥突然就叹了口气,妈妈看了她一眼,妈妈说:“看你做的好事。”苏桥说:“能找到那个女人吗?”妈妈又说:“看你做的好事。”
第二天,苏桥上学去了。但是她一点听不到老师讲什么,她的眼前一直浮现着那双眼睛,那个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的眼睛,她的心一直汪在一片水里,汪得她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苏桥恨不能化成一摊水软软地倒在地上,顺着桌子腿,顺着椅子腿,一直淌出教室,一直淌出去,淌到那遥远的地方。
姑姑又来到家里,她与妈妈还是相对坐在炕上。婴儿就放在她们的中间,已经吃饱了奶,脸蛋红扑扑的,呼哧呼哧地睡觉。苏桥一进门,姑姑与妈妈就一齐将目光投向苏桥。姑姑说:“没找到那个女人,猴子沟没有,并且猴子沟没有一个男青年当兵。在北汪也没找到那个女人,北汪有三个男青年当兵,可是他们家里人都不承认有人捡过孩子,并且那些年轻人都是早上一块坐汽车去城里的。”
妈妈说:“看你做的好事。”
苏桥只觉得委屈一层一层涌上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委屈,她就是觉得这么委屈,于是她放下书包,站在屋子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妈妈决定将孩子收留到找到那个女人之前。妈妈对姑姑说:“总不能也把她丢了。把她丢了的话,我们跟那个坏心眼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姑姑皱着眉头说:“我管不了,随你的便吧。”说完姑姑就走了。
妈妈将婴儿抱在怀里,那个小小的有着眼睛、鼻子、嘴巴的肉团在她的怀里安静地睡着,妈妈说:“你妈妈是谁?你爸爸是谁呀?你怎么这么命苦。命苦的孩子,我给你起个名吧。”
婴儿的名字叫苏拾,意思是拾来的孩子。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经常将讨饭的男女请到家里吃饭,经常送钱送粮食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即使流浪的猫狗跑到家里来,她也将它们收留到它们呆够了为止。猫狗都会收留,何况一个小小的婴儿呢。妈妈说:“桥,你有妹妹了。你要考上大学,给妹妹做个好榜样。”
可是苏桥已经不能好好学习了,她的心跟着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走远了,低头,课本里是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抬头,讲课的老师是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晚上睡觉,一不小心都要梦到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这个时候,苏桥已经在学校里住校了,是上下两排的大通铺,从东墙一直挤到西墙,同学的被褥,一条接一条,紧紧挨在一起。苏桥从睡梦中醒来,听到此起彼伏的呼吸,看到月光从门缝透进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条斜斜的影子,影子里也有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他在影子里冲着她拘谨地笑着。
村里有女同学与苏桥一起住校,女同学有三个哥哥,哥哥对她宠得很,女同学的妈妈也不想叫她考大学,因此女同学总是偷着从学校跑回家去,三里的乡村土路,女同学一边甩着辫子一边走,二十分钟就到家了,家里有暖和和的炕,有花生、苹果,有大大香香白白的馒头和韭菜炒鸡蛋。“韭菜炒鸡蛋那个香呀,”女同学说:“碧绿的韭菜从地里割回来,井水里泡了洗了,切成小小细细的丁,拌到金黄色的鸡蛋里,嗞啦一声倒到热锅里,香味立刻飘出来,小蛇一样哧溜一声钻进鼻子里。”苏桥的口水都要流出来,她跟着女同学一起回家了。
妈妈抱着苏拾站在灶屋口,苏桥的眼睛花了一下,她看到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站在灶屋口,那个男子抱着小小的包裹看着苏桥说:“给你,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年轻的男子离苏桥这样近,不是在课本上,不是在讲堂上,不是在梦里,而是在她家的灶屋口,在她一伸手就能够着,就能摸到的地方。
苏桥伸出手去,她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那是苏拾,是苏拾美丽丰满的小脸蛋。
妈妈将苏拾递到苏桥怀里,妈妈开始生火做饭。妈妈没有做韭菜炒鸡蛋,做的是没滋没味的炒菠菜,妈妈一边做菜一边骂苏桥,骂她不跟着好人学,专跟不爱学习的人往家跑,骂她不爱学习,专爱那些没有出息的人。妈妈的骂声像珠子一样沿着墙壁的四角滚动,最后纷纷落到苏桥的身上,砸得苏桥的肉、筋骨、身子一片疼痛,苏桥将苏拾放到炕上,拿起书包离开了家。
妈妈说:“你这个不听话的闺女,吃了饭再走。”
苏桥不说话,急着步子往村外走,夜色一层一层包绕着她,熟识她的几只狗跟着她一边跑一边叫,苏桥的眼泪扑哧扑哧掉下来,她觉得妈妈不要她了,村子不要她了,她觉得一个人离她远了,越来越远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苏桥回过头来,空落落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人影,就连那几只狗也跑走了,是谁?是谁离她越来越远了呢?
然而苏桥学还是没考上大学,即使她下了决心不跟着女同学往家跑,她还是没考上大学。
姑姑来到苏桥家,妈妈与苏桥都认为她是来问苏桥考大学的事情的。可是姑姑没问苏桥考大学的事,姑姑一进门就哭了:“泉上前线了。”“前线?”妈妈与苏桥都瞪大了眼睛,“太平盛世,哪来的前线?”“你们呀,你们。”姑姑坐在炕上,拍着大腿说:“你们呀,你们什么都不懂,自卫反击战呀。”
自卫反击战,苏桥是知道这个的。虽然知道,但是她感觉它离自己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远。可是现在它却一下子离自己很近了,是多近,表哥,自己的亲人都上前线了。
“我就说嘛,你们不听我的。”妈妈说:“去年招兵的时候,就说现在不太平,你们不听,非叫泉去当兵。泉在哪呀?子弹不长眼呀!”苏桥说:“在前线,姑姑不是说表哥在前线嘛。是不是所有的新兵都去了前线?”“不知道呀。好像是。”姑姑说:“还是别人家跑来告诉我的,我们村去年当兵的孩子都去了前线了。”
看着妈妈与姑姑掉泪,苏桥也难过起来,为年轻的表哥,为那么年轻那么年轻的表哥上前线感到难过,子弹不长眼呀,表哥一下子留在前线回不来了怎么办?苏桥的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她还为另外的人难过的,昨天晚上她还梦到他,她还为他难过,他也是新兵,他也应该到前线了吧?
姑姑却一下子不哭了,姑姑看着放在炕上的苏拾,说:“这孩子有些怪。”妈妈也不哭了,说:“是呀,快一岁了,还不会爬,就是吃饭吃得好,长了一张大胖脸。”姑姑说:“我记得泉八个月就会叫妈了,一岁多一点就走路走得很好了。”
姑姑扶起苏拾,苏拾歪着脑袋看着姑姑,脸上堆着茫然的没有目的的笑。姑姑说:“不对,这个孩子有问题。咱们得送她到医院检查检查。”
姑姑、妈妈和苏桥就抱着苏拾去医院,不是镇医院,而是县城的中心医院,并且挂了个专家门诊。医生将苏拾放到床上,反来复去地检查,最后,告诉姑姑、妈妈和苏桥:“苏拾患的是脊柱瘤。就是在长神经的脊柱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们看。”他指着苏拾后背的一块凸起说:“就是这个。瘤子长大后还会挣破皮肤露出来。这病是先天的,没有任何医治办法。”
姑姑与妈妈决定将苏拾丢掉,就像当初的那个女人,她们决定在一个凌晨将苏拾放在马路上,等待着被好人捡走。她们甚至商量好了什么时候,将苏拾丢在什么地方。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她们甚至没有回家,住进了城里的旅社。黑夜很快来临了,不知道为什么,苏桥感觉今天的夜来得特别快。凌晨也很快来临了,凌晨来临得甚至比黑夜还要快。姑姑与妈妈已经将苏拾喂饱了,苏拾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躺在妈妈的怀里呼呼大睡。妈妈与姑姑要出发了,她们又仔细地看了看苏拾,妈妈甚至掉下泪了,妈妈说:“我这是在作孽,我这是在作孽呀。”
苏桥一直躺在被窝里静悄悄地睡觉,姑姑与妈妈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她们去丢孩子,不要苏桥去的。可是,这个时候,姑姑与妈妈抱着苏拾要出门的时候,苏桥一下子哭了,她像十八岁那年那样,躺在被窝里面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并且哭声越来越大,变成很难听的号啕大哭了。苏桥的哭声惊扰了苏拾,她也哇哇大哭起来。妈妈说:“桥,你在干什么?大清早的,你哭什么?”姑姑说:“桥,你是不愿意叫苏拾走吗?”苏桥还是哭。最后,姑姑与妈妈也哭了,姑姑与妈妈抱着苏拾坐在床沿上,说:“那就不丢了吧。可怜的拾,我们就养着你吧。”
像许多未婚的少女一样,苏桥开始了绣花。妈妈托木匠用新鲜的柳木给她做了绣花架子,雪白雪白的描了墨蓝色花样的布子绷上去,线团摆上去,亮晶晶的细针摆上去,然后将绣花架子架到两张凳子上,苏桥就开始了绣花。
苏桥绣的花将会出口到欧美一些国家,等她用细密的线将那些墨蓝色掩盖住,布子上凸起大朵大朵的菊花、大朵大朵的荷花、大朵大朵的牡丹时,她就要将布子拿下,送到村里专门收花的人家。那户人家会根据针脚的细密、花的美艳、布子的洁净将花分成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然后再用飞快的小刻刀将多余的布子刻去,只留下镂空的菊花、荷花、牡丹花,于是一块美丽的桌布出现了,一条缀着长长流苏的床单出现了,一幅春色满园、活色生香的窗帘出现了。它们会从这座小小的村庄出发,带着少女们的体温,带着少女们的体香,出现在欧美某户人家的房子里。
因为绣花,苏桥大段大段的时间呆在家里面,妈妈也自然而然地将照顾苏拾的任务转移到了苏桥的身上。好在苏拾是个很乖的孩子,除了睡觉就是坐在小推车里静静地玩个娃娃或是纸片。她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并且很少哭。她似乎就是面塑的一个小人,被神仙从鼻孔里吹了口气,于是便有了人的呼吸,但是没有人的活力。苏桥一边绣花一边跟苏拾说话,说她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说她和表哥一起到河里摸鱼,一起到山上摘苹果,说那个早晨,她到姑姑家里去,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将苏拾递进了她的手里。苏桥说:“拾呀,他是你爸爸吗?拾呀,他说:给你,等着我呀。”
是呀,等着他呀,是叫拾等着他,还是叫苏桥等着他,还是叫苏桥带着苏拾等着他。苏桥有些迷惑了,她停了飞行的针,盯着苏拾发起呆来。
屋子外传来激烈的吵闹声。苏桥抱着苏拾走出屋子,看到姑姑站在院子外边,院子外边有几个男人,姑姑说:“你们有没有良心?你们还是人吗?”一个男人说:“你当什么真呀,我们就是说着玩的。”
“说着玩?这种事能说着玩吗?你们不怕天打霹雳轰吗?”
苏桥慌忙拉姑姑,姑姑一边骂一边往家里走。说:“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前线下来一批女兵伤员,说她们的腿、胳膊都被地雷炸了去了,只剩下一截圆桶样的身子。你猜他们说什么,他说要村里的老光棍去接回一个来做老婆,说是接回一个国家一年补贴一万元钱。”苏桥的眼前红光闪烁,她说:“他们是犯罪呀。女兵是功臣,都是国家养活的,他们这样说是犯罪呀。”姑姑说:“为这我才跟他们吵起来的,他们,我都恨不得伸手打他们耳光。”
姑姑带来一个好消息,表哥从前线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毫发未损,还是个完完整整的男儿。姑姑一边说一边掉泪,苏桥也高兴得掉下泪来。她噙着眼泪问姑姑:“还有谁?还有谁回来了?”
“我们村那几个小伙子也一起回来了,都是没受任何伤地回来了。”
那么他回来了吗?他……可是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哪个村的呀?苏桥咬住了嘴唇,苏桥抱紧了苏拾,紧紧的,紧得苏拾都要哭出来了。
苏桥来到城里,县里组织年轻人迎接凯旋的英雄。汽车开来了,车厢里站着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的战士,战士们眼中饱含泪水,嘴巴紧紧撇着,不叫自己哭出来。一些女学生跑到汽车旁边,将巧克力,将苹果、糖果塞进汽车,举着笔记本大声喊:“给我签个名,给我签个名。”一名战士满脸泪水,一把将身上的大红花、肩章抓下来,扔到了人群里面。苏桥的心怦怦地跳,几乎要跳出来。呀,最最可爱的亲人,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里面有他吗?
苏桥拉住身边的一个男人问:“他们都回来了吗?他们……有丢小孩的吗?”
“你说什么呢。”那人不耐烦地甩开苏桥的手臂。苏桥只觉欢呼的声音远了,只觉油油的绿、艳艳的红远了,她挤出了人群,她感觉自己要掉泪了。可是能掉泪吗?苏桥问自己,能掉泪吗?
眼泪还是掉了出来。回家看到苏拾时,苏桥的眼泪掉了出来。她抱着苏拾,坐在柳木板凳上,坐在金黄色的阳光里,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了出来。
临近春节,表哥回家探亲了。这是表哥入伍以来第一次回家。表哥高了,瘦了,可是表哥的胳膊还是胳膊,腿还是腿,什么也没有少。表哥跟苏桥讲前线的事,说开拔前部队首长给他们训话:“我们坚守的地方布满了地雷,那里,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雷山雷海。进驻前线第22天,一位战友触雷牺牲,另一位战友被地雷爆断了小腿,皮肉纷飞,只剩下白生生的断骨。你知道前线的路是什么样的吗?表面踩得稍微发亮的石头就是路,它们形状不一,崎岖不平,但是高于地面,远离了地雷,这是战友用鲜血踏出的一条道路……”
妈妈与苏桥听得心惊肉跳。苏桥抱着苏拾送表哥。夜色一层一层地漫下来,表哥与苏桥一前一后走在乡间的小道上,苏桥一边走一边小声地喊:“哥。”表哥“哎”地一声。苏桥又喊“哥”。表哥又“哎”地一声。两个人慢慢地走到山底下。表哥说:“桥,回家吧。”苏桥说:“好。”看着表哥的身子上了山坡,再上再上就隐进山影里不见了。苏桥抱着苏拾又哭了。
有人上门给苏桥提亲。苏桥提出的条件却把人吓跑了,苏桥说:“嫁可以,必须带着苏拾。”苏拾是个傻子,那么大的一个人了,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后背上有个大瘤子,烂桃子一样裂着口,流着脓水并且散发着恶臭。这样的孩子,谁肯接受呀。妈妈说:“桥,你放心地嫁吧。我会对拾好。”苏桥说:“不。”
也有不嫌弃苏拾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大苏桥十几岁的老光棍就是瞎了一只眼或是瘸了一条腿的残疾人,这样的人,苏桥还不想嫁呢。于是苏桥的婚事就耽搁下来。同龄的姑娘都做了新娘,生了宝宝的时候,苏桥还守着苏拾在屋子里绣花。只是,只是苏桥的脸色不再水灵红润,苏桥的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
风言风语就在村子里传开了。有人说苏拾根本不是苏桥拾来的,苏拾是苏桥自己生的。她不是在村外读过书吗?她不是住过校吗?她那不是读书,不是住校,是跟男人好了,偷偷生孩子去了。有人看苏桥的眼光就变了。
苏拾是在春天死的。医生说苏拾活不到七岁,但是苏拾在苏桥家整整活了九年。这个沉默的,没说过一句话,没走过一步路的小人终于结束了煎熬,快快乐乐地走了。村里人是不兴埋孩子的,死去的孩子都要用毯子包了放到河沟里等待野狗吃掉,村里人说:如果野狗不吃,这个孩子就不会重新投胎做人。
苏桥与妈妈也抱着苏拾来到河边。苏桥说:“我要埋了苏拾。我不让野狗咬她、撕她,拖着她的内脏到处跑,我要埋了她。”苏拾就埋在苏桥遇到年轻军人的地方。在那里,垒起一个小小的坟堆。苏桥站在坟堆前,眼前就浮现出汪汪的绿,那个年轻的军人站在她面前说:“给你。等着我。”苏桥叹了口气,苏桥的眼睛里没有泪了,她说:“现在不用等了。”
又有人上门提亲。苏桥没有了任何附加条件,一心一意挑一个可心的男人过日子,这个眼睛太小,不好,这个个子矮不好,这个一看脾气不好,也不好。妈妈都不耐烦了,妈妈说:“桥呀,你以为你还年轻呀,桥呀,你以为你是仙女吗,差不多就行了吧。”
最后苏桥挑了一个现役军人,相亲那天,军人穿着碧绿的军装,像棵挺拔的杨树站在苏桥的面前。只一眼,苏桥就喜欢上了。苏桥说:“嗯,就是他了。”
结婚前一天,苏桥独自爬上村东的那座山。她坐在那块大青石上看着山下的村庄,明天她就要离开这里了,她要到另一个村子里生活,那里有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那里有一大些人,这些人,因为那个心爱的男人全部成了她的亲人。心爱的男人,苏桥的面前浮现出那个碧绿的影子,苏桥的心醉了。
苏桥要去看苏拾,她要跟苏拾说她要嫁人了,苏拾要有姐夫了。她在山上慢慢走着,看到姑姑家村口的那头石牛了,看到石牛旁边那棵乌黑、弯曲的老柳树了,然后她就看到一个绿点慢慢地走过来。是的,是一个绿点,慢慢地,慢慢地,绿点近了,近得要与苏桥擦肩而过了。
苏桥呆住了,是那个男人,那个穿绿军装的年轻的将苏拾递到她手里的男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呀?他是从天上,从月亮上,从星星上,从空气里冒出来的吗?他还穿着绿军装的,是的,绿军装,可是一条裤腿是挽起来的,并且,他的胳膊下架着一支拐杖。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看着苏桥笑了,仿佛他们已经很熟悉,仿佛他们天天在一起说话,仿佛他们天天在一起生活,男人的笑不再羞怯、不再拘谨,他看着苏桥的眼睛,他说:“嗨。孩子……”
是呀,孩子。苏桥带着他来到苏拾的坟旁。那里已经长满青青绿草,绿草在阳光的照耀下欢快地舞动着。苏桥坐了下来,她坐到坟旁的绿草地上,她的手放在苏拾的坟上,她说:“孩子在这里。”
穿绿军装的年轻男子笑了。
苏桥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