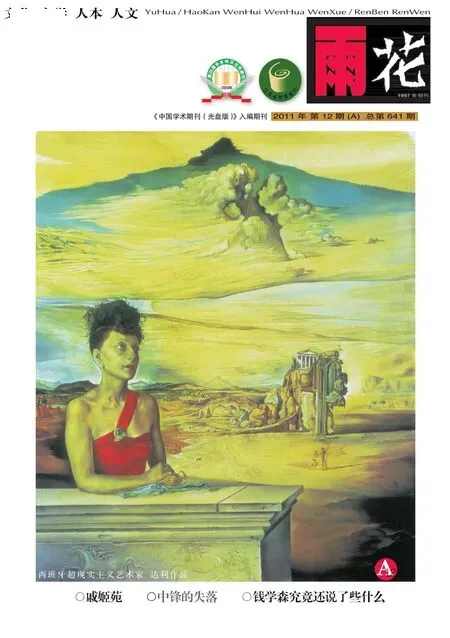小 莫
● 庄晓明
小莫又回到了当初的老样子,憔悴得眼睛里的神一点都没有了,而更令她吃惊的是谭宝,原本150多斤的矮胖子,陡然间瘦得不到90斤,样子简直不能看。
小莫直到去年退休,公司上下都仍叫她小莫。她的身体单薄得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走,脸色总那么憔悴着,她在公司的十八年间,年龄就似乎一直停留在这个“憔悴”上,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我没到父亲的公司前,“小莫”这个名字就印记在脑海了,父亲与手下的人曾担忧地谈到她,说她的神经可能有些问题,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半天,任谁也叫不应。记得那一年,离春节没几天了,父亲从公司回来,沮丧地对我母亲说,小莫又犯毛病了,而公司已放假,叫我母亲有空去看一下。小莫那几天失神得厉害,每天跑到离公司不远的镇上车站转悠,一转就是半天,说是等她的男人回来。春节前,路上人多车多,单薄的小莫万一给撞着了怎么办。小莫的男人叫谭宝,给一家公司在外面跑业务,跑了三年,没有一分钱回来,谁知这次连人也回不来了,他欠了北京一家宾馆三千多元食宿费,被扣住不放。亲友们没一人出手相助,他们早已厌恶透了这个大话连篇、借钱不还的谭宝。小莫一人带着五岁的儿子,一急之下,两眼失了神,每日恍惚着到车站转圈子。
小莫是我父亲在环保局的一位老同学的妻妹,介绍到我父亲这儿来上班,实际上就是托我父亲照顾的。小莫当初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不惜与姐姐翻脸,嫁给了甜言蜜语的混混谭宝,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儿子后,生活更是一团糟,两口子经常发生争吵,小莫的神经也就在这愈来愈频繁的争吵中变异下去。然而,谭宝出远门后,小莫又一人坐在家里发呆,恍惚度日。她的姐夫实在不忍,把她托付给已办了多年企业的我父亲。小莫好歹是个初中毕业生,便让她保管库房,登记材料。公司清理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的房间,母子俩终于有了个安定的地方,至于谭宝,就让他在外面继续混自己。
我母亲叹了一口气:“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吧!”从家里拿了三千元,这笔当时不小的数目,把谭宝从北京赎了回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父亲的公司做副总经理时,小莫的精神状况已有所好转,只是仍经常走神,要放大声音叫一下,她才从梦里惊醒似地“哎”一声。小莫的办公桌放在财务室,桌上堆着材料账本,她干得很细心,没出过我担心的什么大错。但她的动作太慢了,别人一个小时的活,她要三个小时,叫她到库房取东西,往往半天不见回来,待我心急火燎地冲到库房,她还在那儿作沉思状地点数东西。
然而,小莫做饭菜的速度可不慢,大概是被上学的儿子逼出来的。因此,若是公司来客人,我母亲做饭菜招待,都要叫上小莫打下手,我母亲的厨艺,比小镇的饭店好得多。有时,终日鬼混的谭宝也会闻讯过来帮忙,做几个菜。别看他平时“牛皮桶”一个,但在美食上还真有几分心得,几个拿手菜的受欢迎程度,不比我母亲的差。开宴时,谭宝自然地入席,他又矮又胖,光溜溜的大脑门,稀疏的头发上了油,向后服帖着,这一切配上西装领带,倒也令人看不出深浅。
“上个月,我在北京时,曾在赵部长家里掌勺,”谭宝指着桌上的一盘菜,惬意地呷了一口酒,“就做的这道菜。赵部长尝了一口,立即伸出大拇指。”谭宝的出口成谎,连自己都不知道似的自然。于是,众人纷纷伸出筷子。
“小莫,这道菜刀工有问题,应再切细一些!”谭宝时而突然把头扭向厨房,作一种大师教训状。令人称奇的是,谭宝讲话的嘴巴与给嘴巴输送的筷子,同样的敏捷,且互不干扰。
宴席进行到高潮时,更少不了谭宝的“献宝”,比如,他会突然向大家吹嘘自己有一种花粉,洒到碗里后,能使面条根根直立,怎么也打不倒。有人认真地说,也想得到一盒,谭宝一仰脖子:“哈哈!下午我到壮阳春给你买两盒。”酒宴一片欢笑。
“嚼蛆!”小莫从厨房里骂出一句。
众人酒足饭饱后,谭宝立马抱拳离席,奔赴他的麻将桌。一直在厨房忙碌的我母亲和小莫,这才上桌,她们照例也要喝两杯,小莫酒量不错。
一次,乘着小莫几杯酒下肚,我开玩笑说:“嫁给谭宝后悔吗?”
小莫脸上黯然了一下,马上又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什么好后悔的!”她继续喝着酒,脸上突然现出一片迷幻的红晕,“我们中学同班时,他可好哪!嘴巴比谁都甜。”
小莫与谭宝的吵架,好几次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他们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吵闹声渐渐稀疏了,双方似乎都认命了。
小莫的儿子小宝,是跌跌爬爬地熬到初中毕业的,他的成绩一直很糟。小莫把这个儿子惯得要命,母子一直睡一张床,谭宝也无可奈何。有意思的是,小莫又瘦又小,谭宝又矮又胖,却偏偏出了个一米八的大块头儿子,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谭宝怀疑这个儿子的真实身份,但在小莫近乎疯狂的愤怒下,最终不了了之。小宝块头很大,却有些像当地土语中的“大木瓜”,对世界对生活似乎没有一点感觉,只知终日沉迷在电子游戏厅,没有钱了,就和他父亲一样,叫要债人到小莫那儿去。两三年下来,公司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小莫赶快给小宝找个事做做,否则就要像他父亲一样废了。小莫想了一下,也是,虽说住在公司水电不要钱,但父子俩终日这样鬼混,靠自己那一点微薄的收入,将来怎么办。小莫虽穷但很自尊,为了儿子终于放下撑着的面子,与久已疏远的家人们亲戚们联系,请他们帮小宝找个工作。其实,家人们早已淡忘了由她当初固执的婚姻引起的不快,只是小莫自己始终没有除掉心理障碍。小宝很快有了一个工作,在上海近郊的一家合资企业。
谁知小宝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居然在开简单的冲床时,把左手指从根部被齐刷刷地切去了四个。
小宝住院治疗的钱,上海那家企业出了,但接假肢的钱及赔偿费,却不愿承担,理由是小宝还没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这与小莫提出的二十万元,有天壤之别。小莫与谭宝抱了床草席,每天睡在那个企业的大门口。那个挂了合资牌子的企业其实很小,只投了几万美元的台湾老板大概也是个来大陆赌一把的小人物,没见过这阵势,干脆躲回台湾去了,留下大陆方面的副经理处理这一棘手事件。这位副经理翻阅有关资料时,忽然发现小宝还未满十八周岁,他如获至宝,冲到躺在大门口的小莫和谭宝面前,耍起上海人的派头与脾气,威胁要向法院控告小莫两口子,因为他们把未成年的童工送到上海,违反了国家法律。
小莫一时不知深浅,上海人生地疏,就逼谭宝去找他在上海的久未联系的大哥。谭宝的父亲原在上海,文革期间下放到扬州乡村,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上海,在上海有一处三十多平方的老房子。老谭在扬州期间丧偶,谭宝的大哥便以老头子身体不好为由,乖巧地随着住了进去。老谭去世后,小莫和谭宝过来要分遗产,嫂子是个精明又厉害的上海人,拍着巴掌:“老头子看病护理的时候,你们哪块去哪?这破房子,还不够给老头子看病送终的钱!”小莫哪里吵得过。谭宝的大哥手里捏了两万元,摆出不要声张的神秘样子递给小莫,小莫甩手不要,又递给谭宝,谭宝接了过去。别看谭宝是个混球,骨子里的憨,有时也叫人叹息。自尊的小莫转身就走,还抛下一句:“这一辈子也不进你这个烂房子!”
听了谭宝和小莫的诉说,谭宝的大哥皱了一下眉头,说:“侄子的忙,我肯定是要帮的。”他与谭宝一般矮胖,但戴了一副金丝眼镜,颇有老上海滩金融家的派头。其实,他也与谭宝一样,没有固定工作,是个社会上掮客的角色,好在上海这摊位好,总能混到想要的钞票。第二天,他领来一位“戴教官”,称是他的哥们,在某武警学校任教,已帮不少朋友打赢过官司。戴教官听了小莫的哭诉,拍拍小莫的肩:“这个官司赢定了!”甚至商量到赢钱后的提成。
从此,小莫每两个星期,就往上海跑一趟,衣服也穿得愈来愈漂亮,后来还买了件时髦的大红套裙。公司的人忍不住开玩笑:“小莫又要相亲了!”她略有些羞涩地一笑,也不辩解,提上她的金利来小包就走了。小莫四十多岁,但瘦小的身材很适合穿衣服,憔悴的瓜子脸施上妆,倒也自有其风韵。这次,小莫没要谭宝去,让他回到麻将桌上,自己一个人来回地奔波,似乎忙得很高兴。眨眼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戴教官那儿还没有什么进展的消息,我都觉得有些疑惑了。乘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把小莫带上,想见一见戴教官。上车前,小莫用手机与戴教官通了电话,然后高兴地告诉我,戴教官要请我们吃晚饭。到上海后,我们在入住的宾馆等着戴教官,到了约定时间,戴教官没有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才打来电话,说是被一个案子拖住了,让我们先吃晚饭,他来结账。晚八点后,戴教官来了,并没有穿警服,一身军黄夹克,人长得干净端正,油着分头,但机敏的眼睛里总有几分色眯眯的味道。打过招呼后,他没有提晚饭结账的事,也显然不愿与我多聊,而是扳过小莫的肩膀:“我还有一些情况要问你。”然后进了小莫的房间,关上门。
一直谈到晚上快十二点,戴教官才告辞。我问小莫官司进展如何,小莫略带疲惫地说:“戴教官说正在找一个重要人物帮忙,要把前期工作做扎实。”
小宝是在三月份被断掉手指的,到了寒风呼啸的十二月,戴教官还没有把上诉送到法院。我对小莫说戴教官可能靠不住,小莫仍是不信。她一上班,就窝在办公桌前,一针一针地织着一件毛衣,是给戴教官的。考虑到路费的消耗,小莫上海去得少了,但更频繁地给戴教官写起信。我提醒她,与戴教官交往时留点心眼。
十二月底的时候,小莫衣着突然恢复了朴素,脸上也不再施妆,露出往日的憔悴。我们问起戴教官那儿的进展,她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憔悴里却分明隐着几分忧伤与愤怒。我们大概猜到了一些,但也不好深问。
过了春节,小莫向公司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一个人到上海去了。我劝她把谭宝带上,她有点不屑地说:“带他有什么用,多个吃饭的!”确实也是,别看谭宝像是个在外面混江湖的人,到了该正经的场合,他反而嗫嚅起来。小莫找到上海那个企业所在区的法院,坐在大门口,摊开一张大字报,上面已事先用毛笔写好了缘由。瑟瑟寒风中,小莫坐了三天,法院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大姐把她领进办公室。听了小莫的哭诉后,她为小莫联系了一位愿为贫困阶层打官司的律师,收费极低。律师很快把诉状递到当地法院,要求赔偿十五万。那边公司闻讯着了急,便也请了律师,同时到法院找人拉关系。官司拖了五个月之后,判决下来,赔偿五万。小莫坚决不答应,要求继续打官司,律师有些犹豫,小莫一下子跪了下来:“如果官司这样了结,我也不想活了。”律师便又把诉状递到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刚好那段时间,中央对底层农民工的生存非常关注,判决出乎意料地快且顺利:赔偿小莫人民币十二万八千元(含接假肢费),先付八万,余款两年内结清。
小莫的运气似乎从此有了好转,赢得官司的这一年,她又轻易地得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商品房。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公司砌办公大楼的时候,铝合金门窗业务是本镇的一位叫郭庆厚的老板做的。这位醒目着八字步的老板有个习惯,就是每谈成一笔业务或挣到一笔钱,都要浑身上下抖动,尤其抖动着那八字得很厉害的右脚,小镇上炫游一圈。郭老板是我父亲的牌友,几乎每天都要来打上几局。这一天,他忽然抖得比往日哪一次都厉害地来找我父亲,说是在武汉接了一笔五百万的铝合金门窗工程,要我父亲帮他银行贷些钱。我父亲让他小心些,他说工程是本镇的一个穿开裆裤时就要好的朋友介绍的,他已看了工地,也去过那个转包工程的公司,在武汉一个豪华的八层楼办公,办公室二十多个男女,统一黑色西服,每人面前一台电脑。但对方有要求,签订合同时,要付十五万元前期费用(含各种资料费)。郭老板在镇上有两套房子,一套一百二十平方,一套六十平方,我父亲便让他以那一套大房子做抵押,找银行的朋友贷了二十万。郭老板去了半年后,忽然又回来到处借钱,以银行的四倍利息,说已定好合同,预付款很快就要到账,但工程已开工,急需一点启动资金。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说公司已交给儿子,手头没钱,郭老板八字脚一拐,扒开窗户,说借不到钱就从这儿跳下楼。我父亲被缠得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借你五万,你打个字条,年底不还,就拿你的六十平方房子抵债。”
又过了两月,快过春节的时候,郭老板回来了,继续宣扬武汉形势大好。其实他是放心不下他那又老又瞎的母亲,他是个孝子。我父亲把他叫到办公室,他扭着八字步,挺着腰,摆出一付发了财的大老板的样子。我父亲说时间到了,叫他还钱。他不屑地回道,就那点钱,担心什么,我也给你四倍的利息。我父亲走了一辈子江湖,哪里吃这一套,年轻时是体育健将的他一把揪住郭老板的衣襟,把他拧了起来,威胁说要把武汉的真相告诉所有的人。原来我父亲不久前通过武汉的朋友得知,郭老板所谓的大工程其实是上了别人的套子,现在他又下套子骗下家,弥补自己的亏损,并以此作为自己新的事业。郭老板浑身发抖,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父亲咆哮道,那就把房子交出来。郭老板乖乖地做了手续,交出那间六十平方房子的钥匙。而刚好这时,小莫打官司所得的钱回来了,我父亲就让她用其中的五万,得了这市价至少九万的房子。郭老板过了春节走后,就杳无音讯,不久,他的大套房子也被银行封了,他的老婆与老瞎的妈妈便搬到乡下的老房子去了。他的老瞎的妈妈曾拄着拐棍,从乡下赶到我这儿打听她的“厚儿”的下落,她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她的“厚儿”曾经常到这儿来打牌。她那孤独的颤巍巍的样子,实在令人不忍。
小莫搬进自己的房子后,把余钱存进银行,她没有马上给小宝接假肢,而是想寻到一个价格更便宜的医院。家人和亲戚们,这时也感到要给小莫某种补偿,便轮流着把手指残疾的小宝接过去住一段时间。然而,小宝似乎还没有从他的世界中醒过来,除了窝在家里看武侠电视剧,就是要钱出去打电子游戏。一圈下来,家人和亲戚们都有些失望和厌倦了,没有了第二轮的邀请。小宝这个大个子,又回来和小莫睡在一张床上,白天时间,则随他爸爸谭宝出去观摩牌局。大木瓜一般的小宝,偏偏对麻将有悟,一段时间后,就可以站在谭宝的“围城”后,用尚健全的右手指指点点。后来,父子俩更发展到用别人所不知的暗号,悄悄做一些小动作,达到一种“稳赢”的局面。
小莫大概是疲惫了,对之不闻不问了一段时间,在我母亲和我的一再警醒下,才抖擞起精神,再次找她的亲友们帮忙。但亲友们对小宝已没有信心,都打着哈哈,最终还是在她的环保局的姐夫帮助下,在J市的一家宾馆谋得了门侍的差事,为出入宾馆大门的客人们拉门关门。小宝大个子,穿着宾馆制服,双手白手套,倒也像个样子。然后,小莫又托人给小宝找对象,心想或许成了家,小宝会成熟起来。开始谈了几个,不是小莫嫌人家不合意,就是人家嫌小宝手残。后来,媒人终于介绍了一个双方父母都有意的,对象是本镇一家饭店老板的独生女儿,与小宝一般大,都已二十四的年龄,媒人说她的惟一缺点就是有时有点犯傻,复杂一点的算术做不出来。这倒没什么,小莫一想到困窘的家境有可能因此得到改变,那几天上班时特别开心,主动与办公室的人找这方面的话题。到了双方父母带儿女见面的那天,小莫把小宝好好打扮了一下,穿上刚干洗的宾馆制服,在媒人的引领下,踏进对方在镇中心地段的一幢三层小楼。刚见面,双方都感觉不错,小宝站着,又高又大;姑娘坐在沙发上,不说话,还有些淑女的样子。然而,当这边两家父母交谈到一定氛围时,那边两个小的却为电视机遥控器争夺了起来,一个要看武侠,一个要看言情,争夺中,小宝的左手套被扯去,露出残缺。姑娘突然两眼放光,好奇地拉住小宝的双手:“太好玩了!我来数一数,总共有多少指头。一,二,三,不,重来,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转过头,“爸爸,我数得对不对?”她爸爸尴尬地点了点头。姑娘一下子雀跃起来:“哦!我数对了!”双方家长的脸上霎时都蒙了一层阴霾。
小莫再没提这件相亲的事,大概双方都冷处理掉了。而小宝因为贪玩游戏,不久又把宾馆门侍的工作丢了。沮丧的小莫找我母亲商量:“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家以后怎么办?”其时,我母亲已从油田单位退休,到我的公司负责财务,讲话是有分量的。我母亲说:“该下狠心了,小宝与谭宝再这样下去,家就毁了。”我父亲有个朋友在北京做生意,为人严谨,就请他把小宝领了去,报酬暂时无所谓。至于谭宝,就让他到我公司施工队,一有工程,就跟出去施工,这样至少减少了他上牌桌的机会。
谁知道是物极必反,还是俗话说的树挪死,人挪活,小宝到了北京一段时间后,父亲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小宝还是不错的,安排的事情都能做掉。而谭宝这个混混到了公司施工队,还真有了卖苦力的样子,人虽矮胖,两只膀子的力气却不小,一手一桶二十五公斤的漆,提起来直奔,见我在场,奔得更欢。至于业余时间的牛皮,他自吹他的,我只当作看戏。小莫居然胖了一些,憔悴的脸上也添了些红晕。因为她的姐夫渐渐成了环保局有实权的人,环保系统的人到公司来检查工作,我就把小莫拉上陪酒。小莫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我们经理是个读书人,有点书呆子,你们可要照顾啊。”对方自然点头称是,而我则有点哭笑不得。到了收费时,小莫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一千五。”小莫便嚷道:“哪儿有这么多!减五百,减五百。”对方无奈地一笑,就按照她说的写了收据。
转眼到了2003年,北京传来消息,小宝谈了个女朋友,东北人,据说关系已不是一般的好。小莫只看了照片,不放心,又请假专程去了一趟北京。第二年六月,小宝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延吉创天下,做起一种生意,就是收集当地的人参菌菇,制干后卖到韩国。不知是南方人的天生善于经商,还是小宝从他父亲的牌桌上悟得了某种经验,生意居然做得很好。不久,谭宝向我请假,说是上海的哥哥开刀要照顾,其实我心知肚明,他是也想到东北去试试,他一去就没回来。巧的是,小莫这一年五十岁,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她自己也提出了要求。本地乡镇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员工退休时,按在厂里工作的年数,一年补一个月的工资。到九月份,小莫刚好在公司干了十八年,我母亲特意给她多补了两个月,凑个整数,叫她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小莫数着钱,突然抽泣起来,呜呜咽咽地不知对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母亲也陪着掉了泪。
小莫自然也去了东北,帮一家子做饭。两个月后,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在那边很好,那儿的冬天也不是想象中的冷,家里有暖气,一进门就热得要脱衣服。最后说春节回来看大家。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附补:
就在我颇有些慰藉意味地给这篇小说收尾后的第三个月,小莫一家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并没有捱到要给大家分带礼物的春节。据见到小莫一家的我母亲说,小莫又回到了当初的老样子,憔悴得眼睛里的神一点都没有了,而更令她吃惊的是谭宝,原本150多斤的矮胖子,陡然间瘦得不到90斤,样子简直不能看。据街坊间的风传,他们一家可能是在延吉坠入了传销团伙。倒是小莫的宝贝儿子小宝似乎前后并没有变化,仍是高高大大的“木瓜”样,一回来就钻进电脑游戏房。随后的日子,我忽然有些害怕见小莫一家人了,上街时,总要不自觉地往小莫家住的那个巷子里警惕地扫上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