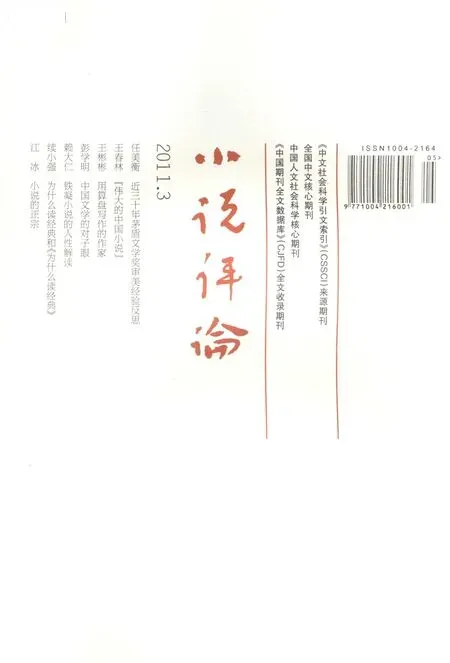论《古炉》的叙事艺术
李震 翟传鹏
论《古炉》的叙事艺术
李震 翟传鹏
从《秦腔》到《古炉》,贾平凹一直在延续着他博大而又细密的历史叙事。无论是被称为“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的《秦腔》,还是讲述文革记忆的《古炉》,贾平凹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与其他当代作家迥异的气象。它就像一条看似静止的大河,用自己的沉默与平静,掩盖着体内每一个水滴的喧哗与骚动。这大河的静默与雄浑,应是那已然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历史,而这无数奔腾的水滴,便组成了作为一种文学的历史叙事。
一、“文革”历史:民间意识与审美关照
《古炉》被作者自己认为是他“迄今为止表现小说民族化最完美、最全面、最见功力和深度的文本。”①作为贾平凹第一次对“文革”历史的集中讲述,《古炉》的所谓“小说民族化”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其迥异于同时代作家的历史叙事。
“文革”叙事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一贯的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分别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一传统在叙事模式和情感倾向上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河流。对于相当数量的一批作家而言,描写生活的苦难、暴露“文革”的黑暗、反思“文革”的教训、凭吊流逝的青春,是他们表达的主要内容。另外一些作家则摆脱了个人情绪上的偏激,以较为冷静的目光审视那段历史,将“文革”记忆转化成一种审美资源,将理想主义色彩浸于其中。贾平凹探索的是这两条河流外的第三条河流。
贾平凹说他创作《古炉》的动机之一是:“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②《古炉》确实有异于先前任何同类题材作品,它既不同于那种义愤填膺式的尖锐批判,又不同于那种理想主义的集中展现,它以一种民间的立场书写着传奇式的历史,既非剑拔弩张亦非沉郁顿挫,而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娓娓道来,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古炉》集中描绘了“文革”初期一个叫古炉的偏僻贫苦的小山村的生活斗争状况。“古炉”这一看似朴拙的命名实乃“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按贾平凹自己的说法:“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③以古炉来喻中国,有多层涵义:其一,古炉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古炉的“文革”是中国“文革”的一个缩影,沧海一粟,窥豹一斑,其间深藏着空间的影子;其二,古炉之“古”与中国之“古”相得益彰,而古炉从以往能烧出精致的青花瓷到今天只能烧出笨拙的器皿之变,隐喻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古炉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其间深藏着时间的影子;韦勒克说:“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④文学书写不是历史书写,以小见大往往能洞见真知。贾平凹对于农村生活无疑是十分熟悉的,对于亲历的“文革”,无疑是刻骨铭心的,这两者促成了其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一叙事中,民间的立场与价值观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了其中。
作品以冬去春来又一春六章来完成时间建构,基于这浓缩的时空之上的,是文本充足而丰腴的内容。贾平凹将一个农村微缩社会的家常里短、矛盾纠纷,将普通黎民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精神世界的空虚和“精神奴役创伤”,以潺潺细流般的笔触描刻而出,绪密思清,不刻意做主观批评,让人和事物呈现本原状态。文本对乡村的描绘是成碎片化的,小说前三分之一的篇章虽略露“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火药味并不明显,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乡土日常生活的描摹上。这种描摹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民间生命、生存的有序、自然状态。即便是在“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进古炉村之后,这样碎片化的描摹依然存在,并不急不缓地向前发展着,这直接冲淡了“革命斗争”的火药味,消解了革命的严肃性与宏大叙事。因而,碎片化民间生活的描摹实为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零散化、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题中之义,诚如詹明信所言:“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的表面感,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⑤后现代主义的能指与所指链是断裂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不屑于分析、是拒绝阐释的,然而,在碎片化历史建构的背后,《古炉》并不缺乏分析与阐释的空间。这种碎片化叙事,在文化血脉上,更贴近《水浒》、《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而非西方叙事模式。
夹杂于碎片化场景描摹之中的,是作者对“文革”的记忆。贾平凹说:“古炉村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都是我的记忆”⑥,“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⑦。贾平凹对“文革”有惨痛的记忆:父亲受到批斗,自己也沦落为“可教育子女”。这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小说主人公狗尿苔身上有着贾的影子。众人的歧视与自身的自卑感,在社会和群体中边缘化的处境,弱小个体在革命风暴中的战栗不安与瑟瑟发抖,狗尿苔的这些情感体验是贾平凹“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在作者心中,经岁月淘去污垢与往事不堪回首之后,“文革”成了民间记忆与传说,留下了痛楚与纯真交织的存在,欲罢不能、欲说还休。这种观念浸润下的文本呈现出与传统“文革”叙事截然不同的面貌。其一,碎片化的历史消解了“文革”宏大叙事,革命所具有的崇高性与严肃性被家族间斗争所取代,历史呈现出游戏性、隐私性、消费性的一面。其二,多具象征性的人物所秉持的历史观念不一,多元民间价值观念使历史叙述充斥着不同的声响,善人“相生相克”、“因果报应”观念中的历史与狗尿苔一知半解儿童视角中的历史截然不同,历史的面目变得斑驳陆离、模糊不清。其三,作者多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态度来结构故事,虽借善人之口不断对社会、历史、人生进行着解读,但这种思索是形而上的,文本本身并无太多感情宣泄。兼之,作者以一种多元民间立场、民间情感来思考这些问题,而非知识分子话语殚精竭虑的思索,作者本身的历史观念并不确定,充满了多种阐发的可能性。最后,作者将“文革”的部分记忆内化成审美资源,即便是古炉村武斗的场景,读来虽令人有痛楚之感,但绝不像阎连科笔下“耙耧山”、“受活庄”中的那样惨烈、暴虐。文本呈现出较多的诗意,而非血淋淋的现实。
二、轻逸:从死亡王国向诗意王国的飞升
陕西文学推崇厚重,陕西文化的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使生长于斯的作家们文风喜沉郁顿挫,感情好慷慨悲歌,叙事则以深沉阔大的文本蕴含厚积的情感,每每欲喷薄而出。贾平凹则是个例外,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沉郁顿挫,其作品在充满人文思索之余,“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曹植《前录自序》),充溢着灵动之气,充溢着一种超尘脱俗的力量。《古炉》是作家以较为平和的心态静,观万象、“以实写虚”的作品,“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烟水迷离,闲和严静,文采斐然,呈轻逸之姿。
“轻逸”(Lightness)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卡尔维诺认为:“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⑧。人类的生活过于沉重,而“轻逸”是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必然需求与必要途径:“那些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东西,诸如喧闹、寻衅、夹马刺、马蹄嗒嗒,等等,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死亡的王国就像一个堆放破旧汽车的垃圾场。”⑨而文学所要做的就是像童话中的情节那样,能够从这样一个“死亡的王国”“飞向另一个世界”⑩。这种飞跃性(轻逸性)在卡尔维诺看来是未来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必备的品质之一。
《古炉》以狗尿苔的儿童视角来结构故事,在这种限制性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折射后的镜像世界,呈现为一种异样状态。通过狗尿苔的眼睛,我们看到古炉的一切似乎都是混沌的,包蕴着未知与不确定性,充满着新奇感。
在天布家门口的照壁前,那蓬牵牛花叶子已经脱落,狗尿苔遗憾着买瓷货的人看不到牵牛花开的景象呀:那所有的藤蔓上都生触须,上百个触须像上百条细蛇,全伸着头往上长,竟然能从那些竹棍里钻一个格儿往上长,钻一个格儿往上长,而所有的花都张着喇叭口,看着就能听见它们在吹吹打打地热闹。⑪(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狗尿苔的眼中,牵牛花这么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都充满着新鲜感。“遗憾”二字点明了小主人公对牵牛花的珍视;“呀”字使得遗憾之情油然而生;触须和细蛇的类比,惟妙惟肖,“伸着头往上长”写得意兴盎然;“竟然”一词道出了狗尿苔对牵牛花“钻”的能力的惊叹,这是对顽强生命力的礼赞;“张着喇叭口”,“听见它们在吹吹打打地热闹”,将视听感觉融为一体,体物细腻、意态横生。这正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对有微妙而不易察觉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⑫。孩子眼中的牵牛花无疑是美的,但这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惊喜、新奇的心理感受。这段描写,似透非透,以“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⑬,呈现出一种“古镜照神”般的轻灵之感。
历经风雨,洗尽铅华呈素姿。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它拥有着许许多多像狗尿苔、像牵牛花一样顽强生长着的生命。“文革”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破坏了古炉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存环境,但人们向上、向善、向美发展的动力和信心不会消退。正如文本最后一段所说的:“狗尿苔突然有个感觉,感觉山门下,碾盘和石磨那儿的牵牛花应该是开了。”⑭
这几处对牵牛花的描刻,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现绚丽,用语平常,描绘却活灵活现。牵牛花这不登大雅之堂之物,在贾平凹笔下具有了生命的质感与痛感,具有了向上飞升的翅膀和力量。这是一种轻逸的写作,也是贾平凹对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小说传统的又一次延伸。沉重的历史、艰难的人生、惨痛的记忆都变成诗意的审美,“文革”的死亡王国变成诗意的王国,细细把味,久而弥淳。
作品对于云和风的描写也是如此。全文有51处对云的集中描绘,对风的描写更多。这成为推动情节发展、映衬人物心理、反映社会环境的重要动力。试举几例:
这一天,刮起了风,刮风的时候云总是轻狂,跟着风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⑮
是天上的云影落在碗里,一吹,汤皱了云也皱了。⑯
云一片一片往山神庙上落,像是丢手帕。⑰
抬头才看见南山岭上满是些白云,入冬后从未见过这么厚的白云,而且从山顶上像瀑布一样往下流。○18
我们惊异于作者对文字的把握能力。云的飘忽不定使我们捕捉起来相当困难。贾平凹对云的描摹,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自成一体的,他有固有的手法与丰富的语料库。对云的这种描摹,清新、自然、恬淡,充满着情趣与鲜活生命力,充满着微风拂面般的质感,充满着大音希声般的美感与诗意,如同云自身一样,充满着飞翔的力量。
这种轻逸的语言俯拾皆是:
回到小木屋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傍晚,镇洞塔上落满了水鸟,河里的昂嗤鱼又在自呼其名,远处的村子,绿树之中,露出的瓦房顶,深苍色的,这一片是平着,那一片是斜着,参差错落,又乱中有秩。哎呀,家里的烟囱都在冒炊烟了,烟股子端端往上长,在榆树里,柳树里,槐树和椿树里像是又有了桦树,长过所有的树了,就弥漫开来,使整个村子又如云在裹住。○19
远村、绿树、瓦房、烟囱,由远及近,层次清晰,这分明是一幅充满乡土乡情的静谧的田园风景画。而炊烟的笼罩,又使这一画面充满混沌感,在隔与不隔中,无以言说的空灵感油然而生。画面中的“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20,这种“空”却非一般人所能及,它需要透穿宇宙的大视野与跳出三界的大境界。可以这样说,《古炉》时代的贾平凹,艺术造诣日趋完臻,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这段风景描摹的背后,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革命,重与轻、激情与空灵、庸实与高蹈、脚踏大地与随风而舞,描物叙事间的张力可见一斑。以如此大境界叙述历史,必定不会陷入就事论事的俗套,而是真正从生活的垃圾场飞升,飞向另一个诗意的王国。
三、神性写作:梵我合一与生死轮回
神秘书写是贾平凹的一贯传统。《废都》中牛月清母亲的“通神”,那头著名的牛所作的哲理性思索;《土门》中主人公的“尾巴”与飞檐走壁的本领;《高兴》中的锁骨菩萨等等,不一而论。贾平凹的写作资源更多的是来自商州这块神奇的土地,商洛地处关中、巴蜀、荆楚文化的交汇之处,巴楚一向是诗人辈出的地方,也是巫祝文化根深蒂固的地方,招魂、避邪、祈福等活动本就是巴楚文化的题中之义,贾平凹文本中的神秘性大抵源于此。
在作品的第23节,狗尿苔和霸槽的一段对话中,两人以动物为喻,以因果轮回说,臧否了古炉村里的各色人物,他们是这样来谈论狗尿苔的:
霸槽说:狗尿苔,那你就真是狗尿苔转上世的。狗尿苔说:我是老虎。霸槽说:屁,说是老鼠还行。狗尿苔说:我才不是老鼠。……霸槽说:你长成这个样子也实在不容易,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狗尿苔想了想,石头也好,守灯恐怕也是石头,但守灯是厕所里的石头吧。他说:那我是陨石!○21
这段描写值得好好体味。说狗尿苔是“狗尿苔”转世,源于二者的形似,狗尿苔的五短身材、草根性、边缘化位置和默默无闻,都使得他与房前屋后那矮矮的菌类植物极其相似。说狗尿苔是老鼠转世,源于二者的神似,作为斗争对象,狗尿苔像老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像老鼠一样只能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艰难生长,像老鼠一样不断被人拿来说事,成为被凌辱、被损害的对象。说狗尿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则更富有戏剧性,我们可以看作是贾平凹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在向《红楼梦》那样伟大的作品致敬。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备受歧视与伤害,狗尿苔幻想自己能变成一块石头:“他的身子紧缩后就慢慢地静静地伏了下来,伏在了路边的一个石头旁”○22,“身子越缩越小,谁也看不见他了。好像是过了一会儿,狗尿苔已经没知觉了,是一块石头了”○23。石头平凡、不为人注意,狗尿苔想变成石头,是一种趋利避害、从革命洪流与漩涡中逃逸的本能选择,这是表层意思。狗尿苔是领养的孩子,其身份一直是个谜,狗尿苔自己认为他是像来回一样从水中来的,而奶奶说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凡此种种,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大自然幻化的结果。因而,往更深处考虑,其想变成石头的愿望,是对自身命名的一种焦虑,是返回本原的一种冲动,是向母体子宫执着回归的一种努力。变成石头的愿望与“陨石”之说相呼应,在这种逻辑下,狗尿苔这块陨石(而非贾宝玉般的顽石)也就有了神性,有了与天地万物对话的逻辑起点。这种神性呈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与虫鱼鸟兽对话的权力;其二是形形色色富含象征隐喻色彩的梦;其三是灵敏的嗅觉及“怪味”。限于篇幅,我们只就第一方面做简单分析。
狗尿苔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能与他们自由的进行交流与对话,这是狗尿苔“怪”的一种表现。这种“怪”,成为文本中最生动、神秘和充满乐趣的部分,平添了文本的诗意与阅读快感。
这只苍蝇叼着米一高一低往前飞,站在石头上还有一只苍蝇在洗脸,说:呀,这么大的米!那只苍蝇就落在墙头瓦上,放下米,说:迷糊蒸米饭啦!石头上的苍蝇听了,嗡的一声往迷糊家飞去。○24
这段描写让人读来忍俊不禁。苍蝇竟能像人一样饮酒看花、征逐花草,描写可谓是画虎画骨。而作者写苍蝇的目的在于烘托写人的氛围,在于衬托狗尿苔和牛玲对于食物的渴望。这种描写暗含着众生平等的思想,人类并不比这些小动物高明到哪里去,都有相似的欲望与本能。这种叙事,反映了作家的某种宇宙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与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是共生共灭、共昌共荣的。这是一种万物有灵、梵我合一的宇宙观。小说高潮部分写白皮松的被砍伐:“秃子金把树砍了七个豁口,七个豁口都往外流水儿,颜色发红,还粘手,有一股子腥味。”○25这哪里是写树,分明是写人!古炉村本来就是一人神共栖、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地方,白皮松的消失,是古炉神性的消失,缺少了白皮松的古炉还是古炉吗?
倘若说狗尿苔是能直接与自然对话的人,那么蚕婆则是能通鬼神的人,小说中多次描述了蚕婆“立筷子”驱鬼的场景。蚕婆是弃儿狗尿苔的抚养者,在她身上积聚了一个伟大母亲所具有的种种美德。她富有爱心与同情心,在来回头脑不正常之时主动投以援手,在杏开声名狼藉之时给予其最需要的帮助;她以德报怨,对任何人都敞开博大的胸怀,即便是曾经斗争过她的人也不例外;她心灵手巧,朴素的生存智慧使她能比常人看得更远,利用手中的剪刀她能为白开水式的生活涂上一抹彩霞。她代表着一种至高的善和美。中国文学的“母亲”画廊因她又增添的一幅新的画卷,这是文学层面上的意义。从人类学意义上来说,博大的胸襟、包容一切的气度,使她成为大地母亲的化身,她就像我们脚下这块坚实的土地一样,虽历经磨难,饱经沧海,却依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呵护着生长于斯的性灵们。从神话学意义上来讲,诸种美好的情操使我们将其与女神自然地联系到一起。她的巧手能剪出惟妙惟肖的动物,且“一剪开了,又立即浸沉在了剪刀自如的走动中”,○26“似乎这手把握不了剪刀,是剪刀在指挥了手○27”,剪出的不仅是形象,更是灵魂,她就是关照着我们灵魂生长的女神。
我们提到贾平凹的神性书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人:善人。在小说中,善人是作者形而上思考的代言人,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诸多看法。善人在小说中的主要活动是说病,不同于今天社会上流行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行径,善人不是利用绿豆汤治病,而是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方法,从精神的解剖入手,以根治人们灵魂中的痼疾来解决生理上的问题。善人是“社教”中被迫还俗的和尚,应是佛家思想的代言人,但在他身上,有着诸种观念杂糅的迹象:
狗尿苔听到善人在说:你的性子是木克土,天天看别人不对,又不肯说,暗气暗憋,日久成病么。你要想病好,就得变化气质。要不化性,恐怕性命难保!……善人说:我常研究,怨人是苦海,越怨人心里越难过,以致不是生病就是招祸,不是苦海是什么?管人是地狱,管一分别人恨一分,管十分别人恨十分,不是地狱是什么?君子无德怨自修,小人有过怨他人,嘴里不怨心里怨,越怨心里越难过。○28
这是小说中出现的第一次“说病”,对象是“很高傲,和邻居们关系紧张,甚至连家人也处不和”“肚里长了一病块”的护院。细绎善人的说病词,“性子是木克土”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最早出自《尚书·洪范》,后被中医理论借鉴;“苦海”、“地狱”等是佛家概念;“君子无德怨自修”,德是儒家所推崇的,古人就有“君子进德修业”(《易·乾卦》)的观念;而“不管人”,“不怨人”,则暗合老庄的“无为”思想。善人的说病词中杂糅了诸种思想,这在文本中并非独例。应该说,善人的思想(这未尝不是作者的思想)是披着佛家的外衣,带着诸多民间思想的一个大杂烩。而相生相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因子。因果报应最明显的例证还是在白皮松的被砍伐上,作为古炉“风水”和标志的白皮松倒了,善人因此大病一场,并自焚圆寂。这棵树不止是一个地方的标志,更是一个族群的精神象征,也是善人的灵魂寄托所在(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拿白皮松和《高兴》中的锁骨菩萨做以对比,同是灵魂的归依所在,白皮松有一种羽化的轻逸感,而锁骨菩萨则不够饱满,缺乏这种飞升的力量)。白皮松消失后,古炉的武斗在外力的干预下迅速结束。“革命”的两派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领袖人物最终难逃法网,麻子黑等恶霸和守灯等道德败坏的人受到了理应的惩罚,砍伐白皮松的主谋更是被推上了断头台,故事在因果报应的大背景下戛然而止。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对于善人的描刻给人以“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的感觉,作者将太多的急于表达的想法集于善人一身,过多的语言诉说反使其性格不够鲜明,或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弊。
倘若说生死轮回的观念在善人那里只是一种理念上的说辞的话,那么对来回来说,她的经历则为这一观念做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同狗尿苔一样,来回的身世也是个谜。因州河发大水,来回被洪水从上游卷下,并被古炉村收留。这种描绘是对创世神话和大洪水传说的呼应,是原始先民的种族记忆在作家笔下的再现。在《古炉》中,来回不是一个主要人物,但充当了重要的行动元,许多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她有关联。更令人惊奇的是,来回如同其名字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老顺说:河里发水啦,来回坐着个麦草集子走了”○29。这就是本文所呈现给我们的生命观:生命就是来回,循环往复,无止无尽。这是历史循环论,是前现代社会的主流历史观与宇宙观,是为现代主义所摒弃、而为后现代主义所重新反思的观念。当我们联想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和“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红楼梦》)之时,贾平凹与前辈传统作家在精神上和宇宙观上的暗合也就呼之欲出了。
李 震 陕西师范大学
翟传鹏 陕西师范大学
注释:
①《贾平凹建议慢读〈古炉〉:纯看故事看情节没意思》,《京华时报》,2011年1月21日,A52版。
② ③ ⑥ ⑦ ⑭ ⑮ ⑯ ⑰ ○18 ○⑲㉑㉒㉓㉔㉕26○27○28○29贾 平 凹 ,《古炉》,人 民 文 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 ,第 603页,封底,第606页,第603页,第17页,第156页,第593-594页,第152页,第306页,第538页,第402页,第210页,第419页,第458页,第52页,第557页,第248页,第295页,第30页,第561页。
④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02页。
⑤詹明信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440页。
⑧⑫⑮○23卡尔维诺著,《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9页,第12页。
⑨⑩卡尔维诺著,《美国讲稿》,吕六同、张洁主编,萧天佑译,《卡尔维诺文集·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第344页,第340页。
⑬○2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5页,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