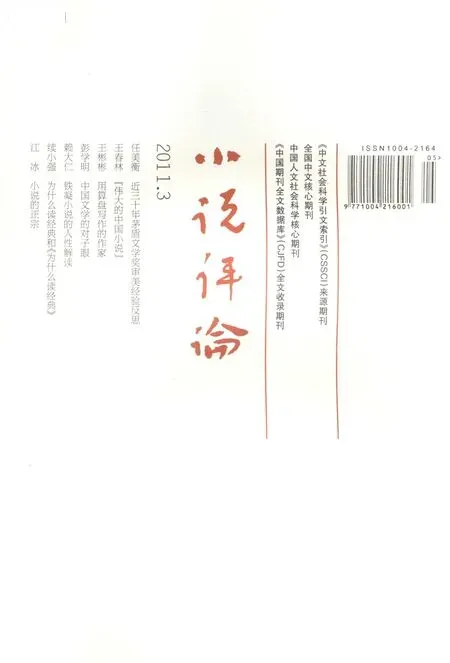论张悦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孔令环
论张悦然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孔令环
当代文坛上,80后作家无疑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创作群体。他们被诸多媒体精心“包装”后重磅推出,宛若演艺圈的明星一样,拥有自己广大的fans群,在市场上为自己赢得盆满钵溢的同时叩开文坛之门,一时成为文学评论界争议的焦点。其中,兼具“偶像派”和“实力派”两者之长的“忧伤玉女”张悦然作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是争议的中心人物,她擅长把成长的骄傲和忧伤、青春的美好和残酷、爱的追寻和失落用奇特的想象收罗进“玫瑰雕花的城堡”,邀读者一起去游历并沉迷,其另类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唯美的小资情调、优雅的语言风格以及诗一般的意境使得她的小说在市场与文坛之间左右逢源,好评如潮。但纵观其到目前为止出版的小说,从主题、人物到情节都有明显的模式化倾向,显示出原创力的不足,并必将严重影响她日后创作的突破性发展。同时这种模式化倾向也是80后作家创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试图以张悦然小说为典型进行剖析,以引起80后作家对这一现象的警觉。
一、主题的模式化
张悦然小说的主题主要有二:成长与爱。在这两大主题上,都存在明显的模式化倾向。
成长是张悦然小说的重要主题,正如莫言所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理极为相称的真实。”①成长是80后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母题,张悦然在此领域有不菲的表现,她以女性独特的敏感,从刚刚经历过的新鲜记忆中打捞同龄人从童年到青春期跌跌绊绊一路走来留下的印迹,特别关注物质生活相对优裕的80后一代精神上真实的痛苦匮乏状态,但由于生活圈子相对狭小、生活阅历较浅以及迎合青春文学时尚等综合因素,她的小说在成长主题上几乎一直延续着这样一种基本模式:本来天真无邪的主人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里主要指精神层面)中形成或多或少的自闭自恋倾向或其他心理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封闭在自我臆想的世界中,成长的向度有二:一是始终囿于其中,左冲右突仍无法突围,其极端表现是施虐或自虐甚至自杀;二是终于突围,走向美与善。成长的忧伤像吹不散的雾气一样,弥漫在她大多数小说中。
故事之初的主人公都像落入凡间的精灵,纯净无瑕,天真可爱。
主人公大多有一个灾难累积的过往,爱的缺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家庭大都粗鄙冰冷,毫无诗意,令人厌恶。
在痛苦和爱的缺失状态中成长的孩子大多有自闭自恋倾向,孤独、冷漠、忧伤,并且有明显的反常行为,如暴食症、虐待狂、受虐狂、畸恋等。《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暴饮暴食到即使胃部剧痛都难以停止的程度,其原因是想通过生理上的饕餮填补巨大的爱的空洞,她的严重的恋父情结也是因为渴望被爱所致。《红鞋》中的女孩亲眼目睹母亲的被杀,孤僻冷酷,以虐待他人和动物为乐,将邻居男孩牙齿全部拔掉,虐猫,拍摄各种阴森恐怖的画面。《小染》中的小染每天重复做的就是清早买水仙花,然后用剪刀剪断根茎,看着它死去。《誓鸟》中的春迟为了找寻爱的记忆,不惜自残身体,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每天做的就是从贝壳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过往。宵行为了帮助春迟,毫不在意自己妻儿的生死,甚至亲手虐杀被他妻子视为性命的香猫。……等等不一而论。
这些主人公成长的方向之一是囿于自闭的自我之中,拒绝成长,沉溺在游戏和童话之中,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有的则有极端行为,如施虐和自虐等。有的以自杀来反抗这个一无是处的世界,还有的以施虐或自虐为乐,构成“残酷青春”的另类风景。这种暴力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可以说是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
张悦然安排的另一个向度则是回归美与善,这种成长的推动力往往是爱。这也是她的小说最能温暖人心的地方。《桃花救赎》中的小蔚在卡其的爱中克服了性恐惧,恢复了爱的能力。《痣爱》中的女孩在母爱里抛弃了自卑和忧伤,一夜长大。
爱是张悦然小说的另一重要主题。以爱情和友情为主,爱与痛苦常常纠结在一起。正如她在《写给令我废寝忘食的爱》中所说:“爱和人的关系也许就像鞭子和被抽起来的陀螺,它令它动了,它却也令它疼了。别去看它在那里疼,你们要和我一样,都闭上眼睛,只静静听那飕飕的风声,那是鞭子和陀螺在一起唱歌。”③
张悦然小说中的爱情属于前婚姻状态的爱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人追随另一人的“骨感爱情”,一种是擦肩而过的两情相悦。这两种爱情都传达了张悦然对所谓“纯白爱情”④的向往,其特征是充满梦幻感,容不下半点瑕疵,像晶莹剔透的易碎品。
张悦然在《霓路》中将电影《暗战》里的爱情称为“骨感爱情”,这也可以说是她很多小说中一直延续的爱情模式。特点是一个人倾其所有地爱着另一个人,而另一个却由于种种原因只是承受而没有回报。这类小说中用的频率最高的词是“追随”、“跟随”、“甘愿”、“心甘情愿”等。从表象上看,这种爱情刻骨铭心,纯澈无比,类似《海的女儿》中的美人鱼对王子的爱和《荆棘鸟》中梅吉对拉尔夫神父的爱,都是从低处仰望高处的“望日莲”式的不平等之爱,极具煽情效果,但实质上都是“空集”,被抽空了生活的内容,像飘浮在半空中的羽毛或水面的浮萍。正如时下流行的骨感美一样,骨感爱情也成为80后心中的一种时尚爱情模式,张悦然显然捕捉到这种流行趋势,并刻意为这种爱情“独角戏”包裹上华丽的霓裳。这里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向往,同时还是一种生命意识,表面上无私的交付掩饰着人在面对“存在的空虚”时的巨大恐惧和挣扎。《霓路》中一对恋人的爱情就像电影《暗战》中蒙嘉慧和杀手的爱情一样,是所谓“清浅之爱”,女孩抛弃一切去追随男孩,男孩却在追随自己缥缈的梦想,顾不上守护这份爱情。《水仙已成鲤鱼去》和《誓鸟》则是集若干个骨感爱情为一体的小说,《誓鸟》中有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世界本就是如此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亏欠,也一定有他的倾囊所出。像一条锁链般一环环紧咬,直至首尾相连,这个世界便是公平的了。”⑤璟对陆逸寒的追随,优弥、沉和对璟的追随;春迟对骆驼的追随,淙淙、苏迪亚、钟潜、宵行对春迟的追随,婳婳对宵行的追随都是一样的倾囊而出且心甘情愿。连非人类的现代爱情童话里也是这样的骨感爱情:《残食》中的蓝色鱼妻子心甘情愿充当丈夫的美食,《葵花走失在1890》中画家文森特·梵高喜欢的一株葵花痴迷地爱上了他,“不是去见,是去追随他”⑥是“葵花”对爱情最确切的表达。
张悦然过于强调爱得干净、纯粹,即使她安排了一场两情相悦的爱情,也让这份爱情只是擦肩而过。
《陶之陨》中的“我”和梵小高、《赤道划破城市的脸》中的“我”和卡其的爱晶莹剔透却难以保存。《樱桃之远》中纪言与杜苑苑好容易冲破重重障碍得以相爱,却因为误会而分开。《谁杀死了五月》中三卓与青春女作家的爱更是短暂到仅仅是拍照和做爱的时段。
张悦然笔下的友情多发生在女孩之间,可以用“双生花”来形容。虽然有时中间误会重重,但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挚友的相互理解、支持,还有亲人间的亲情,且不沾染任何功利色彩。
《这些那些》整个文本都是“我”对小舞的诉说,从这冗长的诉说里可以看出两个女孩有着共同的乐趣、喜好,彼此互相欣赏和惺惺相惜,可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并祝福对方能得到幸福。《樱桃之远》一书的灵感显然来自波兰电影大师基斯洛维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又译为《双生花》),杜苑苑和段小沐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却感触相通,虽然杜苑苑一度因为能感受到段小沐的心绞痛而将之视为魔鬼,甚至想谋杀她,但段小沐一直怜惜杜苑苑的痛苦,杜苑苑也在明白前因后果心生忏悔之后将段小沐视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两人都甘愿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璟和优弥,虽然看起来是优弥帮助璟完成蜕变后悄然离去,但从优弥的话中可知二人的深层联系:“当我遇见你,我把我自己分成了两个,一个是激进、跃跃欲试的我,她像个顽皮的小女孩;另一个是甘于平淡和奉献的母亲,就是现在的我。我早就把我的‘小女孩’交给你管了,……你的任务是好好抚养她,带着她去见识更大的场面,体会更大的成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我肚子里的这个小家伙。”⑦
二、人物的模式化
模式化创作方式通常有自己固定的人物谱系,张悦然笔下的人物以成长中的少男少女为主,此外还有他们的父母。
青春少男少女这类人物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表现出作家对这类人物的熟稔和偏爱,也反映出因创作资源匮乏而造成的重复雷同。
从人物经历看,这类人物主人公大多经历坎坷。最集中的是《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璟、《樱桃之远》中的段小沐和《誓鸟》中的春迟。璟先后经历了父亲、奶奶、继父、小卓、沉和、丛微、小颜的死,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爱,而是痛恨、厌恶、轻蔑。段小沐母亲早逝,父亲将她抛弃,她本身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后又落下腿部残疾,与她相依为命的李婆婆去世,她被李婆婆的家人赶出小屋,病危之际她一生情有独钟的小杰子揭破他从未爱过她的真相,她终于伤心而死。春迟母亲被杀,自己被轮奸,爱人在海啸中丧生,她失忆……像极了收视率颇高的苦情戏的剧情。
从性格心理看,这类人物因为家庭或其他原因,大都有着忧伤的童年,形成或多或少的自闭自恋倾向。《红鞋》中的女孩、《儿童不易》中的侏儒韩勤勤、《樱桃之远》中的段小沐和杜苑苑、《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璟、《吉诺的跳马》中的吉诺、《小染》中的小染、《誓鸟》中的春迟、宵行、《昼若夜房间》中的索索与莫夕姐妹、《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中的次次和小夕等人物都是如此。
从精神气质上看,绝大多数人物都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其中很多主人公的职业和兴趣与艺术有关。《毁》中的毁是画家,《陶之陨》中的梵小高擅长陶艺,《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陆逸寒是画家,丛微和璟是作家,小卓喜欢雕塑,《樱桃之远》中的小沐以刺绣为生,杜宛宛酷爱绘画,纪言是鼓手,唐晓是歌手,《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梵高是著名画家,《红鞋》中的女孩酷爱摄影。《霓路》中的小野和《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中的次次在文学、绘画等方面都有天分。在张悦然笔下,强调的不是他们创作了什么惊人之作,而是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聪慧、敏感、忧郁、耽于梦幻,追求一种极致的纯净唯美的心理状态。男性绝大多数高瘦纤长、性情柔弱,有一种偏于阴柔的美。他们对绝对洁净有着根深蒂固的偏执。这一特征反映了作家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是对成人世界争名夺利、庸俗粗陋生活方式的拒斥,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童话情结。
张悦然笔下的父母形象有更浓重的类型化倾向。最为常见的是暴君式的父亲和懦弱无能的母亲。
这类父亲中好一点的通常粗心大意,从不考虑孩子需要,坏的干脆自私冷酷,经常对孩子虐待打骂。《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的生父、《小染》中小染的父亲、《昼若夜房间》中两姐妹的父亲、《吉诺的跳马》中吉诺的父亲等都是如此。母亲绝大多数屈服于凶恶的丈夫脚下,任劳任怨,任打任骂,怯弱到无法保护自己和孩子,如《昼若夜房间》中两姐妹的母亲、《小染》中小染的母亲等。
还有一种父母类似天使或圣母,特点是纯净高贵,能够给予孩子充沛的爱。《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陆逸寒,对继女璟的关爱远远超越了她的亲生父亲,从不嘲笑璟的暴食,细心地用水果代替高热量的食物,甚至代替了通常母亲的角色,在璟面对初潮感到恐慌时,体贴入微地告诉她这种生理现象的由来。《樱桃之远》中杜苑苑的父亲,不但给女儿无限疼爱,而且将这份美好的爱分给孤儿段小沐,拉着她的手为她买冰淇淋的一幕充满了父爱的温柔。《红鞋》中的杀手,对从他枪口下奇迹般生还的小女孩,既歉疚又喜爱,从他将女孩带走的那一刻起,就充当起父亲的角色,为此过起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对女孩呵护备至,包容了女孩的轻蔑和冷漠,在弥留之际考虑的仍是女孩的安危与幸福。《霓路》中女孩的父母、《樱桃之远》中杜苑苑的父母都可归入此类。
这些形象都缺乏坚实的现实根据,好与坏都走向极致,特别是天使类的父亲,身上放射的尽是神的光芒,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母亲形象也是张悦然想象的产物,且打上了她恋父情结的烙印,既没有现实依据,又没有发展变化,显得苍白、单调、雷同。
三、情节的模式化
张悦然小说中,很多类似情节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中,使人在阅读的时候经常有似曾相识之感。
很多人物都经历了千疮百孔的童年,都曾醉心于一个人的游戏和梦幻的童话世界,渴望超越凡俗的飞翔。有着相似的喜好,诸如喜欢把墙壁刷成蔚蓝色、喜欢Kenzo清泉之水的香水、葵花、草莓、樱桃、水仙、蔷薇等。
自杀的镜头出现频率颇高。如《毁》中的毁、《吉诺的跳马》中的男孩、《昼若夜房间》中的莫西、《领衔的疯子》中的小蔚、《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中的次次和小夕、《纵身》中的女孩都选择自杀,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成功,有的未遂。
在爱情故事中,出现最多的情节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追随,《霓路》《跳舞的人们都已长眠山下》《红鞋》《葵花走失在1890》《翅膀记得,羽毛书写》等都是如此,《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则是若干个追随故事的合集。
暴力镜头一再出现,成功了达到了恐怖电影所追求的惊怵效果。父亲毒打母亲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如《小染》《昼若夜房间》等,最极端的是《船》中的父亲将妻子杀死。冷暴力的情节也很多,诸如春迟对宵行、宵行对婳婳,《红鞋》中女孩对杀手,《霓路》中的小野对女孩。还有畸形的爱造成的伤害:《昼若夜房间》中男孩的母亲对男孩的控制,《吉诺的跳马》中索索对妹妹的监禁等。虐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黑猫不睡》中的黑猫被女孩的父亲暴打后,牙齿被折断,露出参差不齐的血淋淋的牙茬。在《红鞋》中则更进一步,女孩在看过恐怖影片中女人拔光猫的牙齿的一幕后,将之实施于邻家男孩和猫的身上。《誓鸟》中宵行的虐猫更为恐怖,直接将咖啡豆硬塞进猫的肚子,致使其惨死。
综上所述,张悦然小说创作存在着大量的自我重复现象,从主题、人物到故事情节都不例外,反映出张悦然创作的几个突出问题:一、生存经验缺乏。在教授家庭长大的张悦然一直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长期的读书生涯使她的视野受到限制,由此造成创作素材的短缺。二、心理存在偏执倾向。在处理问题时还停留在童话阶段,黑白分明而绝少间色,理想人物都是极力摆脱地球引力向虚空飞升的类型,理想爱情是不染人间烟火气息的纯粹之爱。三、受市场与文坛的双重影响。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不免在文本中设置许多惊怵、煽情、浪漫、悬疑的场面,并在人物形象塑造、主题、意象设置等方面迎合读者心理。为了显示出超越年龄层面的成熟,故意用暴力、反常行为来表现人性的扭曲、变态与邪恶,来制造作品的“深度”。除了不可改变的因素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社会阅历,积累更为丰厚的创作资源,同时调整心态,不为文化时尚所囿,寻求真正的创新之路。
孔令环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①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4页。
②张悦然:《十爱》自序,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页。
③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4页。
④张悦然:《誓鸟》,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32页。
⑤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55页。
⑥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2005年1月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