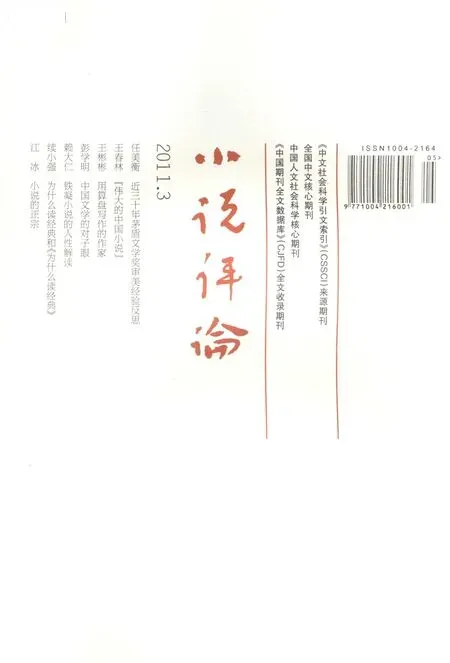温暖世界:论铁凝创作的传统精神追求
刘惠丽
温暖世界:论铁凝创作的传统精神追求
刘惠丽
三十多年前,铁凝带着“会飞的镰刀”踏上了文学寻梦之旅,走过稚嫩的“夜路”,飘过纯真的“香雪”,穿越人生的“玫瑰门”,领略社会风雨的“大浴女”,展示了“笨花”的飞升和沉重。纵观铁凝的创作,成名作《哦,香雪》的基本内涵在她以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了下来,那就是她面对世界的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作家曾表示:“我注重并无疑地相信的是中国土地上的人和事,本土的资源,这是更结实的泥土里的东西,西方作家对我的影响就像空气里的东西,虚飘一些,但也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我们的本土资源是不可穷尽的,我非常珍视。”①我们不难看出,铁凝的文学追求始终洋溢着一种传统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重人重德”的体系。由于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凸显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人的完善,因而被称为“仁学”或“人学”。孔子学说的基本精神就是“仁者爱人”,在此,爱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而且并非特定的君王、阶级或阶层,而是一般的人,普通的人。”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和首肯,才使得人自身的修养,成为文化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关键词。以道德建设为例,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就是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其中儒家的道德文化,对铁凝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善美信仰”及“义以为上”的价值观
对于人性善的追求,传达出中国人对于自我的一种传统态度,不仅支持着铁凝对于人性的信心,而且为她的和谐文化的设想提供了最大的精神资源。艺术就是要表现美,美就是善,善就是完整、健康和自然的品性,这就是铁凝的美善信仰的主要内容。铁凝的这种美善信仰是用一种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中美善信仰的扩充和发展。因为中国传统的美善意识都是对道德的规范和修订,这种敏感的道德焦点,是中国传统的精神内容。铁凝的美善信仰的基本内容还是道德问题,体现着她对道德的极其个性化、极其诗性化的命定和解释。
善良、仁义几乎成为铁凝所有小说中的关键词,评论家们也无不被她浓烈的善良所感染。“我特别看重她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我不知还有哪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作家能此执着地去发现人性的善,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③1982年的短篇小说《意外》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农村姑娘山杏在海岛上当兵的哥想要一张“全家福”。于是山杏带着爹妈去县城的照相,他们搭了50里汽车,走了200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总算在照相馆照上了相。半个月后,他们收到照相馆寄来的信封,撕开一看,照片上是一个他们谁也不认识的姑娘。这肯定是照相馆出了错,是一个意外。但更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是,山杏一家拿到这张弄错了的照片,既没有生气也没有懊丧。“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小说不足2000字,但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铁凝把她对农民的纯朴和农民式的乐观、现实的印象鲜明地凸显了出来。《喜糖》里写了陶媛和白瑛瑛这两位女友好得“分不开”的关系,因为白瑛瑛的自私和庸俗,两位女友终于有了矛盾和裂缝,甚至陶媛都吃不上白瑛瑛结婚的喜糖。陶媛没有去怪罪白瑛瑛,反而自己买来糖果,代白瑛瑛请别人吃喜糖。
如果说《哦,香雪》是铁凝为善良唱出的一支单纯的赞歌,那么《永远有多远》就是以直面现实的方式,为善良和仁义撰写的一份伤残诉讼书。这里凝聚这作家对于中国传统美德——善良和仁义的思考,不过,这份深沉更复杂,更深沉。
白大省可能是一个过时的北京女人,她的仁义、和善,她的吃亏让人,她的热情与痴心,她的拙笨的小计谋……或许都还带着四合院老房子里那常年被雨水泅黄的顶棚的气息,樟木或羊皮箱子的气息,槐花、青枣和雪里蕻的气息。作为社会角色,她是众口一词被人说成理想的楷模,逢到个人生活,她则老是处于劣势。朋友、家人、同学、同事,谁都可以为了自己免遭伤害、获得利益而把麻烦拽给白大省。她所挚爱的男人也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了她。她承接了这一切,且心甘情愿,浑然不觉。这种承接能力仿佛不是后天的训练,而是天然生成,无法更改的。这就使得白大省几乎不像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北京人了,她更像北京的一个死角,死角里一团温暖而略显悲凉的物质,一缕硕果仅存的精神。铁凝曾说:“我们可能会祈祷白大省不变,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永远’一词在世纪末多种声音的喧哗中显得既嘹亮又微弱,既结实又无力。再也没有比‘永远’的内涵更不确定的内涵了,再也没有什么词比‘永远’显得更加滑头和善变。”④这种通过对善良与仁义的倡扬,来营造人与他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理念,一直廷续到铁凝后来的作品中,如《安德烈的晚上》、《省长日记》、《寂寞嫦娥》、《砸骨头》等。善良与仁义是儒家营造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主要理念,对于寻求和谐人性的铁凝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的现世情怀
生活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丑恶的。面对现实,铁凝在思考,在审视,在承担。单纯的呈现善良和仁义似乎已经不能让“善良成为善良者的通行证”。铁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学向上向前的内力,思考民族品德的改造,思考人性的走向。
“当一个作家能够被称为作家的时候,在他的故事,他的梦,也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究里,已经有了社会责任的成分。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文学也可以像蒙克那样对生活表现深深的失望,强烈的失望本身就蕴含着希望,因为没有失望就无所谓希望,正如同我们有时候对生活不恭敬是渴望生活更神圣。”⑤
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评论家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部作品。大家不能接受一贯以善良、仁义著称的铁凝为什么会塑造出司绮纹这个恶毒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地要在时代的剧变中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女人,一个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入(挤入)历史的女人”。⑥面对众声喧哗,铁凝表现得很淡定。“为什么要写《玫瑰门》昵?我想我对生活是没有失望的,因为《玫瑰门》里确实写出了一些惨烈的东西,但是也写出一种生命被塑造的可能、那个主人公,就是那个老太太司猗纹,一方面可以说生命可能被扭曲成那样,一方面你也可以感叹一个生命强大成这样。她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家庭妇女,但是她敢于面对本来要把她踏上一万只脚的社会,她要碰撞出一个高低来,这就是一个家庭妇女的生命,强大的生命力,她的一个姿态。玫瑰门里有支撑我写作的不变的底色,《哦,香雪》还是存在的。它有一个核,这个核是没有变的。最终我觉得我的小说,我要表现的不是审判,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俯视。不管写得怎样丑陋、惨烈,《玫瑰门》这样的故事也好,清新秀丽的《哦,香雪》一样的故事也好,我觉得文学还应该有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有暖意,应该给人类带来一些温暖。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它审判的意义是否大于理解的意义,我想,最终文学可能有审判的成分在里面,或是审判他们或者自我审判。但理解这个事情,理解本身,这个比例还是应该大过审判。因为审判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理解是需要耐烦的,需要有非常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对人生对生活不疲倦的不败的耐心贯穿作家整个一生。作为一个作者对她有一种巨大的理解,这里其实也有暖意在里边,有了温暖和体贴,你这种体贴这种暖意可以用许多不愉快快的表象,或者是通过一些不愉快的故事表现。最终,我觉得读者看到的,它最后还是有一点亮光的。”⑦
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使人们很容易就想到了色情、肉欲、暧昧、淫靡等场所,加之精明的出版商“布老虎”丛书的经营者,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在书籍尚未出版之际就开始通过媒体宣传造势。这种宣传给铁凝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人们也期待着一睹这本书的真容。中国小说学会举办的“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了该年度的五部长篇小说,《大浴女》就名列其中。《大浴女》以它所蕴含的分量还是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得到了批评家们的认同。
毫无疑问,《大浴女》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严肃作品,相比于《玫瑰门》,“三垛”系列,以及90年代以来关于人际关系思考的中短篇小说,《大浴女》更具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力,《大浴女》可以说是一部忏悔小说。小说以尹小跳的自我反省为基本结构,整部小说就是尹小跳心灵的痛苦的蜕变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忏悔意识一直就是尹小跳灵魂蜕变的内在动力。尹小跳的成长经历展示了这一蜕变过程是如何由浅人深,最后直抵灵魂的深处的。尹小跳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在不断的自审中超越自己,获得自我救赎的希望,从而回到无辜的本初,走进内心深处的花园,达到人性的自我完善。
关于《大浴女》,人们从忏悔、自审、原罪、灵魂拷问的角度谈的很多。笔者认为,铁凝的《大浴女》恰恰是作者深受儒家文化刚强自建的人生态度的影响,肯定个体通过道德修养来改变社会文化状态的可能性。但与儒家不同的是,这种个体修养的目的不再是把个体人格伦理化和规范化,而是要把人性健康化、现代化,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弘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是一个文学家用非理性的文字表达自己对人生方式的哲学解释,她强调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强调的是内在超越,以及这种修养和超越的最终彼岸——完善一个完美的社会,成就一个健康的民族。铁凝说:“我们要提倡文学有一种自觉的、向上的精神追求,它在总体上应该有利于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和品位,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因此,文学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应该坚持对其精神品位和精神境界的追求,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也应该对文学有一种自觉的精神性追求,笼统地排斥文学的职责和必要的负载也是一种片面”⑧。
三、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中国文学由古至今的嬗变,是一个不断由旧趋新而没有止境的过程,它在同社会生活与人性发展的同步协调中,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生、衍变、转型的过程。同样,负载在文学身上的文学传统差不多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时空的变幻中,我们既可听到它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也可见到它留在文化陈迹之上的脚印,无形与有形,都是不可抹杀的审美存在。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就是士人阶层,却有着较之君主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奉行“出为帝王师,处为万世师”的人生理想:或作为循吏恪尽职守,为维护现实制度的合法性不遗余力;或作为布衣之士著书立说,为人世间制定法则。他们的主人意识是那样强烈,以至于认为离开了自己这样的社会良心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一片、漆黑一团,因此深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道理,并且拥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如果真正弄懂中国古代的这种圣贤文化的真谛,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以此岸世界为彼岸世界、以人世间为天堂、从人性中发现并发掘神性的文化,它不是宗教,因为它拥有宗教的一切积极功能而没有宗教的弊病,它不是引导人向着否定人自身的方向前进,而是引导人们真正认识到如何才能做一个“大丈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真正的人。
不幸的是随着中国式的现代性工程的开启,随着传统的文人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即作为中国古人对这个世界极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圣贤文化也被当作垃圾而抛弃了。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政客、工具理性的主体、追名逐利者——没有灵魂的人。试问现在有哪位知识分子听到“成圣成贤”、“修身”等字眼而不嗤之以鼻的呢?
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忘记了对其精神之根的积极培育和自觉维系。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就是其独特的文化生命,即所谓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而能始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主要的就是靠着无比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合理性了,甚至仇恨起它来了,对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愤愤不平了:真是“老而不死”。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雄厚基础之上,在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西方文化的滋养之下,在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的浸染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建构新的文化传统的伟大契机。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间概念,是指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达到的水平。从发展的趋势看,现代化并非是以哪一个国家的发展为标准,而是指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中所追求的发展方向。现代化是人们不断追求的方向,而传统文化则是已经积淀了的历史,从二者发展的关系上看,双方必定是处于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过程。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历史的连续,必须以根植中国文化土壤为基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要求相容的内容也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与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它包含的仁爱、宽恕、诚信、礼让、刚直、勇为等道德传统,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不仅在历史上对铸造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以至将来的文化建设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时光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信息时代为我们带来的物质极端富有,我们对传统精神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为什么许多读者会心疼和怀念香雪那样的连什么叫受骗都不知道的少女?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有位我尊敬的老作家说过: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我想,即使有一天磁悬浮列车也已变为我们生活中的背影,香雪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间温暖和积极的美德,依然会是我们的梦。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⑨
铁凝始终坚持以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才情,对北方的山和水,北方的男人和女人表现出充满暖意的东方精神,创造和传达出了养育她心灵的这一文化环境中的那种特殊的壮丽,深邃而又纯真地寄托着她对人类生命和生活永恒的宽厚和体贴,有效地抚慰着人世间的喧嚣浮躁和被无限夸张了的疑惑与冷漠。
刘惠丽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
注释:
①赵燕、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
②张怀承:《天人之变一一中国传统道德的近代转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第54页。
③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一一关于铁凝小说的话语伦理》,《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④铁凝:《永远的恐惧和期待》,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253页
⑤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
⑥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一一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⑦陈俊涛:朱育颖《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
⑧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⑨铁凝:《从梦想出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