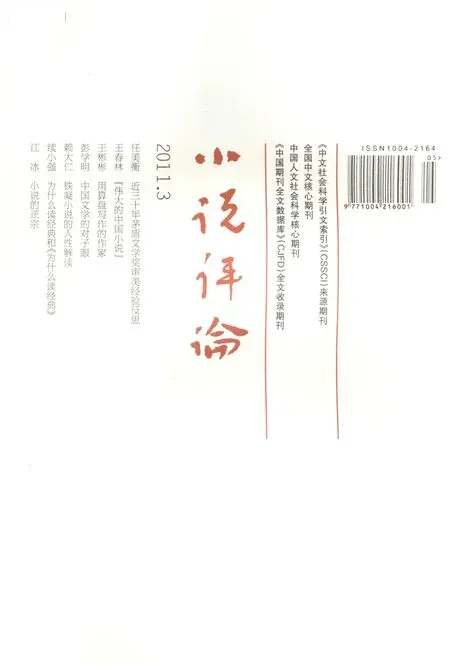为什么读经典和《为什么读经典》
续小强
为什么读经典和《为什么读经典》
续小强
一个怪异的人,一个制造迷恋的写手,一个在叛逆中不断回归原点的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写了一篇《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
“1981年”,中文译本的末尾如此标注。这,是不是有一点“轻率”呢?尽管重复,时间却并不是不重要。从语句的犹疑与徘徊不定去探测,那可能是1981年秋日的一个深夜,繁复的秋雨调子,扰乱了一个老年人的梦境,他起来,靠在床头上,用自己“独一无二”“复杂精致”的大脑演算了一道近似于数学的题目:经典的定义。
一个后来变得无效的前提
文章不长,读过之后,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他老了,如此简单的“数学题”,根本无须如此复杂的“定义”;更何况,他所给出的十四个定义,全然没有个定义的样子,近似呓语,模糊、晦暗,甚至潮湿得泛着霉气。
我想这有可能是他刻意制造的意外,就像他的小说一样,催眠术屡试不爽,我们便每每被俘:你认为他失败了,他却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恬然睡去。
直到确立了第十一个定义时,他感觉我们对他逻辑漏洞的怀疑必须作出适当的说明了,可他的说明却是如此的斩钉截铁:“我相信我不需要为使用‘经典’这个名称辩解,我这里不按照古老性、风格性或权威性来区分。”语气多么不容置疑,他有这个资格,当然,这也是他的需要:面对“经典就是经典”的无限反复,他只能描述,哪怕是一种带有理论色彩的抽象的描述。这是他一个职业小说家的职责。
从始到终,在考虑经典的定义以及思虑如何对定义作出分解和描述的同时,我相信他一直有一个深重的困惑:他在给谁说这样的话,他的定义对什么样的读者是有效的。我为有这样的发现感到欣喜:在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如我一样的很多人,一直以为“经典”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每一个人(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有效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笑了:其实不然;这实际上还是那句口头禅“经典就是经典”在作怪。
在文章的最初,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虽然不会自恋到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博学的人”,但他还是清晰地指出:它(指他给经典下的第一个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不适用于年轻人;紧接着,他又作出了特意的强调:“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他当然不是对年轻人有“不读书”的成见,事实上,尽管他开篇即点明“不适用于年轻人”,但后来我们慢慢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想法除了和“成年人”一道温习一下自己多年对“经典”认识外,更多的还是想要给年轻人布布道的。只是这个“年轻人”前面需要有定语的修饰。按他的说法,这个修饰,应该是读过一些而不是读过一点书(经典)的年轻人。
于是,所有的十四个对于经典的定义,首先不仅是从“读”而且是从“重读”开始的。读,准确一点讲,重读,是经典成立的前提;没有这两个必要的带有劳作色彩的动作,经典有如僵尸并不存在,谈论经典的定义以及其他种种,便无任何一丁点的意义,而且,显得无知而荒唐可笑的。
写这篇文章时,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平和了许多,已不像早年那么气势逼人了,他慈眉善目、循循善诱,他或许注意到了如此“绝对”的前提会伤害到他人,至少会影响到有更多的人进入到可谈论经典的行列,于是他才说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注意:他没有用“经典”一词),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读到这句话,我就为自己仍没有读完《红楼梦》而心稍安慰了。“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这样的话,对于一直读经典的、亲爱的你们,我想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经验的特殊效力
在“重复”、“重读”的前提下,他以对“经典作品”的描述,初步给出了一个关于“经典”的大概的轮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是的,这位有点絮叨的老先生,仍是那么的宽厚,总要给人以必要的情面。对第一种情况,他有多少信心不得而知,他的重点,或者说,玄机之处,仍在于后一句。这有点像望梅止渴的故事,它多少带有那么一点蛊惑人心的味道。在现实的文化生活内,抛除机械的强硬的灌输式的经典教育,其实,我们最容易习惯于日常的荒芜流转,而停滞于阅读和无理由的虚无等待。所以,对他“保留这个机会”的宽容或期许,我们应该有一种必要的自我暗示和警惕。
他当然有过青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要不然,习惯于准确描摹的他,不会就简单地认定“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他认为“价值不大”的原因,不在于经典作品,而在于“我们没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
再往后面,越说越好,但在节奏上讲,似乎和前面有些矛盾。他一方面确证无疑地指出青少年时期阅读的不牢靠,另一方面,却因了自己阅读生涯和写作生涯的经验,用一种近乎和青年人商量的语气说:“这种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
如果有人想扮演经典阅读专家或教父一类的角色,我想这一段话,应该成为他随时随地脱口而出的经典语录。回想我们自身的阅读生活,这真是太准确不过的,经典之于生活经验的表述。
这段话中我特别注意的,是“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即便我们可以承认黄灿然先生翻译的精准,但我更乐意于将“性格”作“人格”的偷换。我还没有去找必要的资料去印证,这位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在专注于小说的虚拟世界之外,是否还有对现实社会公民政治的热情。如此的偷换词语,或者即便我们没有这个略显多余的想法,单纯地把这句话拿出来、放大,还是有足够惊人的效果。在历史书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典,在其成为经典的路途上,是经过无数的大坎坷的,这其中,最为“显赫”的行径,便是查禁、篡改,乃至文字狱,乃至焚书坑儒。它同时,似乎半遮半掩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经典阅读教育,便有可能造就什么样的公民社会。
也许,这位老先生不屑于如此的发挥,他经常性地表现出一种轻逸的姿态,他似乎并没有越轨的打算,回到经典的定义,他再次强调:“在我们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现那些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说到这,他觉得还不够“小说”,于是有了下面这句让人无限回味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却,却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
顺着经验之绳的引导,他提出第三个——第六个定义。这四个定义,都是对“经验”的进一步发挥,有一点同义反复,但指涉的重点却又不尽相同:第三个定义讲经典作品的“印记”性、“隐藏”性;第四个定义说“重读都像初读”;第五个定义更进一步,说“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第六个定义则有些过高地拔举了“经验”的作用:对于读者,经典作品,“永不会耗尽”。
到此,我想这应该是这篇《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二部分。在开端左顾右盼地谈论“读”与“重读”的重要性之后,他深入了经典的内部,转悠了好半天,他实际上一直想说出的是:经典即经验;我们的经验即是经典的一部分延伸。所以,他才会说:“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不真的那么重要。”毫无疑问,在一开始受到必须“读”或“重读”的惊吓之后,我们又一次释然了。或许,还会有人要大做惊恐状,呵,不必读,我即经典呐。
对批评话语的无奈
老实说,从阅读的一开始,我对这位伊塔洛·卡尔维诺老先生,总有特别的担心。这道数学题,大概是最不严谨的一道数学题,一个年迈的老者,何必纠缠于此,为一个经典的定义而失眠伤神、耗费脑细胞。这与写作一篇小说的奇妙、欢快之旅,有太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第二部分,虽然还是有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说家气质,但总归解得还算顺畅,他与我们的想象式的对话,也较为和气,以“经验”作结,大家都不至于很难堪。
第七个定义——第八个定义属于一类,据他说,这是第五个定义所隐含的“更复杂的表述”。这确实有一点危言耸听了,但我们已经习惯这位垂垂老矣者在这篇文章中的惯用语气。
“更复杂的表述”之下,多少是有些对经典作品传播与流转的无奈。
第七个定义: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不愧是经典的小说家,如果把“经典作品”换做一个古老的名字,就不是有点而是十足的像一部短篇小说的开头了。对此定义的描述,同样,他抖出了一个小说家的经典武器库,以荷马、卡夫卡、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为例,他试图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的无比正确性: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究竟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他在思索,或者说他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他再一次陷入彷徨,取消“读”或“重读”的前提还是有一点那么不太合适:读一部经典作品也一定会令我们感到意外;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所以第八个定义,他准确地说,是“下结论”: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这话说得很奇怪,“经典作品”果真能够自己抖掉那些批评的微粒吗?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值得,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料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个经典文本首先说出来的”。但是我们还要问,我们怎么就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东西就一定是那个经典文本首先说出来的呢?他说这需要“发现”,而且他说“这种发现同时也是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那么他所说的“发现”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可以肯定的,一定不是经典作品的“教导”,而是第一部分强调的“读”、“重读”,以及第二部分四个定义强调的“经验”。
于是,他带着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问题的原点:面对经典作品“广泛存在着的价值逆转”,烟幕不会自行散去,我们只得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于是,刚刚有一个不必读的正当借口,我们却又一次垂头丧气了。
确立自己
曾经有一个人和我说,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他也想去阅读,却不知道该读什么样的书才好。我的回答是,问你爷爷或父亲,但不要问我。这句话有点插科打诨,实际上它潜在的意思是:从老书读起,或者说,读老人们写的书。
我们总莫名的担心老人们的啰嗦、同义反复,乃至时空倏忽跨越般的呓语,甚至某种刻意的遮蔽——这是有根据的,对此,我也害怕。但我唯一不害怕的,是这些老人出自老人本能的对未来的善良的期许,或者毫无顾忌的带有矫正意味的教诲。
《为什么读经典》的第四部分,则由第九、第十、第十一三个定义组成。
第十个定义,说“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说得很神奇,似乎在为“经典”作出盖棺定论,而实际上,如此马拉美梦想已久的那种书,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说它虚幻也不为过。他没有在此基础上展开,那才是小说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定义,就只能作为陪衬或反面的论据存在。
这一部分,处处是这位老先生无限善意的教诲。只有他认为经典作品的最终价值是确立一个人的自己时,他才会这么强调经典和个人的关系。
鉴于老先生如此恳切,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他所提供的建议:
必要的姿态:“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
需要坚持:“只有在非强制的阅读史中,你才会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
厌恶感:“但是一部经典作品也同样可以建立一种不是认同而是反对或对立的强有力关系”,以卢梭为例,他抗拒、批评、与其辩论,甚至有不去读他的想法,但最终,他坦率地承认:“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
可以欣慰的意义:“一部经典作品的特别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在文化延续性中有自己的位置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作品那里所感受到的某种共鸣。”
当然,还有一句看似与主题无关却至为重要的:“只有那些你在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
经典和时代
最后三个定义,事关经典作品和时代的关系。
首先,不能搁置的关键问题是,是读经典作品,还是读那些不是经典的如洪水般的印刷品。
读到这里时,我有种看戏的快感。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置身其中的时代,总是有种迷离的错位感。换一句话说,谈论过去的历史是容易的,而面对当下,我们常常无语,找不到恰切的词汇、语句去描述它。我们曾自以为是地找到了,实际却是云里雾里,走不出来,越说越困惑,甚至,越说越疼,这真有点像拿着锋利的刀子,割自己的肉。
伊塔洛·卡尔维诺老先生对此也是避重就轻,他说:“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前半句,大概是没错的,可是后半句,却很别扭,难道我们必须亲自去体验一下腐败官员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写小说、才能够评论如此这类的小说吗?我可能有一点过分的发挥,他所说的“置身其中”,在他看来,或许只是对“经典作品”才有效的。如果这么说,“置身其中”,便又是“读”或“重读”的同义词了。不管如何,我非常认同老先生如此的判断:
“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很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
必须有比较,才可有“位置”感的存在。这需要勇气和付出:我们是否能够摆脱学术考评机制的压力?我们是否能够消除作为一个职业写手的生存压力与欲望?我们是否能够回避作为一个读物生产链条中一环的存在?
而“获取最大益处的人”,一定是最辛劳的人。这样的辛劳一定就有必要和价值?以长篇小说为例,据说一年有近三千部长篇产生,我们的批评家如何选定自己的“位置”,如何走出这“无始无终的迷雾”?
老先生开起了玩笑话,他认为“把现在当做我们窗外的噪音来听”大概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了,我想他还是太过自信了。一个老年人,从生理和精神上,对于外界的声音当然是不敏感的,但对于他一再放不下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如此的假设,未免一厢情愿:时代的喧嚣,绝大多数人是无法抵抗也抵抗不了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一个执迷不悟的人,到最后了,还是那么可爱的坚持,叫人不得不给予十分的崇敬: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第十三个定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第十四个定义)。
写到最后,伊塔洛·卡尔维诺先生对自己的解答充满了深深的怀疑,以致他一再表明自己要必要重写这篇文章。他终归没有这么做。他甚至都没得及把《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写完,1985年,他飘然而逝。
文章的最后,他引了一个不太令人提得起兴趣的段子:
当毒药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首曲子。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之前可以学习这首曲子。”
这能说明什么呢,有多少人愿意步苏格拉底的后尘?就像你在引出这个段子之前所说的:读经典总比不读好。尽管,这是“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但谁能够做到呢。
续小强 《名作欣赏》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