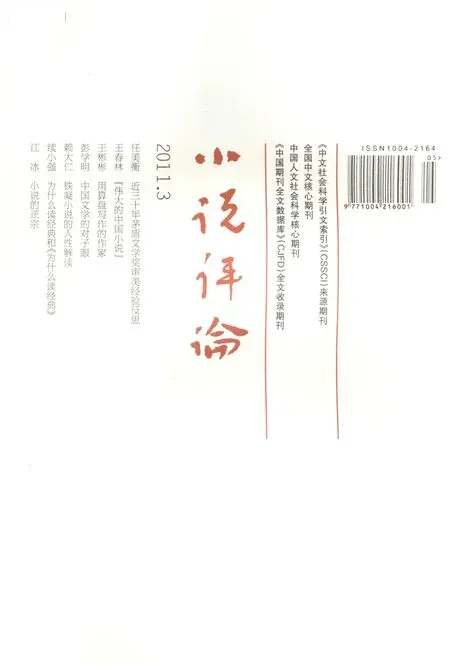用算盘写作的作家
王彬彬
用算盘写作的作家
王彬彬
用算盘写作的作家是高晓声。高晓声1954年以短篇小说《解约》引起关注,但不久便在政治运动中沦落为“贱民”。此后,高晓声以“以戴罪之身”,在泥田水汊中摸、爬、滚、跌了二十几年。七十年代末,高晓声重返文坛。1979年,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在《雨花》第7期发表;1980年,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这两篇小说,引发了“高晓声热”。这“热”,持续了六七年。八十年代后期,高晓声便“冷”了下来。
曾经很“热”的作家,后来“冷”了;曾经很“冷”的作家,终于“热”了。这都是常见现象。曾经极“热”的作家赵树理,后来“冷”了很长时间。这些年,赵树理似乎又有些“热”了。赵树理的再度“热”起来,让我想到了高晓声。赵树理最受人称道的,是对农民心理的把握,是对农民性格的塑造。而我以为,在这方面,高晓声即便不比赵树理做得更好,也丝毫不逊于赵树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作家很多,写农民写得好的作家也颇不少。如果说赵树理是写得特别好的一个,是凤立鹤群者,那高晓声肯定也是。所以,我以为,高晓声也实在不应该被遗忘。倒不仅仅是出于“攀比”才有此想法。更是因为,高晓声特有的叙事智慧、高晓声刻画农民心理和塑造农民性格的特有方式,确乎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
高晓声的叙事方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古代小说。在《读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①一文中,高晓声很热情地谈到了《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妙处。这些长篇小说,当然也曾让高晓声受益。但在古代小说中,《聊斋志异》对高晓声创作技巧的影响又特别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高晓声是从蒲松龄那里学会了小说作法的。我以为,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基本方式,来自于《聊斋志异》,他小说中的某种缺陷,也可视作是《聊斋志异》的一种“遗传”。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是这样开头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力气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陈奂生上城》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高晓声小说。小说的叙事方式,一开始让我有些不习惯。依我那时的审美趣味,我希望小说有更充分更细腻的场景呈现。一开头,应该写陈奂生怎样起床、怎样洗漱、怎样吃早餐、怎样出门上路、怎样在和暖的太阳下悠悠地向城里走着、头上怎样微微冒着热气、身上怎样微微出着热汗……但高晓声却主要以概述的方式说明高晓声离家上城的过程。在开头的两个自然段里,并非没有场景的呈现,但场景的呈现是零碎地夹杂在概述中的。概述,在这开头部分起着主导作用。这两段,以概述带动场景,同时伴有叙述者的议论和评说。当然不仅仅是开头部分如此。整篇《陈奂生上城》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也不仅仅是《陈奂生上城》这一篇小说如此。这其实是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基本方式。
概述和场景这一对概念,我借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石昌渝。在其他一些研究者那里,概述又被称作叙述、转述,场景又被称作描写。我觉得,石昌渝的命名相对来说更妥贴些。在《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中,石昌渝论及了人们陈述某一事件的不同方式。人们对某一事件的陈述,大体上可分为讲述与呈现两种方式。讲述式虽然也不妨以第一人称进行,但常见的是第三人称。在讲述式中,事件中的人物没有宾白和对话,其言行举止,都由叙述者来讲述。人们以口头的方式讲述一件事时,通常是用讲述式。民间口传文学,也多用讲述式。至于呈现式,自然也有叙述者的讲述,但人物的言动,却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呈现式的叙事中,人物时而在特定的时空中对话或独白,在特定的时空中“自由自在”地活动。当人物在特定的时空中“自主”地活动以至一些细枝末节都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就形成了场景。石昌渝说:“这样,呈现式的叙事就包括两个成分,一是概括叙述,叙述者或者直接由作者担任,或者由作者找一个代言人来担任,概括叙述介绍人物事件的背景,把所有场景之间的空白填补起来,也就是连结所有的场景,使之成为连续的而又有一定节奏的情节,概括叙述有时还对人物事件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评论。另一个成分是场景,场景是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持续进行着的事件,场景是由人物的行动和人物的对话构成的,它很像戏剧的一幕。中国古代史传有客观的记事记言的传统,叙事方式一般采用呈现式”。②
呈现式叙事,由概述(概括叙述)和场景两部分构成。在概述中,叙述者仿佛在牵着人物走;而在场景中,叙述者则像是跟着人物走。现代小说,大都是呈现式的。但同为呈现式叙事,概念和场景的关系、概述和场景所占的比例,却各各不同。有的小说家更喜欢用概述的方式,于是其小说中概述就占着更重要的地位,叙述者的声音也就更强烈。有的小说家更习惯展示场景,于是其小说中场景就有着更突出的地位,小说也具有更强烈的画面感和戏剧性,叙述者的声音则更为隐蔽和微弱。从理论上说,概述与场景在具体作品中,可以有着千差万别的关系。一部小说中概述与场景有着怎样的关系,往往也就对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产生明显影响。一个小说家,习惯于如何处理概念与场景的关系,常常也就表现出其特有的艺术个性。重视场景的细致展示,着力使小说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和强烈的戏剧性,是现代小说家普遍的选择。像高晓声这样偏爱概述的小说家,是不占多数的。在高晓声小说中,叙述者总是牵着人物走的。高晓声小说中,很少有大段的场景展示,场景总是“适可而止”。以概述带动场景,同时夹杂着议论、评说,高晓声的这样一种小说创作方式,我以为与他从小熟读《聊斋志异》有关。
石昌渝在《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中,对《聊斋志异》的文体有所说明。石昌渝指出,《聊斋志异》在文体上既承袭了传记文,也借鉴了白话小说。《聊斋志异》某些作品的开头仿效了白话小说的“入话”,某些作品则仿效白话小说在叙述过程中插入诠释和评议。③蒲松龄在继承史传文体的同时,又借鉴白话小说的技巧,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在《聊斋志异》中,往往有鲜活的场景展示,但叙述者的声音始终是强劲的。叙述者总是以概述、诠释和议论,主宰着整个故事。可以说,蒲松龄创造了一种“聊斋体”。正是这种“聊斋体”深刻地影响了高晓声的小说创作。高晓声自己也多次谈到过少年时代读《聊斋志异》的经历。例如,在《曲折的路》中,高晓声说:“不久抗战开始,家乡沦陷,小镇上时时有鬼子来捣乱,不及乡下安稳,我就又回到了乡下家中。这时学校也没有了,我父亲就在村子上办私塾。我开始接触文言文,记得父亲教我的第一篇古文,竟是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之后我就爱上了蒲松龄,《聊斋志异》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我家里有一部版本很好的《聊斋志异》,在不懂的词语下都注有解释,我几乎就是靠了这本书学通了文言文。”④少年时代喜欢的书,少年时代读得烂熟的书,必定在后来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少年高晓声喜欢《聊斋志异》、熟读《聊斋志异》,在学通文言文的同时,也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蒲松龄讲故事的方式。
二
对农民心理的揭示,是高晓声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要准确地揭示农民心理,必须能体察、把握到农民心理中那些最本质的东西,那些最能体现农民精神特征的东西。高晓声对农民心理的揭示往往让我们惊叹,这说明他的确捕捉到了农民性格中某些很具有典型意义的方面。总在算账、总在算细账、总在算小账,可谓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惯常的心理活动。贫穷,这是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生活状态。这使得精打细算,成为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一种精神特征。在高晓声的时代,农民仍然在继承了祖祖辈辈接力棒一般传递下来的贫穷的同时,也继承了祖祖辈辈接力棒一般传递下来的精打细算的本领。中国自古流传着这样一句“人生哲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周一世穷。”如果说这种哲理适合于历代的所有中国人,那对历代农民而言,就更是颠扑不破的至理、真理。所谓“吃不穷,穿不穷”,当然不是说不妨随心所欲地吃穿。这应该看作是为了强调“算计”之重要而做的一种修辞术。对于农民来说,所谓“算计”,主要就表现为在吃穿二事上的“缩”与“节”。要总是吃得很饱、穿得很暖,是不可能的。谁要是图一时享受而尽情地吃穿,那就是不会算计,其结果便可能冻饿而死。所谓“算计”,说穿了便是数米而炊,便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有坚持半饥半饱,才能免于饿死;只有总是穿得不太暖,才能免于冻死。所谓细水长流,说的也是这意思。水只有很“细”,才能长流不息。代代相传的贫穷,使得掂斤播两、锱珠必较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手段。历代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在算账一事上表现得往往最典型。那些较为殷实一点的人家,总是特别会算的人家。这样的人家,总博得“会过日子”的美誉。高晓声对农民的这种总在算账的心理状态,有极精细的表现。在高晓声的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高晓声对数字是十分敏感的。在他的小说里,账目出现得十分频繁,而且数字总是很精确。前面说过,概述在高晓声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概述,就意味着不必很精确、毋须太细致。高晓声小说在概述其他事情时,也的确符合“概述”的定义。但在概述到账目、数字时,却总是精确、细致得令人惊讶。例如短篇小说《水底障碍》中,有这样的概述:“又有一次,一位面孔比屁股还大的人物娶媳妇,一开口就要一百二十斤鱼,指定日期来取。那一天,张雨大领了两只船出去捕捞了大半天,回来只有十五斤四两,来人火冒三丈,骂开了山门。”张雨大是故意只打很少的鱼。在这种时候,鱼的实际重量,毫无很精确的必要,用“十多斤”来概述便可以了。别的作家,在这种场合都会如此处理的。然而,高晓声却将让这数字精细到“两”。但又不能不说,总体的概括性叙述中,忽然冒出这么一个精细的数字,显得别有意味。再例如中篇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这样开头:
陈产丙今天挂牌游大队了。大家已见过世面,见怪不怪了。谁都说不定也会有这一天嘛!
全生产队一共二十九户,十一年来挂过牌子示过众的,已有过一十八名,涉及十六位户主。原因各有不同,总括起来,一概属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你做动力就做动力,需要你做对象就做对象,决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细算起来,平均每年还不足一点七人;全队男、女、老、少一百三十个,按这个比例,每人轮到一次就要七十七年,啊,漫长的岁月!叫人想着好不心焦呀!
如此精确的“概述”,让人忍俊不禁。这是“文革”期间的事。社员陈产丙冒犯了大队书记陈宝宝,陈宝宝便令陈产丙挂牌游乡。在叙述陈产丙的故事前,高晓声先让叙述者算了这样一笔细账。这是叙述者在算,也可以看成是叙述者在替陈产丙算。这实际上是在向读者说明陈产丙被罚以挂牌游乡时的心理状态。这样的算账,让读者感到的是对这种处罚的调侃、嘲讽与轻蔑。账算得越细,调侃、嘲讽与轻蔑的意味便越强烈。
高晓声那些特别著名的小说,那些最为优秀的小说,往往通篇都在算账。算账,甚至成了小说的一种结构性因素。在发表《陈奂生上城》之前,高晓声先发表了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漏斗户”主》。这篇小说不如《陈奂生上城》影响大,但它比《陈奂生上城》更让我感动。《“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勤劳能干,但家中却长期缺粮,背着一身粮债,于是总在算着粮食账。小说表现了陈奂生的苦难、委屈,表现了陈奂生的凄惶、无奈,表现了陈奂生的困惑、迷茫,表现了陈奂生的本分、怯懦,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次次的算账得以表现的。例如,小说中有一次的账是这样算的:“可是有一点,只是一点点,陈奂生却又着实不满。大家明明知道,双季稻的出米率比粳稻低百分之五到十,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替农民算算这笔账。他陈奂生亏粮十年,至今细算算也只亏了一千三百五十九斤。如果加上由于挨饿节省的粮食也算这个数字,一共亏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以三七折计算,折成成品粮一千九百零二斤六两。可是十年中称回双季稻六千斤,按出米率低百分之七点五计算,就少吃了四百五十斤大米。占了总亏粮数的百分之二十三。难道连这一点都还不能改变吗?”只有长期背负粮食债的人,只有天天算着粮食账的人,才能对粮食的事情如此清楚。只有总是饿得发昏的人,才会对关于粮食的账目如此敏感和清醒。只有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粮食上的人,才能把粮食账算得如此精细。高晓声以这种方式,精确地揭示了陈奂生的心理状态,也以这种方式准确地控诉了那个荒谬而残酷的年代。
《陈奂生上城》之所以大受称道,是因为人物性格刻画得好。这篇小说中的“陈奂生”,的确具有了某种典型性。不妨说,高晓声也主要是以算账的方式完成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陈奂生上城》,也几乎通篇都在算账。《“漏斗户”主》中的账目虽然精细,但“账种”却很单纯,只有粮食账。《陈奂生上城》中的“账种”却要复杂些。陈奂生上城是为卖油绳。卖完油绳,高晓声便让陈奂生算账:“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如果说这样的细节已很精彩,更精彩的还在后面:“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主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这是一顿饭与一斤块块糖之间的换算了。历代农民,在生活中常常要以物易物,换算也就成了农民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不善换算的人,是难免要经常吃亏的。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让陈奂生不停地换算着:“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差阳错,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这里的换算就很复杂了。陈奂生上城是为卖油绳。卖油绳是为买帽子。于是,帽子的价格与房钱之间,便自然形成了换算关系。陈奂生是农业社员,挣工分是他换取报酬的基本方式。工分值与房钱之间,当然不能不换算一番……在这种有条有理的换算中,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陈奂生鲜明起来、丰富起来、光彩起来。
说实话,读《陈奂生上城》,我感到了高晓声的“刻薄”。——当然,是作为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刻薄”。
三
读高晓声小说,时时会与账目相遇。高晓声小说的叙述者,常让人觉得像是一个乡村会计,总在以算账的方式向读者说明着各种因由、恩怨。高晓声时常以算账的方式引出话题,又以算账的方式推动情节发展,还以算账的方式让故事达到高潮。尤其他的那些较好的小说,总在“摆账目,讲道理”。
像《“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一样,《李顺大造屋》也是以一串又一串的账目完成故事的讲述的。《李顺大造屋》是这样开头的:“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这可谓是一开始便把读者引入一本账簿。这堪称一本“血泪账”。土改以后,李顺大就立志要盖起三间瓦房。在其他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到1957年的时候,李顺大竟然真的备齐了三间瓦房的材料。这在其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李顺大果真做到了。李顺大能做到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又并非因为他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有着其他人难以做到的节俭和勤劳。高晓声习惯于以概述的方式讲述故事。李顺大全家节俭和勤劳的过程,也基本上是以概述的方式讲述的。以概述的方式讲述农民的节俭与勤劳,容易显得空泛,容易失之于一般化,因而也就不容易感动读者。这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动,小说也就基本上失败了。高晓声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较为空泛、较为一般化的说明与很精细很特殊的账目结合起来,从而着墨不多,却又让李顺大一家积攒造屋材料的过程催人泪下。“从此,李顺大一家,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是非常微小的,但他们完全懂得任何庞大都是无数微小的积累,表现出惊人的乐天而持续的勤俭精神。”——应该说,这样的概述是比较空泛的、一般化的。如果仅以这样的概述来表现这一家人的勤俭,那也只能给读者以模糊的印象。但叙述者紧接着还有这样的盘算:“有时候,李顺大全家一天的劳动甚至不敷当天正常生活的开支,他们就决心带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盈余。甚至还有这样的时候,例如连天大雨或大雪,无法劳动,完全‘失业’了,他们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从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也无非是用米做的……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才吃。”小说的叙述者,在拨拉着一把算盘。这盘算很小,小到算盘珠只有黄豆粒那般大。在这拨拉声中,这家人的生活状态具体起来、清晰起来。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缺盐少油。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中有着缕缕血丝。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积攒着一砖一瓦、一椽一桁。这积攒着的一砖一瓦、一椽一桁上,也就都有着血丝。这样,当这些带着血丝的砖瓦椽桁在“大跃进”中被征收、被糟蹋时,才让我们分外悲痛、愤怒。
不仅在第一次的积攒材料过程中,叙述者的算盘一直响着。在此后的叙述中,算账也仍然在继续。《李顺大造屋》的叙述者,是用算盘完成他的工作的。高晓声许多小说的叙述者,手里都有一把算盘。《柳塘镇猪市》、《水东流》、《送田》、《太平无事》等小说中,账都算得极其细致。这当然并不是说,算账是高晓声小说表现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唯一方式。有些细节的刻画,没有借助直接算账的方式,也很富于表现力。例如《“漏斗户”主》中有这样一段:
陈奂生越来越沉默了,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他从来不叫苦,也从不透露心思,但看着他的样子,没有一个人心里不清楚,他想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粮食。有些黄昏,他也到相好的人家去闲逛,两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产生“他吃过晚饭没有?”的猜测,由衷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而他则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让主人关门睡觉。这样的时候,总给别人带来一种深沉的忧郁,好像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他的饥肠辘辘声。
陈奂生把主人的心坐酸了。高晓声把读者的心也写酸了。这样的细节,让我惊叹高晓声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心灵的洞察。而如果对农村和农民没有相当的了解,恐怕也不容易读懂这种细节。陈奂生经常忍饥挨饿,他甚至连晚饭都不吃就到别人家里闲坐。但是,他决无蹭饭之意。正因为如此,在人家窥破他肚中的秘密后,便立即起身离去。别人可怜他、同情他,但却无力帮助他。因为谁家都不容易。谁家都闹粮荒,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真有那种不缺粮的人家,却又是陈奂生这样的人决不能去闲坐的。主人的轻微叹息里,有怜悯,更有无力帮助的无奈。这是在哀叹陈奂生,也是在哀叹自己,是在哀叹那时所有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而听到这哀叹,陈奂生“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说明他虽然在挨饿,但并未丧失自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细节虽然没有直接借助算账的方式,但仍可听见算盘声。陈奂生在人家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可以想见,他又在心里算账,算着粮食账。我们仍能听见他心中的算盘和他的饥肠一起在响。
陈奂生决不会蹭饭,他只会借粮。他关心其他人家的粮仓甚至甚于关心自家的米缸。自家的米缸反正年年亏欠。自家反正年年要靠借粮活命。而他人的粮仓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他借粮的难易与成败。《“漏斗户”主》中的另一个细节,把陈奂生的这种心态表现得很精彩:“这也罢了。偏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来。公社派到生产队里来的那位‘包队干部’……为了争取产量达到一千斤,稻子轧下后不晒太阳就分给了社员,等到晒干可以上机加工的时候,一百斤只剩下八十九斤,面对这个事实,陈奂生毛骨悚然,他不愁自己少分了粮食,而是担心这样一来,大家的口粮更加紧张,他就更难借到了。”自己的粮食即便不“少分”,也还是不够,也还是要借。借粮,是陈奂生维持一家生命的基本方式。因此,能否借到粮,才是更值得关心的。这样的细节,让陈奂生的窘境纤毫毕现。——当然,在这里,我们又听见了算盘声。
让我们再回到《聊斋志异》。前面说过,以概述带动场景,同时夹杂着议论、评说,高晓声的这样一种创作小说的方式,明显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能说写的是“聊斋体”的小说。必须故事情节本身也与《聊斋志异》相似,方可称为“聊斋体”。而这样的“聊斋体”小说,高晓声也写过一些。《钱包》、《尸功记》、《鱼钓》、《飞磨》、《钱结》、《忧愁》、《外国话》、《希奇》这类小说,则可看作是对《聊斋志异》有意识的仿效。这些小说,篇幅往往都很短小,其中虽没有秋坟鬼唱、月下狐鸣,但故事本身都具有某种离奇性、荒谬性、神秘性。《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高晓声写的是现代白话小说。然而,高晓声的白话小说中,却冷不防会冒出几句“聊斋体”的文言。例如,《尸功记》在用现代白话叙述四类分子被逼挖出王老七尸体时,突然出现这样一段:
终于,头未坌开而尸出矣。遂取绳索,捆而吊之如死狗,连夜送火葬场。冬天夜长,事毕,迄未破晓。
在前后的白话中,突然出现这样一段文言,只能说明高晓声实在按捺不住模仿蒲松龄的冲动。这段文言后,又恢复白话叙述。但在结尾,却又是这样一段:
王老七竟因此使熟悉他的人常常想起他。此人高矮适中,身材微嫌单薄;脸庞小,形长圆;鼻子、嘴巴,小而精巧,似聪明相。走路时身体前倾,脚步重,眼睛特有精神。精力有余,脾气极好,常帮社员干零活。有事请他,招之即来;不受酬金,供饭、烟便满足。习惯迟睡,夜里往往找未熄火人家昂然破门入,点点头,坐片刻,或抽一支烟,或帮做一回工;然后笑笑又离开。尔后数年间,凡社员夜作,若有人蓦地推门,还常以为他来了。
小说就这样结束。这段话,从行文上说,可谓不文不白、不伦不类。对《聊斋志异》的模仿却是很明显的。“昂然破门入”这样的表达,颇得《聊斋志异》神韵。当然,更能显示《聊斋志异》影响的,还是以寥寥数百字写活一个人的本领。小说写的是王老七死后本已被土葬,但公社却一定将其尸体挖出火葬。王老七在小说中只是一具尸体。他生前如何,本无关宏旨。一直到王老七遗体被挖出火化,小说都并未介绍王老七生前行状。这本也用不着介绍。实际上,小说写到遗体送火葬场,也就可以结束了,这最后一段文白夹杂的话,从结构上说,纯属多余。高晓声之所以会来上这么一段,应该理解成是没有控制住“技痒”。这“技”是从蒲公松龄那里学来的,高晓声禁不住要炫耀一下。这段话不到两百字,却把王老七的形象刻画得很鲜明,可谓栩栩如生,颇得蒲松龄真传。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例如小说《鱼钓》中,会出现这样的叙述:
……即使是真正指挥百万大军的英明统帅,对这样普通的技术问题,也难免偶或忘之。若评历史功过,又焉能涉及若是之末端!所以,精明如刘才宝,也难免犯千虑之一失。没有桥,是极简单的事实,刘才宝决不想临时造一座。
在用现代白话叙述时,高晓声会突然来上一两句“聊斋体”的文言,说明《聊斋志异》对他的影响实在很深。
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对高晓声有如此评价:“虽有少数作品流于琐碎,显得过于随意,但从总体上看,其小说创作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方面居于承前启后的位置。”⑤少数作品的随意,也可视作是《聊斋志异》的“负面影响”。《聊斋志异》在篇幅上、文体上,都是颇有几分随意的。从篇幅上说,《聊斋志异》有的作品长达数千言,有的则短至数十字。从文体上说,则既非正宗的“笔记”,亦非正宗的“传奇”。所以,有人说蒲松龄是用传奇小说的匠心写笔记小说,有人则说他是以笔记小说的手段写传奇小说。⑥至于那“异史氏曰”,一般在最后,以此总结全篇,但有时也置于开头,用来引出故事。如果高晓声小说创作中有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这种缺憾,那这也要归咎于《聊斋志异》。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注释:
①见《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②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2月版,第154页。
③⑥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2月版,第220页,第215页。
④高晓声:《曲折的路》,见《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23页。
⑤见《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