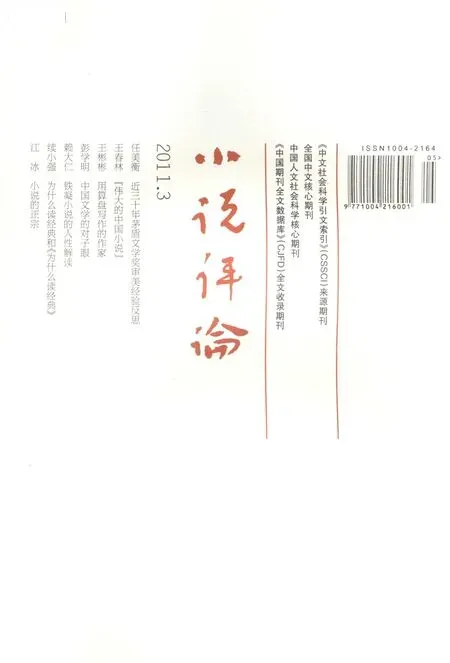近三十年茅盾文学奖审美经验反思
任美衡
近三十年茅盾文学奖审美经验反思
任美衡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茅盾文学奖逐渐形成了部分基本的审美特征,如叙事视角的多元化,正面的价值取向,新现实主义的多边拓展,史诗叙述的精神化,等等。在当代文学不断“世界化”的过程中,这些叙事质素也进行了内在的冲突、裂变和复杂的自我构型。它们交流、对话,不断地衍生、革新,也容纳着别种质素的“介入”。与时俱进既使它们与母体葆有深在的精神联系,又不断地拓展着主体的现代性。从第1-7届获奖作品来看,尽管这些基本的审美特征具有某种意义的“艺术核心”作用,但并非是对茅盾文学奖美学的限制描述,相反,却显示了茅盾文学奖对艺术的宽容与有机选择精神。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尽管它们不断地“新陈代谢”,甚至不乏深在的“哗变”,但却概括并表征了近三十年茅盾文学奖的审美走势,值得关注。
一、有选择的“全知叙事”及变奏。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茅盾文学奖力倡“多样化”的评奖理念,并在具体的评奖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实现。但综观所有的获奖文本,我们发现仍是“有章可循”的。如在叙事方面,评委会出于对茅盾本人及创作实践的尊重,追求文学“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全面反映”的“百科全书”之效果,使全知叙事成为茅盾文学奖主导的叙述形式。
从部分获奖文本来看,这种全知叙事的叙述人有时是权威而主体的,“他”有着上帝般深邃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向着“读者”讲着故事,有着不容置疑的“卡里斯马魅力”,仿佛是真理、人类、民族或者权力的“代言人”,并且喜欢有意识地打断故事进程,在关节处“爱发议论,教诲色彩浓厚,可发的议论并非出自机杼,而是社会通行的伦理准则或道德格言”,或者是具有教益性的人生感悟。①他有着绝对的叙述权力,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策略需要,改变叙述焦点和设置叙述障碍,形成赵毅衡所说的“跳角”效果,或者热奈特所说的“越界”现象,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入场”。如《将军吟》《沉重的翅膀》《黄河东流去》《抉择》《英雄时代》,仿佛是叙述人在安排生活、历史和社会的逻辑与秩序似的,一切都那么“合情”,可一旦遇到“不合理”处,叙述人就慷慨放言。这种“权力”曾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与效仿,但也遭到了不少诟病,如某些批判者所说:由于叙述人过于生硬、频繁地干预情节,以及浓厚的说教味,可能会使读者难于忍受,取消故事的真实感,即希普来所说的会失去读者对情景的接受力、生动性和亲切感,从而令人对文学产生信任危机。
也有这种情况,就象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的,作者“退场”,或者叙述人站在“隐含作者”的立场进行讲述。“他”是“中性”的,仿佛是一个“导游”,带着读者经历文本与人物世界,自己却不发一言。一般来讲,“他”并不自由,通常守在一个叙述焦点上。但“他”又是非常尽责的,陪着读者上天入地或者进入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且和读者保持适当的“距离”,绝不“介入”读者的态度与选择。它使人物与事件都呈现在“前台”,增强小说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如《东方》《钟鼓楼》《白门柳》《战争和人》《湖光山色》。其中,《张居正》无论写主人公在政治方面的铁腕手段,在权谋方面的无穷智慧,在生活方面的侠骨柔肠与贪财好色,对人生悲剧的预感与无可奈何,以及明代后期的社会风俗人情,作者都不动声色,一一道来,让读者身历其境又浑然不觉。不过,这种事实与身历其境之效虽然容易产生令人震撼的穿透力,但也可能会因语言信息的拥挤和想象力萎缩导致叙述的自动化与平庸化。
杨义在考察我国叙事文学时认为,在动态的操作中,全局的全知往往是由局部的限知合成的。他说:“讲话人首先必须和他叙述的人物视角重合,讲起来能够口到、手到、眼到、神到,他采取的往往是限知的角色视角,角色变了,视角也随着流动,积累限知而成为全知。”②在某些获奖文本中,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有时也交错杂呈,取长补缺又相得益彰。或者采取第一人称,如《尘埃落定》在部分扇区,“我”表现得一无所知,只以儿童的眼光打量人间的种种情事,宗教、权力、战争和女人,这样就提升了文本的神秘、空缺与诗性之美,也内在地增加了叙述的旋律感和音乐性。或者虽采取笫三人称,但作者往往以人物行动为中心,对于与他无关的事物通通略去,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所见、所思、所行都被完整地“呈现”但又局限在“个人”的范围之内,如《暗示》就是通过安院长、钱之江、施国光、韦夫以及金深水的眼光呈现了事态的整个过程,“内透视”与“外透视”互相流动旋转,不停地产生悬念,直接生动紧张,有时甚至幻化出多种“视角”效果,令人目不暇接又层出不穷;同时又可延长审美感受并唤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使他们可以充分领略、欣赏事物并陶醉于体验与感受之中。
在获奖文本中,客观叙事也是主要的叙述方式,它与限知叙事一起构成全知叙事的两翼。布斯认为,“艺术家不应该是他的人物和他们谈话的评判者,而应该是一个无偏见的见证人”,保持“中立性、公正性、冷漠性”。③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戏剧式”或“叙述者<人物”。在理论层面,它追求对象的精确性并力求仿真,追求话语与现实的等同;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化虚为实,把生活与事实仿真化,如《茶人三部曲》——这部具有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就有着明确的“书记官”意识,在多方面追求厚重的历史感和事实的精确性,抵制虚构或者想象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苦难以及历史经验的修辞,有着浓厚的实录倾向和认知要求。或者尊重事物的客观逻辑并予以自然呈现,如《历史的天空》对梁必成的成长过程,在很多地方忠实于人物命运,不虚美,不隐恶,作者仿佛一个电影放映员,一旦开机,屏幕中的人物就按照自己的生命逻辑活起来了,谁也无法干预。或者通过行动与对话把人物形象化,以集体无意识的姿态进行叙述,形成“在场”,如《东方》对郭祥的恋爱与生活就过于公共话语化,我们无法窥见或者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也可以说,他是行动的人而非精神的人。实事求是地说,这种“零度叙述”因它的真实性会增强读者的信任机制,并保持读者的冷静与理智,但也可能因客观化而间接地阻碍双方的交流,最终导致文学与人的同时退场。
当然,进入茅盾文学奖多姿多彩的文本世界,我们还会发现诸多标签了中国特色的叙述质素,它们无限地丰富着长篇小说的修辞诗学。其中,以独特的全知叙事为主导,以限知叙事和客观叙事为补充,它们共同地形成了茅盾文学奖基本的叙述框架;这些质素既有机融汇又此消彼长,不断地造型又不断地变革,在这种移形换景之中,茅盾文学奖也不断地拓展了自己的叙述风格及其美学。
二、正面的价值取向及可能性。无论是第一届评奖所要求的“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还是《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所要求的“弘扬主旋律”,以及贯穿每届评奖实践的思想标准,都对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规约与要求,核心在于不遗余力地倡导正面价值。
在当前,这种正面价值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精神,一是新人文精神,如雷达所呼吁的,当今文学亟需增强从正面影响人、塑造人、建构人的精神能力,亟需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亟需明辨是非的能力。④它既立足于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跨文化与跨语际的视野中,关注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与人、科技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种种关系,以便促进人的现代化,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现代人格,⑤如《骚动之秋》《英雄时代》《抉择》《秦腔》《湖光山色》;又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关注如何思考与实践人的存在与意义,以及有关善与恶、生与死、爱与痛的人生问题,以便消除异化,回归自我,真正地实现人的本质。二是新时代精神,也就是茅盾文学奖的与时俱进精神。它既指茅盾文学奖关注时代主潮,也指获奖作品在叙述重大社会变革、历史事件与人的生命选择之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现代性”立场:一方面通过形象,实事求是地表现它们的历史遭遇与进步精神,一方面又从当今的需要出发,充分挖掘它们对时代精神的丰富与增值。三是新中华精神,这不仅指茅盾文学奖对内通过“人”的现代化发现民族的灵魂,对外通过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重铸着崛起的中国形象;也指它不再以他者为镜像但并不否认西方,以东方为主体但并不拒绝批判与否定;还指它以本土性的和谐来取代现代性的对抗,以个体伦理来补充集体的道德,从及时跟上世界潮流到积极地参与世界进程,以整个民族的独特性、包容性和主动精神来构筑人类与世界的普遍的价值体系。
不可否认,茅盾文学奖对正面价值的实际倡导与理想的效果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潜在地弱化了它在当今的“影响力”,不过也从这些基本的价值层面促进了茅盾文学奖的审美重构:
ⅰ、功用性。这种功用性并非是指茅盾文学奖作为具体的“工具”为某项具体的政策或者任务服务,而是如“条例”对主旋律的“概括”: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等等。
ⅱ、文学之“真”。由于深在的“百科全书”情结,所以茅盾文学奖特别注重那些能预测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趋势,并通过人物命运、重大变革和其它事件的“前因后果”来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的作品。因此,“真”几乎成为它的价值基础。如《李自成·简介》就认为,作者试图全面展现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场景,并通过各种艺术形象使读者得到较为广泛的历史知识;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为原则,通过明末李自成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的规律。当然,茅盾文学奖也难以规避它与“真”的内在冲突,如某些获奖小说的部分情节就不是严格地从事实、从人物性格出发来推动故事逻辑,而是根据“正确的理论”予以说明和阐释,这就导致了叙述本身的不可靠,如李自成在某些地方就被认为有拔高之嫌疑,这无疑会损害它的艺术完整性。
ⅲ、“善”是文学的道德意义,与“恶”相对。近三十年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当代文学在走向“自由化”之时,也走入了道德失范的种种误区,如某些文学津津乐道于血腥的暴力场面、不问是非冤冤相报的仇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江湖规则”,甚至完全泯灭力的正义与非正义、人性的善与恶、道德的好与坏之界限,容忍并助长着“恶”的倾向。茅盾文学奖在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的拷问之时,也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基调,大力建构符合社会需要的现代道德,如《平凡的世界》《抉择》《英雄时代》《骚动之秋》《湖光山色》对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之境遇下,人们该如何处理义与利、个人自由与集体伦理、公平与正义、真知与信仰等问题作了深入地辨析、批判与取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鉴照。
ⅳ、在哲学方面,“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客体对象中合乎人性的实现或对象化,它表示的是人的活动及其成果同人的本性的一致,或者说是对人的自由的肯定形式。⑥在文学的价值取向方面,它可以表现为“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充满无限美感的艺术形象和感人肺腑的情绪仪式,其中,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而言,它主要是指“人性的全面发展”,也包括文学对“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东西、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的病症以及龌龊、残忍与乱伦等病态人格进行本体性否定。从茅盾文学奖来看,它对“人性”进行了真诚的预期并力求有效地拓展,如四姑娘许秀云的本然、纯朴以及不乏野性的“乡土性格”,《无字》鞭辟入里地呈现了自私、冷酷、不负责任等人性之“丑”,《钟鼓楼》《东藏记》在如缓缓流水般的诗意之中,展示了由农耕文化所熏陶的朴实、善良、乐观、血性、温情、本真等“人性晶体”。以“美”为镜,茅盾文学奖对人性的表现是万殊的,“在路上”既使它们充满不竭的动力,又与“真”和“善”密切地联系,并融为一体。
在茅盾文学奖之中,正面的价值取向还体现了不少独特的表征,如对时代与社会积极的参与意识,从注重“事”的发现转向“人”的创生,精神资源的多元化,以及对娱乐、消费、启蒙、宣传、教化等价值的理解及深化。一方面,在对各种价值整合的过程中,茅盾文学奖越来越趋向意义的自觉;一方面,面对着价值的泛化,茅盾文学奖也在不断地遭遇“难题”:如何与意识形态对接,如何处理负面价值系统的主体性与杠杆意义,如何对待正面价值的相对性?这些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有限”与“无边”:新现实主义的拓展及冲突。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茅盾文学奖与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复杂关系,只要深入获奖文本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尽管没有出现激烈的“理论交锋”,或者断背式的创作反叛,但它所“积淀”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部分“质素”,仍然真实地“缩略”了“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一方面,它纵向地经历了理想性现实主义、批判性现实主义、个人化现实主义的精神转换及其“变形”,对客观世界的描述由追求“形似”转向重在透视生活本质的“神似”,⑦一方面,它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若干性质“变革”也使茅盾文学奖美学在“合力”之中越来越走向“主体化”。
ⅰ、1978年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学也多方面地重构了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茅盾文学奖深在地表现了这种变化:一是文学反映现实变得主动化了,甚至根据主体与社会的需要进行“有意味地选择”,如《平凡的世界》;二是由于审美主体的出身、经验、才能等素质各异,所以他们的“现实感觉”也出现了“哈姆雷特效应”,“印象”成为文学审美的基础、动力与对象,如《尘埃落定》;三是把现实部分地“当下化”,即从生活实践本身来表征“现实”的本体精神,它自主、鲜活、能动,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外而呈现为无限的本然状态,如《秦腔》;四是把现实部分地“虚无化”,通过“人”的存在境遇而“绝对化”彼岸的灵魂世界。总之,对现实的种种理解,无疑使茅盾文学奖对现实的审美视角、技术及效果发生了种种改变。
ⅱ、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思潮、方法及手段更新的宏大背景之下,茅盾文学奖也接受并促进了现实主义基本元素的变革。在情节方面,许多获奖文本突破了线性的时间逻辑与整体的空间秩序,对时空结构进行打碎并重新安排,顺叙、逆叙、插叙、预叙等叙事方式交互错杂,形成当代独特的叙述诗学,如《钟鼓楼》的桔瓣式结构、《无字》的蒙太奇手法,遵循着心理逻辑,打乱、重组物理世界的先后自然承接关系,形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在人物方面,茅盾文学奖首先把人还原到生活本身之中,从日常的角度来审视人的存在,大力祛除人的概念化、符号化及其意识形态表征;其次努力突破人的心理限制,深入到人的灵魂内面,即非理性和潜意识方面;再次,提升主要人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使之哲学化,如白嘉轩、吴为、傻子二少爷、王琦瑶、陆承伟、杭嘉和。在倾向性方面,茅盾文学奖在追求主旋律之时,也追求无主题变奏,如《少年天子》个人悲剧与历史障碍互相纠缠,象线团一样牵扯不清。在冲突方面,茅盾文学奖追求事物的辩证法,力求符合历史的基本规律并以合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历史的天空》就如实地讲述了主人公艰难的成长过程及其必然性。它们共同地形成新现实主义的“本体特征”。
ⅲ、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时,达尔安·格兰特认为,在批评术语中,由于现实主义独立不羁又富有弹性,不能以内容、形式或者质的方面的任何描述加以限制,所以既靠不住又值得怀疑。⑧不过,这也说明了现实主义有着无边的包容性,可以与其它学科或者对象嫁接,形成新的艺术形式,如《东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之朴素现实主义,《无字》之心理现实主义,《钟鼓楼》之日常现实主义,《历史的天空》《李自成》《暗算》之传奇现实主义,《尘埃落定》之魔幻现实主义,《骚动之秋》《英雄时代》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恨歌》《都市风流》之大都会现实主义,《芙蓉镇》《秦腔》之乡土现实主义。不过,不管艺术形式如何改变,是否具备对现实的深层关怀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根本依据。这种深层关怀既包括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也包括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但关键在于文学是不是在关怀人的本身,即关怀人的心灵在遭受着来自政治、科技、商品、金钱、权力、话语暴力等因素的逼压、摧残与异化的真实处境及其摆脱困窘之努力。⑨茅盾文学奖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如《骚动之秋》《湖光山色》就描述了岳鹏程、暖暖等人在绝对的权力、不规范的经济关系和残酷的市场竞争的挤迫之下人性和道德的沦丧、精神的炼狱。尽管宏大叙事让这些作品承载着过多的意识形态任务,但这些人物无疑是它们的叙事焦点。
ⅳ、茅盾文学奖的深层关怀也体现在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里有对人物弱点、缺陷和堕落的深刻呈现,它们既让我们引以为戒又激起我们的愤恨,如郑百如、王秋赦、鹿子麟等人;这里有对丑恶社会现象的大胆曝光,它们既让我们正视人心的黑暗和社会冷酷的潜规则,又让我们体会无穷摆脱与宿命抗争之矛盾和冲突,如《抉择》就潜入了李高成的内心深处,追索他的选择因由、徘徊与决断;这里有对历史的反思,如《张居正》对改革的代价及其意义所作的估衡与描述;这里有对现实阴暗面的内在剖析,如《英雄时代》对权、欲、金钱的相互交易及其对社会公平与秩序的破坏。不过,由于茅盾文学奖持守着传统的和合精神,所以这种批判也欠缺应有的锐气。
ⅴ、茅盾文学奖的批判性也并不影响它的理想精神。在获奖文本中,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有一种根柢性的精神存在——它让人在黑暗之中看见光,在失败与沮丧之时看见希望,在恶践踏着社会的公平与秩序之时看见正义和善良;这种理想也让我们执着地相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尽管工作组被撤了回去,但金东水仍然对社会主义事业满怀信心并为葫芦坝设计了近期和远景规划;《黄河东流去》《茶人三部曲》《额尔齐纳河右岸》则让我们触摸到民族强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现实主义与茅盾文学奖由此实现了“共生”。
韦勒克说过:“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它可能并不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而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又肯定会同各种不同的特征,过去时代的遗留,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各种独具的特点结合起来。”⑩所以,我们无须否认茅盾文学奖与现实主义实践之间的差距,如陈建功所说,由于某些作品的思想欠缺深度与厚重,茅盾文学奖在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上,在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上,在对历史环境的营构上,还显得不够;所以,茅盾文学奖亟需从经典性出发,处理好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分解裂变状态,处理好文学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从多元化文学发展格局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美学”。⑪
四、“规范”与“精神”:茅盾文学奖深在的史诗情结。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来之后,面对着众多的质疑与争议之声,终审评委曾镇南这样认为:由于茅盾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他的长篇反映的就是时代,为时代描绘出广阔的社会画卷,因之,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不可能与茅盾对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要求及追求风格相背离。⑫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情,但从所有的获奖文本来看,“史诗叙事”确实成了茅盾文学奖的“潜规则”或者基本的审美特征。
不过,这种史诗叙事又并非完全等同于“有头有尾地描绘了生活的长河”之“茅盾经验”,也非完全渊生于“用诗的语言记述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徒、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规模比较宏大的民间叙述传统”,⑬甚至还突破了它的“现代模式”,如人们常常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优秀长篇小说称作史诗。其实,这种史诗叙事既积淀了上述史诗文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又在创作与评奖实践中不断地拓展着新的表现形式,并大致呈现为这样几种类型:
ⅰ、重客观写实的“现代史诗”。假若我们不过于苛刻的话,可以把大部分获奖作品归入其中,包括《东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自成》《将军吟》《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白门柳》《张居正》《茶人三部曲》《秦腔》。这些作品在创作观念上普遍认为,文学就是对生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攫取现实世界的一鳞半爪予以印象化或者扫描,而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深入时代与社会,进行宏观的叙述,通过众多人物与广阔场面的辩证法凸现出历史的合力及发展规律。因此,它们讲究巴尔扎克式的冷静态度、百科全书式的创作视界和精雕细刻式的场景描述。它们所反映的是具有“节点”性质的关键事件,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和风细雨,在情节与故事深处,总是内在地涌动着主体的情感与忧愤,并诗意地贯穿全文。如《平凡的世界》就被雷达认为是“史与诗的恢宏画卷”:作者“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⑭其实,评论界对《白鹿原》《张居正》《茶人三部曲》的核心评价,也大多是从这些方面展开论述的,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观念、创作到评介来看,这些作品几乎都有某些的基本规律可“循”。当然,也无需否认,它们在形成了茅盾文学奖独特的叙述特征之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审美的单调与重复。特别是史诗变成作家潜在的文学范式,创作就变成了史诗的“填空”,而非寄托著作者心血、生命与经验的“创造”了。正如朱伟对《白鹿原》的评价:“在《白鹿原》中,我们感觉到的是陈忠实的生命形态被他所要寻找的形式与框架不断的阻隔。这种阻隔的结果,使他的生命形态在其中越来越稀薄,最后就只梨下一大堆材料艰苦拼凑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⑮
ⅱ、“心灵史诗”的“再现”。这种心灵史诗,既吸收了苏联20世纪“70-80年代”小型史诗、《诗经》的周民族史诗、屈原的《离骚》以及现代派文学经典的艺术精神,又深入百年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与历史实践,表现出了与现代史诗若干不同的叙述“创新”:即高度地浓缩与概括生活。按照艾尔雅舍维奇的说法,就是实践了“大规模集约化”的文学叙事。如叙述视角由过去的“非聚焦型”转向“内聚焦型”,承担者往往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它有利于敝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并通过这种心理活动来反映历史和现实。⑯叙述时间则采取了闪回、闪前、重迭、交叉、压缩或者扩张手法,使时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无限的绵延与轮回中,化解主人公的现代性焦虑,赋予他们永在的生命意识和自觉的主体性;在空间方面,无论是宇宙之大还是粒子之微,无论是客观的存在还是日常想象,都被重置了它们的常规秩序,空间的整体性支离破碎,在叙述中飞舞,并多方面地环绕着主人公;时空交错,形成非线型的立体结构,它超越传统的复线类型,既在多种可能之中表现出无限的开放性,又使情节淡化,不以高潮与悬念取胜。
心灵史诗不完全“束缚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它也广阔地追求平民的百味人生与生老病死,并在咀嚼与体验之中,引发对生命的哲理思考,有的文本甚至呈现出浓郁的寓言与象征意味。如《无字》隐在的叙述人——“我”与“吴为”是部分重合的,作者以吴为的人生为主线,既讲述了她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描摹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色人等的与世浮沉、坎坷人生,展现了百年中国的风云际会,并通过独特的记录与审视,写出了一个说不尽的时代;⑰又渗透了作者饱经沧桑的精神创伤,对生命境遇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刻探究。《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讲述了卾温克族人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它是作者与之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18总之,心灵史诗的出现,不仅仅是突破了传统史诗的形式束缚,在更深的层次上,它还突破了传统史诗的思维障碍,即在保持史诗的基本原则之时,它还“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生命活力。
结 语
从理论上来讲,作为一个面向未来、追求“多样化”的第一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不能重复,正如陈忠实在《白鹿原·序言》中所说,无论是重复别人还是重复自己都令人悲哀,也会导致艺术创作的萎缩。然而,由于共同的文化语境,总体的审美原则与精神追求,文学传统的运行合力,以及整个社会所积淀的平均接受心理、水平和视界等因素,都使茅盾文学奖在评选实践之中又延续了某些基本的审美特征。尽管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遮蔽甚至损害茅盾文学奖的丰富性,但在内部,这些因素既没有断绝与外界的文学交流,又不乏与时俱进地自我更新。因此,在看似“平静”之中,茅盾文学奖不断地“融入”当代文学潮流,这种“融入”不但改变着茅盾文学奖的外在特征,而且还深入到它的思维逻辑,使之形成了开放的审美体系。当然,这些由传统所积淀的基本的叙事形式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质疑并阻碍着当今的文学创新,使某些优秀的文本暂时得不到认同而被拒之门外,从而留下“遗珠之憾”,使茅盾文学奖显得保守而招致严厉而苛刻的批判。不过,正是在这些张力之中,茅盾文学奖困苦而又坚定地开拓了自己纷纭复杂的审美旅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反思”。项目编号:09YJC751023,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茅盾文学奖研究”项目编号:09B018)
任美衡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211、221-223页。
③[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5-98页。
④雷达:《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个发言提纲》。《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⑤蒋述卓,李自红:《新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⑥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⑦李运抟:《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三种精神类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⑧达尔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⑨雷达:《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⑩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征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⑪王冠:《现实主义:当代文坛的新惊喜》。《文学报》。第898期。
⑫曾镇南:《孰是孰非“茅盾文学奖”》。《深圳商报》。2000年9月17日。
⑬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程郁缀主编:《文学百科大辞典》。华龄出版社。1991,第557页。
⑭雷达:《史与诗的恢宏画卷》。《求是》。1991年第17期。
⑮朱伟:《史诗的空洞》。《文艺争鸣》。1993年笫6期。
⑯单之旭:《视角、时空与结构——苏联70-80年代小型史诗叙事手法分析》。《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
⑰张洁:《无字·内容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8迟子建:《额尔齐纳河右岸·授奖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