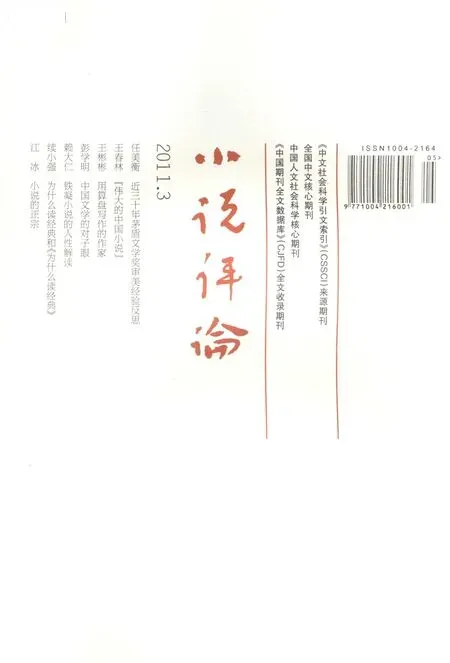何英的锋芒与视野
雷达
何英的锋芒与视野
雷达
新疆年轻的女批评家何英,其尖锐鲜明的批评姿态,冷静出色的判断力,幽默泼辣的话语方式,连同支撑着她的扎实的理论根柢,以及善于学习,默默耕耘的勤奋品质,使她的出现被看作一个奇迹,一簇闪光。
的确,除了偶尔进京到鲁院学习过一回,何英很少抛头露面,一直坚守在新疆。熟悉她的人觉得,作为一个出生在新疆的异乡人,一个由兵团子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她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以相夫教子为乐,安静,踏实,没有怎么显出“学者相”和争辩欲。她的样子更像是一位劳动妇女。可是,你真要把她当作一个北疆的农妇,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早就在磨“自己的剑”,貌似质朴,内藏刀锋。她一旦写起文章来,能熟练地运用整套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新语,她可以对全国一些重大文学问题和重要现象作出令人惊讶的评判,她尤善于感受和渲染文坛变幻莫测的气象,对一些风头正健,踌躇满志的作家,她发出的质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绝非扮酷。她的声音是内行的,富于学理的,打中要害的,却又布满了芒剌。人们会奇怪,她是在什么时候掌握了那么丰富的信息,暗藏了那么多绝妙的、尖利的、有趣的想法。
我以为,在今天的文坛上,出现何英这样人物的机率仍然是比较小的:现在固然信息发达多了,但地域——不但是空间上的,却也是心理上的间隔,还是制造着困难,何况是遥远的新疆;现在固然早已是男女平权的社会了,可是,作为一个女性,要在边地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哲学研究一类行当,又不在高校,要坚持下来,委实不容易——既要跨入“全国的”言说竞技场,又要逾越“女性的”身份和心理障碍。
然而,何英并不是以一种即兴式的、印象式的写法崭露头角,也不是以一种小聪慧偶露峥嵘。她的从事文学批评,理论准备相对充分,充分得出人意外。在《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等综合论述当代文学发展的批评文章中,她能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以一个处于文化研究中心位置者的自信和从容谈问题。其实,这些文章都写于新疆。这些文章在《小说评论》《文学自由谈》发表后立即引起反响,前者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者被多家网站、杂志转发。她的另一论文《王安忆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得到了苛刻的上海批评家们的称赏。《文学自由谈》一度是她的主要园地,她在那里臧否人物作品,时有锋锐之见。在那里,她是继李美皆之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批评家。
批评家之间在深度与广度上,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并不缺少就事论事的评判者,缺的是能发人之所未发,能打通现当代或中与外,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视野比较广阔的人。对于何英,我最欣赏的,首先还是她对时代与文学之关系的某些深度思考。她能清晰地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看法,有些看得还相当准。比如,她剖析了所谓“理论过剩”现象。她说,我们的理论果真到了过剩的境地了吗,事实是,现代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过剩只不过是引进、运用西方理论的过剩。当代文学在理论的引进和运用上的过剩实际上反映出自身理论的饥渴与贫乏。引进的理论正在脱离本土经验而显现出意义踏空的理论游戏化。这是当代中国理论的特征之一。
在她看来,当理论与作品不能相互融会,相互激发时,理论往往呈现出意义的虚无。她发现,现在理论本身已成为某些理论家的象征资本,这个象征包含着一些确定的头衔、某所著名的大学、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等等,这些资本如期货一样在市场里以货币的形式流通,某种程度上说,现今最活跃的某些理论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资本,貌似科学严谨地制造出一批批理论商品,而这些商品也正显出过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症状来。
这些话比较尖刻,却并非无理,于是,她看到了某些庄严事象背后的可笑之处,有如戳穿皇帝的新衣。她并不反对“现代性”这个术语,但却指出:“现代性”这个词儿,刚出来的时候满天飞舞,好像什么都可以套上现代性,鲁迅自然是现代性的了,那么沈从文就是反现代性,张爱玲则可以是被压抑的现代性那一路,总之学界的论文一派现代性,后来出了几位“后主派”,一意高扬后现代,宣称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也便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意思。没想到哈贝马斯一句:现代性远远还没有终结,又被哈贝马斯专家们发掘出来大大地发扬了一番,于是现代性又复辟了。现在关于这个词的言说也仍然一派混乱各说各的,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授都难以说清到底什么是现代性,考博要是出了这个题目,考生只有诅咒出题的人了。
再比如,她对以“后”的集体称谓方式来划分作家代际的命名方式的批评,也是尖锐的。在她看来,这种代际划分法一下子深入人心且大有正式演变成文学史言说方式的架式,仔细想想十分滑稽。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这种集体化的分期也不会是作家所愿,哪个作家愿意跟别人放在一个集团里来讨论评价,抹杀忽视创作个性不说,谁又会和谁的写作真的那么类似?因而她判断,这种称谓法必将是速朽的。她不无调侃地说,自“80后”新闻化、娱乐化之后,这一称谓移用漫延到各个领域,成为可以任意使用的媒体符号之一。70后作家在这样影响的焦虑之下,还要面对80后市场媒体双受宠的新局面,他们要在哪里找到自己?不由人不替他们叹惋:前面的辉煌让先锋占尽,后面的风头让80后出光,两大光团之间的黯淡却属于他们。然而,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她问的好!当我看到今天的文坛上,人们仍然以“后”为言说的重要依据,讨论得十分庄严,甚至已经溢出了代际划分所本有的那么一点点认识价值时,我并不认为何英显得多么孤单无助,相反,我觉得她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清醒者。
何英对万花筒般急遽变化的当代文坛现状的描绘,是富有幽默感的,读来常使人忍俊不禁。也许她有一种天生的善于捕捉、描述和概括的才能。她自创的“十个词组”,什么“空虚时代”、“突然沉默”、“道德正确”、“追新至死”啦等等,俏皮尖刻,嬉笑怒骂,往往能说到点子上。谈到文坛风景,她的出语总是清新。比如,“我们在学人家的时候,把自己丢得太干净。血液里灵魂里的东西都渐渐忘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成功地将自己蜕变异化成一种亚西方文化的产物,其间的几次断裂都堪称前无古人,每断裂一次,我们新变一次,也丢掉一次。”。又如,“一切可资利用的都在被转化为商品,作为商品的文学不再能摆出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大家最终的去向都是市场;而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在这个浮躁甚至狂躁的时代也早已失去耐心,短、频、快的出书策略既是作家的主观选择,也是读者喜新厌旧的接受条件使然。这是一个读者主导口味的时代,读者有时候被出版商的炒作忽悠,被众多的冒牌排行榜欺骗”。此类话颇为精彩,与我的观察不谋而合。我在机场、火车站,闹市等人口流动最大的地方的书店里,常看到正被码成垛儿大肆推销的图书,许多是并无道理可言的,却占住了高地,人们就只好买他的书。孟子里的“垄断”一词就是这个意思。总之,这些地方的进货渠道完全被人垄断了,他给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这些人实际上左右着今天大众的读书趣味。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面子文化、人情文化无所不在,即使最桀傲的人,也没法抵抗它的束缚,有的人正在痛斥别人讲人情,可一陷入具体情境,他同样摆不脱人情的控制,形成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何英似乎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一个隔离层,使她很少顾及批评对象,能发出相对自由的、锐利的声音。作为批评家,何英有自己坚守的衡文尺度,而这尺度是变动不居的,具有现实感的,有活力的。例如,她很强调如何确立小说叙述的“信”,一个“信”字是她最看重的,但也并非事实的真实之谓。她说,那些学来的现代、后现代叙事,学得再好,短期内也不可能转化生成为纯粹中国的叙事。它们没有根基,即使生出一些根须,也不牢实不壮大,这也是为什么先锋文学演变成了一场小说的语言革命,而实质上的革命内容却被忘记或丢弃了,后面没有自然附着上精神与灵魂的语言游戏自然难以真正打动人心。所以她认为,到《生死疲劳》为止,我们看到的莫言小说,不论他怎么动用中国元素玩地道的中国故事,实际上还是一种西方小说框架里的叙事结构和形态。总之,她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苏童,闫连科,残雪等人的批评,各各不同,却也不无参考价值。
密切关注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及时给予总体性评价与总结,并能客观解析几个典型作家,是何英近年来写作劳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赵光鸣的抒情性的辨析,对董立勃的悲情叙述和简约风格,刘亮程的新疆时空观,对新秀李娟的散文,都有切实的解析,但对他们各自的问题却毫不容情,态度是冷静而客观的,没有发生对外酷评,对内谀评的自我分裂。她在《当代新疆小说的叙事困境》中的一段话,深得我心,不妨一引:“新疆的当下与全国一样,现实生活前所未有地复杂多样,既有土得掉渣的民粹的内容,也有洋得跟内地沿海无甚区别的全球化,还有不洋不土的县城生活,有既传统又不乏现代的牧区生活、还有全国惟一的兵团农垦生活……。面对这些现实生活,作家已不可能躲在家里想像编造一些符合内地人心理的新疆、或原始荒蛮的与现实脱节的新疆,如何表达出现时态的真实、而不是夸张的传奇,是新疆新一代作家努力要上的台阶。在边地传奇、荒蛮落后的咏叹调或牧歌式作品的绝对数量中,是否也应该有大量城市题材或其它类型小说的出现,追求小说种类的多样化的同时,提升纯文学、严肃文学的形式品质。”
边地新疆出现了何英这样有生气、锐气、才气的青年女批评家是令人高兴的。任何人都只能是自己塑造自己,谁都难以越俎代疱,要求她以后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何况在今天,做一个批评家是很难的。从这部书稿来看,何英的评论实践涉及面较广,既有宏观批评,也有个案细读,既有建构性的解读,也有解构型的批评,对当代女作家研究和新疆文学研究似乎占去了更多的篇幅,但她又一度沉迷于《红楼梦》人物论的写作。我看,不管今后她的兴趣在哪里,只要像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是有胆识的,批判精神应该是他的第一性。这是一个理论家本应持有的最基本的专业道德。倘能一直坚持下去,可以无憾矣。
雷达 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