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吴越》:“黏板”的艺术
/[山西]韩石山
《千年吴越》:“黏板”的艺术
/[山西]韩石山
释题
题名中的“黏”字,不能读作“年”,也不能读作“占”(很长一个时期,黏简化为粘),要读作“然”。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这个读音,陕西关中一带肯定是有的。我老家晋南,与关中仅一河之隔,比如西安有种面食,叫黏面,就不能说是年面或占面。
再说黏板。这也是个别处不会有的词儿。还是那句话,关中一带会有的。晋南的地方戏叫蒲剧,关中一带的叫秦腔,都是那种高亢悲怆的腔调。唱者的行腔,主要靠一种型如扁鼓,名为板的打击乐器伴奏。比如起唱,谓之叫板,跑了调叫走板(成语“荒腔走板”即取此意),整出戏唱完叫翻板。不管是须生、老生,还是青衣,如唱得兴会淋漓,老乡不会说如醉如痴什么的,而说唱得黏板。意谓,其声调与板的打击声相颉颃,如同附着在板的声音上一样。
一个出生在晋南乡下的穷书生,要说清读了一本书的感受,光题名就得解释这么一大串,借用赵本山先生的腔调说声“悲哀啊”,该是最恰当的感叹。要叫司马迁知道了,写进《史记》,一定会说“北蛮夷之鄙人”怎样怎样(《史记》中说秦舞阳的话);要叫当今北京城里的大教授知道了,一定会笑话“偏远省份”的人就是这么没有文化。然而,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一个更文化的词儿来说我读了《千年吴越》的感受,只能这么笨拙,这么偏远。
这对愚夫愚妇,就有这么股子犟劲
《千年吴越》,作者刘炎平、解艾玲。全书八十八万字,分上下两册。
两位作者系夫妇。艾玲是医学专家,长期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做研究工作。炎平也有自己的事儿。夫妇俩未赴美前,在太原这个小小的省城,我们是时相过从的朋友。炎平当年已是颇有声名的青年作家,艾玲在自己的领域里,声名亦不在其夫君之下。按说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攀不上这样的高人的。落魄人也有过发迹的时候,只是前后颠倒了而已:中学时我曾上过晋南一所最好的中学,且比刘、解二位还要高出一个年级。一个人的好运到中学即止,上帝的这种公道,只能让人报以苦笑。有了中学校友这层纠结,远赴美利坚之后,仍时有电话问讯。早就听说两人合力完成了这部巨著且在国内出版,一直盼着早日拜读,直到辛卯年春天,炎平才托人送到舍下。
七事八事的打扰,总算细细地通读一遍。几天来情绪仍在书中,难以自拔,也就难以落笔,今日忽然开了一窍,马上坐在桌前扯过键盘。写作也如同逮鸟雀,手一松说不定就会跑掉。
既是一部历史小说,总得先说史料多么丰富,搜集又多么艰辛。如果是明清史,各家文集,野史家乘,多不胜数,这么说了会有人信。然而,名为《千年吴越》,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春秋时的事儿,吴越楚晋诸国的成败纠葛,说史料多么丰富,搜集多么艰辛,可以骗愚騃,蒙不住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吴越的史事,就是加上与楚晋诸国的交往,见诸《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的文字,满共不会超过五千个汉字。要搜集这些资料,在一个不大的图书馆里,以我这半瓶醋的水平,用不了两天的时间。若我说用了三天的时间,肯定有两个半天的时间是站在路边看过往的老少美女。
然而,凡事架不住一个人有了广事搜罗、求全责备之心,那就跌入一个无底洞里。吴越争斗的正经史料不多,但是,后世以此为题材,写小说、诗歌、戏剧者不知凡几。说是连篇累牍,说是汗牛充栋,一点也不为过。而这对愚夫愚妇,就有这么股子犟劲,非要将之尽数搜掠到手不肯罢休。搜掠不比劫掠,劫掠只要踩好点,可毕其功于一劫,而搜掠,掠只是极言其贪,功夫全在一个搜字上。只是搜书不比搜索枯肠,肠子再曲折暗昧,再盘绕重叠,不出胸之下髀之上那个小小的皮囊。搜书,尤其是僻书,那可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仍难见。可怜两个薄命人,容易搜掠时,尚在史籍如海的大中华,搜掠艰难时,已身处一粟在海的美利坚。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用了十数年之功,总算如愿以偿。仅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吴越争锋题材的小说戏剧作品为例,就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穷搜旁绍,务期完备了:
顾一樵的四幕话剧《西施》(1932年)
梅兰芳演出的京剧剧本《西施》(1940年前后)
萧军的长篇小说《吴越春秋史话》(1952年写成,1980年出版)
曹禺等人的五幕话剧《胆剑篇》(1960—1961年)
谭诗军的五幕话剧《勾践复国》(1971年)白桦的七场诗剧《吴王金勾越王剑》(1994年)杨善群的纪传体小说《顶尖人物》(1994年)李劼的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2002—2003年)董云卿的长篇历史小说《西施》(2003年)
加上古代的诗歌、志怪、说唱、演义,尽数入于囊中。且一一认真看过,细细分析研究。有借鉴也有规避,有沉潜也有升华,化腐朽为神奇,汇众妙于一心。又精心结撰,反复修订,务臻至善,始成今日之模样。《自序》中有一段话,说得最是透辟,不妨一看:
这部书是抄来的——抄自历代史籍的零星记载,诸子百家的驳杂论述,以及汉唐以来同类题材的文艺创作。有道是抄一个人的叫剽窃,抄众家的称研究,品评名家乃学识,无中生有属创新。本书虽然诸毒俱全,却仍算得上一部以吴越史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们也期望读者将它视为一部企图集众家之大成,彰显一己之异声的尝试之作。
这段话,大可揣摩,一是可以看出搜集材料之夥,二是可以看出立意之高,自负之甚。还可以看出行文之洒脱与机警。
写出了声响,和这声响带出的气势
材料搜集之夥,并不一定能保证一部小说的成功,更多的时候,恰会带来叙事的繁冗与累赘。是有益还是有害,端看作家有没有超越材料之上的神思结想,有没有曲折达意的生花妙笔。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是不是能达到黏板的艺术境界。
吴越的历史,虽有数百年,激烈的争斗,不过集中在两代人数十年之间。吴越的位置,偏处东南,因为牵涉到楚晋之地,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假定那时已有了中国的版图)。而事件中的人物,主要是两国的国君,各自身边的一班文武臣工,就是加上什么划船的渔夫,浣纱的西子,对这样漫长的时间,这样广阔的空间来说,如同空旷的舞台上跑着几个小如芥籽的人物,纵使战车千乘,冠盖如云,也不过是蚂蚁搬家,只见一条黑线慢慢蠕动。
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却也正是历史小说书写者必须跨越的壕堑。越之则生,坠之则亡,没有什么可借助的器具,唯一可依凭的只有自家的身手。
结体上,也算挖空了心思。全书用倒叙法,不是从吴国攻越开始,而是从越国复仇搭笔。与此相适应的则是,章节倒排,从第一〇〇章始,往后回溯,写到第〇〇一章。再就是,书中多数人物,均给了新的装扮,赋予多重的性格色彩,配以相应的举止言谈。用作者的话说则是,很难一语道尽他们的好坏:为君者不只有昏明之别,为臣者亦不仅具忠奸之辨;坦坦君子常藏难言之隐,戚戚小人时有可炫之德;尖酸刻薄者不乏忠厚之举,作恶多端者每陈悲悯之词。即使是坏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物,也都让他有表述自己“非为不可,不为不行”的堂皇理由,绝不刻意美化圣人或丑化“贼坯”。
用心固然良苦,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也不过是惯常的路数,未跳出“小说作法”的陈腐窠臼。若以行窃而论,只能说是穿墙逾户者流,江洋大盗者看不上眼,飞檐走壁者不屑为也。
拨动我的心弦,叩击我的心扉,或许是作者无意间达成,却最为我心仪且心折的,是几乎每个重要的章节,都有一处或几处写出了声响,和这声响带出的气势。充斥着这寂寥空旷的历史舞台,撼动着这吴越之地的山峦河川。这才是作者的大手段,这才是这本书的大境界。声响不光是金戈铁马的呼啸,也不光是刀枪剑戟的撞击,更多的是人物的谈笑声口,举止神态,一句话,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
不必说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还有范蠡、文种、伍子胥这几个重量级人物了,且看勾践夫人与美女西施的摹画,就知道作者是怎样的匠心独运。西施是几乎每部小说、每台戏剧,都要着意编排的人物,不必说了,而勾践夫人如此浓墨重彩的书写,可说是此书的一个创举。
不必责怪过去的写作者,勾践夫人这位女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典籍中的记载均十分简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竟简略到只有“夫人自织”四字。或许正是史籍的简略,给了我们的作家以更为丰盈的想象空间,也让他们写作的才华得以从容地施展。多方设色,精心描绘,使之既有端庄淑贤之美,又有深谋远虑之智。最重要的是,写出这个女人的复杂性,多重人格与复杂性格。鄙视勾践,还是为之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倾慕夫差,此人却是她与丈夫的生死仇敌;暗恋范蠡,身份所限不得不将这份情感压在心底。书中将她在这三位男子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一一展现而又绝无割裂之虞,举止得体,分毫不爽。看书的过程中,我甚至担心,这样的拿捏,该是怎样的严谨,又是怎样的率意,稍一不慎,鄙视便是厌恶,倾慕便是投靠,暗恋便是淫荡。一着之失,全盘皆输。万幸万幸,我是捏紧了手,却没有流出了汗。
这位国君夫人,与西施的关系最是微妙。作为端庄自负的女人,对清水芙蓉般的西施姑娘,不无嫉妒之心,作为复国大业的幕后策划者,对这位负有重要使命的乡间女子,只有多方训诫,诚心安抚,以求万无一失。且看她与西施的一段对话(将动作神态描写略去):
西施:“夫人在吴王面前还护着大王,要是吴王不高兴,该怎么办?”
勾践夫人:“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在一个死心塌地护着自己丈夫的女人面前,任何男人都会理短三分的。哪怕这个丈夫……”
西施:“你在那么艰难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护着大王,大王一定会报答你的。”
勾践夫人:“不说这个了,咱们还是说你到吴国的事吧,西施,记着我的两句话。”
西施:“我听着,你说。”
勾践夫人:“别怕见吴王。见了吴王你就知道了,任何男人在吴王面前都会露出他的短处的。吴王的长处没人能比。”
西施:“第二句呢?”
勾践夫人:“到了吴国什么都不干,专心专意服侍好吴王。只要让吴王知道全越国的人都像你一样忠于吴王,对吴王好,就行了。”
“什么事都不干”,正是身处虎穴,达成目标的箴言。一有了功业心,做事便不自然,总有一天会被吴王觉察,一旦觉察,不说西施本人如何,复国的大业就全泡汤了。这正是勾践夫人的过人之处。与丈夫勾践,也有几句既见心机也见情感的话,太长,不抄录了。
看的过程中,我在想,这些精彩的对话,定然是炎平和艾玲夫妻两人,在他们的卧室或书房里,一一模拟人物的动作声口,务其毕肖,务其精彩,然后将之落在纸上或电脑上。又想,要是多出一个人物呢,暂且以一把椅子代替其位置吧,随之炎平或艾玲过来接上说话。而在这方面,艾玲这个灵慧女子,更有其性别与心机上的优长。只是我想象不出,若夫差与勾践同时在场,炎平怎么一会儿扮演残虐的夫差,一会儿扮演阴狠的勾践,真也难为这老实人了。
不管用了什么样的手段,都得承认,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书中西施、勾践夫人等女性人物形象,是鲜明的,也是丰腴的,是多重的,也是浑然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好的文章,应当如丽人出行,身佩琼琚,仪态万方而叮当有声。那是以丽人出行来比喻好的文章,借用在这儿,不是说文章之美,乃是说美人之美,不管性格如何,使命如何,西施与勾践夫人,本身就是美人,有了这声口,有了这些举止,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些各自隐秘的心事,其出行也,真是身佩琼琚,仪态万方而叮当有声。
长于女性人物的描写,可说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我有个偏见,一部长篇小说,若写不活一个或三两个(多了不可能)女性人物,就是一种最大的失败。事件如骨骼,男人如筋络,女人如血脉。写好女人,成功的不仅是女人,男人不再是单纯的男人,顿时便有了阳刚之气,事件也不再是单纯的事件,顿时便成了有情有义,生机勃勃的生活场景。写不好女人,没有血脉流淌全身,只剩下单纯的事件,单纯的男人,难怪整部作品只会是干硬的骨骼,干瘪的筋条。可以做重棰,可以做响板,却难以奏出丝竹之音。
《千年吴越》作者的着力之处,肯定不止此一端,而成就了作品“黏板”艺术,使之达到一种较高境界的,不能不首推几个女性人物的精心设置。
文化密码与历史的律动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千年吴越》这部小说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据说有上千部。可是真正像小说的小说,或者说起了小说作用的小说,为何寥寥无几呢?赶紧补上一句,我说像小说的小说,起了小说作用的小说,不是指那些能上了大学讲堂,或是能让评论家写出精致文章的小说,是指那种真正能让人当“闲书”翻看,消磨时光的小说。
不能说这些作家不用功,也不能说这些小说就不好,只是说,他们的功没有用在这上头,在这上头不够好。
当代长篇小说究竟缺了的是什么?
不必作繁复的论证了,一言以蔽之,缺了的乃一种内在的历史的律动。从阅读者这边看,或许更为显豁。我们的身上,有种自远古一代一代积淀下来的文化密码,一切阅读的暗中的动力,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便是寻求与这种密码相契合的历史的韵律,也即是历史的律动。《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小说,文字并不怎样的优美,手段也不怎样的高明,为什么一拿到手,就能看个津津有味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里面的那种历史的律动,与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密码有叠合的地方。它的事件离我们很远,但它的历史的律动,恰与我们精神的脉搏一同翕张。许多作家的失败在这里,少数作家的小说获得意外(实为意内)的成功,也在这里。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檀香刑》,均可作如是观。
文化秘密与这种历史律动的契合,或许才是“黏板”艺术的根本所在。
《千年吴越》成功,就在这里。只是两位作者,太喜爱篇帙的宏大,一写就是八九十万字,多少会伤害读者的接受情感,不能说不是一个不大也不算小的遗憾。举重若重,固然恰如其分,举重若轻,能说不是另一种高明?
2011年6月7日于潺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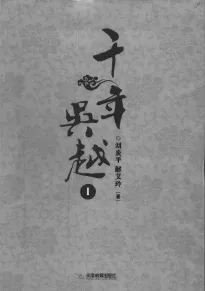
《千年吴越》,刘炎平、解艾玲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2月版,定价:120元
作 者:韩石山,作家,学者,有著述多种。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