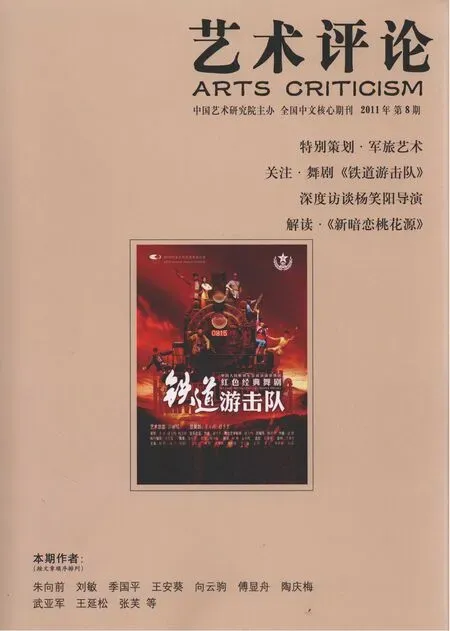希区柯克的应答——但要去问齐泽克
孙 柏


本文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与阐释的关系,它聚焦于希区柯克电影与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积极而富于创造性的互动之上。当然,关于艺术作品的阐释(批评、分析、理论化的努力)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让我们从希区柯克的一句口头禅说起。
“这只是一部电影!”
希区柯克的这句口头禅,曾被广泛地征引,以用来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艺术作品反对阐释。
尤其在大卫·波德威尔等“后理论”的倡导者们看来,电影研究中的理论偏执与阐释狂热,主要应归罪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所产生的后果严重的影响。的确,1970年代以来,以精神分析为主导的电影批评就把希区柯克的电影当作是理论操演的最佳场地,而像《后窗》、《精神病患者》、《鸟》等伟大作品似乎也不负理论家们之所望,为凝视、俄底浦斯轨迹、厌女症、镜像阶段、缝合等精神分析(以及女性主义)的关键词或核心议题源源不断地提供例证。以希区柯克的理论释读而确立学术地位的研究者不乏其人,像罗宾·伍德、威廉·罗斯曼、塔尼娅·莫德莱斯基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也正值电影研究学科化、机构化的高峰,作为理论队伍后备力量的电影学硕、博士生们也纷纷跟进,围绕希区柯克展开各种讨论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以汗牛充栋来形容绝不为过。可以说,希区柯克在电影学界享受的待遇,正堪比文学研究领域的莎士比亚。然而,理论的兴盛进入1980年代已尽显疲态,电影学科机构化的负面效果也很快暴露出来(不无讽刺的是,波德威尔本人的学术取向恰恰是这一学科机构化的典型例证)。原本富于创见与活力的理论思考开始流于僵化、狭隘,此前精神分析与希区柯克电影之间的积极对话逐渐被套路化的思维定势和理论话语所取代,电影研究乃至整个的人文学科正为一种新的学术拜物教所笼罩。——当你看到这一时期贫乏而又臃塞的希区柯克阐释的时候,很难不产生“审美疲劳”之感;每当此时,希区柯克自己的那句口头禅就会不自觉地袭上你的耳际:“这只是一部电影!”
照这样看来,希区柯克阐释可以休矣……
不过,如果我们据此就得出结论,认定艺术作品反对阐释,以为这就是希区柯克对待理论或者电影严肃性的回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希区柯克这句话唯一不能说服的,就是他自己。这句口头禅来自希区柯克的工作现场,他身边的人都十分熟悉,大师总是用它来安抚他的合作者,从普通技工到大牌明星概莫能外。对此感受最深的要算是英格丽·褒曼了,她经常来找希区柯克,神经兮兮地向他表示对自己能否胜任她的角色缺乏信心,或是面对某一细节处理不能从容应对;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希区柯克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她:“这只是一部电影!”——然而,唯一一个无法接受这一安抚、无法借此轻易化解内心焦虑的人,就是希区柯克自己。他越是故做轻松地对自己施加这样的暗示,就越是说明他所面临的困局之严峻。[1]这难道不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吗?仿佛执著于电影这件事本身的情感力量太过强烈,而不得不通过贬低它来获得释放。但这样的态度又会引起另一波的情绪反弹,也就是说,会因为有意贬低它(某人倾尽一生之所爱)而深感歉疚与不安。这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需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以至成为一句口头禅的原因。希区柯克对待电影的这一态度——即这样轻描淡写地打发他戮力毕生之事业——不正符合拉康关于焦虑的定义吗?焦虑是由于主体太过靠近小客体、太过靠近欲望的客体-成因而引起的。换言之,焦虑就是主体面对他的曾经失落的欲望对象,而踌躇于坚持与放弃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是处在积蓄与释放之间的情感能量,是永远无法彻底解脱的挣扎与决定的时刻。“这只是一部电影!”显现的,就是希区柯克之于电影的焦虑时刻,他在那里遭遇和逃避他的欲望。
希区柯克之实在界
既然莎士比亚都读过拉康,希区柯克一定也读过。难怪齐泽克建议我们,想要了解有关拉康的一切,应该鼓起勇气去问希区柯克。[2]我们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只是一部电影……”然而,希区柯克的这一应答——关于电影,关于阐释,关于他自己——就是实在界的应答。他这句口头禅,完全可以被置换为一个拉康术语的肯定句:“这就是实在界!”
那么,何谓实在界?简单说,实在界是在主体形成过程中,交付、抵押给符号—社会秩序的原初欲望客体;但实在界并不能直接作为实体而存在,它只是符号性去势造成的主体自我与欲望客体的创伤性分离留下的空洞;因此,实在界首先应被理解为匮乏、否定和彻底的空无,符号界为维持现实的幻觉一致性而始终致力于将这一匮乏抹销和排除,但也正因此反而使之成为抵制符号化过程的不可化约的核心;从实在界对符号界的抵制中,在实在界与现实的对立中,一种激进的快感得以产生。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实在界的理解,其要点在于:实在界自身并不具有本体论的一致性,而是只有在回溯性的效果中才能获得实体化的显现。——在与符号界的复杂关系中,实在界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显现:一种是作为创伤性的回归,一种是作为对符号界的应答。所谓“创伤性的回归”,是指被社会—符号秩序从现实表层抹除的否定性存在,以幽灵般的方式回返并宣示它们的权利,它们闯入现实,它们的爆发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平衡,像污渍一样弄脏了“完满”的社会图景。与这一充满激进色彩的形态不同,实在界还可以其纯粹的偶然性来印证符号—社会秩序的必然,从而为我们既定的生活现实提供支撑,确保符号性交流的实现,这样的“一小片实在界”即构成对符号性质询的应答。
当然,拉康关于“实在界”的讨论是非常复杂和缠绕的。要想彻底廓清这一概念,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不断递增的补充论述中去。这是由实在界自身的含混和暧昧所致,它关涉的是对那一根本性的匮乏予以实体化的各种(不)可能性的争夺……
所幸,我们还可以去问希区柯克。实在界的回归与应答的各种形式,无不在希区柯克的作品里获得了体现。例如,希区柯克中前期的电影就提供了实在界应答的两种客体:著名的麦格芬和用实在界的碎片来充任的主体间交换客体。前者如《三十九级台阶》中的发动机图纸,《贵妇失踪案》的密码乐曲,以及《美人计》中装铀的酒瓶——它自身并无意义,只是一个空洞的空间、纯粹的表面,其唯一任务就是发动故事。后者如《电话谋杀案》中的钥匙、《疑影》和《后窗》中的戒指、《火车上的陌生人》中的打火机等,它们表现为碎片化的“一小片实在界”,因为失去了在符号网络中的合适位置,它只能在对立的主体之间流转。当然,实在界应答的更典型例子出现在《申冤记》和《西北偏北》中,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因遭误认而被迫卷入到运转着阴谋或罪恶的符号界中去。而在其伟大的后期作品中,希区柯克常常调用一些没有出处、也无从解释的景物,来充当创伤性的、不可能之快感的实体化表征:如《鸟》中的鸟、《艳贼》中横陈在街道尽头的废弃船体,《晕眩》中女修道院的参天大树,以及在《西北偏北》结尾的拉什莫尔山达到极致的一系列影片中的巨大雕像——它们就是拉康所说的菲勒斯或原质,它们的出现往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骇性的效果,系由剩余快感的过量涌现所致。它们像污渍一样出现在电影的画面上,彻底扭曲了“现实”的时空,使之不再透明。
如果被要求用最简明的语言来总结希区柯克电影无以穷尽的迷人魅力,齐泽克一定会说:它们搬演了实在界与现实的对立——这正是后期拉康的理论核心。它集中体现在希区柯克后期伟大作品的几个颠峰时刻,那也是齐泽克倾尽其理论热情反复予以论述的:《鸟》和《精神病患者》中的凝视作为小客体。与“标准的”精神分析电影批评不同,齐泽克强调凝视是在于客体这一方。在“标准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凝视就是无所不在地笼罩和监控着我们、作为大他者的代理向我们发出质询的目光,主体只能通过认同于凝视(在电影中,观众是经由对剧中人物和电影摄放机器本身的二次认同)进入符号—社会秩序;而在经齐泽克阐发的后期拉康这里,凝视虽然确实是促成现实虚幻一致性的那幅焦点透视图景上的没影点,但在那一点上弥漫的空洞、空白也正是大他者及其主体建构中需要抹销和排除的匮乏所在,它恰恰勾划出实在界的场域,在那里,凝视会作为小客体、原质和污点,简言之,就是作为实在界的某种物质化而获呈现。
《鸟》中出现在博加德湾上空的“上帝视点镜头”,是齐泽克最喜欢引述的一个例子:在那部影片中,鸟本身就是作为母性超我的快感化身而出现并扭曲了现实空间的;在博加德湾加油站陷入一片火海之后,希区柯克用了一个大远景的鸟瞰镜头来表现那触目惊心的场面,当观众以为这只是司空见惯的表现整个场景的客观镜头的时候,群鸟从摄影机后方悄然进入画面,使之完全变成一个代表着邪恶上帝的主观视点镜头。这一手法在《精神病患者》中的运用更为丰富和系统:当死者的姐姐莱拉走向汽车旅馆对面神秘的哥特式房子时,那所房子竟然也在“看”着莱拉(凝视在客体一方);私人侦探被杀那一场戏,先是在一个俯拍的客观全景镜头中,我们看到凶手扬刀冲出卧室,紧接着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切为一个凶手的视点镜头,仿佛我们被带入到行凶者的主体位置,实现了与莫名的原质污点的认同;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最具震撼力,完全被母亲的声音(代表着母性超我)占据了身体的诺曼·贝茨抬眼直视着摄影机镜头也即观众,画面叠印出母亲干尸的恐怖形象以及警方从烂泥塘里拖出的玛丽蓉的汽车——那一时刻,我们彻底被(拉康所说的)粪便—客体的凝视所笼罩。
阐释何为?
上文的举例并不是要介绍齐泽克对希区柯克的阐释,而是旨在说明阐释与艺术作品的相互容纳。而且,这种关系并不仅限于电影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印证,两者更为深刻的同一性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真正的阐释,和真正的艺术创作一样,是由同一种动力装置驱动的,它既是精神分析的对象,又是精神分析自身的伦理目标:这一动力装置就是实在界之快感。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与希区柯克是高度一致的。齐泽克说:“关于希区柯克,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了如指掌”。[3]这句话难道不也正适用于拉康,以及齐泽克自己吗?
这种一言难尽的特质集中表现在齐泽克那滔滔不绝的失语中。他的说话方式本身就接近某种精神病的症状:一方面,他就像是受到安装在他身体内部的一架永动机的驱使,高度紧张和神经质地不断讲着,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停止;另一方面,他的手势、身体姿态常常领先于他要说的话,也就是身体已先完成表达,语言却被留在后面、留在身体当中。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标志性的滔滔不绝的失语。领略过他演讲风采的人都会对此留有深刻印象:在他的语言和需要用语言进行组织的、从他高速运转的大脑或心智中迸发出的“内容”之间,仿佛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声音、语词如骨鲠在喉,无法直接、畅快地倾吐而出。我们在他这里遭遇的,不正是拉康对声音作为小客体的精确定义吗:在喉之骨——它因为过度焦虑、因为情感能量太过强烈而无法释放的声音。
齐泽克的写作也与此相似,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他的生产力之丰沛、写作效率之高、著作数量之惊人,当今世之思想界,无能出其右者。有论者赞叹说:“齐泽克大脑的运转速度有多快,他写书的速度就有多快!有时甚至写得还更快些!”实际上,这与他用英语写作也很有关(齐泽克是在1989年用英语发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名声大噪的)。英语作为一种较少自反性、而较多及物性(英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与此并非没有关系)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较其它语言更容易达成一种直接和稳定的对应连接,使作者能够清楚、明了地抵达他所要表述的思想、概念、内容。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已经做到了、占有了这种透彻和准确,但齐泽克仍旧不厌其烦地对相同、相类或相关问题进行周而复始的论述,仿佛从这种论述的及物性中永远不能获得满足。
这一现象,这种表达的强迫症,这样登峰造极的阐释狂热,也只能借助精神分析自身的理论来予以阐释。发动齐泽克之思想、表述和写作引擎的,是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说的“驱力”。虽然在论述希区柯克的时候,齐泽克曾把阐释的运动等同于欲望的能指转移过程,欲望满足于阐释过程中的意义释放;同时他指出,驱力与符号性的欲望相反,它属于不可能的实在界,而总是包含在自己的封闭性循环中。但驱力和欲望的关系应该辩证地来看待:驱力恰恰是因为执著于欲望的客体—成因,执著于创伤性的匮乏而围绕它展开封闭性的循环运动,它才会调动主体尽其一生去徒劳地追寻那不可能之客体(即小客体),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快感。精神分析也是齐泽克本人的看似无止境的阐释工作,正应该被理解为驱力的欲望式不满。
与这种把阐释本身作为欲望与驱力的辩证关系来看待一样,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得意门生和学术继承人,也是齐泽克的老师)也曾区分出两种相反的阐释。[4]在弗洛伊德那里,阐释是为了通过解码信息以解除征兆,通过建立理性的因果链条来还原和清除心理病灶——从这个角度来看,阐释的时代确已过去。因为,照此理解的阐释,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快感整合到语言结构里,整合到符号界当中去,而这样的阐释又总是在呼唤更多的阐释,于是形成一个不断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但这一理性化、符指化的努力终归是要失败的,因为那个被废弃的小客体总是会成为最后的阻碍,也就总是会有剩余快感会逸出这循环往复的阐释程序。然而,到了拉康那里,准确说是后期拉康那里,精神分析的伦理姿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阐释的目的不再是通过解码征兆以平息创伤(那是快感之源),而是把目标转向幻想;幻想就是储存着快感能量的编码信息,而阐释的(无意识)动机就是执著于欲望,阐释本身就是受快感调遣的驱力运转。因而,照此理解的阐释,就是受那创伤性内核和主体建构中的匮乏的牵引,陷入驱力的循环运动而不断追逐那不可能之快感的过程。这里涉及到的,其实是拉康精神分析最终极的伦理教诲:永远不要背弃你的欲望……这个意义上的阐释正方兴未艾。
齐泽克在论及拉康的立场转变时,也谈到阐释方向的移转:“在语言中,‘它’并不言说,‘它’享乐着;在对无意识形式的精神分析的解读中,我们处理的不是阐释——这种阐释旨在获得隐蔽的意义——而是阐释者快感的显示。”[5]——这不仅适用于精神分析,而且适用于一般的文化评论和艺术阐释。希区柯克的电影召唤阐释,构成对理论的应答,是因为它不断地激发实在界之快感。几乎无庸赘言,不存在可以穷尽对希区柯克电影的理解的基本事实,而对所谓“事实”的盲信恰恰是今天电影研究的最大误区。归根结底,实在界是不可化约的,符号化的现实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全部。唯一正确的阐释,就是像齐泽克那样,浸淫于实在界之快感中,忠实于“欲望的律令”,享乐。
注释:
[1] 夏洛特·钱德勒:《这只是一部电影——希区柯克:一部私人传记》,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 Slavoj Zizek: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London: Verso, 1992.
[3] 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Jacques-Alain Miller: “Interpretation in Reverse”, The Later Lacan: 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Véronique Voruz and Bogdan Wolf,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5] 斯拉沃热·齐泽克:“定位:自我访谈”,《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六论》,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